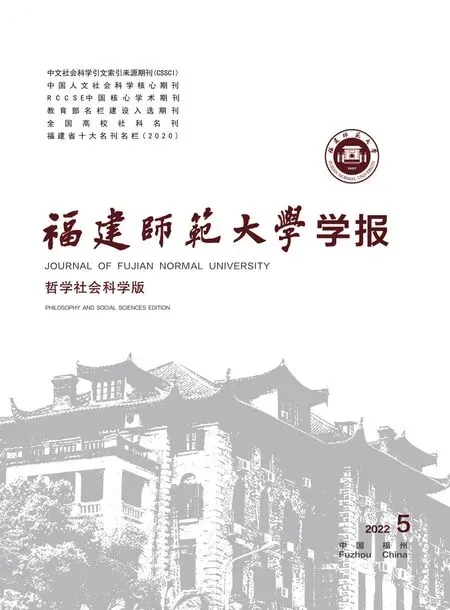虚拟主体性与虚拟物质性:论数字人形象
王 莹,梁雪媛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在人类文明史中,人类把自身形象投射于图像,在对图像的观看、凝视中感知自我,构建主体,近年来呈爆发趋势的数字人形象延续了此种文明范式。异于传统图像创作和电脑游戏中的人物形象,当下融媒介时代的“数字人”形象建基于数字图像计算技术,突破了“赛博格”式的人机结合体形象,精准呈现自然人形态,模拟人类能力,展开类人行为,表征为具备能动性的虚拟图像系统。(1)数字人又称虚拟数字人、虚拟人、虚拟形象等。“他们”借助计算机技术,存在于网络世界中。通过计算机图形学、图形渲染、动作捕捉、深度学习、语音合成、AI算法等技术手段,数字人获得多重人类特征。德国学者韩炳哲,国内学者王峰、汤拥华、蓝江等对相关问题也有所论述。但对融媒介中的数字人如何获得主体性和物质性,似尚未涉及。缐会胜在《韩炳哲“数字人”美学思想研究》中,总结了数字人的三种内涵,并概括了韩炳哲思想中的数字人概念。韩炳哲倾向于将数字人描述为“人的数字化”的生存图景,这与本文所使用的数字人概念并不相同。
数字人形象冲破了传统图像中原本与摹本的关系,打破了视觉经验与图像再现的区隔,推动了视觉与图像的贯通。自然人与数字人互观、互动,图像呈现与观看者的心理映射交融,数字人形象的自我指涉在融媒介中转化为向真实世界开放的阐释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数字人获得了虚拟主体性,构建出虚拟物质性。将数字人形象置于中西图像艺术和视觉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深描其图像样态,揭示其蕴含的视觉经验和物质性特质,进而分析其形象系统所蕴含的感性价值,成为当代美学迫切面对的问题。
一、数字人形象类型及其进化
周宪认为:“(形象)建构乃是借助于视觉符号或形象所实施的。”(2)周宪:《视觉建构、视觉表征与视觉性——视觉文化三个核心概念的考察》,《文学评论》2017年第 3期,第17-24页。数字人形象随技术进步历经三种类型进化:横空出世的初代虚拟偶像林月美、初音未来和洛天依等保留着传统漫画式的形象特征;第二类数字人如清华虚拟学生华智冰、虚拟艺术家夏语冰等,着意模仿人类行为,努力消除数字人和人类的隔阂感;当今借助元宇宙概念而生的虚拟人柳夜熙和AYAYI等为第三类数字人,她们频繁参与商业代言,引领、重塑、甚至超越日常审美。数字人的视觉形象在数字技术发展的助益下日益精细和逼真。从漫画式的异己形象到与人类外貌几无二致的日常形象,再臻至人类理想化的形象,这既是数字人形象进化的三个阶段,又是其三种类型。
(一)数字人形象的三种类型
洛天依是全球第一位配有中文声库的虚拟数字人。她的视觉形象保留了较多漫画特征,灰发圆脸,大眼绿瞳纤鼻,体型纤小,达成了其豆蔻少女设定。(3)《上海禾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官网:虚拟歌手洛天依介绍》,2022年3月28日,https:∥vsinger.com/vsinger,2022年5月11日。洛天依形象中的中国风短裙等图像元素,配以漫画式的叹息、低吟及欢笑等,辅以甜美的主打歌与舞蹈,化静为动,丰富了洛天依的形象维度。作为国内数字图像世界中的首位数字人偶像,洛天依代表了早期虚拟数字人的形象特征:呈现效果上,夸张的光影制造出绚烂的舞台效果;呈现方式上,其形象在屏幕建构的平面剧场中单向度呈现,只允许观看,屏幕隔绝了洛天依与观看者的互动,彰显出早期数字人形象的虚幻性;就观看者的视觉经验而言,数字技术赋予“她”以人的“形”,但观看者的视觉经验恰恰可以辨认出这些漫画式形象,并判断出其形象的非真实性;就图像与视觉经验的关系而论,早期数字人处在对象化观看体系中,是观看者的客体,屏幕外的观看者与数字人之间继承了古典式的非参与式观看关系。在此种混合着窥视欲望的凝视中,早期数字人“通过获得客体的地位,其特有的性质、其难以捉摸的色彩、其独特而转瞬即逝的形式都具有了重量和坚实性”(4)[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6页。,进而获得了一定意义的物质性。这促使单向度的数字人形象借助技术进一步拟象化,在变得更具真实感的同时,提出了在真实世界之外构建数字世界主体性和物质性的新方向和新要求。
第二类虚拟数字人形象沿此方向继续前进。借助图像捕捉与实时渲染、人脸识别、人物建模等技术,以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为支撑,以真人面容和声音为辅,数字人已逐步抛弃漫画造型并摆脱剧场化、程式化的录播表演,获得了与屏幕外观众场景化、动态化的实时互动能力。如清华虚拟学生华智冰等不仅频繁上传表演视频,还进行直播并在此期间不断与粉丝进行情感互动。不同于洛天依时代的单向传播,第二类数字人虚拟形象被赋予想象性的生命力和人格化特征。受制于动作捕捉等技术因素,此类数字人形象往往并非原创,而由复制、改造某位自然人的形象与行为而成。如华智冰形象系统中的肢体动作、吉他弹唱表演等,采集于其技术团队成员录制的原始视频。这使得此类数字人的形象看似具有独立性,实则为自然人的数字翻版,其形象创造范式与传统现实主义艺术并无不同,因此并不具备主体性,是第一类与第三类超写实数字人的过渡形态。

图1 柳夜熙定妆照
第三类超写实数字人昭示着数字人形象的发展趋势与美学特质。作为超写实数字人的典型,柳夜熙和AYAYI等的形象特征与自然人几乎等同的同时保留了幻想元素,呈现出真实与虚幻融合的视觉经验。(5)知满、新播场:《创壹科技:我们做“柳夜熙”,终极目标是元宇宙版迪斯尼》,2021年11月10日,https:∥mp.weixin.qq.com/s/3d294DO0NIEcbLq_p6xvhg,2022年7月27日。这种同异相统一的辩证性形象具有连接网络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力量。以柳夜熙和AYAYI为代表的新一类数字人形象是写实和超现实的统一。以柳夜熙为例(见图1),她的五官整体呈现东方女性的典型特征:脸型线条柔和,以额间花钿和花瓣唇妆作为点缀,配以中式长细眉和上挑丹凤眼,明暗不同光线条件下近乎完美的皮肤质感和表情细节,使她的形象真假难辨。作为数字人形象的有机元素,她动作飘逸飞扬,身姿瘦削而有力,眼神淡漠空濛。柳夜熙所处的环境、衣饰、陈设物组合一旦被置换,观看者在新的视觉构造中所能汲取的内涵、意义与功能也随之改变。这昭示着数字人的现身与消失、在场与缺席、绽出与遮蔽,都是未知和不定的集合,仅仅映射着观者想象中的元宇宙图景。总之,柳夜熙的图像中尚含有幻想性元素,构造了视觉的疏离感,表征着我们对元宇宙等异托邦的遥想。

图2 AYAYI在日常场景中
与空濛疏离的柳夜熙相比,AYAYI等和自然人类形象近乎相同甚至无法分别。她们努力抹去数字人的技术征候,突破屏幕限制,如自然人一样身处花园、演播厅或书房等日常空间,与自然人平等而自然地交流、互动、合影或参加商业宣传(见图2)。AYAYI的数字人形象系统体现了试图复制甚至取代现实自然人的雄心,其虚构性已无法直观地察觉,算法的产物获得了物质性的存在方式。
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技术赋予这些数字人形象更加强烈的“人”性意味。在这里,观者悬置了对自我存在的反思,在与数字人虚拟目光的互相凝视中,获得了真实可触的具身性体验。“在视觉关系中,依赖于幻觉且使得主体在一种实质的摇摆不定中被悬置的对象就是凝视。”(6)[法]雅克·拉康、[法]让·鲍德里亚等著,吴琼编:《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吴琼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第三类数字人面容之无瑕、人设之完美,使这些数字人形象获得了逐步取代文化工业所塑造的真人偶像的可能性。在对真实人类的模仿转而成为完美人类形象的代表过程中,数字人形象逐渐塑造成为人类的理想形象。
(二)风格化的审美理念
社会文化的发展伴随着人的形象重构,形象表征实践与观者的视觉经验重塑参差相契,人类观看场域扩容,主体知觉延伸强化。数字人形象的色彩画面追求惊艳的视觉效果,其深层原因阿比·瓦尔堡(Aby.M.Warburg)已有预言:“我们必须到放荡的大众癫狂的领域中寻找那个制造所,它将极端情感表达的表现性动作深深铭刻到记忆中,以至痛苦激情的经验的这些记忆痕迹作为储存于记忆中的遗产留存下来。”(7)[英]E.H.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李本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280页。数字人形象对观者带来巨大的审美惊奇,凝结为“精致化”和“赛博朋克风”这两种最具代表性的风格。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精致”为“精巧细致”(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691页。,当下语境中常引申为“有情调”等意涵。“精致化”贯穿人类文化生产与观念演进的全部历史。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认为:“视觉文化并不取决于图像本身,而取决于对图像或是视觉存在的现代偏好。”(9)[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页。数字人形象所呈现的强烈的“精致化”风格源于当今大众对“精致感”的审美追求。

图3 AYAYI精致的面孔
中西美学史中的“精致化”趋向推动了艺术创作的精细化和审美经验的敏锐化,又因审美活动、审美对象之专业化或自律化而使审美趣味日益精致。现代生活中的“精致”成为认真生活和自我提升的代名词。在大众传媒中,所谓的精致裹挟了现代女性,从美好生活的选择之一,抬高为现代人必备的道德义务。(10)薛富兴:《精致化:一个古典美学标志性范畴》,《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3期,第72-83、158页。早期的数字人形象仅仅是对人外表形态的漫画式模拟,当下数字技术的发展促成了数字人形象的极度精细化,人物形象显得生气十足。数字人形象提供了“外貌方面的无限微妙精致的东西”(11)[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40页。。精心雕琢的面部轮廓,漂亮的眼型,优美而坚挺的鼻梁,柔美的唇部线条共同构成了近年来数字人形象的基本要素。(见图3)异于百花争艳、风格各异的自然人面孔,洛天依、华智冰、柳夜熙、 AYAYI等不同数字人形象的面容,在精致化程度和风格取向上一致。数字人形象的精致化风格还源于他们形象系统中虚拟场景的极度精细化。当前数字人身份多定位为虚拟偶像,主要从事唱、跳、展演,间或从事各类商业宣传,参与文化传播。这些特定的人设,需要向观者呈现精致化的趣味,同时规定了他们的形象风格要求。
此外,当代社会审美风尚对女性外貌的严苛要求也影响了数字人形象的呈现。数字人形象中女性占据了绝大多数,男性数字人形象仅有川(CHUAN)等少数个体。男性数字人形象多为真实世界中的主持人或企业家的形象映射,而女性数字人形象的制造则多摆脱了直接的摹本,其原创、全新的面孔在“看与被看”中成为社会窥视欲的对象。“女性作为指称阉割的表征,突出了自身的被观看性……因而创造出一种按欲望度量剪裁的幻觉。”(12)Mulvey Laura,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Trans.Fan Bei and Li Ershi,“Film Theory Reader,”Beijing: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2017,p.531.洛天依、A-SOUL女团成员的图像呈现效果容易诱发受众的视觉消费。女性向明显的图像特征尤其能够激发男性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同时制造时尚噱头,在女性受众中引发跟风,以创收利润。因此,在技术驱动、视觉窥视欲诱惑和资本增殖等多重合力下,精致化风格成为数字人形象的必然选择。
从威廉·福特·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到沃卓斯基兄弟(The Wachowskis)的《黑客帝国》,小说和电影中创建了近乎无穷无尽的赛博空间,反复展演着具有反叛精神、追求自由解放的审美形象。时至今日,作为对技术进行幻想的最佳视觉风格,“赛博朋克无处不在”(13)Anna McFarlane,Graham J.Murphy,Lars Schmeink,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Cyberpunk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2020,p.1、255.,提示着真实与虚幻差异性的碰撞,在虚拟与真实的夹缝中呼唤着本真的存在体验。“赛博朋克协商了人性与本体论,通过区分真实和虚拟的困难,突出了真实体验的中介性质。”(14)Anna McFarlane,Graham J.Murphy,Lars Schmeink,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Cyberpunk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2020,p.1、255.为保障数字人形象的真实感且区别于真实物质世界,第二类、第三类数字人多配置以极具视觉冲击性和未来感的赛博朋克风场景。以柳夜熙为例,在她的形象系统中,其图像后景多是霓虹闪烁、群楼耸峙,巨幅影像横亘天地,构造了典型的赛博朋克风场景。这一图景配合极具真实感的光影、透视和实时动作捕捉,试图构造出具有自然性特征的、难辨真假的“自然身体”。这种“浓缩了想象与物质世纪的一个形象,赛博朋克与想象及物质的两个交合中心建构着历史变更的所有可能性”(15)张进:《物性诗学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59页。。柳夜熙封闭在相对固定的场所中,其形象约束观者的观看,同时提供了被凝视的可能,这种凝视带来屏幕外的观者与数字人目光的交合,同时改造着双方的目光与身体感。
赛博朋克作为“科技沦陷”幻想的产物,契合了当代人对数字人形象的风格设定。自然人与算法混融创生的形象,带来近乎真实又超越现实的视觉经验,呈现出现实与虚拟的交融和相互改造。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与渺小脆弱的人类在图像中形成鲜明对比。数字人形象中赛博朋克风大行其道亦源于自然人对现实生活的厌倦与逃避。作为一种反乌托邦的艺术,赛博朋克强化了虚无感和沉浸式的涣散情绪,那些外表与内在、机械与肉体、现实与虚拟、物质与精神等冲突对立的元素,在数字人“赛博朋克风”的图像世界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借助视觉效果,在虚拟的图像中追问着人类的本真存在。
尽管现有的数字技术水平进步巨大,数字人的赛道看似正在不断被扩宽,但目前风格化的数字人仍居住在屏幕之内。这些数字人图像制造了错觉,这些错觉已经突破E.H.贡布里希(E.H.Gombrich)“象征的图像”的窠臼(16)[英]E.H.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学文集》,杨思梁、范景中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1页。,抛弃了心理学的象征意义,而诉诸观者的直观视觉经验,驱使观者将超级写实接受为真实,并试图在超级写实中重建典范。
这些典范重塑了人们的观看方式和生活世界。在短视频突起、社会时间加速的时代,近乎审美理念的精致化与赛博朋克风数字人形象牢牢把握观者的瞬时注意力。更新形象以避免观者注意力的消散厌倦,成为数字人形象的核心能力。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感慨说:“在视像屏幕时代,观看视点显得至关重要。在这个图像的漩涡里,观看远胜于相信。这绝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正是日常生活本身。”(17)[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页。
总之,数字人借助数字科技构造了多个类型的形象系统。观者沉浸在精致化与赛博朋克风的视觉世界中,进入一个可融合、移动、参与和相互凝视的虚拟空间。正是在相互交融、相互凝视的虚拟空间中,数字人的形象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获得了迥异于自然人的主体性。
二、数字人形象的虚拟主体性
数字人形象借由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介入现实日常生活,无所不在的数字人视觉图像,在与自然人的互相凝视中,成为知识生产与传递、情感建构与交流的途径之一,并由此获得了建构数字人虚拟主体性的能力。
(一)凝视的交融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认为,身体介入艺术的关键技术是眼睛的“观看”,这种观看是可协商与可逆的:“如果人们不再把原初的感觉定义为属于同一个‘意识’,而是将感觉理解为可见的回到自身,理解为从感觉到被感觉者,从被感觉到感觉者之间的肉体联系,身体的视景就能相互交错,它们的行动、它们的热情就能准确地相互配合。”(18)[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75页。凝视作为观看的核心技术,是自然人交流与感知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介入性的凝视与被凝视的循环往复,人完成了主体性的感知和主体性建构。数字人和自然人互为对方的凝视者,在相互配合中建造了互动的理解性视景。
数字人的静态和动态图像充满故事性,凝视者可以根据自身经验想象性地补充前景与后象。“视觉经验是由主体所制造,也在主体中产生。”(19)[美]乔纳森·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蔡佩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2页。这种凝视的技术诉诸凝视者的知觉能力,依赖凝视者的记忆和运行于其心灵中的想象力,使凝视者在经验世界中将数字人图像中的种种元素对应于真实世界。“这种反应产生于图像的力量,也产生于图像与其对面的观赏者、触摸者乃至倾听者之间的相互作用。”(20)[德]霍斯特·布雷德坎普:《图像行为理论》,宁瑛、钟长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41页。进而,数字人和虚拟世界图景的物质性有了存在的可能。数字人的形象要素紧密关联虚拟图像与现实物象,使屏幕内的虚拟世界和屏幕外自然人的体验实时联动,虚拟世界在凝视者视觉经验中的现实感、真实感被实时唤起,进而赋予数字人以虚拟物质性。与此同时,数字人也被赋予了虚拟的主体性特征。
以柳夜熙为例,她的形象系统中以毛笔和镜子为主要道具,其动作和光效虽化用传统道教的部分元素,但其形象反复强调的美妆元素,展现出现代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化妆行为并试图引领美妆风潮。其他数字人形象如AYAYI和Lil Miquela等,在网络中分享日常、有规律地发布短视频和穿搭效果图,在社交媒体上的一言一行和自然人明星、网红等几乎一致。数字人凭借虚拟图像和现实进行的契合呼应,利用极具力量感的图像冲击观者的视觉经验,赋予了凝视虚拟图像时的视觉经验真实感。
瓦尔堡认为视觉经验“扮演着一种双重角色。它是图像的仓库,这些图像是凭借以虚构的生物来代替真正原因……通过这些名称与图像,我们得出受到规律支配的客观宇宙的观念”(21)[英]E.H.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李本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51页。。凝视者对种种图像的反应经过文化系统的选择,作为感性经验的永久记录储存起来。瓦尔堡将对这些刺激做出的语言反应或图像反应称之为“表达”,也就是视觉经验引发的自我感知。数字人本质为虚拟形象,我们对它的体验和感知产生于凝视其图像时目光接触的事件。不可见的算法构拟为可见的人的形象,在看与被看的凝视中,双方重构着彼此的主体性。“可见的本身是属于不可穷尽的深度之表层的:正是这不可穷尽的深度使得可见的可以向我们的视觉以外的其他人的视觉开放。”(22)[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77页。屏幕上的图像力求呈现出幻觉和视觉上的丰富性,凝视者则在凝视中最终被驯化以至于认同图像。“虽然现实中的屏幕只是一个尺寸有限的窗口,放置在观众所处的现实空间之中,但观众……聚焦于窗口内的再现性场景,同时忽略窗口之外的现实空间。”(23)[俄]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6页。物质的屏幕锁定视窗的同时,也规定了凝视者视觉经验生成的场域和可能性途径,凝视者将注意力集中在该窗口中看到的图像上,而忽略了外部的物理空间。
凝视者专注于图像而忽略其存在于虚拟世界这一事实,提示此凝视并非单向度的观看,而是自然人和数字人平等相待的介入式交互凝视的视觉过程,数字虚拟物凝结为可感的图像,获得了确证自身主体性的可能。数字人透过屏幕看向自然人,其目光贯穿虚拟世界达至自然人的身体,经由对存在与否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式追问,在数字人透过屏幕的凝视中获得了新的解答:“主体或者自身的解决:其消解和松懈。那个与自身的关系的问题在一种没有关系的凝视中得以展示和解决,这种凝视凝视着它自身,而这个自身凝视仅仅发生在这一确切的范围内,即它画出自身并且由此走出自身。”(24)[法]让-吕克·南希:《肖像画的凝视》,简燕宽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第76页。数字人向外伸展的目光和自然人向内探入的目光在屏幕间碰撞、融合,造成实时互动的假象,双向凝视的同时也双向模仿,缝合了数字人和凝视者的距离,消弭了虚拟和真实之间的区别。
虚拟的自然或模仿的自然,虚拟的人和想象中的人,在这种互动与缝合中被共情为数字人的自然。算法的世界以人类世界为镜像,模拟、虚构自我感知。数字人的图像是虚拟的,但他们的目光凝视着屏幕外的世界并将之转化为自身图像的行为却是真实的,数字人和数字世界由此获得了非自然的虚拟主体性。
治愈系绘本通常是符合大众审美的绘本,使用一些温暖的色调,可爱的人物形象并且又富于想象的分镜,这样特点都能够是读者感受到来自绘本画师的温暖与宁和。治愈系绘本的还具有趣味性,但是治愈系绘本的趣味性不仅仅是通过可爱的人物形象或者是幽默的故事情节来表现,而是通过感染读者的内心,治愈系绘本就想是桥梁一样沟通读者与绘本画师的内心,来让读者产生共鸣。治愈系绘本通常运用简单的故事来传达一些正能量,每个简单的故事中又蕴含了不同的大大小小生活中的一些道理。它可以是读者能够有所触动,也能够体现一些我国我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能够引发读者的深思。这些都能够通过治愈系绘本的方方面面有所体会。
(二)主体植入和虚拟主体性
在与自然人的交互式观看过程中,数字人形象使观者将自身植入数字人,二者的主体性被双双重构。
植入感是数字人形象的逼真性呈现的结果。超写实型数字人形象真假难辨的皮肤、表情和动作,图像系统内部场景、环境人物、道具与真实世界的互动,提供了无限接近于现实的可能。随着技术的突破,制作数字人的电脑技术也逐渐溢出,流向普通的电脑用户。普通用户借助简单操作,无须理解复杂算法即可构建出一个以自身为原型的数字人形象,将自身植入虚拟世界。这样,普通用户得以将自身的历史、情感和经验全部数字化,利用数字文档、照片、影像等数字材料,在网络中构建自我映像或全然虚构的自我。此构建过程在自然人和数字人形象间循环往复,每一次观看数字人形象,都推动自然人将主体性植入虚拟世界的过程。
借助数字技术,任何自然人都能够在数字人的世界中找到自己对应的数字副本。由视觉形象做媒介,通过凝视行为植入自我而重建的主体,糅合了凝视者的自然身体和承载数字人形象的物质身体,在虚拟空间中往复交融。人机融合躯体的赛博格人阶段被悄然跨越,数字人和自然人的形象、情感、经验纠缠在虚拟的、数字化的具身性感知中,呈现出全新的感性经验模式。
虚拟的数字化身体图像在面对不同的场景和情况时,试图做到和真实人体一样的调整、适应与变化,以期待凝视者通过视觉经验对数字人产生具身化的共情。“当身体被描写在文学文本中时发生的各种变化,与文本身体被编码到信息媒介中时产生的变化,具有非常深刻的联系。”(25)[美] N.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页。自然人的感性经验被植入数字人形象,自然人面对数字人形象时产生的情感,实则是自然人直面自我产生的共鸣。真实的自然身体处在被驯化的规范性体系中,而虚拟的数字身体则是“真实化”的行动或过程,即将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有机链接的过程。
华智冰等数字人形象借助身体图像来宣示她们的在场。通过凝视,AYAYI等第三类超写实虚拟数字人形象产生的视觉经验,使得凝视者被卷入特定的时间、地点、生理状态和文化语境中。因自然人主体植入而“真实化”的数字人身体图像成为人类身体的理想化的表现形式,拥有了类似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审美理想”式的典范意义(26)[德]伊曼努尔·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7页。,使超写实数字人具有了本质性实存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具身化则永远是从嘈杂的差异中生成的特殊实例,是处于无限的变化、特性和异常之中的过度与不足”(27)汤拥华:《重构具身性:后人类叙事的形式与伦理》,《文艺争鸣》2021年第8期,第56-63页。。数字人的身体图像创造了凝视者具身化的感觉,为了适应具身化的不同经验,用来定位和建构身体的方式和途径都做出了相应的改变。“具备人的形象具有重要意义,无论这是实质的,还是想象性的。它以一种亲近的方式提出了潜在的人格化诉求,即一种特殊的主奴辩证法。”(28)王峰:《人工智能形象与成为“我们”的他者》,《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4-23页。数字人形象诱导社会情绪转向一种数字人化的视觉体验,数字人的自然人化和自然人的数字化,在这种视觉经验中混融为一。
数字人形象继续发展需要突破的是技术创新和思想局限。其图像最终摆脱抽象的身体,预测和模拟人类的情感反应,从而构建数字化的情感系统,吸引沉浸式的视觉投入,诉诸自然人的主体植入和情感共鸣。数字人的进化摆脱了被概念化、类型化的身体,承载了自然人的个体记忆和经验,通过虚拟的物质性重塑了数字的、虚拟的主体。
三、超文本性与返魅:数字人形象的虚拟物质性
数字人形象虚拟物质性的重塑,有着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发展路径以及完整的经验世界支撑,并非全然是无根之木。
(一)图像的超文本性与“人—物”互观
20世纪以来,文图融合、以图代文成为文学生产的重要方式。视觉时代汹涌而来,图像生产冲击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文本不再局限于语言符号构成的文学空间,影视作品、广告图片等视觉文本、声音等听觉文本等都被纳入其中。各种媒介的交互、相融使“超文本”替代文本,成为当代审美经验的核心生产方式之一。超链接将不同空间的文字、图像、视频等信息组织在一起,构成多维度、多感官经验的网状超文本,开放性、多样性和变换性成为超文本的自然属性。(29)张进:《论物质性诗学》,《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18页。依托数字技术,超文本具有了“秩序层面”“内容层面”和“语境”的物质性。(30)张进、王眉钧:《论数码媒介技术的物质性——以“数码人类学”为中心的考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63-70 页。在数字化的艺术创造中,媒介与文本无法分离,艺术的主要意义呈现方式是媒介的“自我再现”,其主要特点是媒介的“自反性”,即符号文本的自我再现。超文本有着超越对象的趋势,其文本朝更丰富的解释项开放。任何文学艺术作品多少都符合这一规律:诗歌韵律平仄之精致,无助于再现对象,只是再现自身之语言美;书法的笔触狂放恣肆,无助于再现对象,而是再现了笔墨的韵味。越到后现代,再现对象越淡出,而各种人工智能艺术,更以媒介的变化为最大特征。(31)赵毅衡:《人工智能艺术的符号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07-115页。媒介一旦变化,数字形象的审美特质也随之改变,媒介的物质性也就影响了数字形象的物质性。
数字人形象正是这样一种超文本,其形象依赖多维度的秩序构造,涵括多维度视觉内容,集合了多重媒介的呈现方式。在平面杂志上,柳夜熙、AYAYI等图像和采访文本交互穿插,其形象在多重媒介的边界中穿梭,多维度展现精致风和赛博格风格。数字人形象的超文本性打开了与真实物质世界不同的虚拟空间,但图像本身依存于数字算法,此虚拟空间的物质性不同于真实世界,而是虚拟物质性。
自然人将主体性植入超文本进而构建了虚拟空间,数字人形象通过虚拟的具身性而感知真实世界。图像本身即是内容的物,在此意义上,数字人形象是真实的或现实的。这种“图像直接、集中和情感地描述身体。媒介是物质/物化的:它们像克劳夫所说的那样深入肉体,或者像拉什所说的那样通过身体工作,即创造身体”(32)Rebecca Coleman,Transforming Images:Screens,Affect,Futures,New York:Routledge,2013,p.36、45、39.。因此,数字人形象不是单纯的表征,“它们不是那种独立的、有边界的单位,在其他独立的、有界的身体之间起中介作用,而是与物质和将被物质化的东西存在着构成性关系”(33)Rebecca Coleman,Transforming Images:Screens,Affect,Futures,New York:Routledge,2013,p.36、45、39.。真实世界和被物质化的虚拟世界互为中介,构建了数字人形象的虚拟物质性。但作为非天然的物质性客体,其“虚拟物质性”只能依存于屏幕、电脑网络等技术而显形。图像的屏幕与网络世界就是物质实体,数字人形象透过这一实体使观者看到,在其中,“图像不(仅)作为文本存在,而且作为事物、物质或更好的物质化存在”(34)Rebecca Coleman,Transforming Images:Screens,Affect,Futures,New York:Routledge,2013,p.36、45、39.。正是在透过物质性屏幕的人与物的互看互融中,数字人获得了虚拟物质性。这一虚拟物质性的存在范式中,非自然身体与自然身体互相观看,非物质世界与物质世界互相映照。由此,非真实物质世界的产品与生产、固定和支配它们的物质世界有机联结在一起,真实物质性和虚拟物质性在联结中不断进行角力、协商、重塑。技术的发展或许使图像得以呈现的中介改变,但数字人形象的虚拟物质性,则始终向当下和未来的时空开放,其形象系统将获得越来越多能动的力量。在此虚拟物质性中,传统“人—物”观被颠覆并重构,数字人形象被赋予类似于自然人的生命意义。
数字人形象的理想效果是将自然人的生命赋予数字形象,进而在虚拟世界中重建世界和物的系统。此过程将自然人视为特殊的物,从而进行创作、改造或重塑。自然人与数字人之间互为模型,产生了类似闭环的双向反馈。“它们通过自身与接收者之间的反馈来发挥作用。人们根据图像来塑造自己的行为模式,图像通过捕捉他们的行为而越来越高效地运转着。”(35)[巴西]威廉·弗卢塞尔:《技术图像的宇宙》,李一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25页。当下在对数字人形象的“人—物”观讨论中,多将自然人与数字人二分。《银翼杀手》《黑客帝国》和《头号玩家》等作品多利用视觉技术完成自然人与虚拟人的区分,判定纯粹的自然人而非虚拟人或数字人才能真实且独享“人”的概念,甚至仍然寄望于以自然人之间的情感来推翻虚拟世界的强权。(36)汤拥华:《重构具身性:后人类叙事的形式与伦理》,《文艺争鸣》2021年第8期,第56-63页。这样极具古典人文主义色彩的“人—物”观,悬置了数字世界中人和物何以关联这一关键问题,强调了虚拟人或数字人仍以自然人为核心的理念。
随着自然人的图像在数字世界被不断调整和重塑,我们从数字人形象中“选择出来一些特征”(37)[美]乔纳森·卡勒:《当今的文学理论》,《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第49-62页。,并将其与人类相联系,从而建构出我们对数字世界的感知。感知的物质性,也在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中使得静态、固定的图像在数字世界中逐渐具备独立性、感知和形塑自身,并反向影响现实世界中自然人形象的构造。这一虚拟而能动的物质性状态正重构着“人—物”的关系,虚拟与现实逐渐等量齐观,虚拟的形象也开始具备现实的能动性的物质性,这就是“虚拟物质性”。
(二)数字人形象的附魅、祛魅和返魅
数字人形象与其他数字世界的图像相比,其虚拟物质性的能动力量促使数字人和自然人往复交流和情感共鸣,使数字人形象在其系统内部经历了附魅、祛魅、返魅的物质性循环。
数字人形象映射进自然人的心灵世界,存在和作用于真实的感知中,“他们”直接、集中和感性化地呈现“人”。借助物质和物化的融媒介形式塑造“有血有肉”的形象的同时,映照出人对自身肉体的感知,从最初单纯的视觉惊奇逐步拓展进入人的日常感知和社会实践。数字人形象征引自然人的情感、经验、身体和对世界图景的感知,扭转人的自然存在为虚拟数字形象。这同时使自然人的形象在虚拟世界延伸,在自然人的心灵世界中再联结,融合了现实和虚拟两个世界。从无生命静物到动态物,再到虚拟主体的进化和转换,这正是数字人形象的附魅过程。
凝视者在凝视数字人形象时,模糊了传统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分野,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感知联结共轭,虚拟物和实在人产生了新的可互相感知与传达的扭结。传统的实在物质性或现实物质性逐渐解蔽,而陌生遥想和神秘魅惑的数字世界在凝视者的注目、多感知共轭中失却神秘,实现了祛魅的过程。
在祛魅的同时,返魅也伴随着自然人的感知与数字人形象在融媒介中的邂逅而发生。在此现实信息和虚拟信息相遇的非传统空间中,“‘关系性’”是‘返魅’世界的典型特征,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单一的、高高在上的主体,使得意义产生机制的双方成为一种‘交互主体’或无主体的存在”(38)张进:《物性诗学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97页。。虚拟与现实在扭结中混合交融与互相模仿,产生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融合空间。数字人形象也就在融合空间中实现其返魅循环。
数字人形象在经历附魅、祛魅、返魅过程中,展现了数字时代物质性样态和审美范式的转变,“‘返魅’是一种升华,将‘关系性’‘活态性’‘物质性’‘实践性’都拢括进来……正是在描述之物与人的阅读的相互作用中,意义得以产生”(39)张进:《物性诗学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97页。。自然人与数字人打破对立和分裂,在互相观看中生成整体性的、内在性的、感性共轭的世界,真实而坚固的世界转化为虚拟且流动的数字物质世界,真实世界的物质性转换为数字世界的虚拟物质性。
四、结语
从洛天依到华智冰再到柳夜熙、AYAYI,三种数字人形象类型历经三个阶段的进化,塑造了精致化风格和赛博朋克风的形象系统,融媒介中的数字人形象在与自然人的互相凝视和交互模仿中,人类将主体性植入数字人形象,使其获得了虚拟主体性。数字人生活在虚拟的数字世界中,重构了“人—物”关系,介入并影响着真实世界,数字世界也因此具备了虚拟物质性,生成了全新的感性经验,并由此完成了附魅、祛魅和返魅的感性重塑。当代人对数字人形象的凝视,使得自然人的视觉与数字世界实现共振。视觉的张力、虚拟空间的牵引力,在图像运动和述行中与知觉共轭,将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融于数字人形象体系中,当代人的感性世界由此拓展。
在数字技术和消费主义浪潮的叠合中,数字人形象突入艺术史的形象谱系,带来了泛美学的审美经验,改变了艺术史发展的流向。数字人形象的进一步发展,或许将突破融媒介的限制,虚拟主体性或许将由虚入实,数字世界及其居民将进一步获得独立的主体性。
-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立法法理学视野下政策法律化的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