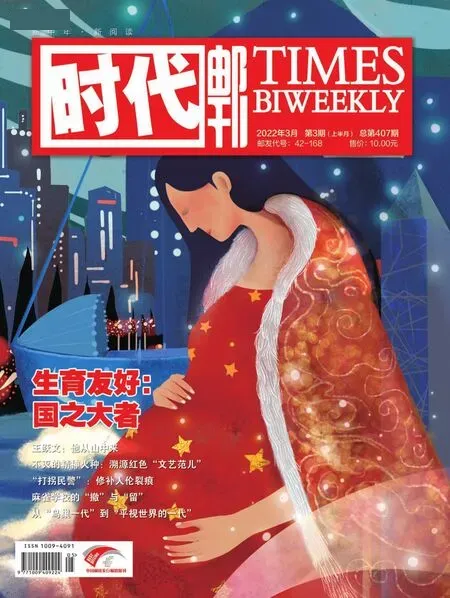片段
首位从白区到延安的女作家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位侧身微笑的女战士。她就是第一个从白区到达延安的女作家——丁玲。
1932年,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呼吁抗日救国,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特务绑架。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丁玲不曾动摇,甚至不惜以死抗争,最终还是顽强活了下来。
1936年5月,她设法通过鲁迅联系到党组织。同年,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她辗转多地,最终抵达陕北。中央特意为丁玲举办了欢迎宴会,丁玲被安排在首席,宴会期间周恩来还为她倒水。宴会结束后,丁玲提出想上前线。毛泽东点头赞许:“好啊,壮志凌云,不让须眉。”随后,丁玲怀着满腔热情投身战地生活:行军、训练、采访、写作,夜以继日。毛泽东还亲自为丁玲写了一首词:“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旧地名,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瞿秋白评价丁玲:“飞蛾扑火,非死不止。”1922年,丁玲去上海平民女校寻求真理之火,1930年参加左联,1932年入党。“是的,我就是这样离不开火。三三年几濒于死,但仍然飞向保安。”丁玲曾这样评价自己。(摘自《延安日报》,文/白慧)
第一面军旗是如何诞生的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次起义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使用的却是国民党的旗帜。
8月中旬,毛泽东回长沙调研,目睹了国民党军队镇压革命的暴行,认为秋收起义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于是,他以湖南省委的名义写信给中央:“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根据前敌委员会的指示,制作军旗的任务落在了师部参谋处处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和副官杨立三身上。
三人经过反复研究,借鉴苏联红军军旗的样式,设计出工农革命军军旗。旗帜底色为红色,象征革命事业;旗帜中央为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内是镰刀和斧头图案,代表工农;靠旗杆处缝有白布条,上面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军旗样式确定后,师部决定立即批量赶制。裁缝出身的班长张令彬购买了布匹,修水县总工会委员长徐光华请来了县里几乎所有的裁缝。在县城的一家祠堂里,40多名针线工加班加点,在飞针走线中将100面军旗如期制成。
9月9日,在秋收起义誓师大会上,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正式军旗飘扬起来。从此,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迅速燃遍了湘赣边界的土地。(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文/颜芳明等)
一张雷锋照片背后的故事

自1960年底,全军开展了“两忆三查”教育活动,发动官兵忆苦情、挖苦根。
雷锋所在连队第一次开忆苦大会时,他没讲几句话就泣不成声。运输营副营长付永东见状,只好让雷锋先退场,并告诉李超群连长:“这里肯定有隐情,你要关注这个小兵,找他好好谈谈,看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那么伤心?”
为了帮雷锋打开心结,李连长把他叫到自己房间聊起了家常。“我们都是困难家庭出身,都是阶级弟兄。你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你家受的委屈就是我们的委屈。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这一点儿也不丢人……”
“连长,我不哭了!我讲!”原来,雷锋3岁那年,他的祖父因地主逼债而含恨去世。父亲雷明亮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1944年被日寇逮捕,遭受严刑拷打,后因伤势过重去世。哥哥雷正德,12岁就当了童工,因劳累过度,昏倒在机器旁,被轧伤胳膊和手指,后又患上肺结核,不幸去世。弟弟因家中缺粮被活活饿死。母亲因受到地主凌辱,上吊自尽。
团机关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指示连队再次召开忆苦大会,邀请已经打开心结的雷锋上台。再次听到雷锋的身世,李超群依然忍不住流泪。参加会议的机关摄影干事拍下了雷锋在连队教育中忆苦的画面。(摘自《解放军报》,文/卜金宝等)
李克农排除香山双清别墅炸弹

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唯一一位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开国上将,他就是有着“中共特工王”美誉的李克农。
北平和平解放后,城内仍有非常多的特务组织和特务,形势不容乐观。1949年2月,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按计划,党中央5月就要正式进入北平。若不铲除这些特务,就无法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面对严峻形势,李克农命令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开展国民党特务秘密自首登记工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前来自首的特务达2000多人。
尽管“肃特”工作成效显著,但仍有不少特务潜伏在城内。为确保万无一失,李克农建议中央领导人暂时住在香山。在征得同意后,李克农和警卫战士们一起赶往香山双清别墅,检查毛泽东住所。在进行最后一次清查时,李克农接到警卫战士的惊人报告:在安排毛泽东居住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枚炸弹!
按理说,双清别墅有哨兵日夜看守,应该是极为安全的。李克农出于谨慎,让战士们进行最后一次检查,没想到真的发现了问题。面对炸弹,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李克农大吼一声:“愣着干嘛!”大家很快回过神来,彻底排除隐患后,毛泽东等人才进入房间。当年6月,领导人搬进城里办公,但毛泽东依然对香山情有独钟,他白天在中南海,夜里仍回双清别墅休息。(摘自《环球人物》,文/肖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