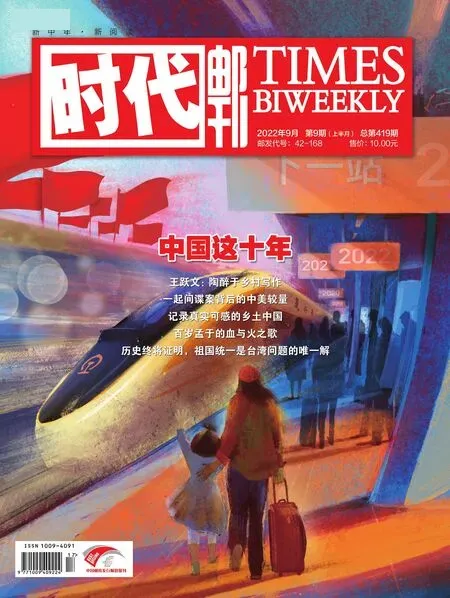县城里的陪读妈妈
● 魏晓涵
近年来,“陪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这股兴起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育风潮,在城市、农村日渐蔓延,且愈演愈烈。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在教育期望和焦虑的裹挟下,走上陪读之路。

妈妈是陪读的一个主要群体。她们一般租房住在县城,主要精力是管孩子,闲暇时有的做点手工或开个小店。她们的主要经济来源靠丈夫在外打工,生活与精神压力都不小。据估计,一般县城有陪读妈妈两三千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湖北、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农村家长因为陪读进城的比例达到60%~70%。照此推算,全国陪读妈妈有四五百万人。
陪读妈妈们一天的生活,通常是在学校附近一间小小的出租屋中展开的,像是一场紧锣密鼓的战役。
齐薇薇正在湖南师范大学读博士,每年都会去往全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广东、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村进行社会学的调研。她发现,安徽许多年轻的女性放弃工作,回流到县城,照顾孩子读书直到高考结束。
孤独的陪读妈妈
孩子们放暑假,妈妈们也跟着孩子回村了,齐薇薇见到了其中一位。她不到40岁,丈夫在北京做装修。因为大女儿转到县城读初中,她放弃了在外打工的机会,回来做了全职的陪读妈妈,带着4岁的小女儿,母女三人在县城生活,日子过得节俭,家里一半以上的收入都用在了陪读的租房和生活开销上。
见到的陪读妈妈越来越多,齐薇薇得知,这是她们的生活常态。当农村家庭面临孩子的教育问题时,妈妈通常是放弃工作、回来照看的一方。
其中,有一个妈妈就是这样,本来夫妻俩在上海打工。孩子留守在家读小学,天天不做作业,爷爷奶奶也没有办法,老师直接打电话给她,“你再不回来小孩就毁掉了”。她没办法,跑回来陪读,县城工作机会少,她就去了一个母婴店里卖卖奶粉。
齐薇薇发现,孩子升初三,是妈妈们回流的主要时间点,“普职分流引起了家长的警觉。大部分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进职校,为了确保孩子能考上高中,有机会考大学,在孩子上初三时回来陪读。”
这些妈妈和城市里的女性没什么两样。她们是80后甚至90后,许多人回乡之前,在城市里打工。唯一不同的是,她们经历了一场生活状态的巨变——原本在都市里有朋友,有社交,有自己的时间。而当下,生活的时间表都围绕孩子进行。
在陪读妈妈们的描述中,一天的生活像是一场紧锣密鼓的战役:卡着点做饭、接送孩子,放学之后,甚至会仔细观察孩子脸上的表情,随时陪在孩子身边。“有的妈妈会对孩子做特别细微的管控,比如她知道放学回家大概需要20分钟,如果20分钟后孩子没到家,她就要跑到学校找老师了。”
齐薇薇能理解妈妈们的无奈,“其实有的妈妈严格,是因为觉得自身读书太少了,希望孩子成绩好。这样一来,小孩有很大的压力,会当面反抗、顶嘴,觉得没有自由。亲子关系也会长期紧张。”
交谈中,她们脸上有着明显的压抑和苦闷。她们倾诉着日常生活的孤独——远离村庄,为数不多的社会交往也是和一同来陪读的老乡,也仅限于偶尔打打麻将、出去逛街;她们大多没有工作,和县城普通上班族的时间是错位的,很难融入这个陌生社会,妈妈们被悬置在一个独立的时空里。
一位陪读母亲讲述着,当场流下泪来。
“她讲到自己有一次崩溃了,大半夜睡不着,就独自在马路上走来走去。陪读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背负着很大的责任。老公在外面打工,也不可能天天向他诉说自己内心的委屈。”
一些苦闷的情绪在棋牌室、跳广场舞的地方寻找出口。齐薇薇觉得,县城对妈妈们来说更像是一个“半熟人社会”,人和人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
无奈的选择
陪读妈妈的涌现,是过去10多年的现象。2001年农村开始推行“撤点并校”的政策,乡村学校在短时间内大量关停。2001年至2012年间,全国乡村小学从44万所下降到15.5万所。
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村镇里的中小学越来越衰落。年轻一代农民的教育意识提高,然而在他们打工的城市,孩子很难获得户籍,于是去县城读书,成了一个折中的选择。
县城里,能提供给陪读妈妈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且大多是服务类,工资也比较低。实际上,对大多数中西部县城来讲,甚至连类似的工作机会都无法提供,大部分陪读妈妈是没有工作的。
在齐薇薇的眼中,这是一代在农村和城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她们感受过城市生活,相比上一辈农民更理解和认可教育的价值;也存留着传统的底色,更重视家庭和孩子,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回来陪读。
这更像是一个无奈的选择。留守在村庄的老人大多跟不上这个数字时代了,老师通过手机和家长进行沟通,老人们既不懂,也不知道怎么管。代际冲突不在少数。齐薇薇也问过很多村民后发现,是否选择回来陪读,妈妈们面临的外界压力比想象中更复杂。
也有少部分妈妈是为了逃避外出打工,以留在县城陪读的名义,每天在麻将馆打麻将打到忘我。但更多妈妈面临着社会和孩子的压力——别人都去陪读了,你不去,亲戚朋友都会议论:“孩子看到别人妈妈陪着,也会要求妈妈回来。”
期待同样来自学校。县城中学和小学的校长告诉齐薇薇——学校肯定更希望家长回来陪读。家校之间的合作更为顺畅的话,对孩子的性格和习惯的培养总归是有好处。
去县城陪读,在近10年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卷入其中。原来是高三陪读一年,现在从初三,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学校周边的旧居民楼变得紧俏,房租连年上涨,又增加了陪读家庭的负担。
要如何面对一个似乎徒劳无功的结果?一位妈妈是这样描述的,“希望孩子不要变坏,能平平稳稳度过‘叛逆期’,哪怕只是读个高中。我尽力就可以了。”
走不出的循环
有学者认为,陪读是农民家庭在教育上的一场风险投资。当一个家庭把所有的资源和注意力都倾注在孩子的教育上,考上一所好的大学,意味着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否则意味着“陪读失败”。
现实是残酷的,县城的教育资源有限,恐怕后者才是大多数陪读妈妈面临的结果——孩子成绩平平,或者无法考上大学。
除了需要面对挫败感,妈妈们也无法从这场投资中全身而退。“很多妈妈,等陪读结束,已经四五十岁了,基本上无法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只能要么依赖老公,要么在县城里找一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洗碗工等等。”
她们的遗憾藏在心底——工作没有了,朋友没有了,社会交往没有了,自己也没有意义了。齐薇薇也是母亲,对于人到中年,家庭和孩子教育带来的压力,她感同身受。
“总体来说,陪读妈妈还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脱离家庭又脱离工作,把教育变成了单独的一块,从家庭中剥离出来。”
受传统性别分工影响,妈妈是家庭陪读中主要承担责任的一方,成为城镇陪读大军中的主力。她们分布在全国2000多个县城里,而县城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
生活负担同样压在丈夫们的身上。齐薇薇在村里见到一位父亲,老婆带着孩子去县城陪读,他就在家独自种几十亩的水稻,收入仅仅能维持家庭开支。“家里不能有任何风险,压力非常大,感觉被生活推着走。”这位中年男人如此描述。
在齐薇薇看来,家庭教育责任不断被强化的当下,学校和相关的公共教育机构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县域教育的规划和布局尤其重要。“为无法进城的农民办好乡镇教育,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城镇的学校要为这些孩子配备相应的公共服务;最后,教育是高度专业化的,还是要让教育回归到学校。”
那些陪读“成功”的母亲,现在又在做什么呢?齐薇薇见过一位“成功”的陪读妈妈,她的女儿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即使代价是,在女儿的中学阶段,母女关系非常紧张。对于她而言,“陪读很有意义的,付出是值得的”。
如今,她陪着刚上初一的儿子在县城继续陪读。生活像是落入了逃不出的循环,她也无奈——“如果不陪读,小孩发展得不好,没有考上好大学,会责怪我的是吧?我把该做的做到,结果如何,至少是问心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