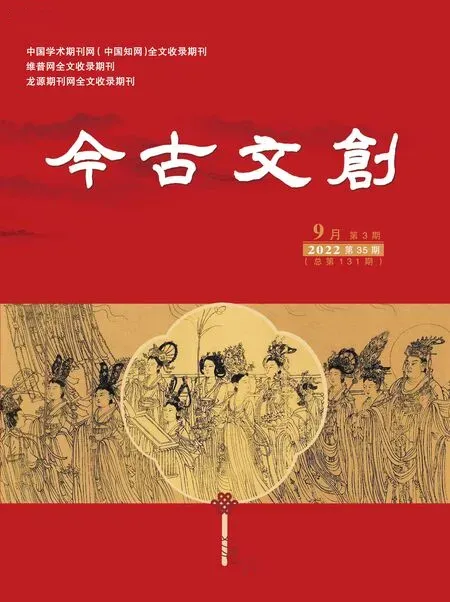从《广艺舟双楫》尊碑思想论清碑学兴起的原因和实质
◎霍 喜
(新疆艺术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9)
清代在中国书法史上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这种特殊意义表现为一种变革,即帖学衰微,碑学兴起。这个时期,书法界的关注点不仅仅只是在流传下来各类书帖,也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大量古碑的出土、碑学理论的确立等因素,让书家开始从古碑中取法。这种背景下推动了碑学的兴起,碑学兴起的主要原因是时代、社会及书法自身发展所决定的。清初的帖学发展到一定时期,已出现许多弊病,书法想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要革新,而通过六朝古碑来复古出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来说,算得上是正确的选择。清末,康有为“上书不达,谣谗高涨”,为了避免因谈国事而受灾,于是其以金石碑版以自娱,著《广艺舟双楫》。康有为进一步阐述了千年帖学已有的诟病,提出“尊碑”才是书法革新之路。
一、达于鼎盛转式微——帖学的衰微
清中期以前,帖学在中国书法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直至乾隆、嘉庆、道光时期,随着碑学的逐渐兴起,帖学的地位有了动摇,产生了由盛转衰的面貌。帖学的衰微的原因是有很多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典刻帖流传千年,因纸本易坏,难以保存,流传下来的也大多为宋明翻刻。
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广艺舟双楫》
作为传统艺术的书法,是不可能离开“继承”二字,因此对于书法家来说取法乎上是必然遵循的,但是六朝遗墨流传至清,鲜有真迹,就算是刻本也大多经历代多次翻刻、摹拓,版本众多,早已面目全非,不再适合学习,就说书圣王羲之所书的《兰亭序》,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学习书法的人奉为绝世经典。其真迹殉葬于昭陵,但就其摹刻本便有数不胜数的版本。如:冯承素神龙本、定武古刻本、定武阔行本、定武肥本……经过如此一代又一代的翻刻、摹拓,所流传至清也早已非原貌,越发失真。其学习的价值也就越来越低,弊端也就越来越凸显。
清杨宾察觉到了这种现象:
宋理宗一百一十七种,桑泽卿百五十有二,毕少董三百本,杜器之、尤克斋各百种,贾师宪八千……亦有三十五种。
——杨宾《大瓢偶笔》
经过历代多次翻刻、摹拓,《兰亭》的摹本多以面目全非,其余古人神韵俱佳的书迹也是这种“旧拓既难,佳刻亦少”的境地。阮元在《揅经室·三集·王右军兰亭序帖二跋》也叙述了王羲之书法经过一翻再翻的摹刻,早已非原貌,而北朝之碑仅经过一次加工,我们所见之碑为下真迹一等,因此他认为北碑更适合我们取法学习。失去传统神韵的摹刻、拓本,难以推动帖学的发展,这种情况也就成为了使帖学逐渐衰微的原因之一。
(二)清初社会书风上不仅尊王,使《兰亭》泛滥,而且还十分推崇董其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使得世人多在学董,而造成众多名家书风无人继承,无人学习,使得书坛风格单一,并因一味效仿董书,也阻碍了自身艺术风格的形成。
康熙曾对董其昌书法真迹题跋:
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
——《跋董其昌墨迹后》
可见其对华庭董其昌书法的偏爱,和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书法一样,这种喜爱造就了一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现象,也致使庙堂与民间都将董其昌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种神化董其昌的原因主要归因沈荃,沈荃为董其昌同乡,有名人效应,其全乡在书法风格上皆学董,沈荃也不例外,后沈荃为帝师,定会影响圣上喜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庙堂与民间皆学董的风气也就盛行开来。
在清初崇王推董的风气下,其余帖学经典便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大流中受到冲击,这种风气导致了取法于其他经典的人较少,这一时期的书坛所展现的艺术风格的丰富性也就相对泯然。此外,这一风气的弊端还体现在文人乡绅们对董书的一味效仿,不思变通,不懂其他经典,这对于自身艺术个性的形成与发展也是有着巨大阻碍的。
(三)帖学的衰微也受到金石学兴起、大量六朝碑刻出土所带来的影响。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
——《广艺舟双楫》
此时金石学的兴盛,大量碑刻的出土,逐渐使得碑学兴起。又因发现的新碑刻多了,使得金石考证的兴盛,其又反过来推动了碑学的发展,而帖学衰微的程度也随着碑学的兴起而更甚了。在顾炎武、朱彝尊等人的影响下,缺乏生气的书坛掀起了金石学研究和寻访古碑的风气,众多书家对碑上的文字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就揭开了碑学运动的浪潮,这个浪潮中既有对碑学书法实践的研究也有对碑学理论的探索。
二、根植传统萌新芽——碑学的兴起
清中后期碑学的兴起与清初帖学的衰微有直接关系,帖学在书坛的主导地位也随着碑学渐兴而渐微。碑学的兴起除了六朝古碑的出土及金石学的兴盛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便是因清人入关以后,为了束缚人们思想而大兴文字狱,使得不少文人学者不得不将研究注意力集中在古籍、金石之上。
(一)不断出土的大量古碑,为碑学提供了研究对象;金石学的兴盛为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众多书家学者又在此时不断地发展、改进、完善碑学理论,为碑学的屹立提供了理论支撑。
故今南北诸碑,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见碑,亦多《金石萃编》所未见者。出土之日多可证矣。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適乘帖微,入缵大统,亦其宜也。
——《广艺舟双楫》
众多新碑的发现,丰富了碑学取法的宝库,也推动了碑学的发展,加之书家对碑学理论的研究,致使到咸同时期碑学广为传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皆有谈论北碑,书写魏书之人。
郑燮书法的独创性体现在他的“六分半书”中,杂真、草、篆于隶中,他曾说“字学汉魏,崔、蔡、钟繇。古碑短碣,可以搜求”;邓石如是在碑学兴起后首位对碑学进行全面实践的书法名家,他的隶书喜用篆法并加入魏碑笔意,楷书得力于北朝墓志,行草也加入篆隶、北碑的意趣,他的实践对后来书家在碑上的探索有十分强大的启发作用;后来的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众多名家也是在碑中找到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名家们的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推动了碑学的兴盛,而碑学的兴盛又反过来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碑派书家。碑学书法从兴起到兴盛离不开书家的实践,也离不开文人书家们在书法理论上的探索。清朝的碑学理论著作《南北书派论》《艺舟双楫》《北碑南帖论》《广艺舟双楫》等对碑学书法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影响力也是极为显著的。
(二)文字狱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恐吓对自己不利的思想、言论而设立的一种统治手段,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文字狱越是在统治稳定的时期,对思想的镇压就越是的登峰造极。清朝文字狱对文人迫害之大,文人们不敢对前代和当时的诗词文赋等内容做过多的评价,众多文人不得不将精力转到对古籍、古代碑刻等内容的研究上,这也造就了碑学理论的丰富。如阮元《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包世臣《艺舟双楫》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论著。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便是在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的基础上所作,文中也对阮元有这样的论述:
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此盖通人达识,能审时宜、辨轻重也。惜见碑犹少,未暇发撝,犹土鼓蒉桴,椎轮大辂,仅能伐木开道,作之先声而已。——《广艺舟双楫》
清中后期,乘帖学之衰微而兴起的碑学,被康有为所推崇,在《广艺舟双楫》中“尊碑贬帖”思想其自身也是有着合理与不合理之处。合理之处主要有以下2点:
1.帖学发展到一定时期,在清朝确实已经出现了很多弊端,开始式微,通过“尊碑”来促进书法的繁荣发展,对于缺乏变革动力书坛来说,算得上是一剂猛药。
2.“尊碑贬帖”的思想促进了碑学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书法艺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当然其不合理之处也是极为明显的:
1.“尊碑贬帖”的思想对于“帖学”过于偏激,对帖学的造成了消极影响。
2.“尊碑贬帖”思想采取的是对帖学的过度否定,未能看见帖的价值,在真迹不复存在的经典作品中,就算是宋明翻刻本,也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总的来说,碑学兴起的意义是极大的,其对于清朝书坛的意义更是重大。当今时代也流淌着碑学的余音,碑学已经成为书法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三、探索实质求真相——碑学兴起的实质
碑学在清朝兴起,看似新产生,实际上它借助的载体大多为六朝及其之前时代的铭石,就其兴起的实质而言,应当为书法发展到一定时期,采取了“复古以出新”的方法来促进书法的发展,这种复古通变思想与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康有为提出“变者,天也”的思想既是在说书法的革新也是在指他自己的变法思想。
(一)书法艺术发展到一定时期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状况,这就要求必须探索艺术的新出路,邓石如、包世臣等人将北碑作为武器,使得碑学在那个时代乘帖学之衰微而产生,这种“复古出新”的艺术思想与他“托古改制”的政治思想相似,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广艺舟双楫》
碑学的出现一改传统帖学笼罩下的书法特点,对笔法、章法等都进行了革新,打破了原本帖学所带来的桎梏,促进了历史发展。康有为将碑学的兴起阐述为“变”,而这种“变”又因为“天”即“变者,天也”的思想。而碑学的“变”又是借助六朝碑刻来实现,归根结底,碑学兴起的实质就是一种借古变今,复古出新,复古通变的思想,这一种思想在西方也是极为流行的,西方的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都是一种文艺思潮,二者也都是强调继承古典,在古典的基础上发展现在文艺。碑学兴起之时也是在通过复古(借六朝及六朝之前的铭石)来发展清当时的书法艺术。
(二)“变者,天也”是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在这规律下“复古而出新”造就了碑学的兴起,碑学的影响很大,清代的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近现代林散之、谢无量等人都通过碑,进而变法找到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当今时代是被称为“后碑学”影响的时代,对于碑学和帖学也都经过了前辈们的反思,对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贬帖”的思想已得到了修正,这也就要求我们对于传统中优秀的帖学经典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坚持,对于碑学我们也要辩证地吸收。
四、结语
帖学在清初开始式微,碑学在清中逐渐兴起,而碑学产生的原因源于书法发展的规律。正如康氏“变者,天也”的观点,认为世间任何事物的规律都是发展变化的,书法艺术的发展也不例外,书法艺术需要发展下去,而书法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新动力新方向,而时代因素使得书家们选择了一条复古通变的道路。碑学兴起的实质是复古出新,这种实质对于当下也具有启示意义,启示在书法研究中,要立足于传统,通过传统来促成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启示了书法创作者在当下这种古朴厚重大气的碑版书法与雅致流动的帖学书风都繁荣的时代,应当兼容并蓄,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