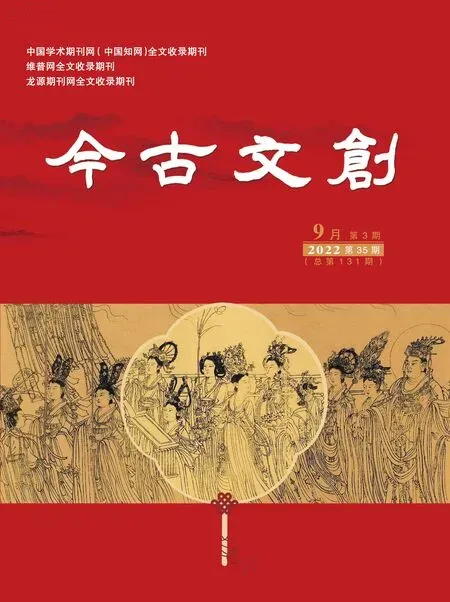自我与他者
——《宠儿》中的女性主体性建构
◎李丹琳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一、引言
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黑人家庭,在浓郁的黑人文化氛围的熏陶之下成长。她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作家,善于从美国黑人的历史和真实生活中挖掘文学素材。《宠儿》(Beloved,1987)的写作灵感来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玛格丽特·加纳一案,为了不再让孩子遭受奴隶制的迫害,不再过那种非人的生活,玛格丽特带着她的孩子从肯塔基州落荒逃至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然而天意弄人,事与愿违,奴隶主紧随其后找到她的藏身之处。玛格丽特不想她的孩子再被抓回去过那种苦不堪言的生活,她痛下杀手,了结了未谙世事的小女儿的生命。
在美国历史上,黑人曾经是奴隶,长期以来遭受白人的压迫和歧视。1619年,第一批黑人以奴隶的身份被贩卖运往美洲,尽管他们和英国白人殖民者同时踏足美洲,但因身份性质不同,黑人们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如同牲畜般在南方种植园辛勤劳作,生活艰辛。特别是黑人女性,她们饱受压迫,沦为奴隶主的生产机器和泄欲工具。黑人遭受奴役,是因为他们的肤色,并非因为他们的懒惰,更不是因为他们的无知。南北战争结束后,虽然奴隶制度被废除了,但是黑人的生活状况并无多大改观,黑人的解放只是徒有其名,黑人依然遭受着压迫和歧视。
自1987年发表以来, 《宠儿》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博得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基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分析可知,大部分学者从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母性象征、叙事风格、非洲传统元素、创伤理论等视角对小说进行解读,然而对小说中女性主体性建构进行研究的文章较为鲜见,所以笔者认为对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性建构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研究价值。托尼·莫里森于字里行间透露了黑人女性塞丝和丹芙的生存焦虑,她们在与他者的交往中历经考验,于困境之下通过审视自我进而建构女性主体性,最终生存焦虑得以消除。
二、他者对主体生存焦虑的影响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认为,人先于他的本质而存在,人的本质是在后天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人生下来,并无善恶之别。人通过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塑造自己的人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人。在个体进行主体性建构的时候,他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1943)中,萨特还认为,“在主体建构自我的过程中,他者的‘凝视’(gaze)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者的‘凝视’促进了个人的自我形象的塑造。”在他者对自我的凝视和判断中,我们作为凝视的对象开始对自我发问“我是谁”“我来自哪里”。在与他者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积极地融入他者。主体是认识者、行动者,如果对自我认识模糊,不能与他者和谐相处,将激发主体的生存焦虑。
(一)塞丝的生存焦虑
“弗吉尼亚州1662年通过的法令允许男性白人占有女性黑奴。如果母亲是奴隶,她的孩子也将是奴隶,女性黑奴成为提供奴隶劳动力的生产工具。”就社会地位而言,男性和白人位于黑人女性之上,是她们的统治阶级。女黑奴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其地位形同牲畜。奴隶主强迫女黑奴不断地为其生孩子,为庄园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但身为一名奴隶,母亲对这些孩子没有所有权,爱与被爱的权利被无情剥夺,她不能去爱这些孩子。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生了八个孩子,她只留下了塞丝的丈夫黑尔,对别的孩子的记忆几乎为零。她憎恨白人,她认为“这世界上除了白人没有别的不幸。”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奴隶制对黑人身心的摧残程度之深。
塞丝的生存焦虑主要源自残忍的奴隶制以及弑婴的内疚。在甜蜜之家,塞丝遇见了黑尔,并与黑尔育有四个孩子,她以为自己会继续在甜蜜之家快乐地生活下去。真正让塞丝下了逃跑决心的是那次听见“学校老师”跟两个侄子的对话。“我跟你讲过,把她人的属性放在左边;她的动物属性放在右边。别忘了把它们排列好。”学校老师作为站在塞丝对立面的他者,让塞丝认识到在奴隶主的眼里,虽然同是有血有肉的生物,但是奴隶却不配被称为人。她想成为人,想获得爱孩子的权利,她意识到甜蜜之家并非真的甜蜜,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这里不是乐园反而是地狱,这里充斥着歧视和压迫,奴隶主视奴隶为牲畜般的财产。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和渴望自由,塞丝带着孩子们走上了逃亡之路。虽然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但是她被迫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这致使她一直活在焦虑之中。
(二)丹芙的生存焦虑
丹芙虽没有亲身体验过奴隶制度的残忍,但是她的生活并没有好过多少,因为她周围没有一个正常人来引领她的成长。她与母亲塞丝、奶奶贝比·萨格斯住在与外面世界隔绝的124号,这里充斥着怨恨,小鬼魂经常出来捣乱。母亲塞丝是一个有着铁的眼睛、铁的脊梁的黑人女性,她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所以塞丝无法给予丹芙正常的母爱,她把丹芙圈在124号,这让丹芙感到孤独,缺乏安全感。在奶奶去世、两位哥哥相继离家出走后,小鬼魂成了和她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保罗·D的到来把她唯一的小伙伴鬼魂给赶跑了,她非常排斥这个他者的到来,所以她只能去林间的祖母绿密室寻求安慰。
丹芙的生存焦虑一方面是由家庭原因造成的,另一方面还来源于黑人社区的孤立。黑人社区的居民因塞丝一家获得自由而心生嫉妒,他们纷纷跟塞丝一家断绝来往。黑人社区的其他黑人居民对丹芙而言,是把她从社区生活中驱逐出去的他者。在童年时期,丹芙渴望学到知识和拥有自己的玩伴,她曾在琼斯太太那里求学。她的同学内尔森·洛德问:“你妈妈不是因为谋杀给关起来了吗?她进去的时候你没跟着吗?”自此之后她开始封闭自我,双耳自动失聪整整两年,听不到外界的声音,除了鬼魂爬楼梯的声音。小说中丹芙双耳失聪象征性地说明她想与外界隔绝开来,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内。
三、女性主体性建构
(一)塞丝的主体性建构
塞丝的弑婴行为是由美国社会奴隶制的残酷无情造成的,是奴隶制催生出来的产物,同时也是她奋起反抗奴隶制的一种表现。奴隶法规定奴隶是奴隶主的所有物,奴隶的孩子也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塞丝坚定地认为她杀害孩子,只是想把他们都送到安全的地方去,这样子他们就不会遭到白人社会的迫害。作为奴隶,活着和死去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们无法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完整自我。黑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劳作只有利于他们的奴隶主,他们的贫困和悲惨是奴隶主一手造成的,他们渴望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拥有完整的人格。
塞丝一直想把自己的记忆埋藏起来,这跟美国社会想要忘记奴隶制那段黑暗历史是一样的。美国白人不愿记起,是为自己实施的惨绝人寰的行为感到羞愧;黑人排斥记忆,是不想让曾经的痛苦经历打扰现如今的安逸生活。正如莫里森所言,《宠儿》在发行的时候,她认为《宠儿》是她众多作品当中最滞销的一部作品,因为就这部作品的内容来说,它是所有白人、黑人以及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极不愿意再去回忆的一个故事。简单地说,就是全民记忆缺失症。塞丝深知黑人女性的痛苦,在当时,女性被当做“物品”“动物”,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来对待,处处惨遭践踏。她预估宠儿的命运将会跟自己的命运一样,她不想她的孩子重蹈覆辙,所以她痛心将孩子扼杀于襁褓之中。当我们变成凝视的对象时,他人的承认能使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反之我们会在他人的否认中迷失自我。黑人社区的其他黑人无法理解塞丝的弑婴行为,在他们看来,塞丝太孤傲了,她与黑人社区之间产生了隔阂,以至于后来“学校老师”追来的时候,都没有人给她通风报信。她被逮捕带走后,社区的人们也反应冷淡。
塞丝是黑人社区的凝视对象,黑人社区的他者无法理解塞丝内心的痛苦,只看到了她的孤傲和残忍。在塞丝的内心,充满了内疚、悲伤、爱等各种各样的情愫,她的精神备受煎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快乐生活,逐渐迷失自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但过去的经历一直停留在脑海里,到某个时机,它就会再现。“因为虽然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结束了——它将永远在那里等着你。”保罗·D与塞丝过去同在一个奴隶主庄园工作,看到保罗的时候,塞丝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过去的事情。萨特认为,他人同我一样,都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是具有“否定性”的自为的存在,因而他人是另一个我,萨特对他人存在的证明是从注视理论开始的。保罗·D是塞丝的另一个我,在跟保罗在一起的时候,保罗的注视让塞丝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羞愧和内疚,过去不断地在塞丝的脑海里闪现。
回忆就像住在124号里的鬼魂,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她。她的心灵充满着内疚,依然被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中。被保罗赶走的鬼魂后来重新回到124号,因为塞丝把孩子视为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她答应宠儿的一切无理要求。萨特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正在往门内偷窥,当你听到脚步声的时候,你怕被别人发现,因此你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宠儿因为记恨塞丝,所以疯狂报复塞丝。塞丝因为对宠儿心怀愧疚之情,为自己的弑婴行为感到羞耻,所以只好默默地承受来自宠儿的报复。
萨特在对他者的分析中存在着一种悖论:一方面,我们作为凝视主体,能感受到自我和周围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我们在认识他者的同时,也不断地对世界产生新的认识,并且为自我在世界中寻找定位。塞丝认为孩子是她最宝贵的东西,但保罗不断地给塞丝灌输一种思想:世间万物,惟有自我最为宝贵。塞丝任凭宠儿无理取闹,但在此过程中,她开始意识到她太过于在意过去了,以致差点儿让自己窒息。“我和你,我们拥有的昨天比谁都多。我们需要一种明天。”塞丝在与众多他者的交往中,开始寻找构建主体性的路径,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应该放下过去,才能在这个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明天。
(二)丹芙的主体性建构
长年累月的孤独生活使丹芙失去了自我,她虽然已经成年了,但内心与刚出世的婴儿差不多。在保罗·D来到124号,母亲塞丝把一部分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他身上,这让丹芙很恼火,她讨厌塞丝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讨厌听到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后面宠儿的还魂归来给丹芙的生活带来了新转机,宠儿不仅是她的伙伴,还是她的另一个自我。在与宠儿的朝夕相处中,丹芙意识到她们之间的区别。宠儿虽然已经长大成人,但缺乏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母亲塞丝要去上班赚钱养家,丹芙只好担负起照顾宠儿的责任,在悉心照顾宠儿的过程中,她得到了快乐,也开始成长起来,变得越来越有责任感。丹芙从宠儿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只要宠儿回以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微笑,都让丹芙感到非常地满足,丹芙能从宠儿身上得到抚慰。“能够得到她哪怕短暂的注视,即使在其余时间里只当个注视者,也让丹芙感激涕零。”他者宠儿掌控着丹芙成为自我的秘密,丹芙心里的安全感、身份认同感,能够从宠儿身上获取。这使得丹芙觉得宠儿就是她的全部,在宠儿的注视下迷失了自我。随着时间的推移,丹芙逐渐习惯了依托宠儿的存在而存在,他者宠儿对丹芙的认可能让她安心,对丹芙的主体性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丹芙看到宠儿在疯狂地折磨妈妈塞丝,宠儿占据了塞丝全部的生活,使得塞丝也不出家门,彻底迷失了自我。“她必须走出院子,迈出这个世界的边缘,把那两个人搁在后面,去向别人求救。”丹芙这个时候意识到她必须走出124号这个封闭世界的边缘,她勇敢地迈出家门向琼斯太太和黑人社区求助,黑人社区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纷纷给丹芙一家捐赠食物。“我”除了直接与其他客体他人发生关系,还可以与其他客体结为群体——我们,而我们是在与他人的联合的过程中发现我们自己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我们”,当被第三者注视时,我与他人发生的关系称为“对象——我们”,反过来当我在一些个人的集体活动或集体劳动中形成的“主体——我们”。丹芙融入到社区生活中,这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主体——我们”。社区中的黑人默默注视着丹芙,对丹芙的求救及时作出回应,帮助丹芙融入社区。主体性的构建要建立在认同和团结的基础之上,社区人们对丹芙一家伸出援手,能让她感受到她是真实存在的主体。
丹芙靠自己的努力求得生存,赢得自尊。丹芙开始去打工还有学习文化知识。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黑人是无法像白人那样正常接受教育的。黑人被白人奴隶主强行灌输了太多错误的观念,禁锢住他们的思想。白人剥夺了黑人识文断字的机会,把他们当牲畜一样对待,营造了白人高人一等的错觉,让黑人失去自我。奴隶制度否认了黑人是一个独立个体的事实,扼杀了黑人的权利。因此,黑人如若想获得解放求得自由,首先得认真地审视自己,对自己形成一个充分的认识。丹芙通过融入黑人社区和努力学习新知识,实现了自我主体性的构建,从一个孤独懵懂无知的少女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
四、结语
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有一句千古名言:认识你自己。通过不断地感知周围环境的变化,我们会渐渐对自己形成一个清晰的认知。这个过程需要与他者发生碰撞与融合才能完成。小说中出现的他者对塞丝和丹芙的主体性建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者是自我的一个反照或投射,塞丝和丹芙在与他者的冲突碰撞中,挣脱社会制度、种族和性别的桎梏,实现自身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消除自我的生存焦虑。
莫里森借此小说揭露了美国主流社会对黑人女性施加的压迫,批判了致使黑人女性丧失主体性的行为。塞丝和丹芙的主体性建构也象征着整个黑人社区主体性的建构,她们主体性建构的成功经验为饱受苦难的黑人女性指明了一条可行的救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