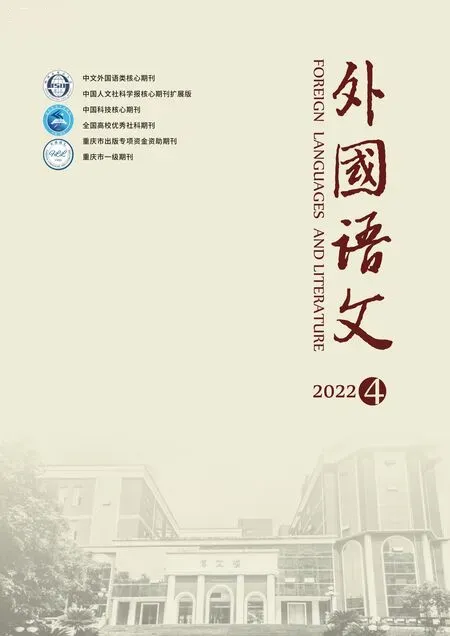与时代共名:新民歌运动与域外诗歌译介
李金树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 重庆 400031)
0 引言
1 新民歌运动:语境与规范
1.1 “新民歌”语境的生成
“新民歌运动”的开展或语境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有其酝酿、发展、鼎盛、衰落的历史脉络。“新民歌运动”萌芽于“大跃进”的时代土壤,经由领导人倡议、文艺官员的阐释和推介、各级党政机关的呼应和运作、主流媒体的跟进和鼓动、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和实践,层层聚力,酝酿烘托,并逐渐衍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文艺实践活动。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李慈建,1999:177),为新民歌的滥觞定下基调。
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新民歌”的创作和采风运动。同年5月5 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扬代表文艺界作了题为《新民歌开辟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高度评价新民歌运动,认为新民歌“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周扬,2009:54)。1958年7月,《红旗》创刊号正式发表了周扬的《新民歌开辟了诗歌的新道路》,在公共空间正式传达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对新民歌这个崭新的文化现象进行理论上的论定和支持”(谢保杰,2005:29)。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县党委宣传部纷纷发出通知,强调收集新民歌、创作新民歌是“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创作、研讨民歌,成一时风尚。参加讨论的有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诗人、批评家。先后发起讨论的刊物,主要包括《星星》《处女地》《诗刊》《萌芽》《文汇报》《人民日报》《文学评论》《长江文艺》等,争论十分激烈(郑青,1959:118)。讨论或批评恰恰为民歌的“经典化”提供了流布渠道和传播途径。
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不仅倡导写民歌,还编民歌集(如郭沫若所编《红旗歌谣》等)。宣讲民歌,刊发民歌,编辑民歌,展开诗歌争鸣,使民歌这一主题逐渐“经典化”,形成全社会(至少是文学艺术界)的共识。《文学评论》更是在1959年刊出系列文章,讨论诗歌的创作,包括王力《中国格律诗传统与现代格律诗的问题》、朱光潜《谈新诗格律》、罗念生《诗的节奏》、金克木《诗歌琐谈》、唐弢《从“民歌体”到格律诗》、周煦良《论民歌、自由体和格律诗》及袁可嘉《彭斯与民间歌谣——罗伯特·彭斯诞生二百周年纪念》、郑青《诗歌发展问题上的争论》、力扬《诗国上的百花齐放》等。
综上所述,在政府赞助人、主流政治话语、专业人士、普通大众及主流报刊杂志的“介入批评”下,新民歌被誉为“最好的诗”(萧三,1958:25),已然成为彼时“时代的最强音”和“探照灯”(郭小川语),确立并规训着彼时诗歌创作及译介的诗学规范和审美趣味。
1.2 诗歌规范的形成
作为“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天鹰,1959:2),“新民歌运动”甫一开始就从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体裁上对诗歌创作提出了规范要求,成为此一时期诗歌创作和译介的圭臬。诗歌应该写什么,怎么写,为谁而写,是主流话语关心并倾力主导的核心议题。在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年代,必然产生对于文艺的“规范性”要求,“不仅明确规定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而且规定了理想的创作方法;不仅规定了‘写什么’(题材,主题),而且规定了‘怎么写’(方法,形式,风格)”(洪子诚,2003:128)。
1.2.1 思想内容
新民歌的思想内容虽丰富多彩,具有多面性,但其政治面向处于主导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从其界定可知一二。例如,“新民歌”在一定意义上被称为“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郭沫若 等,1959:2),是“群众共产主义精神高涨的一种表现”(柯仲平,1958:6)。也就是说,诗歌思想内容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审美作为基调的。正如郭沫若与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所论,其选材标准是“要有新颖的思想内容”。从所选300篇民歌来看,内容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歌颂祖国,如《过去与今天》《长岭坡》《百草万物也心欢》等;其二,歌颂共产党和领袖,如《毛主席像红太阳》《歌唱共产党》《太阳的光芒万万丈》等;其三,歌唱社会主义新生活,如《合作化道路通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万人齐唱东方红》等;其四,英雄颂歌,如《英雄本色就是诗》《战士个个花中花》《古战场上扎军营》等。若细读这三百首民歌,不难发现,编选者聚焦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其歌谣内容政治叙事是第一位的。正如何其芳在《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一文中指出,新民歌“最吸引人的还并不是它们的形式,而是它们的内容表现出来了神话中的巨大的惊天动地的征服自然的精神,反抗的精神”(郑青,1959:118)。
甲洛洛便抱着小阿布坐在营业部门口的木桩上,他今天特别开心:小阿布,你的糖是从哪儿来的啊,是不是爷爷给你的留着没舍得吃。小阿布认真起来:这是阿爸给害病的哥哥吃的,让我看见了,阿爸才给了我一小点,让我吃完才准出门,还不许我告诉任何人家里有糖,不然饿鬼会把我吃掉。我想到爷爷,就悄悄的把糖藏了一半。
1.2.2 艺术形式
在主题先行的制导下,诗歌的艺术性虽说退居次席,但也并非可有可无,也有较为突出的艺术特色,成一时风尚,引为诗歌创作和翻译的典范。有学者总结道,大跃进初期出现了一些情感质朴、格调清新明快、抒发群众尤其是农民真情的民歌,这些民歌的特点,如质朴的语言、直白的表达、丰富的想象、炽热的情感、明快的节奏等,初步形成了新民歌的特色和风格。简洁、明快、质朴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是新民歌较突出的艺术特色(郑祥安,2006:27)。
作为“新时代的人民的诗歌”(徐迟,1959:14-15)和“绝妙好诗”(徐迟,1959:18),新民歌的艺术形式颇具“大众化”,即在民族形式上追求“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1952:522-523),在语言层面提倡与大众现实生活贴近的“口语化”方向。鉴于民歌接受主体为工农兵大众(这和毛泽东提出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是相吻合的),他们所受教育有限,文化水平不高,难以理解意象丰富、辞藻晦涩的诗章,因此,选择用词简单朴素、曲调优雅上口、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诗歌,极力表现大众情调,将劳动生活或场面“民歌化”或“诗歌化”,展现普通百姓的基本价值诉求,是全体诗歌创作或翻译工作者遵从的规范。从《红旗歌谣》所辑民歌的标题即可窥见一斑,例如,《想起来公社忘不了你》《我们幸福了》《花也舞来山也笑》《叔叔三次到咱家》《大河和小河》《一天变作两天长》《村东有一个水库》《田里的河泥》等。正如天鹰(1959:27)所论,“所谓新诗歌的基本道路,我的理解是指一个国家的诗风和诗歌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也就是诗歌的民族化和群众化的问题”。
简言之,新民歌在思想内容上遵循主流政治话语,亦步亦趋,唱赞歌,颂大众;在艺术上, 则有“形象的鲜明, 音节的整齐、响亮, 色彩的明朗, 语言的精炼生动”(邵荃麟,1981:372)等特点,从而为异域诗歌的译介营造和奠定了充分的范型语境。
2 “新民歌运动”指导下的异域诗歌汉译
“新民歌运动”为域外诗歌汉译提供了历史语境,为其出场烘托并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渊源。此一运动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彼时的文学界和诗歌界,绝大多数诗人和作家都纷纷“以新民歌的美学特征来规范自己的艺术个性”(谢保杰,2005:34);同时,这一运动也强烈地波及至翻译界,众多译家都积极译介域外诗歌,从译介主题、译介语言、译介批评等多个方面探索诗歌译介与“新民歌”的关联,“总是附加有一定程度上的目标文化主导价值观”(邵璐 等,2022:11),以期跟上或适应新民歌“节奏”,“趋时性”特征明显。
2.1 异域诗歌成译介新宠
新中国成立之初,域外诗歌的译介可说是“不愠不火”,但“新民歌运动”的开展及其所营造的诗歌氛围,为异域诗歌的汉译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化为翻译的内在驱动力。国内翻译界和出版界极力译介异域诗歌,尝试从外国诗歌中寻觅灵感和给养,配合国内民歌运动。正如力扬(1959:32)所呼吁,“我们要发展民族诗歌,是不能不汲收和借鉴外国文学中好地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因此,1958—1959年出现了异域诗歌汉译的高潮。
笔者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编《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和提要》(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手工统计了“十七年”(1949—1966)异域诗歌翻译出版数据(见表1 、表2),并借此图表对比,结论便一目了然。

表1 十七年间翻译出版多国诗歌集一览表

表2 十七年间翻译出版外国诗歌作品一览表
由表1可知,1949—1966年共翻译出版多国诗歌集26部。其中,1958—1959年合计出版10部,占比近40%。由表2可知,1949—1966年翻译出版或再版或不同出版社重版外国诗歌作品(集)共计503部(种)。异域诗歌翻译自1949年始,逐年呈增长趋势,1959年达到顶峰,多达72部(种)。1958年和1959年共翻译出版高达139部(种),占比27.63%。
表1和表2的数据表明,仅以诗歌体裁翻译的数量而言,1958年和1959年这两年达到“十七年”间的巅峰。数量的骤增和“新民歌运动”的消长高度吻合,这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其来有自。由于特殊的历史语境,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高度工具化。前文已述,“新民歌运动”所营造的诗歌规范,也成了翻译题材选择的“导向标”,引导或敦促译者贴近或服膺它所确立的诗歌规范和秩序。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译介就较为典型。袁可嘉(1959:88)就曾坦言彭斯的译介动机:“彭斯与民间文学的血肉姻缘很自然地引起正在讨论的新诗与民歌关系的中国文艺界的兴趣。”王佐良(1997:761)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在 50 年代的大规模新民歌运动中,这位苏格兰民歌的作者、保存者被视为同调,又恰逢他的 200 周年纪念来临,于是条件具备,对他的翻译和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据袁可嘉和王佐良的论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彭斯之所以获得译介资格,并非来自其诗歌的审美性和文学性,而是其诗歌的特质正好吻合国内新诗运动的诉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学艺术对政治诉求的皈依。
2.2 诗歌选材的趋时性
作为“一场有组织的文化生产运动”(巫洪亮,2010:83),“新民歌”探索诗歌艺术审美的意愿和努力要远远低于其文化政治表现力。“新民歌”着力于为社会主义的人和事唱赞歌,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或战斗意志鼓与呼。对作品“思想性”的甄别是彼时翻译工作的重中之重。正如卞之琳等(1959:42)指出:“对于外国文学遗产,特别要首先看清楚其中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思想究竟怎样,……本着‘政治标准第一’的精神,首先分析其中的思想倾向,也就成为我们的特别迫切的课题。”这一选材理念反映到异域诗歌的译介上,就是对诗歌思想内容和译介策略的“精挑细选”和“反复琢磨”,极力“趋时”。一方面对异域讴歌人民生活旨趣或坚强不屈斗争精神的诗歌青睐有加,积极译介,而另一方面却对西方现代派诗歌进行民族性“祛魅”,视而不见或“译而不宣”(内部发行)。
下面以1958—1959年多国诗歌集的翻译出版为例,加以说明。1958年翻译出版的七部多国诗集包括《歌颂新中国》(作家出版社)、《阿拉伯人民的呼声》(人民文学出版社)、《滚回去,强盗!》(作家出版社)、《美国人,滚回去》(拉丁美洲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牢狱的破灭》(印度、巴基斯坦现代乌尔都语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阿拉伯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非洲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翻译出版的三部多国诗集包括《愤怒与战斗》(上海文艺出版社)、《伊朗、阿富汗和平战士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平战士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这些诗歌的主题基本上是反映和颂扬亚非拉人民反抗压迫、争取民族合法性、祈愿和平的心声,与新民歌所倡导的“反抗精神”步调一致。
再来看看英美诗歌在1958—1959年的译介情况。美国诗歌共六部(种),包括朗费罗所著《海华沙之歌》(王科一译,上海文艺出版社)、《伊凡吉琳》(李平沤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新1版)、《朗费罗诗选》(杨德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玛·米列所著《米列诗选》(袁可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洛森堡夫妇纪念诗选》(朱维基译,新文艺出版社)及路温菲尔斯所著《路温菲尔斯诗选》(方应旸译,上海文艺出版社)。英国诗歌共15部(种),包括拜伦所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杨熙龄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新1版)和《唐璜》(朱维基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新1版)、约翰·济慈的《济慈诗选》(查良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弥尔顿的《复乐园》(朱维之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新1版)《科马斯》(杨熙龄译,新文艺出版社)《失乐园》(傅东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弥尔顿诗选》(殷宝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彭斯的《彭斯诗钞》(袁可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彭斯诗选》(王佐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的心呀,在高原》(袁水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乔叟的《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方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新1版)、莎士比亚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屠岸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新1版)、大卫·乌莱特的《裴欧沃夫》(今译《贝尔武甫》)(陈国桦译,中国青年出版社)、雪莱的《云雀》(查良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雪莱抒情诗选》(查良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原著者的身份而言,乔叟、弥尔顿、莎士比亚属于古典主义诗人,朗费罗、拜伦、雪莱和济慈属于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而米列、路温菲尔斯和彭斯则代表工农阶级,具有“革命性”的初始立场。就诗歌的主旨而言,朗费罗的诗歌着力于“自我民族的赞美、对人生的光明向往”(吴赟,2012:55);米列和路温菲尔斯的诗歌反映了美国左翼进步作家对和平与民主的追求和向往;雪莱的诗歌“揭露现实”“刻画理想,表达对未来社会的热爱”(吴赟,2012:51);拜伦的诗歌具有革命反叛性,启示人们抗争;彭斯的诗歌扎根民间文学,表现普通大众的人生历练和革命情怀,如此等等。显然,上述作家身份及其诗歌所表现的诗学特征深度契合了新民歌所倡导的诗歌的“浪漫性”和“现实性”,因其“进步”和“革命”,为其诗歌译介赢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反观英美现代派诗歌,其身影在整个“十七年”几乎绝迹。除零星的全面否定的诗歌批评外,无一本现代派诗人的诗歌得到翻译出版机会,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决定介绍与否的一个重要条件”(卞之琳等,1959:42)。现代派诗歌被定性为“政治上反动、思想上颓废、艺术形式上形式主义的文学,是反现实主义的反动诗歌”(吴赟,2012:87),自然无法取得译介的政治合法性,被弃绝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2.3 译介批评的“新民歌”倾向
“新民歌运动”期间,文艺批评界对新民歌称许有嘉。翻译(批评)界一方面“身体力行”,积极翻译符合新民歌诗学规范的异域诗歌;另一方面,基于“民歌”立场,他们或积极撰文或通过翻译“副文本”如前言、译序、译跋等,研究、审视、解读异域诗歌的思想主旨和美学特征,嘉许与新民歌“同调”的异域诗歌。
首先,对待译诗人展开研究,嘉许诗人与“新民歌”的关联性,进一步夯实译介的合法性。例如,随着“新民歌运动”的展开,对彭斯的译介和研究逐渐升温。1959 年,恰逢诗人诞生 200 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袁水拍翻译的《我的心呀,在高原》,录诗30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袁可嘉翻译的《彭斯诗钞》,录诗89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翻译的《彭斯诗选》,录诗37首。据不完全统计,研究彭斯的学术文章包括王佐良的《彭斯诗抄》(《诗刊》1959年第5期)和《伟大的苏格兰诗人彭斯》(《世界文学》1959 年 1 月号)、杨子敏的《罗伯特·彭斯——伟大的人民诗人》(《诗刊》1959年第5期)、袁可嘉的《彭斯与民间歌谣——罗伯特·彭斯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和《彭斯诗三首》(《世界文学》1959 年 1 月号)及《彭斯的诗歌》(《文学知识》1959年第5期)、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二年级八班集体翻译的刊载英共名誉主席威廉·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的文章《罗伯特·彭斯:纪念苏格兰人民诗人彭斯诞生二百周年》(《西方语文》1959 年第 3 卷第 1 期)、范存忠的《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彭斯诞生200周年纪念》(《南京大学学报》1959 年第 2 期)、南星的《略谈彭斯的诗歌和技巧》(《新港》1959年第6期),等等。这些研究文章“均充分探讨了彭斯诗歌充分的人民性、革命性与战斗性”(吴赟,2012:47)。王佐良在《彭斯诗选》前言中就指出:“彭斯……走了一条唯一该走的路:用随母乳以俱来的活的方言去写劳动人民的生活。表面上,这似乎只是一个语言上的改变,一件纯粹属于形式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是使诗重新受到本土方言文学的深厚传统的滋养,从而使诗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头等重要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彭斯,1959:14)这种批评着力拔高了彭斯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切合了彼时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流露出某种批评的泛政治化倾向。正如袁可嘉(1959:43)所言:“今天我们广泛介绍彭斯的作品……我国文艺界正在热烈讨论新诗与民歌的关系问题。这时来探讨一下彭斯怎样吸取歌谣中的精华,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创作,而这些诗歌创作中的优秀部分后来又回到民间,反过来丰富了歌谣传统,这无疑是既有趣又有益的事情。”
其次,对诗歌聚焦政治审美,“以点带面”,选择性褒扬,有意凸显或拔高诗歌的政治旨趣,在“新民歌”的诗学轨道上框范和阐释诗作。因此,对政治面貌清晰的诗人,极力总结其诗歌的政治表现力,往往忽略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如方应旸(1959)在其译著《路温菲尔斯诗选》的内容提要中这样介绍,路温菲尔斯“是美国的共产党员,曾受美国反动当局的非法逮捕”,他的诗“有的猛烈地谴责了美帝策动的侵朝战争,有的尖锐地抨击了美国统治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有的愤怒地抗议美国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虐待,有的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对和平的热爱。总的来说,这些诗表现出作者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和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的气概”。而对一些政治面目不甚清晰的诗人,译者往往会特别突出其人民性和革命性。如查良铮(1958:5)在《济慈诗选》的译者序中就特别指出,济慈的诗歌所表现的“人文主义,对自然和对人所持的自发唯物主义的、享乐的态度,激进的社会观点,对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本质的抗议——这一切使济慈和湖畔派诗人们迥乎不同,却使他和革命浪漫主义者颇为接近。”济慈的诗歌,“都是充满了热爱生活的乐观情调的”,“后期的济慈不但接近现实主义,也更接近了人民”(查良铮,1958:7)。他注意到民歌的写作,更多地看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他的语言也由最初典丽而模糊的辞藻趋于单纯的、富于表现力的口语(查良铮,1958:8)。“这样的作品在教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明朗的性格方面,当然还是有所帮助的。”(查良铮,1958:8)译者一语道破天机,翻译的真正动机在于教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明朗的性格,这和民歌的思想主旨是不谋而合的。
最后,对不符合新民歌诗学规范的异域诗歌(主要是英美现代派诗歌)极力贬抑、挞伐,对其“异质”思想进行批评,力陈遭弃绝的合理性。例如,“新民歌”的盛行,对结构严谨、节奏匀称的十四行诗产生了时代和社会的审美错位,称其为“洋八股”,予以否定和批判。有批评者认为,“创造定型律的形式,我们早已深恶痛绝的了,即近来什么十四行,以及每节四句的样式,我们都不要他”(转引自王亚平,1996:49)。还有论者认为,十四行诗“更是僵化了的西欧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诗歌形式”,“这种形式已经没有一点生命力”,“已经随着产生它的时代和阶级一去不复返了”(安旗,1958:56-57)。又如,袁可嘉更是称英美现代派诗歌为“腐朽的文明,糜烂的诗歌”,抨击现代派诗歌“宣扬凶暴淫乱、梦幻和歇斯底里”,“既反映了资产阶级作家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精神崩溃,又通过对读者的麻痹和蒙蔽作用,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解体过程”(袁可嘉,1963:84)。
绿源曾说:“诗不是哲学和历史,不能以真为美,诗不是伦理道德准则,不能以善为本,诗是艺术,是审美活动和审美对象,只能以美为本。”(孙郁,2015:146)反观“新民歌运动”期间的诗歌批评,唯思想性马首是瞻,以“人民性”“革命性”“现实主义”等条条框框来界定或限制诗歌译介的主题和精神内核。此种批评也在隐性地引导、彰显民歌化诉求的社会政治功能,实质上是呼应整个赞助系统对民歌的政治功能定位。
3 结语
十七年的文学场域,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政治具有压倒一切的统摄力。那时,“批评家格外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温儒敏,2003:41),“译介何种外国文学不再是一种个人兴趣的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行为”(方长安,2002:88)。因此,诗歌翻译被赋予了时代的文化政治意义,成为彼时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纵观1958—1959年的异域诗歌的译介,无论是诗歌的主题选择还是具体语言的调适,都与“新民歌运动”亦步亦趋,引为同调。此一时期的外国诗歌汉译蕴含了彼时的政治美学,实质上是对流行观念的演绎,译者是以翻译的方式响应和践行了自身对诗歌世界与政治秩序的关怀。也就是说,彼时的异域诗歌汉译都是诗歌与历史相互对话与彼此诠释的结果。很大程度上,这种“同调”并非异域诗歌汉译本身的审美诉求,而是彼时诗歌运动规约下的历史抉择。研究“新民歌运动”前后异域诗歌的汉译,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主流政治意识与诗歌译介的关系,探讨诗歌翻译的策略、接受和影响,而且还能发现特定历史语境中诗歌翻译的规律、特征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