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林、蒙森到尼采:19世纪德国语文学的理念、争议及其对数字人文的启发
程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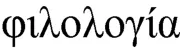
一、格林:非精准科学及其精准化愿景
雅各布·格林及胞弟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不仅是《格林童话》的搜集整理者,也是《德语辞典》编纂工作的发起人。雅各布主事法律史、语言史、德语语法等方面工作,威廉则侧重英雄史诗、民间诗歌等古代文本,他们在德国民族语文学研究起步阶段扮演着决定性角色。在1846年第一届日耳曼学大会上,雅各布·格林(本文简称格林)提出了“精准科学”与“非精准科学”(exacte/inexacte Wissenschaften)的概念:
属于精准科学的是那些每句话都要求精确无误地计算证明的领域:数学、化学、物理,它们一旦缺少这种精准性,其所有尝试和努力也就无法结出果实。属于非精准科学的正是我们献身的学问。在这类研究中,我们能够容忍自己在实践中迷途,容忍相关研究可能在长时间内存在的谬误和不足,直到它们在持续的进步中摆脱错误和缺失,变得日益纯粹,例如历史、语言研究[……]陪审团的判决不是计算题,而仅仅是简单的人之理性。这种理性也往往无法避免出错。(Grimm,“Über den Werth”59)
在当时人文研究理解阐释性与自然科学构建规律性的分野还不明显的时代里(例如大文豪歌德就对解剖学、光学和植物学感兴趣),格林已简明扼要地指出了精准与非精准科学的特点和内容,即精准科学可被视为自然科学,包括语言和历史的语文学研究则属于非精准科学。在格林看来,精准与非精准科学各有所长,精准科学“可将最原始的物质拆解,然后重新组合。一切使人震惊乃至恐惧的杠杆和发明都独出于此”(Grimm,“Über den Werth”59)。但同时他也高度认可“非精准科学”的特点、价值及它在民族认同中的作用,认为非精准科学研究者“有勇气挑战最艰巨的任务,而精准科学研究者反倒会避开一系列未曾解答的谜团。精准科学研究能向我们解释,植物是如何发展出不同的颜色和芳香气味的吗”?他还指出,“化学坩埚能在任何火焰下沸腾,新发现后用冰冷拉丁语洗礼命名的植物在同样的气候和海拔环境中能到处生长”,但相比“遍布寰宇、有利于外国学者但却无法抓住人心”的精准科学,语言和文学意味着更多,“敢问哪位自然研究者曾像歌德与席勒那般构建过德国”(60)?可见,虽然格林强调语文学的严谨性和规范性,但他同样重视语文学之于人心特别是之于民族认同的功能。正因对非精准科学价值的凸显,格林这次讲话后来被题为《谈非精准科学之价值》。
当时学界正呼吁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民族语文学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德意志民族认同感。格林的讲话掺杂着政治因素,但他关于“非精准科学”精准化愿景的判断仍值得特别关注。格林将专著《德语语法》(1819年)献给了恩师、法律史学家卡尔·冯·萨维尼(Karl von Savigny),献辞中表露出了其严谨治学的初心:
被拯救和夺回的古迹会得到谨慎的维护;我们并不想纯粹为了满足好奇而心急火燎地将其付梓,而是应该为还原并保持它们原有样子而努力。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东西不能为了迎合今天的眼光和需要被随意使用。相反,今天的人们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它们忠实地经过我手、未经篡改地留给后世。(Grimm,“An Herrn Geh.Justizrath”V)
“经过我手、未经篡改”堪称格林语文学基础工作的准则。德国学者威廉·舍勒(Wilhelm Scherer)指出,“从仓促假设到精准研究的过渡以及所取得成果(尽管开始时仅是大胆假设),没有人做得像雅各布·格林如此纯粹”(13)。德国文豪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曾写道,“仅一个雅各布·格林为语言学所作的贡献就超过[……]整个法国科学院的贡献”,在建造《德语语法》这“庞大的语言学建筑物”时,格林“或许把他的灵魂交给了魔鬼,以便魔鬼向他提供那些资料,并作为帮手为他服务”(Heine 646)。帮助格林完成宏大项目的不是要求交易灵魂的魔鬼(当今类似的学术工程也无需魔鬼,而是技术——除非技术被视为魔鬼),而是他孜孜不倦的工作和各地同仁的帮助。在专著《德语语法》出版之后,格林在给语文学家卡尔·拉赫曼(Karl Lachmann)的信中写道:“在我尝试出版语法书之后,经过我不间断的学习,我现在感到我的知识和著述多么不完美和不足。但我不后悔写了这本书,因为我在继续前行的道路上了解我自己。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觉得学海有涯。”(Grimm,et al.22)
格林虽区分了精准和非精准科学,但并不认为两种科学在精准性上完全无法通约,即“精准”在格林眼中并非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专属,而是包括语言、历史研究等在内的所有学术研究的理想趋势,它是格林兄弟的“方法论理想”(Lauer,“Über den Werth”156)。通过对严谨和考证的不断追求,格林兄弟把“语文学发展成了一门具有共同研究对象的学科,规定了语文学学者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定义了语文学的研究方向,同时也指出了适用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可视为“精准的科学,即使是身处德国浪漫派时期,他们的严谨性也丝毫不减”(157)。可见,格林的研究工作内化了人文“精准化”的追求。至于语文学乃至人文领域的工作成果精准的标准何在,格林并未展开讨论。从格林的讲话可看出,他所言的人文“精准”首先是实证的,理论上也可由计算而来。稍后登上学术舞台的蒙森注意到以往古罗马语文研究即存在大量“不足和错误”,同样不允许自己“在实践中迷茫”,并且在方法和实践专业化方面比格林走得更远,与尼采成为19世纪后半叶德国语文学的两个典型代表。
二、蒙森:“大科学”、历史 实证主义与转型时期
18世纪下半叶起,德国出现了以温克尔曼和洪堡等为代表并强调古典语文教育功能的人文主义热潮,其后迅速进入了历史 实证主义(Historischer Positivisimus)流行的阶段,并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早期走向繁荣,蒙森和乌尔里希·维拉莫维茨 莫伦道夫(本文简称维拉莫维茨)即为历史 实证语文学的代表(参见Weißenberger 38)。蒙森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罗马法、铭文、钱币学、罗马编年史以及罗马通史,他从方法和组织方式上为古典语文学研究带来了深度变革。面对规模空前的研究素材,蒙森选择了“大科学”(Großforschung/Großwissenschaft)式研究理念。除研究本身规模大,在20世纪英美自然科学和理工研究领域被称为“big science”的“大科学”通常还具有“团队合作、众多人员参与、学术产出不断、国际合作、精专工作方法以及与其它学者竞赛的意识”(Bruch 127)等特点。19世纪后期,“大科学”模式就已在德国人文研究中萌发,蒙森及其合作者阿道夫·哈纳克(Adolf Harnack)的“科 学 大 工 厂”(Großbetrieb der Wissenschaft)理念就属于这类研究模式。
在格林“非精准科学”讲话四个月后,蒙森向普鲁士皇家科学委员会提交了《拉丁语铭文全集(CIL)的计划与实施》(以下简称《计划与实施》)——这被视为首个“大人文学科”项目申请书(Wellmon 94),并于1853年开始领导这个项目的实施。在这份计划书中,蒙森指出了已有铭文整理工作方法的局限,例如内容残缺不全、材料可靠性成疑、对伪造性铭文的批判筛选不利、以及分类和索引时有冗余或残缺等。鉴于此,蒙森提出:“CIL旨在将所有拉丁铭文汇编成集,以方便查阅的顺序进行整理。待筛除伪造的石碑后,在尽可能原始的资料文本中准确再现这些铭文,同时对数量可观的各类异文进行说明,并设计有效的索引来减轻使用的困难。至于评论,有固然好,但非必要。”(Mommsen,“Ueber Plan”3)换言之,蒙森要求有三。一是保障文本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为真实性奠定基础。二是保障文本的准确性、可靠性,以供永久使用。鉴于以往铭文信息不够精确并且存在大量伪造铭文的情况,蒙森追求文献应建基于可信任来源,因为“一切批评倘若不能回溯至最初来源,就不够圆满”(Mommsen,“Ueber Plan”4)。三是保障有科学索引,“制作实用的索引与整理铭文同等重要”(23)。蒙森建议结合内容系统和地理位置两种方式以取代之前的分类方法,“帮助学者们发现和揭示数万铭文之间的关联”,他“并没有采取线性阅读的句法来组织证据,而是想象了一个多维度、更具空间感而非时间性的档案”(Wellmon 99)。此外,蒙森还要求确保工作的执行力度,“若可观的财力和合适的人才均不到位,那么宁可延迟行动,也不要凭打了对折的工具和热心仓促开始”(Mommsen,“Ueber Plan”27)。
德国语文学家卡尔·赖因哈特(Karl Reinhardt)在评价奥古斯特·伯克(August Boeckh)等前辈学者时就已注意到,“与以往学者和人文主义者一代不同,他们用新方法理解材料,抛弃了传统形式,更注重精确性”(Reinhardt 339)。在精准和考证方面,蒙森比同事伯克更彻底。除了CIL,蒙森在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还规划或实施了《罗马帝国人物传记》《拉丁语词典》《古代作家》《钱币集成》以及《希腊基督教作家》等一系列任务。为实施这些大工程,蒙森在研究组织形式和方法上都有严格要求。
在学术组织形式方面,蒙森的学术大工程组织形式严密,时间跨度拉长,跨学科团体合作紧密。在就职演讲中,蒙森指出德国和外国学者必须在政府资助的项目中合作,传统但无效的零散工作须被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法学家的跨学科合作取代,因为对学术研究伤害最大的是人为引发的各学科分立(Mommsen,“Akademische Antrittsrede”35 36)。蒙森模式改变了以往独自埋头苦修的传统语文学家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更重视历史和实证、探索新方法的新型研究者。他还认为必要时需有研究员或外国通讯员在铭文实地,以保障合作的流畅性。不仅他领导搜集的文献应该通过科学的索引形成有网络性质的文献集,其跨越国界的团队成员本身也是一种行动的团队网络,并且网络上的每个成员都是资料的提供者和验真者。此外,他在回应哈纳克就职演说时写道:“大科学就如大城市或大工业,它不是由一个人完成,而是由一个人领衔。它是我们文化发展中的必要因素,而它真正的推动者和实施者是研 究 院,或 者 应 是 研 究 院。”(Mommsen,“Antworten”209)研究院不像大学那样以教育年轻人为核心任务,且可实现集体协作,更适合蒙森完成学术大工程。
在工作方法方面,蒙森追求方法正确、成果可检验,相对于完整和精确的数据库,阐释是次要的,因为数据库应面向未来研究。对他而言,“只能存在正确的,亦即方法上可控的、客观的、可检验的、能够扩充现有知识的科学;或者就是没有被做好的,亦即非科学”(Bruch 125)。蒙森并未完全拒绝阐释,但担心随意和主观的推测会损害资料系统编纂的严谨性。类似“至于评论,有固然好,但非必要”的取向必然会引发语文学阐释派攻击,类似于当数字人文研究疏于阐释时,其意义也会被质疑。
组织形式和研究方法上的严格让蒙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大工程无论是方法还是内容上都影响了古典学的发展,而且不仅是在德国学界”(Rebenich 137)。维尔蒙等学者将蒙森视为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的代表性人物,并敏锐地发现了这种研究所涉及的学者伦理范式转变。在19世纪德国语文学迅速发展和走向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过程中,众多学者前赴后继地加入了搜集、整理、编纂等工作,为相关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舍勒在纪念格林诞辰时指出:“19世纪下半叶不仅仅是数学 自然科学以及技术 推演的时代。人文学科同样繁荣,一如在19世纪上半叶。”(Scherer 21)在此过程中,不断精进的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稳固地抓住18世纪最好的学术成就,并通过更好的成就来整合和细化这些研究,德国语文学家、语言研究者和历史学家为一个历史的和比较的新方法以及一种敏锐、精确和公正的新批评奠定了基础。”(12—13)在德国语文学实证化、精准化和科学化方面,除了格林和蒙森,拉赫曼、伯克、维拉莫维茨等一代代学者也功不可没。
1846年下半年至1847年初,在德国语文学的两个重要文本《谈非精准科学之价值》和《计划与实施》中,即在生涯晚期的格林和年富力强的蒙森之间,语文学的历史 考证研究在研究方法论、规划和内容等方面完成了接力。两者工作有很多相通之处:格林编纂的是古德语文本,即德意志民族语文学,而蒙森整理的是拉丁语铭文,即古典语文学;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建制中,历史和语言是属于同一部门,即蒙森长期掌舵的语言历史分部;面对不计其数的资料和文献,两者的工作都曾被同行或后世认为是“赫拉克勒斯[式]的”的艰巨任务(盖斯特涅尔208;威尔逊1);格林兄弟重点在于“展示与注释文本”,而“在语文学基础工作的第二层面上,即在文本分析和阐释方面,格林兄弟做得相对较少”(Bluhm 473)。蒙森同样如此。蒙森还追逐着格林的朴素愿景:他的“大科学”项目实践就是“[让研究]变得更加纯粹”的过程。尽管批判了以往研究,蒙森的语文学研究并不以学科内部的根本性生存危机为动力,而是历史 实证主义的内在演化要求语文学研究不断精准化、实证化与科学化,但这意味着语文学的去审美化:“与词汇和内容解释相比,对文本的文学批评及审美性解读则退居到次要的位置。”(克拉夫特156)实际上,格林兄弟在19世纪上半叶“经过我手、未经篡改”地搜集和整理童话、语法、史诗,这些民族文化宝藏尚能贴近人心,也有民族教化功能,但蒙森所领导的高度工程化和专业化的拉丁铭文集已无法再轻易“抓住人心”(而且在18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潮中,古希腊远比古罗马受推崇)。事实上,蒙森并非完全的“资料机器”,他的晚期著作《罗马史》使其成为德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为他“结合了丰富的数据和精确的判断、严格的方法与年轻的活力,而又以艺术的形式将它呈现出来”(威尔森2)。但蒙森并未在所有工作中兑现这种赞誉。
19世纪后半期,蒙森开始引领学术大工程,英国语文学家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在编纂《基于历史主义原则的新英语词典》时也广招志愿者,以完成浩大的语文学工程。从项目规模以及组织方式来看,人文基础工作来到了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单兵作战转变为合作工程,其背后是语文学的历史化和社会科学化烙印。以蒙森的拉丁铭文项目为代表的历史 实证语文学和“工业化学术”(Wellmon 91)带来了“信息洪流”(Baaertschi 234),造成了当时部分学者的焦虑。当语文学走向高度专业化和科学化时,就如同演化成了大机器生产那般时,学科内部的争议也无可避免。在萨维尼面前,格林谦称其“工作成果不过是一堆原始材料的集合,其重要性只能待后世评估”(Grimm,“Über den Werth”III)。后世既有夸赞,也有贬低,如有学者指责格林兄弟的研究著作“只不过是堆砌了没有被理出头绪的大量数据[……]提供了僵硬的、而且不科学的大量资料,缺乏在精神中的合成”(Martus 371)。蒙森也未能避免类似批评。这种批评见证了19世纪中后期德国语文学巅峰之中和之后的危机。关于当时语文学的争议,“尼采事件”颇具代表性。
三、尼采事件:两种语文学之争
在后世,尼采的语文学学者标签完全被哲人身份所掩盖,但古典语文学是其初心。实证史学化和祛魅的古典语文学令尼采深感不安。他虽未点名道姓,但从讲座、信件和笔记可看出,蒙森及其普鲁士语文学和工业化学术模式的确在他的瞄准镜内(Wellmon 118)。在尼采看来,历史 实证研究带来了文献和档案,但这些专业性信息一方面令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也并未关注古代经典的思想内涵,这种“对科学客观性的信念切断了古代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克拉夫特160)。尼采希望结合古代与当代、古典与生活,并以古代为镜来理解当代。实证史学化的语文学无法实现他对语文学的赋能,而且语文学也不止于蒙森的学术工程。尼采认为,“如果语文学家以借助古代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在时代为已任,那他的任务就是永恒的”,“它的材料是可以穷尽的”,但“不可穷尽的是每个时代对古代的重新适应,并依照古 代 来 衡 量 自 身”(Nietzsche,325)。
尼采反对对古代资料的机械性搜集和古典语文学中史料为王的历史学思维(凌曦99—100),因为在他看来,对古代事物盲目的搜集使人失去了创造性,实证作业消磨了古典语言学的灵韵和光华,对艺术的玩味被当作工厂作业,导致了古典文化的机械化和平庸化。与之相反,尼采重视古典思想的审美维度,认为人们应带着想象力和创造性去感受古典,在语文学中修养与陶冶情操,这意味着尼采接近于温克尔曼和洪堡的人文主义德国语文学传统。尼采在《朝霞》中指出,语文学是“一门值得尊敬的艺术”,首先要求崇尚语文学的人“走到一边、留出时间、静下来和慢下来[……]它不会随便轻易地完成,它教我们好好阅读,即缓慢地、深入地、有保留和小心地,带着敞开了门户的隐秘思想,用敏感细腻的指头和眼睛去阅读”(Nietzsche,1016)。尼采受过语言学专业学术训练,他对待文本的方式并非不严谨,但他在《悲剧的诞生》中的阐发方式却与同代学者分道扬镳。在他看来,语文学家应不断地认知、感悟、观察与判断,并在其中陶冶情操。此外,尼采还曾在“给语文学家的话”中指出,语文学家应挑起甄别和剔除的任务,出于道德动机清理古书(Nietzsche,108)。这种姿态与格林“经过我手、未经篡改”的准绳以及蒙森的治学理念都相去甚远。
在19世纪语文学追求精准性、实证性和科学性的大潮中,蒙森认为语文学成果应完整、精准和实证,而尼采则崇尚治学为修身、教养和生活。“学术大工厂”甚至可能威胁尼采式天才阐释者之存在和语文学家之主体性:“在蒙森领导或参与的项目工程中,管理决策者的光芒逐渐遮盖了阐释大师或有直觉力的评论者;组织者取代了天才。”(Wellmon 109)1845年,蒙森表示,“我们仅是科学的仆人,被召唤时,我不能说不”(Mommsen,25)——在尼采眼里,当时青年语文学人已沦为聚力于细枝末节、缺乏反思和感悟的专业流水线工人;及至1895年,蒙森承认:“单个的劳动者显得越来越渺小和微不足道[……]我们的工作没有称赞任何一位大师,大师也没有对此工作投以欣赏的目光;因为没有大师,我 们 所 有 人 仅 仅 是 帮 工。”(Mommsen,“Ansprache”723)此外,尼采要求对古典文本进行内化与阐释,这亦非蒙森及其同仁的首要追求。尼采和蒙森虽都推崇古典及其文本,但代表了两种迥异状态,即语文学家是个体阐释者还是团队协作者(Wellmon 123),语文学是生活艺术还是学术工程,语文学工作是教养途径还是知识积累。
面对当时占据主流的历史 实证语文学,尼采走到了“不合时宜”的境地。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并未遵守当时语文学的学术规范,这成为非同道者手中的把柄,引发了德国语文学史上的“尼采事件”。在书评《未来语文学!对尼采〈悲剧的诞生〉的回应》(1872年)中,以格林和蒙森为榜样的青年维拉莫维茨写道,尼采的作品从语文学常识、写作方式到学术规范都存在严重问题,“缺乏对事实的爱”,无法保持其作为科学的尊严和价值;他要求尼采承认《悲剧的诞生》是“狄奥尼索斯 阿波罗式艺术品”,并敦促“非学术研究者”尼采“离开他讲授科学的讲台;他应在膝旁聚集老虎和豹子,而不是德国语文学年轻人”(Wilamowitz-Möllendorff 55)。维拉莫维茨后来成为“历史主义语文学最后一位大师”(Reinhardt 346),而尼采认为他的攻击“散发着来自柏林的气息”,并借此暗指蒙森的影响(凌曦87)。虽然维拉莫维茨和蒙森在古典语文学领域不可一概而论,但在尼采面前,他们均属历史 实证派。除朋友埃尔文·罗德(Erwin Rohde)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无人公开声援尼采。
尼采式语文学在20世纪才重获认可。维拉莫维茨的弟子赖因哈特指出,19世纪末的语文学已是“外表光鲜”,但“内在僵化”,成了“吃力的、过度组织化的、兀自空转的工厂”,而问题并非源自“迟钝”,而是“清醒、禁欲、尽职和坚忍的英雄品质”(Reinhardt 342)。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古典语文学陷入了双重窘境:一是古典理想破灭,以致它被以学术之名蔑视它;二是不断增强的专业化引发的悲观,如它导致研究个体在发展大局中和学术大厦前越来越渺小(Reinhardt 342 343)。在德国古典语文学家维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试图融合两者之前,此时的语文学学术研究与古典理想近乎非此即彼般的存在(Reinhardt 348)。尼采早就想终结此种语文学工作的工厂化,但暂时湮没于时代潮流中。20世纪上半叶,语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又重归人文主义(Weißenberger 40),但出于理论热潮、学科分化以及理工强势等内外原因,语文学的黄金时代实已结束,直到20世纪尾声才有了“回归语文学”的呼吁。
尼采视古典语文学为艺术以及生存和修养的方式,这在语文学治学史中远非孤例。关于古典语文学“促进人的教养”、保障古学“在生活中的地位”还是为积累知识而堆砌材料,早在15世纪的语文学研究中就已出现(克拉夫特159)。赖因哈特也指出,古典语文学在19世纪末陷入了“古典主义理想与语文学工作的历史主义现实之间的困境”(Reinhardt 342)。在此,赖因哈特的“古典主义理想”即可简化或类比为对古典文本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追求。这种困境在当今仍值得关注。
四、语文学与数字人文:史前理念、争议与启发
在19世纪德国的语文学走向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进程中,格林提出了语文学“精准化”愿景,蒙森沿着格林的脚步,将历史 实证主义语文学推向巅峰,它的内在危机也在此孕育。与格林、蒙森和维拉莫维茨所代表的严谨学术研究相比,尼采式语文学加载了更多教化意义、审美意味和人文温度。尽管双方在当时看似分出胜负,但这并非他们在语文学具体目标上决出高低,而是在古学之爱中的不同价值取向和任务认领,即双方的差异和争论实质为语文学内部方法论与价值观之争,且类似争论并非局限于当时:中世纪已出现,19世纪更明显,当今仍有类似讨论。“语文学是19世纪德国发展完善的学科,其命运代表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科学和人文”(Wellmon 123),这意味着关于19世纪德国语文学原则与走向的讨论近似于对整体人文领域的讨论,这让它可与当今传统和数字人文讨论进行类比。从以上综述可见,谈论19世纪语文学与当今数字人文,绝非因为格林和蒙森开始了数字人文研究,而是因为他们身处人文学术转型时期,其理念、争议与启发在当下数字人文时代仍值得关注。19世纪德国语文学的精准化和科学化追求不仅是数字人文基础工作史前理念的萌发,其争议对当今的传统和数字人文讨论也有启发。
在数字人文基础实践方面,智能技术发展可协助追求格林的愿景和蒙森的精准规划。从当今视角来看,蒙森是19世纪德国语文学黄金时代的历史 实证“档案派”或“数据库派”,其治学准则是忠于历史原貌、坚持严谨治学、走向精准实证、学者协作共进、服务未来研究。格林强调以民族语文来培育民族之心,但也同样遵循历史 实证原则。如将数字人文分为基础工作(资料集成及其数据化等)和进阶工作(方法多样的分析和阐释),那蒙森的“大科学”中已有当今数字人文基础工作理念的萌芽:这不仅体现在人员组织形式上,例如参与人员“忠实的工人”(Wellmon)的定位,也体现在工作过程和结果上,即在缺乏当今数据分析、知识推理、可视化呈现等智能技术的前提下,通过人工方式实现文献资料的准确化集聚和科学索引,通过长期的学术工程建立资料库或“数据库”,所以是技术前时代语文学精准化、客观化和实证性尝试,同时还具有开放性、协作性以及面向未来的特质。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Bol)曾如是描述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
[两者]不是从研究一个具体问题开始的[……]不是专门为我或其他人的特定选题服务,而是可以给学界整个历史研究领域服务[……]我希望这个数据库能包含一切中国历史研究的内容[……]数字人文研究一定是相互合作(collaborative work)才能发展,不可能是一个人或独立的结构可以做出来的。
[……]就我们的数据库项目而言,有很多合作方的参与,由多个国家的学者共同合作开发[……]如果要说我在这里有什么独特作用的话,就是我需要向基金会申请资金,促进多个单位的合作。(包弼德 高旭东 尹倩3—4)
可见,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包弼德扮演着与蒙森类似的角色。在蒙森的工作中,劳尔看到了科学史转向现代的标志,即“对待数据的新方式”(Lauer,“Die Vermessung der Kultur”102),并认为这些学术工程是“精准人文科学”的例子,是“当今数字人文研究计划的榜样”(劳尔 程林6)。相比这种数字人文基础工作理念的史前萌发,当今数字人文在技术基础、研究谱系和阐释分析等领域都改变显著,技术会显著减少人文学者做“科学仆人”的艰辛。电影《教授与疯子》(2019年)将语文学工作之艰辛展现得淋漓尽致,默里的同事因久未寻得“approve”词条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应用例子而失去耐心、爆发言语冲突,默里建议他们去翻阅弥尔顿的《失乐园》。这种耗时费力的查询在当今技术和数据环境中可在须臾之间完成,语文学基础工程在数字化中也获得了新活力。法律判决因非“计算题”,在格林眼中本不属于精准科学,但当今部分法律判决也开始借助算法计算以求准确或提高效率。如果将数字人文视为语文学的延伸,那么数字人文基础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计算机辅助方法的当代语文学。
格林、蒙森的研究在阐释和“精神合成”方面所受的批评,与“尼采事件”一样属于语文学乃至整个人文领域的传统争论。格林和蒙森对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并非人文研究旅程的终点,类似于部分学者要求数字人文研究不应止步于数据及其大致分析。蒙森“仅是科学仆人”的定位看似是对科学和学术的献身精神,但无法满足治学修身和阐释解读的人文要求。蒙森的学术工作品格是精准工程式的,而非内化阐释式的,尼采对这种语文学的轻视,令人联想到当今部分数字人文研究遭受的批评。用当今视角看待19世纪德国语文学精准化和科学化的理念和争议,并不旨在将当时观念、愿景或争议转换成当今数字人文的术语,而在于思考格林、蒙森和尼采等人理念和争议带来的启发。
其一,“精准”看似自然科学之专属,但并非与人文绝缘,且可成为部分人文研究的愿景。例如,在数字人文及其计算机辅助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劳尔就在格林启发下重提“精准人文”(Exakte Geisteswissenschaften)理念。罗德在为尼采辩护时曾指出,历史 实证派语文学所追求的绝对客观、实证和精准实际上仅是幻象(Rohde 74)。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但人文与精准并不必然是非此即彼的,人文研究并非走向数学或物理式的精准,其“精准”标准也难以统一,但在科学方法范围内、在不断实践中不断科学化仍可以是人文学术追求。而且,这种追求在人文研究中有着远早于计算机与互联网的传统。例如在19世纪的德国学界,“有学者希望精准地确定语言演化的法则,或发现各民族合乎规律的发展趋势,或展现文学所遵循的原则,或更精准地去确定人类行为的规律”,为此,“学者们发展出了实验和实证的方法,或是搜集和应用了大量的数据”,这意味着“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迥然差异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当时的这些学者有意识地将人文和自然科学理解为一个整体”(劳尔 程林4)。对格林来说,“精准”和“人文”并非“矛盾性的组合”(Lauer,“Über den Werth”159)。尽管“精准人文”的标准、方法和体系仍待进一步厘清,但借助智能技术带来的契机,人文领域在注重“精神合成”“抓住人心”的同时,无疑可通过符合自身特点的方式逐步靠近严谨、精准和科学的目标。
其二,“蒙森和尼采关于如何、为何从事人文探索的论点是宽谱的两端,只取一端会限制人文能带来的好处”(Wellmon 126),蒙森 维拉莫维茨和尼采的两种理念又各有所长,其差异有助于当代学者进行自我审视,并在宽容的态度中寻找平衡。从尼采对工业式语文学的轻视,到维拉莫维茨对尼采的批评,一方面源于他们研究阶段、治学方式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表明单纯的历史实证或阐释研究都并非无懈可击。从当今视角回望百余年前的争议会发现,两种研究均非面面俱到,但两者均是语文学任务,都有其合理性和颇具特点的成果,两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学各有志:尼采坚守了语文学的人文精神、教养功能、时代关切和阐释要求,其价值无需赘言;格林和蒙森提高了语文学基础和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当时的维拉莫维茨追求的无非是语文学治学的规范和严谨。以语文学基础工作为例,格林发起的《德语辞典》编纂工作耗时178年才在一代代学人接力中完成,在电子化之后成为德语词源研究的核心资料库,在词汇的文学溯源方面尤其不可或缺;蒙森式语文学工程本就面向未来,一方面,它并非语文学研究的全部,另一方面,其精准考证又能为进阶阐释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蒙森主持拉丁铭文搜集工作成果早在一战前就已获得国际学界的高度认可。回望19世纪语文学,值得警惕的是维拉莫维茨以正统之名将尼采赶出古典语文学界的学术霸权。从当时德国语文学的争议可看出,争鸣必不可少,但包容而非敌对另一种成果、探索而非排斥其他方法也是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不同的方法和取向应找到平衡。
其三,双方差异及“尼采事件”表明,实证、数据与阐释、思想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但两者的交锋、互鉴和融合应给人文学术带来契机,数字人文能否在两者之间实现平衡值得关注。以数字人文文学研究为例,“横亘在经验研究和阐释学传统之间由来已久的沟壑”需被填平(赵薇72)。一旦实证、数据与阐释、思想无法兼容或耦合失败,尤其当一方声音过响,争议声音也会变大,这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语文学中已有预演,例如单纯追求实证的语文学(人文研究)就备受争议——这种争议在当今仍然适用,如有学者认为,“我们数字时代的人文正被实证主义的幽灵纠缠”(Wellmon 123)。作为“丈量文化的新方式”(Lauer,“Die Vermessung der Kultur”109),数字人文并不必然意味着实证与阐释、数据与人文的冲突以及传统与数字研究的替代关系。除开辟新的领域,数字人文也应助益传统人文研究,而不是颠覆人文。人文研究最好集实证、精准与阐发之所长,实现两者的并行、伴生、互鉴与各擅其长。
数字人文的施展空间有其界限,也要面对着传统人文的质疑和部分尚不完善的数字人文研究实践,但其兴起仍可成为人文研究固本求新的再出发。基于人文,尝试数字,并在合理阐释中回归人文,追求阐释与精准的有机耦合,可实现人文研究的试新法,求新知,出新见。同时使用数字人文与传统阐释方法研究相同问题(例如接受史研究)时会发现,数字方法既是传统方法的镜像,也是其优势与边界并存的增强技术。此外,数字人文能为人文研究带来新技术工具,也有更多元的阐释要求,会刺激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阐释习惯乃至身份认知。如在问题意识方面,有学者认为,人文学研究者从问题意识层面出发的内发式改变是数字人文成为人文学发展出路之一的前提(日比嘉高92)。部分人文领域的学者需熟悉新技术工具,在跨学科对话中保持好奇和宽容,在计算思维实验及在数据、图表等辅助素材应用中自我调试,在“尝试 误差 调试”中优化研究路径,在传统与数字方法之间找到互补性平衡——这些都要求时间和实践的积累,也都需要对传统方法的再思考、对新研究可能的开放求索。但在这些探索之后,人文学术会从不同方法和理念的伴生互鉴和多元融合中受益。数字人文在多大程度上可通过传统与数字的深入有机融合来缓解或解决精准实证与阐释传统、人文精神之间长久以来的潜在冲突,值得继续观察。
注释[Notes]
①从20世纪末起,保罗·德曼、赛义德等学者均论及“回归语文学”。沈卫荣的专著《回归语文学》、编著《何谓语文学》以及郭西安的论文《回归什么语文学?——汉学、比较文学与作为功能的语文学》等有相关论述。参考沈卫荣:《回归语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沈卫荣编:《何谓语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郭西安:《回归什么语文学?——汉学、比较文学与作为功能的语文学》,《中国比较文学》4(2020):77—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