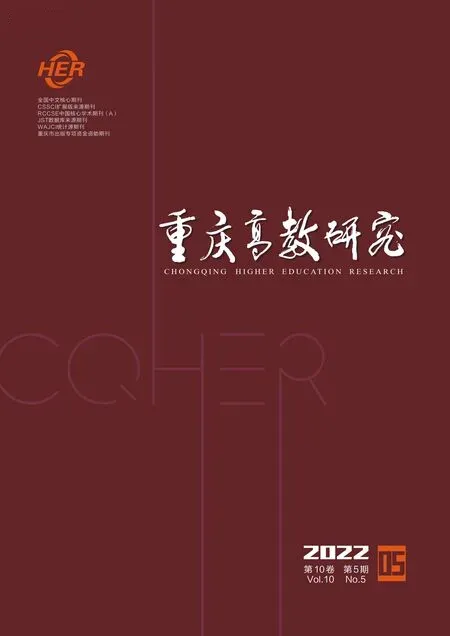论美育是一种他者教育还是自我教育
蔡震洋
(伦敦大学学院 教育学院,伦敦 WCIE 6 bt)
一、问题提出:美育是他者教育吗
美育也称教育美学、审美教育,是教育学和美学的交叉学科。美育以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以美学学科为理论分析框架[1],用美学视角审视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以美育教养下的学生达成某种美学上的目的为旨归。“美学的许多基本问题同时也是它的前沿课题”[2]前言,加之它又要跨学科地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并遵循教育活动的规律,这导致了美育研究与实践的困难性和复杂性。
美育受到普遍重视,但实践长期受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2年,学校美育取得突破性进展……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明显提升。到2035年,基本形成全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学校美育体系”[3],表明了国家对美育工作的重视。《1990—2010年中国美育研究脉络》指出美育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4]。美育越来越成为“教育现代化的关键”[5]。审美情趣是中国学生核心素养要求[6]。然而,美育在实践上缺乏突破性进展[7],逐渐沦为教育体系的“多余人”[8],故美育的实践出路是重要研究问题。
有关美育实践受阻的原因众说纷纭。邱地、谢朝晖认为美育实践存在“轻视美育、师资缺乏、审美活动缺失、课程设置不合理”[9]的问题,应该“提升美育的法律地位,加强高校美育管理、美育师资队伍建设、美育课程建设以及校园文化建设,将美育融入高等教育教学全过程”[9];赵伶俐、余立新认为有待于“认识美育全面价值、建立理论系统、衔接传统与现实、研究科学化实证化实践化、融入现代化和市场经济”[10]等;张正江认为美育实践受阻的原因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美育理论、我国人民长期处于对温饱的追求、美育是不是全面教育的重要组成长期存疑、市场经济下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盛行”[11]等等;张笑梅则认为美育受阻是因为“重视不够、缺乏有效课程体系、师资不足、经费匮乏、学生审美素养不高”[12];孙荣春则认为美育“基础薄弱,机制不畅;领导乏力,内涵不清,实施浮泛;课程建设严重滞后,师资力量匮乏,缺乏评价体系”[13]。
我们认为已有研究还没有揭示当前美育实践的真正阻力,因为更为隐秘的症结在于对美育实现形式的误解。美育由于借代以他者为特征的教育形式去实践,无法回归自我教育的本然方法与目的,才造成了一系列后续问题。他者即“从主体出发、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及其一切关系”;自我是“以主体为基准的内部要素,即主体(人)自身”,包括自我意识、自我尊严等。在人学上,他者与自我分别对应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现实活动与意义活动;在教育方面,他者与自我在目的上对应人的社会化与人的个性化,方法上对应认识论与存在论;在美学上,他者与自我对应虚无主义与意义。
因此,假若从教育形式即“美育是一种他者教育还是自我教育”的角度入手审视,就会发现当美育以他者教育形式实践时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美育在性质与方法论上主要以认识论而非存在论论教育,目的主要以现实关怀而非终极关怀为旨归,造成实证主义与虚无主义问题,泯灭了审美的形而上学意蕴及其救赎功能;其次,遮蔽了美育在教育中事关人的自我整全与终极关怀之高级地位、无法充分激发美育意识,助长而非阻滞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再次,囿于传统认识论知识论藩篱,总是期待把美育以课程的形式进行,而不是倾向于用对话法、教育现象学体验交互法乃至文本意义阐释的诠释法去勾连个体的自我体验进行;最后,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角度而言,作为他者教育的美育无法使学生主动索求意义,却只能教人期盼从外在于主体的物和人那里去寻找主体自身的终极关怀,最后势必坠入虚无主义泥潭。这不仅难以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也难以为后代培养出合格的美育师资。以上种种问题都指向美育是一种他者教育还是自我教育的辨析,这需要从教育学和美学两个方面去交叉探讨。
总之,由于美育乃至教育的他者教育观念与形式长期盘踞,使得美育实践避开了教育本质与美学本性,导致美育“人人都知道有什么问题,但问题从未被良好地解决”的实践困局。本研究拟从教育形式归属的新视角探究美育的本质和实践出路,先讨论自我教育的内涵及其与教育、他者教育的关系,然后分析美育作为他者教育的异化问题,并借助美学视角探究美育的本质,提出通过建立意义意向性实现美育的本质复归,最后总结美育的应然形式。
二、自我教育的真谛
学界对教育、他者教育研究颇多,但是对自我教育的合法性地位、功能目的指向一直比较模糊,对教育、他者教育、自我教育的关系问题也不明晰。研究首先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为讨论“美育是一种他者教育还是自我教育”的探索奠基。
(一)学界对他者教育的观点
教育学界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教育是一种他者教育”,支撑这种观点的核心在于教育具有社会性。例如,《教育大辞典》认为,“教育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14]725;袁振国在《当代教育学》中认为,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期望他们发生某种变化的活动”[15]4,并且强调“教育活动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15]71;王道俊与郭文安在《教育学》中认为,教育是“根据一定的社会现实和未来需要,遵循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受教育者主动地学习,以适应社会需要的活动”[16]16;胡德海从人类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认为教育和自我教育都是文化传承的手段,而教育在传承中具有师授性、他控性,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只有在人际关系交往中才能进行[17]。统而论之,这一类教育观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认为教育具有他授性,是“人—人”交互形式,是一种社会性活动。
(二)学界对自我教育的观点
教育具有社会性。自我教育既然是自我的,似乎谈不上社会性,更难以称其为一种教育类型。国内学界自我教育理论研究较成熟者主要有东北师范大学的张晓静和西北师范大学的胡德海。张晓静指出:“平常所说的‘教育’概念已被窄化,它实际上指的是‘他人教育’,而非完整的教育含义。把自我教育当作德育的一部分,甚至方法或途径之一去解释……从根本上讲是逻辑的混乱,必须对之加以纠正。”[18]她认为自我教育是教育的实现形式之一,与他者教育相对,同属于教育的下位概念(如图1)。自我教育不是他者教育的附庸和手段,也不是德育的一种类型。她对自我教育和他者教育的关系持二位一体观。

图1 张晓静“自我教育”和“教育”关系图
胡德海认为,教育和自我教育同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途径,同是文化传承的下位概念[19](如图2)。

图2 胡德海“自我教育”和“教育”关系图
但是,胡德海的教育分类其实还是指向了教育的二位一体观。“所谓教育也就是他人教育……两者是一种并列关系……对于社会文化来说,教育和自我教育都是并列的下位概念”,“教育与自我教育都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传承手段”[19]。他人教育与自我教育都是人类社会文化以教育为途径的传承手段,人类文化(传承)可以同理置换为教育(意为以教育传承人类文化)。简言之,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是同位概念,是教育的共同下位概念——只不过胡德海将他者教育替换成了教育。
(三)教育社会性的界定问题
张晓静与胡德海都没有陈述清楚自我教育和他者教育的核心区分,即教育社会性的界定问题。教育的社会性被认为是“教育的根本属性”[14]736。其内涵有二:一是“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现象……最终目的是使人社会化”;二是“教育的性质和发展受社会的性质和发展制约”[14]736。有研究者提出,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意识文化、精神现象的变迁,有必要深化对教育的社会性的认识。第一,教育的社会性是教育的本质属性之一;第二,教育的社会性目的是使人社会化,但教育的最终目的不只是使人社会化,它的整全内涵还使人个性化。有关这一问题最权威的探讨,应回到马克思人学思想上去看。
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看法,在性质上可以统归为“自然性—社会性—发展性”,与之相对的就是人的3种发展阶段,即“自然人(或者说生物人)—社会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自然人即“人作为一个生命体的最初自然存在物”[20]37,突出的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人指人具有社会性,包括3个方面。首先,社会性指“人的进化是自然本性的社会化过程”[20]94。其次,人的特殊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意指“人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人创造了社会关系”[20]96。人类以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存在,并以社会关系的形式生产劳动,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征。再次,“人虽然无法脱离社会存在,但是人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超越现实社会关系……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创造出属人的世界”[20]96。这种社会性的内涵揭示了人的社会性阶段不是人的停滞和结局。尽管作为现实世界的人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人不受社会关系的束缚,能够超脱并最终指向自我创造和实现。发展的人指的是人作为“超越了自然、社会存在的,追寻人生意义无限趋向生命价值的价值存在”[20]136。这种发展是无终结性的、超越性的,更是自我突破、自我发展式的,因为“只有一个强大的自我才能认识到这一自我边界的狭隘性,认识到向自我解体升华”(1)见勒德雷尔.人的需要[M].邵晓光,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154.转引自刘黎明.教育学视域中的人——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思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67.。
关于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的关系,马克思总结到:“人的起初完全自然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是第二大形态,在其中形成全面的社会物质交换和全面关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社会生产力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21],“人的需要的丰富是人的本质的充实……人对自身需要的全面占有即人占有自身的全面本质”[22]。一个整全的人不仅是生物人、社会人,还自我发展的人;不仅有自然需要、社会需要,还须有个体发展需要。人在本质上是自我定义、自我负责的,社会性不过是现象界人的肉体、行为、关系的总和,还没有定义人全部属性的合法性。如果说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社会化便是引领人改造世界、生产物质资料(就业劳动)、结成社会关系,以人的个性化作最终的目的——解放人,即使人依着自己的目的全面自由发展。
可见,教育社会性的确是教育的本质特征,自我教育不是一种自我封闭教育,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交往关系,学生和这个世界的互动关系是教育乃至人类活动的基石。然而,教育社会性不是教育的目的和终结,教育培养社会人的阶段是教育升阶发展的一个被批判扬弃的中间环节,它所要导向的最终目的是人(自我)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时,学生主体性凸显,他者的存在完全是辅助性的、第二性的。当人实现自我的个性发展时,并不否认人和教育的社会性,相反,自我的完满能让人更好地走向他者。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的观点需要辩证看待,它不是否定自我教育的理由,因为教育不能阻碍人的发展,它的全部目的只能是帮助和促进人的发展。由此,自我教育是教育的合法下位概念、高级形式和最终目的。自我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其与高层级的精神教育联系紧密。本研究发展张晓静的二位一体观,认为教育存在两种实现形式,一是关注人的社会化的他者教育,二是关注人的个性化的自我教育。二者在实践中相辅相成、相互交融(如图3)。

图3 教育、他者教育、自我教育关系图
(四)自我教育的哲学基础
自我教育的哲学基础在于对其使人个性化、超越社会关系束缚及进行意义活动的理论支撑,可以基于马克思人学观,并借由康德人学观和马丁·布伯-潘知常人学观加以解释。
首先,尽管康德未正面表明他对人的看法,但已经通过其哲学体系交代了人的“本体界与现象界相综合”之特征。他对笛卡尔的人学观进行了批判与扬弃,提出关于自我的先验主体论,认为应该将现象与本体作区分、将认识论与本体论视域相区别。康德认为,“‘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实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我’,它是‘物自体’”[23],并且“作为物自体的‘我’不可知……因为认识论主体的自我是现象界、科学认识范畴的主体,而本体论的主体自我属于本体界、实践领域的理性主体”[23],“知性永远不能把它的任何一条先验原理作先验使用,而只能在经验上使用它”(2)见温纯如.康德和费希特的自我学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29.。康德对自我划分出了两个视界——现象界的我与作为物自体的本体界的我,本体界的我可觉但不能经验表征,它交由人的意志与理性去统摄(3)康德对“自我”概念的现象与先验区分的当代合法性在于,其后的胡塞尔对该自我观作了批判继承,而海德格尔也没有全盘否定胡塞尔的自我观,乃至后来的分析哲学也没有全盘否定康德自我论的基本立意。因此,人自我的不可知性、隐秘性也许正是一种有待科学解释的科学判断。见李晓进.自我的哲学追问:从笛卡儿、康德到胡塞尔[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4):22-27.。
在康德的体系划界中,“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概念领地和作为超感官之物的自由概念领地之间固定下来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至于从前者到后者不可能有任何过渡”,但是“作为超感官之物的自由概念领地应当对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概念领地有某种影响”[24]226。“终归必须有自然界以之为基础的那个超感官之物与自由概念在实践上所包含的东西相统一的某种根据,关于这根据的概念虽然既没有在理论上也没有在实践上达到对这根据的认识,因而不拥有特别的领地,但却仍然按照一方的原则的思维方式向按照另一方的原则的思维方式的过渡成为可能。”[24]226从自由向自然过渡的根据,就是第三判断力所指的合目的性以及共通感,这种根据不能保证道德选择在执行了合理性的A时必然会在现象界实现合目的的B,但其仍然构想一种道德律作用于自然界的合目的性结果,这在现象界体现了强烈的应然味道。“并不是说好像一定要以这种方式现实地假定这样一个知性。相反,这种能力借此只是给它自己而不是给自然提供一个规律。”[24]230足以看出,人的审美判断力在做一种横跨现象界和本体界的过渡性努力,并且这种联结并不是一种平分的融合,而是人的本体界意志向现象界的输出,使人得以在现象界展现出一种人为的意志统摄。总之,康德对人的自我作出了先验转向,承认自我的超验特性,人有着来自本体界的超验性,而又存在在现象界中统摄现象并趋向超验事物的努力。这是自我的重要特性,也是自我教育形式所要关切的人学内涵。
其次,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认为惯常的人类生活活动是“我—它”的人与物的关系,是形而下的功利活动,而“我—你”关系则是意义活动。潘知常发展了马丁·布伯“我—你”关系论,认为“人与世界之间在三个维度上发生关系……第一进向是‘人与自然’,涉及‘我—它’关系;第二进向是‘人与社会’,涉及‘我—他’关系……第一、第二进向共同组成现实维度与现实关怀,其涉及的只是现象界、效用领域,关注人的形而下求生存维度与功利活动……人与世界之间第三个进向即人与意义的维度——‘我—你’关系,构成超越维度与终极关怀。置身超越维度与终极关怀的人类生命活动是意义活动,有宗教、哲学与审美三种”[25]。潘知常关于人与世界交往的“三进向”说与马克思人的三阶段发展观一一对应,也与康德的“本体—现象”划界遥相呼应。第一、第二进向是人在现象界的活动,第三进向是人在意义维度的活动,关注人的超越与终极关怀。所谓超越,超越的是现象界的有限性;所谓终极关怀,关怀的是自我在超验层次的终极性、无限性和永恒性,也是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实现和自我达成的一种精神生存状态,简言之,就是对“人生如何值得一过”这一意义问题的个人回答。如果强行以现象界的规律及功利活动的满足替代人的自由与超越活动,就势必导致现象界对人之为人的取消——意义活动的缺失会造成“人”的不完整。
总之,马克思人学观解答了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他者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分界与范畴问题;康德人学观表现出以自我为内核的人对现象界的意志统摄和对本体界的超验趋向;马丁·布伯“我—你”的关系论及潘知常“人与世界交往三进向说”揭示了人的功利活动和意义活动之区别。3种哲学观指明,人在现象界的功利活动作为一种教育活动时属于人的社会化,关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主要以他者教育形式完成;人在超验界的意义活动作为一种教育活动时属于人的个性化,关注形而上的终极关怀,主要以自我教育的形式完成(4)有必要对人的意义活动合法性作出辩护。人本主义教育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有5种升阶等级的需要,分别是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自我实现。5种需要又分缺失性需要(deficiency needs)和成长性需要(growth needs)。马斯洛认为在缺失性需要满足以前,成长性需要无法满足甚至不会产生。一些研究认为缺失性需要与成长性需要并非必须尊崇等级关系。首先,人可以带着对成长性需要的追求去满足缺失性需要,而非一定要“先满足缺失性需要,再追求自我实现”,这不仅违背常识(譬如有人认为尊严比温饱更重要,民族大义比个人生死更重要,就“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并且这种分级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逻辑。相反,带着对收获爱情的渴慕、对受人尊敬的向往、对自我实现的追求的同时勤恳工作,反而能让一个人更好地满足缺失性需要。更重要的是,这才能避免“为了满足缺失性需要而去满足”的手段对目标的僭越,人才不会把自我交给自我之外的对象化“他者”去定义。人的成长性需要和缺失性需要可以并行满足,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可以同时发生。。最终,我们可以对他者教育与自我教育作出概念界定,并初步比较各自的不同。
(五)他者教育与自我教育的辨析
他者教育内涵定义可以根据他者、教育的定义得出。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言的“非我”,而“非我”指“从主体出发,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包括它的一切关系”[26]69。自我与非我的区分是“以主体为基准的内部与外部的区分,主体(人)自身是自我,主体以外的一切存在都是非我”(5)见高清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M].人民出版社,1987:40.转引自张晓静.自我教育论 主动积极求教的教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70.。据此,他者教育即教师根据一定的社会现实和未来需要,遵循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受教育者主动地学习,主要关注学生社会化的一种教育。
自我教育的内涵定义可以在张晓静定义的基础上结合前文自我教育的哲学基础进行讨论。张晓静把自我教育界定为:“个体作为教育主体,在自我意识支配下,把自我作为教育对象,按社会的要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求教的活动,是自教和自学的统一体。”[26]100自我教育的机制是“自我意识是自我教育的发生机制;自我尊严是自我教育的动力机制;自我反馈是自我教育的调节机制”[26]108。本研究将自我教育定义为基于一定的社会需要和个人发展目的,学生以自我意识为发生、自我尊严为推动、自我反馈为调节的,指向个性化自我超越与自我实现的一种教育的高级形式和最终目的。自我超越,超越的是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束缚;自我实现,实现的是在对形而下生存活动超越之后人对以“人生如何值得一过”这一“大问题”为代表的意义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思考、关切和践行。说它是个性化的,就是因为个体对自我有限性的无限超越形式不尽相同,也许是宗教的、理性的、哲学的抑或美学的(6)张晓静认为,“追求审美的人生境界及美感的产生……也主要是通过自我教育获得的”。见张晓静.自我教育论 主动积极求教的教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149.。
自我教育与他者教育的区分只是在逻辑层面,在实践中“两者不可分割地互相渗透,不存在纯粹的‘自我教育’或者‘他者教育’”[26]175。尽管如此,我们现在所讲的自我教育(以自我教育为主、以他者教育为辅的教育),和已经经过杜威学生中心转向的“以学生为主、教师辅助引导”的他者教育仍然存在区别。他者教育在功能上主要面向的和能够企及的,是学生在康德所说的“现象界”、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化”这个层面上的教育,这时教育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师生的社会关系传递和教学能够被实证的经验知识。因此,他者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在学生身上注入人力资本和劳动技能,以期满足社会生产、自身生命存活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这种形而下的功利活动是必要的,也为人的高阶发展奠基。当然,这其中也存在自我教育要素,譬如智育终归需要以学生为主体、以其个人的心理动机和脑力消化为条件,并且还存在赫尔巴特所说的“教育性教学”活动,涉及一些形而上的因素。自我教育面向的是学生作为一个独立“人”的发展事宜,包括他对自己生命有限性的超越,对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层面的、高扬人性的,为着为人的尊严而自我提问、自我追寻、自我辩驳、自我回答、自我创造的过程。这关切学生自我的整全,而自我整全不存在终点,没有完成的标志和固定的标准,它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是一种“一人唯心、如此而已”的动态个人完善与承诺。即便如此,这种教育类型也需要教师的在场,需要社会关系的条件。
总之,自我教育具有作为一种“教育”的合法性,由学生自我尊严启动、自我建构、自我调节,关注人的个性化和终极关怀,在人的整全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美育适用他者教育还是自我教育形式,取决于美育所要规避的误区及其所要回归的本然使命。
三、美育的异化
由于教育社会化功能对个性化功能的遮蔽,目前教育实践面临教育实证主义下“有教无人”和教育虚无主义下“有人无心”两大弊端的挑战,学生自我遭受他者转移和他者消解,意义维度的活动受到蒙蔽。美育受其影响,被理解为艺术知识与技能训练的实证美育、情感美育、审美愉悦论美育、生活泛审美化美育,这些都属于他者教育,都存在他者对自我的僭越和对意义的消解。更为关键的是,因美育的审美形而上学本性,美育本应主要完成对现代人的实证与虚无症候之超克(7)超克指超越并克服。、为人提供审美救赎,但现在却反而被实证与虚无所解释和掠俘。这是美育本性的他者性丧失——由“内求”转为“外求”、求他者的实证证明、他者的伪意义慰藉最终堕入实证主义与虚无主义困境,这些问题需要揭示并克服。
(一)美育存在实证主义困境
1.实证主义问题
实证主义(positivism)可追溯到孔德提出的实证哲学观。孔德声明,“科学的任务就是探寻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之中的确定性客观规律与法则……任何知识的产生都应完全归于可证实的经验”[27]。对可实证者的笃信和对不可实证者的拒斥,导致实证主义产生经验主义、自然主义、客观主义(8)经验主义问题在于认为“科学、知识都是建立在实证数据的经验基础上”,不可实证的既不是知识也不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主义局限,指研究没有主观能动性的纯客观的具有律则性(nomothetic)的“物”,认为对客观规律的追求永恒有效且是社会科学的全部目的及科学性来源;客观主义问题指完全拒绝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和意识意向的介入。实证主义见物不见人的观念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对真实验和准实验的盲目笃信,缺少对复杂的动态事实进行非实证观察和意义感知的维度,造成对世界实证化、平面化和机械化的理解,将“人”的丰富内涵囿于客观规律和量化指标。问题[28]。胡塞尔切中实证主义滥觞的要害,“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实证科学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命运攸关的‘关于这整个人的生存有意义无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恰都占有比事实问题更高的地位”[29]。实证主义的泛滥首先造成的是对人内涵的实证化、单向度理解,归根结底造成的是人的意义虚无。
2.教育实证主义问题
教育实证主义承接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的病症,左右人的教育活动的进行,核心症结是对人的自我评判、自我存在确认权的他者转移,转移给外在于主体的客观事物,如用标准、量表、规律等去统摄,致使实证主义教育下“有教无人”。例如,在以人为对象的教育中,却恰恰不见以情感、意义和灵性为代表构成的自我的“人”的踪影。学生执着于成绩的表征、“考上哪个大学”的结果正义,却没有“我在大学生活中有什么体验”(9)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中针对常青藤盟校资优生的普遍心理问题,引用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名词“斯坦福狂鸭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意指“一只悠闲的鸭子在湖面上逍遥自在地飘过,水面上的平静掩盖着水面下鸭掌的疯狂拨动”。具体的实例是:“这些年轻人没有与自己建立起深层的关系。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开始,这些名校生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磨炼’甚至‘魔炼’:学校俱乐部、乐团、大小团体(音乐、体育等)、AP课程、SAT考试、晚间活动、周末安排、夏季课程、体育训练、课业家教、‘领导能力’、‘为他人服务精神’等等。为了能够‘修成正果’,学生们已经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被引导和教授去思考自己的追求,包括对大学的憧憬。从小到大,这些年轻人为了名校的炫目光环而奋斗。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生的目的和内心的热爱从未被给予足够的尊重,从未被思考和探索过。当他们被常青藤名校录取之后,不少学生迷茫了。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那里,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些什么。”见威廉·德雷谢维奇.优秀的绵羊[M].林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5-6. 无独有偶,刘易斯用“失去灵魂的卓越”一针见血地概括了顶级高等教育文化中实证与虚无的联结实质,认为“大学的任务变成让学生开心,而不是引导他们追求灵魂的内在卓越”。见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38.。这些是人的物化与异化。
3.美育存在实证主义困境
杜卫认为,艺术教育首要指的是作为艺术知识与技能的培训,这是最基础的艺术教育内涵。在此之上,出于对艺术教育内涵的整全要求,艺术教育还要引导学生感知艺术作品所生发出来的涵养意蕴,让学生既有实证知识技能的习得又有精神的领悟成长。艺术教育的问题“在于一切教学内容都必须是可知识化考核评价的,对艺术的理解是知道了作品的作者、创作时代、背景、主题、思想内容、风格……因为这知识化的内容便于标准化考试评价。但艺术品往往又是不可评价、清楚明白言说准确的,这是美学上的一个常识”[30]。艺术教育着重于知识技能之上的“培养艺术兴趣、提高审美能力、具备初步艺术创作能力这些目标,而不是单纯的知识和技能学习”[30]。相应地,“把知识教学混同于美育,就是无视美育与知识教学的一个显著差异,前者诉诸智力,主要是认知活动;后者诉诸情感体验,主要是审美活动”[31],“区别是艺术知识教育过于重视艺术技巧,忽视儿童青少年情感的发展和对艺术作品的深刻体验……美育教学不仅要解决知道和会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获得审美情感体验,解决‘有感’的问题,这样才有美育的效果”[31]。杜卫的观点具有建设性意义,它区分了惯常所理解的艺术教育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美育”,说明教学“如何欣赏一幅画、如何跳好一支舞”的单纯艺术知识与技能训练不是美育的整全内涵。这是我们所要避免的美育作为实证主义艺术教育之弊。
(二)美育存在虚无主义困境
1.虚无主义问题
虚无主义(Nihilism)是一个时代性问题。克罗斯比将虚无主义分为5类:政治的、道德的、认识论的、宇宙论的、生存论的虚无主义[33]12。除政治虚无主义外,其他类型都属于哲学虚无主义。生存论虚无主义是最主要的虚无主义(道德的、认识论的、宇宙论的虚无主义都能够被并入生存论虚无主义),指“人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荒诞的……人没有理由活着,也没有理由不活着。那些宣称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了意义的人,要么不诚实要么受到了欺骗,不论何种,他们都难以直面人类境遇无意义的残酷现实”[33]39。基于生存论虚无主义,人的其他观念都陷入意义拒斥和相对主义。如道德虚无主义指不承认普遍道德原则的存在;认识论虚无主义强调不可知论,认为“所有理论体系本身最终都是任意性的,因为他们超越了理性的批判和支持”[33]24;宇宙论虚无主义认为整个宇宙不具备为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提供支撑的可能。
2.教育虚无主义问题
教育虚无主义是本研究界定的一个自主概念。它承领生存论虚无主义的内核,既指教育活动主体(教师和学生)缺乏意义感,也指教育活动不关注或错误地引导学生的意义生活,造成或加深学生的无意义感。虚无主义教育下学生“有人无心”,症候表征为“空心病”。“空心病”概念在国内最初由北京大学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借由“北大四成新生感到学习生活无意义”的数据而提出(10)徐凯文2016年11月5日在第九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主题演讲《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中提出了“空心病”这一概念。见北大徐凯文:学生空心病与时代焦虑[DB/OL].(2017-08-25)[2022-04-11]. https://www.sohu.com/a/167174789_770822. 另外,“空心病”问题不是中国教育系统所独有,美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亦十分严峻,不少病症体现出了“空心病”的特征:“The 2010 National Survey of Counseling Center Directors found that 44 percent of counseling center clients had sever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 sharp increase from 16 percent in 2000. The most common of these disorders were depression, anxiety, suicidal ideation, alcohol abuse, eating disorders and self-injury. A 2010 survey of students…found that 45.6 percent of students surveyed reported feeling hopeless, and 30.7 percent reported feeling so depressed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function during the past 12 months…however, these percentages are probably even higher since students with substance abuse and eating disorders are less likely to seek treatment at counseling centers than stud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isorders.”见EISER A.The crisis on campus [J/OL].(2011-12-19)[2022-04-11].http://www.apa.org/monitor/2011/09/crisis-campus.,核心特征是学生无力回应“人活着意义是什么”的自我提问,进而“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34],导致一系列生活无力感或自残行为。根据潘知常人与世界三进向理论分析,在人与自然的交往维度,患空心病的学生能够达到较高的水平,因为“一个理工科博士生在博二时就已经达到了博士毕业标准”[34],他对自然规律的掌握与利用是高水平的。然而“他屡次三番尝试放弃自己的生命……用了所有的药物和电抽搐疗法都无济于事”[34]。在“人与社会”的交往维度,这些学生也是无可挑剔的——“原生家庭幸福,父母关系和谐。孩子没有创伤、没有寄养经历、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糟糕环境”[35],这些面临自杀问题的青年身上“没有传统的心理学所说的那种阴影”[35]。在第三进向的“我—你”意义维度上的问题凸显为“所有所说的学生在大学都特别优秀”[34],但是他们来访时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习、我为什么要活着……学习好、工作好也不满足,因为这样的人生似乎没有头”[34]。值得重视的是,空心病类似但不同于抑郁症,所有的抑郁症治疗法并不能缓解和抹去“他们内心强烈的孤独和无意义感”[34]。简言之,学生过于关注形而下的现实活动,缺乏超越性的意义追求,造成了主体的缺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着”[34]。
一条实证主义和虚无主义相辅相成的逻辑理路浮现——由于无力回答意义的问题,便转而寻求一些社会暂且能够公认的、时间上暂且可及的实证目标作自我的他者转移,以此支撑自己生命存在的理由(11)实证极端与心灵意义的虚无具有相关性。学业实证化的盲目追求及其光鲜的结果,挤占了师生双方对心灵安定与意义追求的关注,并进一步掩盖了对这种需求满足的缺失所导致的病症:“追求卓越的学生就如同‘瘾君子’,‘药物’对‘瘾君子’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带来快感,更是为了消除痛苦,而这种痛苦恰恰是来自对药物的依赖。以此类比,追求卓越的学生往往需要‘外界的肯定和赞美’,才能够感受到父母和老师的爱,才能心安。每取得一次‘A’,就如同‘瘾君子’每一次用药,能给自己带来短暂的慰藉,就像针对失败的恐惧注射了一剂镇静剂。”见威廉·德雷谢维奇.优秀的绵羊[M].林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45.“客观知识为我们达到某些目的提供了有力工具……但终极目标本身以及要达到它的渴望却必须来自另一个源泉。只有确定了这样的目标及其价值,我们的生存和活动才能获得意义。这一点几乎已经没有加以论证的必要。”见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73.吊诡的是,由教育实证的极端化导致的教育虚无主义困境,似乎正是爱因斯坦这句话的表意在现实中的颠倒——客观知识不仅为我们达到某些目的提供了有力工具,并且我们为自己所设定的终极目标及其渴望也来自于教育实证理念本身——确定了这样的目标与价值,我们的生存和活动彻底失去了意义的可能。。但是,当这种实证目标果真实现时,背后意义虚无的问题终于无法隐藏,被赤裸地展现出来。这实属效用界对意义界的僭越、他者对自我的掠俘。
3.美育存在虚无主义困境
杜卫的情感美育论存在发展空间。他认为美育即情感体验教育,功能是承领席勒所说的感性教育“去中和与反拨由于理性极端主义所带来的人的失衡,恢复人感知的敏锐、情感的丰富、想象的多样,重归感性与理性的和谐”[30],杜卫认为“美育以感性教育为其本质特征,以情感体验为过程,即个体基于知觉的对于对象和自身内心的品味、体悟等情感感受经历”[31]。杜卫所扬弃的理论阶段之低级决定了其理论建构还没有涉足人的高级发展需要。审美相对于理性主义的极端化、科学主义的碎片化后果而言确有完善人的感性进而完善人格的作用。但是,情感体验缺乏一种终极性,即它主要还是关切人的现实关怀和现实和谐,缺乏超越性的终极关怀,没有显现审美的形而上本质,也就不能彻底地进行审美式人格完善。杜卫的美育观是形而下的、促进学生社会化而非个性化的。他所谈的美育促人完善,是使人更多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更少地作为一种人性缺失的社会一分子而言的,它不关切人本身的超越与实现境界。
叶朗的审美愉悦论美育观存在发展空间。他认为,审美教育“中心是个体审美发展,成熟的标志是审美态度、审美直觉感兴力和审美趣味的形成”[32]310。他承认学生在美育中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受教育者在体验中感到一种进入自我实现境界的愉悦……这使他们必然以浓厚的兴趣介入审美教育,以便不断重温这种曾经体验到的愉悦。”[32]319但这种停留在“因着学生追求愉悦所以才进入美育”的观点未免肤浅。其实,就在这段表述所在的“审美教育的形态特征”的前一节“个体审美发展的当代紧迫性”中,叶朗已经看到,“由于时代科技的进步与物质丰盈,一切都逻辑实证化、符号程序化,人的和谐全面人格发展遭到空前严重的肢解……审美教育可以使人摆脱由于片面理性化而成为‘单向度的人’的危险,承担着解放‘感性’的历史重任”[32]189。学生的美育动机不可能是简单的对“愉悦”的向往,而是关涉个体阻拒自我尊严感的丧失与对完满人性的坚守。美育的动机是沉重的,也带有崇高的意味。在狭义上就人自我实现地“做一个人”的努力而言,叶朗的美育观还是局限在形而下层面的他者教育式的。这是我们所要避免的美育作为形而下教育之弊。
实证主义美育观、形而下的情感美育观存在导向虚无主义及“空心病”的可能(12)譬如舞蹈的优美展示对于舞者本身而言,究竟是作为一种哗众取宠的技艺、一种博得朋友圈“点赞”进而获得一种“意义感”的途径而存在,还是舞者与身体、艺术和价值的灵交,值得体察。,而“审美的日常生活(泛)化”美育观是一种典型的虚无主义美育。“审美的日常生活泛化”是对“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作为一种世界潮流而言的批判。前者意指对审美作日常生活泛化理解,什么世俗活动都是审美的,可能带来借审美行消费主义世俗化之实;后者指在日常生活之中进入审美意象的升华(13)鲁枢元做过一个形象比喻:日常生活审美化“就炸油条这一日常生活活动而言,假若小贩有那么一刻全神贯注地炸他的油条,和面、扯面、拨动着油条在滚烫的油锅里变形、变色……让食客都心满意足,乃至他自己也被自己的‘作品’所感动,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愉悦……这便是进入了审美的境界;相反,如果运用艺术手段来策划、制作,将油条精心包装……包一只精致的纸盒,彩印绚烂的图像,附上如诗的广告文字:‘巴尔扎克曾用于早餐并激发了创作灵感的油条’,又在设点兜售时用貌美的年轻女性,配以《欢乐颂》作为背景音乐——油条因此畅销起来。这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见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J].文艺争鸣,2004,19(3):6-12.。两者的区别是将超越活动牵引向世俗活动,还是将现实活动牵引向超越活动。
刘悦笛推崇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而建立起生活美育观。他说生活之美在于“鉴人形貌”“饮饌啜茶”“山水景观”“日常书写”“身体塑造”“艺术设计”等。在“身体塑造”一节他分析了“中韩日美星的脸型比较”[36]317“从美发、美容、美体到美甲”[36]321以及所谓“对身体进行审美化塑造”的整容[36]325。他所列举的生活美学形式聚焦于世俗愉悦,这种“美”还不是一种经由审美体验进入的形而上审美意象,甚至其作为一种精神性的美的身份都值得怀疑,作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实在难以堪当,实属审美的日常生活泛化。毋庸讳言,刘悦笛关于生活美的描述带有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成分。譬如他讲到深山饮茶时的震撼:“宝岛北山深,偶遇山房主人,邀品高山茶尖……三人静坐,青烟朵朵……茶过六杯,空心净谧……空山鸟鸣,悟吾刹那。这次啜茶经历不是一种单纯的‘喝茶’,而是一番彻底的‘生活审美化’经验”[36]144。尽管如此,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形而上学存在“生理快感和精神快感的综合”与审美精神超越之间的区分,刘悦笛的理论还没有进入作为审美形而上学的境界,只能说是带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意愿去践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
基于生活美学的生活美育观的目标是“塑造生活艺术家们……他们不是以艺术作为自己的职业,但却以艺术的、审美的态度去对待生活、社会与人生”[37]。不可否认,这种美育观引领人发现生活中美的价值,但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美学观下的美育势必导致对审美超越的曲解、对审美形而上学的放弃和对世俗生理愉悦的固执。刘悦笛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全部在现象界展开活动,就客观事实的美而谈美,很容易导致人对意义的虚拟置换,对超越的现实置换,走向建立在拟象上的“审美泛化”,“最后势必走向虚无主义,人将自己一笔勾销给拟象生活,是对最可珍贵的生命的一种不负责任”[38]。生活美学没有看到审美对抗虚无的厚重内涵,从理论上否定了美学的神性,实质是一种审美泛生活化。生活美育观无法践行审美给人带来的意义感,在本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美育,是个人审美的他者托付,代表以往美育在抛离实证线路后,走进虚无主义式超越的迷途。
实证主义与虚无主义是人的现代生存亟待超克的泥潭。实证主义美育和虚无主义美育相辅相成,都是他者教育式的,也都是“他者”式的。它们抑或不关注人的意义活动,抑或消解了人的意义活动,这是美育的失败。因此,美育亟待规避他者教育形式与问题,在意义活动的层面上向学生自我复归。
四、美育的复归
美育需要从他者教育向自我教育复归,讲求对美育美学本性的关切。现代中国美学界的观点主要分成两系,一是“实践-反映论美学”,二是“后实践-体验论美学”。以“实践-反映论”为美学立场的美育将审美的形而上功能重新贬低至人对现实功利活动的关注,把自我的意义回应消释在以“他者”为表征的社会关系之中,违背了美育本质。只有“后实践-体验论”美学观展现出审美形而上学的核心内涵,揭示、坚守美学本义。美育理应回到“后实践-体验论”的美学立场,最终作为个体精神为人的高级活动赋予生命统摄其整体的意义。
(一)超越实践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
“实践-反映论”美学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美学方面的再阐释,认为美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属于这一派的包括持实践美学观的李泽厚、将审美和美作认识论理解的陈新汉、作关系论理解的尤西林和周长鼎等。限于篇幅,仅取陈新汉的理解进行审视。
陈新汉认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感性显现”[39],“审美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反映着与客体形象相联系的主体本质力量”[40]。“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美的内容,但它本身不是美;具体事物的感性形象是美的形式,但它本身也不是美。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即‘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成为在主体意识中的客体的‘感性显现’,使主体感受到主客体之间的融洽才成其为美。”[40]他也承认审美的超越性和自由境界:“要领悟、达到美的自由境界确实有许多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这是一种理想的审美境界,但绝不是唯心主义的梦呓。”[40]陈新汉的观点和朱光潜、叶朗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非常相像,抛弃掉他认识论的审美解析框架,几乎就是后实践美学的缩影。不过他对美的马克思主义式阐释“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其形象使人在情感上感到愉悦,从而产生了美。同时在劳动中审美的感觉器官也随之发展起来……美的产生离不开这两个根据”[40],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他将美产生机制的解释等同于对美的本质的发掘,犯了将人的个性化发展阶段混淆于、最终等同于社会化阶段,导致人的现实化、世俗化、物质化的错误。王元骧为实践论美学进行了辩驳:“后实践论美学认为,只要强调从主客体关系出发就脱离了人类生命活动的纯粹本原……使美学成为一种知识型的、见物不见人的‘冷冰冰的美学’,这就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本质空谈抽象的纯精神美……实践论美学从本体论层面说明了美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表征成果。”[41]美和审美的产生与人的社会性活动当然相关,因为任何人的活动都以生物性和社会性为基础。但不能混淆的是,美感的诞生本就是人的个性化对社会关系总和束缚的解脱和超越。在此意义上,我们不能回到实践论并止于实践论去解释虽然源于实践但毕竟超越了实践的审美。正如梁光焰所指出的,实践论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泛化,是美学研究上的鹦鹉学舌、生搬硬套[42]118。
“实践-反映论”美学观的科学性所在也是其谬误所在,它就部分而讲部分,没有看到社会性的从属关系,将社会性作为原因的同时也作为了结果,反而造成了审美形而上的世俗堕落。这种美学观指导下的美育,只能教人“认识到”美“为什么”,而不能引领人体验美本身(“怎么样”),进而纵容了美育的实证与虚无问题。对于美学而言,承认“审美体验”作为一种非认识论、非实践论、非本体论的人类精神活动,发觉审美的形而上学意蕴,越来越在人现代生存的终极关怀上起作用。这是新美育观所要坚守的美学本性。
(二)审美形而上学的启示
1.审美体验的特性
“审美体验”是美学的核心关切,其基本特性包括无功利性、直觉性、创造性、超越性和愉悦性[32]189。一段完整的审美体验,总是包含上述5个要素,它们互相融合、相辅相成。“审美救赎……关键在于审美的特殊本性:意象呈现。”[43]人借由审美体验进入审美意象世界,进而与真善美永恒价值共在。不同的美学理论家对审美意象论述不同。叶朗主张“美在意象……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2]55,认为客观的审美对象提供了审美的现实质料,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对客观物(包含情感、想象等要素)进行主观创造,人的主观情感和现实质料相综合才使人进入“意象世界”;杨春时认为审美意象是人与世界的主体间性同一,即人通过审美体验进入“与宇宙共在的完整体验……审美对象成为与审美主体同一的另一个主体,它非物也非精神,有生命、有灵性……彼时我即是你、你即是我”[44],它是人与世界万物在意义维度相遇、合一的一种精神状态;颜翔林的怀疑论美学认为对美学的理解应当运用与逻辑智慧相对的“诗性智慧”,诗性般的审美体验将引领人“逾越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制约……以审美活动为目的和手段……实现主体对事物存在可能性的诗性领悟”,最终“走进一个澄明而自由的诗性世界”[45]。
审美意象展现出终极性和永恒性。审美终极性和永恒性意指“在审美体验过程中人对生命意义和终极价值的触碰与把握”,这是一种审美的形而上学境界。柏拉图曾如此描述道:“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涌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后,人终于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这是一种与人类核心价值的共在,把人“从感性个体的有限性中超越出来……去把握永远存在的绝对价值”[46]27。这也是一种《论语·里仁》中所言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理状态,一种马斯洛自我实现中的高峰体验。“你恍然觉得企求已久的天堂之门豁然打开,蓦地见到了永恒、无限、绝对……仿佛自己也做了上帝。这一切令你狂喜、战栗乃至禁不住渴望着死——当这一切都已经历,何妨现在就死。”[47]审美意象最终导向的正是这种挥舞人性意志、足以回应死亡对意义横扫后遗留的虚无和使人当一回真人的终极价值关怀。
2.终极价值在审美体验中莅临
人在审美体验中进入审美意象,与审美形而上学境界共在,这可以从真、善、美的角度解释。审美体验带人走进“存在的真”(而非认识论的“真”)。在现象学看来,“不是我们去认识事物,而是世界万物不断地对着我们的意识显现自身”[42]141,其间,事物本身向人的意识“展示”和“敞开”,而非“人用一个预设的抽象概念规定和统摄它”[42]142造成对事物本身的遮蔽。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说:“审美对象所暗示的世界……是迫切而短暂的经验,是人们完全进入这一感受时,一瞬间发现自己命运的意义的经验。”[48]28他描绘了人的意向性的真理背靠——“这是一个可能的世界,而且可能证实现实,我投射的可能就是真正的真理,它携带我并为我辩护”[48]29。审美的经验意象何以具有这种意义的蕴含?又何以先验地蕴藏着终极性的真理呢?审美“不是向我提出有关世界的一种真理,而是向我打开作为真理之源的世界……审美对象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假如我专心于(审美)对象,我便能立刻获得它,因为这是感觉的能力。审美对象以一种不可表达的情感性质概括和表达了世界的综合整体:它把世界包含在自身之中时,使我理解了世界。同时正是通过它的媒介,我在认识世界之前就认出了世界,在我存在于世界之前,我又回到了世界”[48]26。我与世界同样站到了原初的位置,我使用“本质直观”去审美体验,世界“如其所存而显之”(王夫之),于是有关这世界本原的一切,有关这先验的存在和真理,便当然进入了审美者的审美视界体验而得之。所以,“这种以情感性质所揭示的世界的意义,就是审美意象的意蕴”[2]62。海德格尔一语中的:“艺术者的本性将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14)见颜翔林.怀疑论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9.,“美是作为无弊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美属于真理的自行发生”(15)见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7.。
审美体验引人向善。审美的德育作用在于,学生借由审美体验见诸美好事物,这种特殊的与“美好事物站在一起”的感受促使审美主体自觉地趋向和追求人在生活中的“善”。檀传宝提出了“德育美学观”和“美学是未来的教育学”[49]65的观点,认为“由于审美体验的超越性和非功利性,时下中国‘普遍的庸俗的只求来现的功利主义’便可以美学解决……功利主义的救赎必须从非功利、超功利的逻辑开始”[49]67,这是对审美德育功能的一种解释。审美的向善理路还在于它给予人的一种尊严感,这种尊严感和审美尊严息息相关。如果说美作为一种意象所引领人企达的是对自身有限生命、对自身生物性和社会性的超越,那么丑就不是简单艺术意义上的不美,不是缺乏技巧或明暗对比后拙劣的艺术品的丑,而是对人的有限性的全盘承领和不带意志反抗的接受。即“对人的有限性的固执肯定”[46]146——认为人只能是有限的,生命是无意义的,所有的挣扎都显得幼稚而徒劳。反之,审美尊严就体现在当面对生活事实可见的苦难和难以实证的审美超越时,我仍然相信审美超越带来的精神自由与栖息,坚信人性的真善美内核,坚信生命的意义所在。“美是对人的有限性的否定”——这只能是一种人的自由意志体现而不可能是别的他者性事物使然。在这个意义上,审美尊严也是人性尊严的展开,“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在审美活动背后彰显的是“人”本质力量的挺立。人和审美体验是互为成就的,审美使人不断触碰美的事物,不断地向终极意义生成。反过来,人借由审美表明对有限世界超越性的拒斥态度,对无限与先验的追求和向往。据此,审美也是彰显人的尊严的活动。
审美体验使人求真、向善,最终在“循美”处集合。这里所循之“美”比纯粹的“美感”内涵更加丰富,它指向一种人存在状态的整合描述——人对真善美的信仰。
首先,审美信仰是一种无宗教的信仰。审美所导向的审美形而上学给人审美式的超越,并且建立起人的真善美信仰状态,这是一种审美的客观,而非某家某派的意见。蔡元培认为,宗教“各家恒各以其习惯为神律,党同伐异……大背其爱人如己之教义而不顾”[50],加之宗教存在反对科学的倾向,于是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兼有宗教超越性、普遍性、信仰性,却无党同伐异倾向的“审美”被认为具有代替宗教的潜力。“无宗教而有信仰”是潘知常发展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而提出的命题,他认为贯穿在西方人历史生活始终的精神力量来自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信仰,基于目前社会生活普遍弥漫的虚无主义氛围,比之20世纪改革开放“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亟待“先让一部分人信仰起来”[51]。由于中国人不能够“重新进入一次宗教衍生的熔炉”[51],故提出“无宗教而有信仰”,而美学审美便是这种信仰的一个通路[52]。审美信仰的建立没有宗教派别的内核,有的是以审美体验为通路的对人类真善美核心价值的中立追求。
其次,审美信仰的建立,不倚靠实证逻辑去拥有存在的合法性,也不是一种宗教式的或虚无主义式的超越。审美信仰是体会过审美意象所昭示的终极价值后烙在人心中的一块永恒印记。这印记是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所说的“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未曾见过阳光”的震慑人心,以至此后人为之反刍、为之维护、为之追求,乃至“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审美信仰表现为人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坚定意向。人在看到生活的苦难和心灵的虚无之后有4种出路[53]475:第一种办法是逃避,如宗教式的超越,或转移注意力到可实证的事物上去(使用对现实关怀的注意去掩盖终极关怀的无解)。第二种办法是自杀,用死来表达对生命的困惑,如海明威、王国维以及由于“空心病”而自杀的学生们。第三种是虚无式的超越,即通过沉浸在虚无中去表达对虚无的不满。例如沉浸在拟象中,通过无节制的享乐、沾染产生幻象的毒品等把自我交给他者去回答和把握。这也就变相承认虚无的不可战胜。第四种道路是一种循美的信仰,即正因为“我”曾经在审美体验中见过审美意象所莅临的终极价值,所以虽然“我”承认“人生就是没有意义”,但是“我”“还坚信——光明在前、意义在前。所以我转过身去,与光明同在”[53]476。“明明人的虚无不可战胜,我还是要去和黑暗赌博,去赌爱存在、赌光明在前。在此意义上我作为人就表示了黑暗与虚无的可以战胜。”[53]476审美透射出人统摄现象界的力感,因此人才能自我定义、自我负责,彰显出人格尊严。在批判与反噬场域的往复辩驳中,“人”能够借由审美企达自我救赎,在自我中找到精神内守的坐标。这是审美信仰所体现的对人性价值的恪守。
总之,“审美活动在对人的有限生命的无限超越方面,起着深刻而其他活动无法取代的作用”[46]27。在教育虚无主义背景下,美育建构审美信仰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要走出虚无,应当背靠什么?无论背靠什么,都离不开这一点——新型的人的生成,在体验中向着人生的终极意义去生成”[54]372。美育作为美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必然要重视审美的体验本性。而“自我”与“体验”又是同一的,体验在自我中发生,自我在体验中存在。
(三)建立美育的意义意向性
基于终极价值在审美体验中的莅临理路,本文提出了建立美育的意义意向性。
1.建立意义意向性的必要性
建立美育的意义意向性是对美育乃至教育本质认识中价值判断缺失的补充。教育本质的特点包括:有目的地培养人的活动;教育者引导受教育者传承经验的互动活动;激励教导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活动[16]17。然而,这几点都是教育活动的客观属性,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本质判断,产生“有教无人”“教出非人”的教育效果。比如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甚至是在具备这几个要素的教育中获得极高成就者,却感到人生没有意义,没有动机去追求些什么。难道这也是教育的结果?教育必然导致人的虚无?显然,单纯的知识与技能培训乃至恶价值观的教唆,都会满足上述要求,这些属性满足的是能被客观表征的“教”的要素,不包含一个真正的教育所应具有的价值判断,即“育”。
2.教育意向性的内涵
意向性(intentionality)原是一个哲学概念,指“人把握外在对象的方式。人们不能直接把握外在对象,但是心灵在感知、思维时总有内在的对象呈现出来,因此通过意向性把握这种内在的对象,心灵便能认识外在的对象”[55]。换言之,人的生命活动总是仰赖某种意识指向而存在。布伦塔诺(Brentano)还将有无意向性作为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的区分,认为“心理现象是那种在自身中以意向的方式涉及对象的现象……任何物理现象都没有这种特征”[55]。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意向性建构学生的人性。石中英将“教学意向性”解释为“(教师)意在引起学生的学习行为以达到某种特定的发展目标”[56],认为教学意向性是一种教师在进行教育活动前对教育目标、教育价值、教学理念所作的现行思考与确认。从这个角度看,并不存在“无意向的教学”。刘铁芳认为“教育意向性”指“个体置身教育情境时潜在性的接受结构……即个体求知过程中的内在意向”,事关“个体如何意识和期待教育情境所指涉的事物”[57]。教育意向主体涉及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具有原发性的重要地位。
3.教育意向性存在“自然正确”理路
教育具有“自然正确”理路,因而教育的意向性也就存在一种应然导向,美育的意向性应符合这种要求。詹姆斯·莱德菲尔德在20世纪末出版的《塞莱斯廷预言》(TheCelestineProphecy)一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洞见:自人类轴心文明时代伊始,无论是西方的苏格拉底还是东方的孔子,都在追寻人生的意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将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寄托在柏拉图的“相”论上,后又转为对中世纪神学的信仰。在理性和上帝(宗教)这两个西方精神世界的支柱倒塌后,人们又转而派出科学家求索人生意义。由于长时间得不到答案,人们决定先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力改善人的生存境遇。未曾想,这种对物质的歇脚性追求演变为执念,人们渐渐忘记了求索存在的意义的初衷,“把努力改善生存境遇当作生活的意义,一步步忘掉了精神追求这个原初目的”[58]。由于对意义追寻的悬置和遗忘,科学主义甚嚣尘上,消费文化泛滥,导致现代性危机。“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现代性教育的批判在于把它归结为一种价值迷失的虚无主义”[59]14-27。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古典理性的温良转向现代理性的自负的过程……古典理性限度在于尊重自然、本然与偶然。现代理性认为可通过精密制度的设计,掌握人的命运与幸福及其余一切。逻辑实证主义式的极端理性要以非科学的名义把一切价值和信仰全排除出去”[59]51。吴元发力主回归“教育的自然正确”,即“因其自身而永远正确的教育,追问的是人的终极完满生活状态”[59]85。这种自然正确教育的“目的为解决现代性教育虚无主义困境提供出发点”[59]71。“教育的自然正确就是教育对终极价值的承诺。”[59]101总之,教育导向意义追问是一种必然复归。
4.建立美育的意义意向性
既然人的价值虚无问题可以美学回应,而对意义的追问又是教育的本然使命,那么教育意向性就真正具有了指向——追寻意义。真正的美育应当引导学生感知并且建立一种终极的审美意义意向。首先,教师要思考自己的教育理念,对世界终极问题进行思考,并树立一种意义导向。换言之,一名真正的教师本身不应秉持虚无主义价值观,做一名只传授实证主义知识与信念的“教书匠”,因为“只有当学生见识过好的教育,他才会产生对好的教育的追寻”[60]。正如徐凯文先生的反省:“我跟那些空心病的学生交流时,他们为什么找不到自己?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和老师没有能够让他们看到一个人怎么样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地活着。”[34]其次,教育要引导学生通过审美体验建立一种对意义渴求的意向性。这并不代表学生找到了世界的终极真理,而是在一种价值选择之间,教师向其展示人性所能拥有的力量并促进其对超越性真善美的坚守——甚至即使这种乌托邦并不存在——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这是对人性的笃定坚信,对终极意义和超越性价值的知其不可为而为般的大义坚守。
为什么说是牵引学生建立对“意义渴求的意向性”而非直接对某种价值真理的确信与笃定?若非如此我们如何保证这并非落入更深一层的虚无?人的生存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这种意义不是实体的,无法实证,也并非是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上的事物,但这种对意义的追求它是真实的。“如果说哲学的意义不在于发布真理,那么教育哲学的意义也不在于发布教育的真理,而是在于促进对教育实践本身的哲学思考”[60],更在于对思考后所建立起来的人类终极价值的坚定追求。每个学生的意义信念都有所不同,但重要的是学生需要建立这种意义的意向性。这本应是教育在哲学层面的高级追求,但现在我们把它作为教育的起点和美育的主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明白,纯知识技能的训练、“坏”价值的教唆,这些使学生患上“空心病”、走上价值歧途的“教育”是一种伪教育,不是美育的本质。
人在审美体验中进入审美意象,并借此把握和触碰人类真善美的终极价值。美育活动应该抓住审美活动的这个重要功能,以建立意义意向性的方式达成审美与自我教育、美学与教育学的契合,并着意于对实证与虚无主义困境的超克。最终,人、教育、美育达成从“他者”向“自我”的复归与升华。
五、作为自我教育的美育
教育包含4个基本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活动方式)。结合前文所述,我们不妨从美育的功能目的及其内部诸要素的剖析入手,厘定其是一种他者教育还是自我教育。最终,以意义体验论为美学立场的美育审美体验在需要、发生和效用落点上都围绕人的自我而展开。美育不是一种以促进学生社会化为旨归的他者教育,而理应回归作为一种学生自我教育的正途。
(一)美育的功能与目的决定其是一种自我教育
审美的无功利性、直觉性、创造性、超越性、愉悦性使得美育不是一种促进人的社会化的活动,也不是关注现实功利活动。相反,美育面向促进人的个性化发展,关注人的自我对现实功利活动的超越、对以审美意象为代表的审美体验的主体创造、对进入审美意境把握和触碰真善美终极价值进而不断意义生成的追求。有关这种意义的定义与追求,都不能交给外在于“我”(主体)的“他者”(实证逻辑指标、拟象)去决定和回应,否则就会陷入“空心病”与生活拟象化,重回虚无主义的俗套,泯灭美育的本质。美育的教育立场表明了它处于促进人自我实现的阶段的性质,其美学立场决定了其以审美形而上学牵引人建立意义意向和审美信仰的特征。综合而言,美育的功能与目的决定了它是一种自我教育。
(二)美育的活动方式、活动内容、教师角色决定其是一种自我教育
审美共通感(common sense of aesthetic)昭示了美育的活动方式。审美共通感作为一种普遍个体经验,不是一种知识经验的普遍可传达证明,这昭示了美育的自我教育活动方式。审美共通感是康德共通感概念的一种。有关审美共通感康德本人并没有专门的概念界定,周黄正蜜对该词在康德哲学中的不同含义作了归纳:“(1)一种普遍的情感;(2)‘只通过情感而不通过概念,却可能普遍有效地规定什么是令人喜欢或讨厌的’主观原则;(3)一种公共感受的理念和普遍的判断能力……把自己从私人立场中抽象出来,置于一种普遍的立场之上。”[61]100第二种定义和第三种定义相互联结,表明“审美共通感原则从主体间的角度解释了审美的必然性……它要求每一个人对鉴赏判断作出普遍赞同,以便这种普遍必然性‘看起来像是客观的’”[61]114-115。关键是,共通感的普遍必然原则“通过感觉而非通过概念被规定”[61]106,这种普遍性“只能被表象为主观的”[61]115,依循这种原则人们“普遍可传达地‘判断’什么是令人愉悦或不愉悦的”[61]106。可见,经验与体验有别,可传递性与普遍有效性有别。审美共通感本身作为一种判断而非认知,作为一种体验的反思而非经验的体认,以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孤立验证和纵向的个体应验来奏效,无法建立起审美体验的横向人际传递通路。这样,审美体验作为一种不可实证之物具有不可教性,是无法作为事实知识言传口授的。“‘手把手’把这些东西教给学生的企图肯定是一种徒劳……这些东西要靠个人自我教育‘悟出来’……并内化为自己的心成。”[26]114不过,知识经验与审美激发并非非黑即白,知识经验通由概念与想象力的调和而触及审美生成,这为教师与学生的审美联结开辟了一条重要而广阔的通路。
“审美是概念和想象力的调和”(康德),教师应当通过概念的通路有限度地参与学生审美体验的生成,这为教师对学生在美育上“导”的角色地位留下必要且合理的空间。朱会晖与刘梦瑶在《如何理解知性在审美评判中的作用——康德美学关键问题新释》一文中厘清了认知在审美中的作用定位:“虽然审美是前概念的,认识不作强制性的规定,但在审美活动中,认识也是起作用的,只不过是以一种给主体的想象力服务的姿态,提供多种多样不确定的像是背景一样的知识,来使想象力活跃起来,扩大审美感受。”[62]审美不受认识的强制规定,但认识在审美中起作用,“以一种给主体想象力服务的姿态……来使想象力活跃”,最终也就能够明确美育的师生关系定位——美育以学生自我体验、自我教育为主,以教师引导为辅,教师无须(也无法)作强制性的知识定义,只是适当地提供认识材料,呈现艺术熏染(包括艺术品鉴赏与艺术创作参与等)辅助性地服务学生的自我美育。美育不仅存在自我教育,而且存在他者教育,这与把他者教育放在主体地位,继而成为认识论教育的形式有本质不同。
就以认知途径展开美育的方式而言,社会建构主义教育观提供了关键线索。胡学亮提出对话学习模式,由“与自我对话、与客体对话、与他人对话”[63]三要素构成。在与自我对话中,学生面对疑问,将自我新旧概念作出内部比对;在与客体的对话中,事实与自我思维不符,学生产生认知失衡,激起概念重构的欲望;在与他人对话中,学生能够就自我与他者关于某事物认知与解释的差异作出识别与反思,最终将互动经验内化为自己的知识。这个教学模式与自我教育机制“自我意识、自我尊严失衡、自我调节”及审美发生机制十分相似,其目的在于“有效促进学生对科学概念本质的理解,大幅提高学生概念的转化率”[63]。如何将其运用于审美体验的主体间性对话,处理好认识论概念认知与存在论体验的过渡与融合,使其成为一种美育法,有待探究。
另外,基于审美作为一种体验的特性,运用教育现象学方法进行师生主体间对话,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美育方案。教育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是对现象学“本质直观”理念的延续,既是一门新兴学科,又可以直接作为一种方法论付诸实践。教育现象学先驱、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范梅南指出:“教育现象学定位于现象学和解释学,最终目的是理解与学生共处情境的教育意义。”[64]2这种意义具体所指“生活体验、生活经验的意义、人类生存意义”[64]11-15,其研究方式不是理性结构量化的,而是“以轻柔、微妙、敏感、深度、初始”的方式“将生活现象的意义带入我们的意识”[64]22。因此,教育现象学“区别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更关注变量间的统计学关系”[64]14。李树英概括了教育现象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出前者是“胡塞尔超验现象学‘悬置、还原、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走向事情本身、此在’”[65],后者则是“生活化选题、对话式访谈、描述性写作、现象学式反思”[65]。可见,教育现象学的目的是回到生活世界,直观隐秘体验及其蕴含的意义,其方法是主体间性的、对话的、质性的。这契合以审美体验为核心、以建构意义意向性为目的的美育要求。教师能够通过主体间对话,以另一名审美者的身份与学生作审美经验的描述与交流,以一种“兴”的经验挑起引导学生向往乃至进入审美体验。限于研究主题和篇幅,美育的教育现象学方法论有待另行阐述。
上述两种美育方案是“美育主要作为一种自我教育,次要存在他者教育因素”的为自我教育服务的他者方法,指向美育的师生互动实践瓶颈的破解。它们既表明美育是一种自我教育,又指明美育是作为一种自我教育的方法论。美育的活动方式、活动内容、教师角色决定其是一种自我教育。
(三)学生的角色需要决定了美育是一种自我教育
根据自我教育的定义和美育的功能与目的可推导出,美育是以学生的自我意识为准备的、以自我尊严失衡去启动的、以自我调节去动态调整的一种自我教育——学生对现实生活的有限作出体现主体意志的无限超越,树立自我尊严感、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意义感,寻求自我的动态平衡,实质是对人生如何值得一过这一问题的美学解决。自我美育方法的总结需要关切审美心理学,中国古典美学提供了一定启示。朱良志在《中国美学十五讲》第八讲提及“四时之外”的审美时间超越理路:人能通过“禅修”企达“无时间性”的审美生存状态[66]。禅修存在“主体进行禅修—主动超越时间—主动进入审美境界”的理路。换言之,主体可以借由主动进入禅修,主动地超越意象、企达意境,超越现象界的束缚、企达审美境界。这一方面显现了自我美育主动求教、求教者自教的特性,挺立了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将人由被动、偶然的审美灵交跃迁至主动的进入。另一方面也昭示了一条自我美育的通路。就自我美育法而言,可以跨学科汲取佛学禅修的方法论启示。当然,自我美育法的进入逻辑应不止这一种。碍于研究者视界的局限,这方面的探索尚不周全。仅举一例,以求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总之,学生的角色需要决定了美育是一种自我教育。
综上所述,美育主要是一种自我教育,是一种以学生自我意识为发生、自我尊严为推动、自我反馈为调节,教师提供审美材料、营造审美环境并作为另一审美主体与学生交流美感而引导辅助的,学生在审美体验中建立意义意向性并指向自我超越与自我实现的个性化活动。在其中,学生借由审美体验对怎样的生活值得一过的生命意义诘问作出个性化回应,不断地在个体生命进程中向着人类真善美的永恒核心价值作意义生成。
六、余论:美育困局存在美学难题
“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甚至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因为它既不是‘可以通过观察、检验获得精确实证的独立知识体系’,也不是‘具备独立、完整、普遍的范畴、方法、规律和体系’的学问门类……美学应当如何既成为科学和成熟学科又能保持、伸张它的诗意冥思特性呢——以现有的条件看,这是一个目前尚不可能圆满回答的理论难题。”[67]10-31美育的最重大现实问题就是寻求审美形而上学的某种确定性证明,对这种确定性的渴望可谓是在“与灾难相赛跑”。因为,美育是将审美的形而上性体验倡议通过教育活动传播给更多的后代青年,而由于审美体验的难以实证性和不可传递性,审美形而上学受到严重怀疑,使得美育举步维艰。
有学者否定审美的超越性,进而否定审美形而上学:“比如去峨眉山游玩三天……当我们最后身心俱疲地回到家中,在72小时里,我们能有一个小时在凝神静观地审美吗?也许会有瞬间的审美体验,但自己根本无法把握这来无影去无踪的瞬间体验。因此,那些所谓的‘超越’只是一种理想性的虚诳。”[42]184薛富兴的批判更加辛辣:“(后实践美学家们)自己研究什么,就把什么说成是人类生命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实在是由自恋而自大的职业病。将审美置于云霓,以此寄托人生,实则管窥蠡测,徒增笑柄。”[68]361进而,他声称美学亟待“走出哲学,走向实证科学,才能成为‘科学’……审美现象的考察只能走实证研究之路”[68]361-363,由此才能“弄清审美意识发生情形、说清人类审美经验构成机制……积累有关人类审美活动的确定、共识的知识”[68]364。可是他又说:“倡导美学的科学主义道路,并不否定审美活动的人文性质,只是倡导走出主观抽象的概念游戏,做些实在研究而已。‘科学’、‘实证’并不等于‘数学’、‘心理学’、‘统计’。”[68]366那么,在薛富兴的理解里,什么才是“既承认审美活动的人文性质,又能对审美活动作实证研究”的“方法”呢?研究者并没有在其所著的《分化与突围中国美学1949—2000》一书中找到确切的答案——这种“方法”的具体形式恰恰是美学学人亟待跨学科攻克的重大难题,也正是美育度过“科学身份认同”浩劫,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所在。不过,“美学真的能交由以确定性、严密性为主要特征的科学去处理吗?疑问是无法消除的……因为科学无法把握审美体验的活的风貌”[67]23。
这对科学和美学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要么科学在实证科学这一狭隘身份认同中扩展开来,成长为一种能够使人文科学具有相当程度实证性的科学(16)这个方向有不同学科的同侪在默默耕耘。譬如从审美心理学出发者(如王一川试图阐释审美心理层次,将审美心理分层为“历构层、临构层、预构层”,审美体验是三层次的统一结构。历构层指审美体验是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历史总和;临构层是审美体验作为一种时空突现;预构层指在审美体验中对未来图像的预先建构、共时统一。见王一川.审美体验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91,98,102);从形而上学心理学出发者(如郑荣双将心理学研究分为形而上学世界、科学世界、生活世界来考察,将形而上学世界的心理学视为先验和超验的,并定义为古典哲学心理学在现代的延续。进而,他从量子心理学、深度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等维度作探索。见郑荣双.形而上学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前言.);从神经美学出发者(如王延慧的博士论文《西方神经美学的审美认知理论研究》、孟凡君的博士论文《认知神经美学视域下的美感问题研究》)。,或者美学永远不能作为一种科学受到一部分人的承认(17)这与后形而上学家们的意思相似。比如罗蒂声称:“哲学、文学、美学统统是一种‘自我想象’,是‘个人完美向度’的自我建构,与真理无关。”“罗蒂不仅取消了本体论意义的形而上学,而且取消了哲学,将其等同于文学……一切哲学、美学建构都是文学叙事,不过是一场‘有趣的谈话’。这是对形而上学最为彻底的解构”。见李晓林.审美形而上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10.。但问题或许可以通过视角转换得到缓解。
首先,就审美的形而上学体验来看,有些人感觉到它的存在(研究者本人亦如是),提供了它存在的证据;有些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却不能证伪它的存在。对于“审美超越是一种学术门派的概念捏造”的批判,如果引入康德的审美共通感来审视,就难免使人怀疑——这或许是批判者们鉴赏判断力的有待完善所造成的乌龙。审美形而上体验的合法性是由人的普遍事实体验所验证的,学人们的理论是描述和解释这种体验的努力。因此,认为审美超越是理论家的臆想恐难成立。
其次,审美是人在现象界做着趋向超验的努力,审美形而上学体验是否需要以及能够被现象界的科学所解释十分可疑。目前审美仍然作为一种“神秘体验”存在,审美体验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领地”(18)“给神秘体验下定义就像解释和评价它的意见一样看法纷呈而又彼此冲突。这并不奇怪,因为用来描述和表达神秘体验的语言是极为悖理的、象征性的和诗意的。即使体验主体选择看来像是严肃而又精确的形而上学术语来表达,那也只是一种对逻辑的表面让步。”见王晓朝.神秘与理性的交融 基督教神秘主义探源[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10.王晓朝先生指出:“希腊人作为‘理性’的先驱者出现在舞台上,但同时存在希腊精神的另一极:神秘主义。用‘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来概括希腊文化精神的两极最为贴切”,并且“‘神秘主义’指神秘主义者们指出的与最高实在直接灵交的经验……‘神秘’不是单纯的认识论问题,不是‘尚未被彻底认识的客体’,‘神秘’必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总是个体的,或以个体为基础的群体感受,难以用言辞(更不必说‘概念’)来表述。”见王晓朝.神秘与理性的交融 基督教神秘主义探源[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1,序言.。从内部批判和外部批判的视角看,如果自持理性主义内部的科学主义认识论,进行针对存在论审美体验的外部批判,那么后者也许无论如何不会有成立的理由。如果审美体验根本不是一种认识论问题(19)“Physicalist aesthetic realism is false……if aesthetic properties exist at all, they are a certain kind of mind-dependent property.”ZANGWILL N. 见The Metaphysics of Beauty[M].New York: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2001:Introduction.,而是一种存在论问题,审美体验的实证问题就可能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是一个“伪问题”。
再次,倘若科学决计不能走出实证的身份认同,而美学的实证科学化又决计不可能,不妨参考学者赞格威尔(Nick Zangwill)的做法,即他不提出任何一种审美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意见,只是单纯地确认审美经验让人生值得一过。对那些未曾接受过哲学、美学理论训练,但又体验着并承认审美的形而上性的人们而言,也根本无须进入任何一种实证的、理论的承诺。“审美体验触及生命的终极意义、终极境界,它如理念、神性一样不能够被理性思考出来、推演出来,而只能凭直觉企达、凭信仰去相信。相信,这就够了,谁又能证明它呢?”[54]374“只要人类存在,就有对永恒世界的向往……在这样的大美体验中声称体验到真理或神,或与宇宙万物合一,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后形而上学时代的人们,不要以自身想象力的贫乏来诋毁他们的劳作吧。”[69]
然而,疑问并未因此消除殆尽。确认审美形而上学体验其所“必定是”还不足够,因为对于一种只能说是却不能说明如何是的事情而言,人类对它的困惑与好奇是无法消除的,对它的求索是不尽的。这关系到审美体验的自我朴素承诺如何在实证性存疑的情况下传播给更多人的问题。两百多年前,康德因为科学奠定形而上学基础的使命发出了富有力感的判断:“如果它是科学,为什么它不能像其他科学一样得到普遍持久的承认?如果它不是科学,为什么它竟然能继续不断地以科学自封,并且使人类理智寄予无限希望而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满足?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弄清这一所谓科学的性质,因为我们再不能更久地停留在目前这种状况上了。”[70]我们认为,美育困局存在美学难题,这既是科学的充分发展造成的,又是科学的不足所导致的。现在,这种有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冲突提问亟待累积、分化与突围。
本研究只是对美育的本然状态作了一个教育形式角度的论述:“美育解决的是个人的终极关怀问题,不是一种他者教育而是一种自我教育。”这种信念亟待连同审美形而上学的某种确定性方法一起,让更多人感受、体验,而不只是一小撮人的呓语。如果审美的确存在实证突破的可能,本人十分愿意成为研究同好。在种种问题背景下,研究者感到既迷惑又兴奋,同时也相信,本文的立论及其信念在时过境迁之后,终将以某种目前已知或未知、已预期或未预期的形式,在某种突破发生时随即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