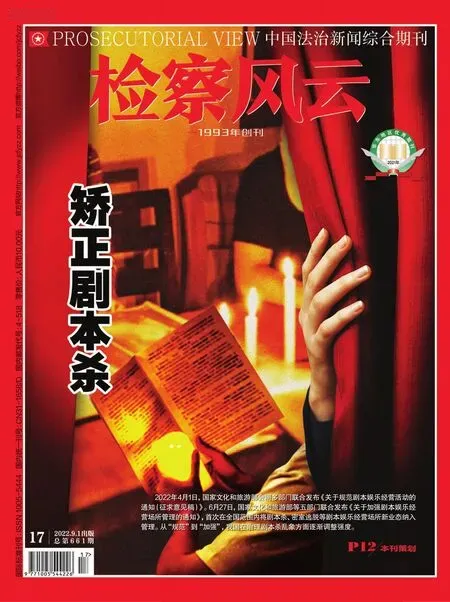土地经营权流转法律规制探析
文/丁文
“流转”一词作为具有特定含义范围的法律术语,是一系列法律性质与法律效果各异的,由法律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关系的统称。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具有独立法律内涵,是指以农村土地为客体,借助出租(转包)、入股、融资担保等形式实现权利变动的法律关系的集合。
土地经营权流转具有主体开放性、客体特定性以及流转方式多样性等特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法政策考量,既包含“经济利益与粮食安全的价值兼顾”,又应顾及“规模经营与小农经济的利益平衡”。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内涵
首先是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立法沿革。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地制度经历了从禁止流转到限制流转,再到鼓励流转三个阶段。
在禁止流转阶段,农户与集体为承包关系,集体拥有统一管理和使用土地的权利,过度偏重保护耕地的政策考量阻碍了土地的初步流转。在限制流转阶段,土地使用权通过转包、入股等形式依法有偿转让,可供选择的土地流转方式较少,且须经发包方同意,流转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农户通过流转获得收益尚处于探索阶段。在鼓励流转阶段,2021年开始施行的《民法典》沿袭了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规定,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为了适应现实中农户利用土地进行融资、流转以获取利益的需求,经营权与承包权进行了分置,以实现为农户提供基本保障与提高经济收益的双重功能。
其次是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应有之义。
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性质分析:第一,土地经营权流转主体的开放性。在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中,流转双方分别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与土地经营权人,受让方只须具有农业经营能力或资质,而不必一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中,流转双方均为土地经营权人。承包“四荒地”所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是通过市场化的行为并支付一定对价获得,其流转对受让方没有特别限制,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主体。第二,土地经营权流转客体的特定性。在土地经营权流转法律关系中,正如租赁权系通过实现物的使用价值满足权利人的需求,租赁权人通过使用土地而非土地使用权来满足其需要。在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过程中,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价值也在于,土地经营权人依法有权占有土地开展经营并取得收益。第三,土地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多样性。《民法典》在将“三权分置”这一政策语言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范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包括出租(转包)、入股和其他形式,而不再涵盖互换、转让。至于其他形式中包含哪些流转方式,存在不同的解读。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法政策考量
目前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保证农户经济利益的价值兼顾;二是顺应规模经营趋势同时稳定小农经济的利益平衡。
当流转土地经营权已成为农户的普遍选择,如何使流转行为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不违反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的耕地保护制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承包土地的农业用途。
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特别是口粮生产,承载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承包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及其农业用途,确保农地农用,优先用于粮食生产,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部分乡镇村庄通过探索种植粮食作物以外的作物,以发展当地经济。在面临如何平衡经济收益与粮食安全双重价值的关系时,实践中从两个方面展开规则设计:从地理空间维度进行地块分割;从时间维度进行分时耕作。
相比于农户的分散经营,将土地配置给有经营能力的主体更能有效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
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保持规模经营与小农经济并存的状况,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流转规则的制定应该注重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平衡。
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土地经营权流转。
若承包方为实现个人耕种目的而不愿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属于正当行使权利,只有在故意或过失使他人无法通过统一流转取得规模经营收益时,方构成权利滥用。村集体或其他农户可要求承包户停止滥用权利的行为,并就一定的损害进行赔偿,但依然不得强制承包户进行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完善
为回应土地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实践问题,一方面,须对未尽其用的规则进行适度调整,以发挥规范之间的协同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弥补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中可能存在的漏洞。
首先,发挥集体所有权的协同作用。
强化集体所有权管理权能,在农户流转土地经营权过程中,由集体寻找合适的经营主体并进行谈判签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在将土地规模流转以前,集体需要通过集中流转、集中整理的方式实现土地成方成片,并在此基础上改善土壤质量,提升“地力”。对不愿意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农户,通过承包地互换的方式保障其合法权益。落实集体所有权收益权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进行集体资产的清产核资。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有必要在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将整理后新增的集体资产纳入集体收益权能的对象范围,由集体经济组织来决定收益的分配比例及资金用途。
第二,有序开展承包地的退出和转让。集体在逐步引导农户通过自愿有偿的方式将承包地退还给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时,也承担着将退还土地进行有效利用和规模经营的责任。
第三,利用好经营权放活带来的收益。允许集体经济组织收取适量管理费用,能够发挥所有权主体的优势,在承包农户与经营主体之间进行沟通协调,提升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规模和效率,实现规模经营效益的最大化。
其次,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调节机制。
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平台: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建设,完善土地经营权市场规则。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以面积的明确为前提,由政府建立统一的流转交易平台,确保土地资源数据的准确性,便于通过登记备案及时记录权利变动信息,明确权属关系。
发挥政府规范引导作用:政府须发挥监督管理作用,促进农地资源实现最优化配置。落实对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的监督,通过建立信用评估机制以及流转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起事中事后的监管防线,及时查处流转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承包农户合法权益。
最后,保障流转农户与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农户的保障:在合同的订立阶段,应规范完善合同签订的程序及内容。农户可以采取书面方式订立合同,并选择是否由第三方进行公证,也可以私下作出口头约定以达成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合意。任意性存在的同时意味着规范性的缺乏,口头协议约定的事项较为简略,也难以为流转合同纠纷提供裁判依据。村集体应承担起监督职责,在流转合同中完善对违约责任承担的规定。
对经营主体经济利益的保障:应放宽对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的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对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是否具备农业经营能力或者相应资质进行审查,确保其在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后能够作为适格主体进行开发经营。资格审查制度的建立在于加强事前监管,与项目审核、风险防范制度一起构建起对承包农户权益的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