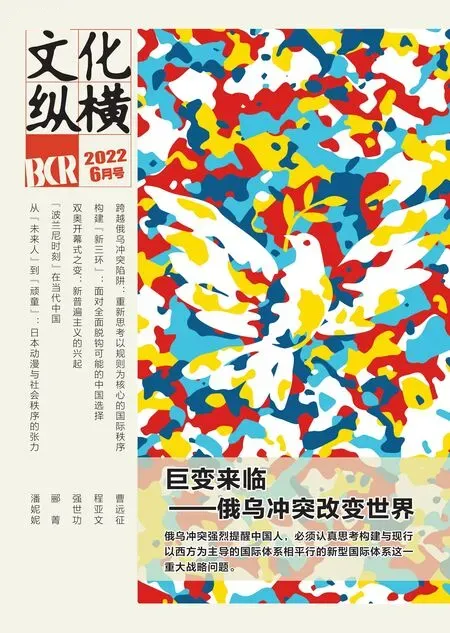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学”*
——一个世界史的视角
方 旭
2021年3月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其就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将中国称为“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在此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美国老牌政治家基辛格已三次对中国发出战争警告。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老生常谈”:中国能赢“地缘政治奥运”金牌吗?他通过引证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即将发表的《大竞争:21世纪的中国与美国》中的数据,客观展现了中美这两个竞争对手在诸多领域的实力水平,并得出结论:“现在是时候承认中国是美国的全方位竞争对手。就中国本身而言,它构成了美国人目前已知的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1]言下之意,中国作为崛起中的超大型国家势必控制更大的地理空间、获取更多的资源,而世界的地理空间本身是有限的,中美之间地缘博弈必然导致零和争夺。
无论布林肯、基辛格抑或艾利森,他们的论调显示出他们是欧洲传统地缘政治学忠实传人,只是这些观点大有令人困惑之处: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与美国远隔重洋,为何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上的最大威胁?而中国也从未将“地缘政治”作为一种主流外交话语,更多赋予的是负面政治寓意,如何理解他们所谈到的“地缘政治”所指内涵?
国家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生命体
对世界各国的合作或竞争来说,“地缘政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地缘政治学”由19世纪的契伦(Rudolf Kjellén)与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创立,本是地理、政治、人类学、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理论学说,后经20世纪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麦金德(H.Mackinder)、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乃至当代的布尔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亨廷顿(Samul P.Huntington)的发展,“地缘政治学”成为一门事关国际战略和大国关系的“显学”。国际主流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地缘政治学的内涵是“战争”与“强权”,与“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背道而驰。在当代中国和平崛起已成为历史事实的情况下,国内学界已经意识到,基于地缘政治的相关主张无力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新问题提供答案,中国应尝试超越地缘政治,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内学界已经意识到,基于地缘政治的相关主张无力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新问题提供答案,中国应尝试超越地缘政治,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美国远隔重洋,美国为何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上的最大威胁?
曾经前白宫首席战略师、总统高级顾问班农为代表,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对此另有主张。早在2017年,班农就在日本发表演讲称:“19世纪和20世纪有三个伟大的地缘政治理论。中国一带一路的大胆之处,是把三个地缘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计划。”[2]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代中国提出的新地缘政治论,它将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陆地说”和斯皮克曼的“陆海边缘地带理论”三者结合,谋求与美争霸。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有此等想法并非不可理解,因为19世纪“世界史”欧美诸国的成长史的本质就是争夺大国地位,构建具有“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的国际秩序。在他们眼中,中国传统“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或者今天“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只是一厢情愿,即便是有新的国际秩序建立,也是崛起的大国说了算。
在班农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代中国提出的新地缘政治论,它将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陆地说”和斯皮克曼的“陆海边缘地带理论”三者结合,谋求与美争霸。
除了欧美诸国自身的霸权发展史,班农们之所以所以会持有上述观点,还得回到“地缘政治”概念本身来观察。按照美国权威教科书上的说法,1899年,契伦发明了地缘政治(Geopolitik)一词,并在1901年《科学的政治学》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地缘政治”的概念,但直到1916年《国家为一有机体》一书出版,他才正式将“地缘政治学”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他将地缘政治学描述为一门“将国家作为地理有机体或者空间现象的理论”。[3]契伦受拉采尔的影响甚多,虽然后者并未率先提出“地缘政治”概念,而是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西方学界仍公认他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开创性的人物。

19世纪欧美诸国的成长史的本质就是争夺大国地位
据说,拉采尔受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影响,提出有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地理概念,认为国家就如生命体一样,会根据人口的规模和构成而不断发展变化,国家的“边界”也会像生命体一样扩大或收缩。“人们谈及边疆时,就好像它是一种不言自明可移动的东西,边界的推进以获得国土为前提,边界的后退以国土丧失为前提。”[4]作为“生命有机体”,国家会为了生存而“吞并”较小的“有机体”以壮大自身,这正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国家的灭亡不应被理解为“毁灭”,而应被视为“重塑”——国家作为一个成长中的有机体重新加入到新的空间政治秩序中。
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普鲁士历经数次与周边大国的战争缔造出“新帝国”,拉采尔设计的“中欧大空间”(德国、奥匈帝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为西抵美国为代表的“门罗主义”、东拒俄国为代表的“泛斯拉夫联邦”的现实挤压寻找理据。随后,契伦以德国为中心的“中欧空间”,力图构建德国以日耳曼—北欧为中心,以柏林—巴格达铁路为串联,形成覆盖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共同体,其意在凝聚分裂的中欧国家,形成一个巨大的陆地联盟,以对抗西班牙—荷兰—英国海上霸权。可以说,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思想主线在于强国政治,成长中的国家之间生存竞争和博弈是宿命的、永恒的,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为了实现生存空间的安全,就应该采取各种方式(如联盟与瓦解联盟,干涉与抵制干涉,封锁与反对封锁等),在其生存空间中建立权力主导权。
上述思想构成了现代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底色。故而,现代地缘政治学区分“海权派”与“陆权派”实有局限。从学理本身来看,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分,都反映了作为有机体的国家成长、冲突的历史。“陆权论”代表麦金德和“海权论”代表马汉,无不是在自己国家处于积极向外扩张、殖民的势头上,从全球争霸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地缘政治学理论。若按照思想史传统划分,地缘政治学可划分为英国地理政治学派和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前者代表自由主义式的“遏制理论”,倡导均势制衡;后者则代表民族主义式的“成长理论”,主张“有机”扩张。“成长”与“遏制”实为“地缘政治学”的一体两面,国家为应对生存空间的威胁,采取“成长”与“遏制”两种不同手段处理现实的地缘冲突,维持国家生命体之延续,或者确保世界帝国统治之稳定。作为后起帝国,美国在名义上继承了英国地理政治学派,同时在理论实质吸收了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观点,他们将任何国家视为一种成长中的生命体,但凡面对逐渐崛起的国家,必然引发其对生存空间遭到压缩的恐惧。
美国地缘政治学界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一种军国主义式的侵略理论,可在现实层面,美国和西方国家常用“地缘政治”指责他国复兴之路是纳粹扩张逻辑。
“遏制”:地缘政治的另外一面
美国地缘政治学界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一种军国主义式的侵略理论,可在现实层面,美国和西方国家常用“地缘政治”指责他国复兴之路是纳粹扩张逻辑。殊不知,“成长”是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学的核心内涵,“遏制”同样也是,两者皆为“政治话术”。
海权大国如何应对陆权大国成长?这可以说是“遏制论”的主要理论动机。拿破仑通过军事征服获取欧洲大陆霸权,却在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中被英国击败,被迫放弃侵英计划,1806年11月21日,拿破仑又在柏林发布敕令,宣布封锁不列颠诸岛,旨在切断英国对反法同盟的经济支持,迫使英国求和,但英国利用英吉利海峡据险而守,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牢牢地把握住制海权,并依靠广阔的殖民地以及强大的海上贸易对拿破仑 “大陆封锁体系”开展“反封锁”,最终导致欧洲秩序和“封锁体系”崩溃。海权大国对陆权大国全面胜利,激发了后世地缘政治学家的思考。马汉在总结拿破仑“大陆封锁体系”失败后得出结论,自人类有史以来,海权都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要称霸世界,并在国内达到最大限度的繁荣与安全,控制海权为首要事务。如果陆权国家没有出海口,无论其国土如何广袤,最后终难免于衰亡的命运。[5]海权国家对海上重要咽喉要道以及航线实施控制,以获取制海权,实现对陆权国家的封锁,被西方海权大国长期奉为圭臬。
海权国家对海上重要咽喉要道以及航线实施控制,以获取制海权,实现对陆权国家的封锁,被西方海权大国长期奉为圭臬。
英国学者麦金德常被奉为地缘政治学创始者之一,后世多认为他对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具有强大影响力。但他在1941年接受美国《生活》杂志采访时极力否定他与地缘政治学的关联,故在前文中提到英国学派时,专门以“英国地理政治学派”来区分。其中缘故,可能不只因为他想与纳粹划清界限,更因为他的理论本身是披着陆权外衣的海权主义者。国际关系学界广为流传的麦金德关于“世界岛”的三句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6],不过是对马汉为代表的“海权论”的修正。
麦金德曾告诫英国:如果德国和俄国结盟,或者德国征服俄国,德国就奠定了征服世界的地理基础。麦金德在《世界历史的枢纽》中将俄国腹地这块“天然堡垒”命名为“枢纽地区”,后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又称欧亚大陆为“世界岛”,“枢纽地带”则变成了“心脏地带”。“世界岛”的出发点并不是创造如何让陆权走向强盛的理论,而是提醒英国,“离岸平衡手”具有终极遏制目的,一是撕碎欧亚大陆,即不能允许欧亚大陆出现一个强大到能把陆上势力联合起来的政治体;二是掌握全球海洋枢纽的开关命门,绝不给陆权大国留有控制海洋的任何可能。
如果将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视为对海洋国家的一种警告,其“德国学生”豪斯霍弗则反其道而行之,意欲建立庞大的陆海联盟。按照以他为代表的第三帝国德国地缘政治学派观点,要建立以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为基础,用铁路构建德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以巨型欧亚国家为主体,形成海陆双元联盟,从而对抗英美海上同盟国家。日本入侵中国打破了豪斯霍弗组建“海陆双元同盟”的构想,他几次劝说日本放弃侵占中国领土,未获成功。最终,第二次世界大战演变为惨烈的“欧亚内战”,第三帝国的失败彻底使“地缘政治学”被打成“异端邪说”。相比之下,麦金德的另外一个荷兰裔美国学生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则是对麦金德的“世界岛心脏地带”的发展,即“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而非心脏地带,才能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掌控全球”[7]。由此可以看出,海权论与陆权论并非决然对立,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交织,甚至是继承或者“反向继承”。
1942年,斯皮克曼就指出: 地理是美国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因素,也是最永恒的因素。他又感叹:美国的地理位置处在欧亚大陆、非洲和大洋洲被包围的危险之中。[8]这一论断让我们惊讶不已。熟知的地理知识告诉我们,美国的地缘位置堪称绝佳,其东部和西部分别是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道天然屏障让美国得以远离欧亚大陆纷争,并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新兴大国发展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斯皮克曼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是受到了墨卡托投影法制图的“视觉规训”:打开古代世界地图,就能看到世界的中心位于“欧亚大陆”,美洲(美国)甚至欧洲都只是亚洲文明的附属。当双半球地图出现之时,美国才有了独立的地理空间展现,而这种世界图景至今只有不足两百年的历史。再把世界地形图铺开,便可看到,除却澳大利亚和美洲诸国外,美国实际上是被欧亚大陆的东西最远端欧洲德国与亚洲日本“首尾环抱”。在这种视觉感知下,斯皮克曼延续了麦金德提防“欧亚大陆”势力联合的教诲,他更进一步提出,能够主导“旧大陆”联合的真正政治力量是“中国”。
打开古代世界地图,就能看到世界的中心位于“欧亚大陆”,美洲(美国)甚至欧洲都只是亚洲文明的附属。当双半球地图出现之时,美国才有了独立的地理空间展现,而这种世界图景至今只有不足两百年的历史。
来自中国的地缘政治威胁?
美国何时开始感受到中国的地缘威胁?1900年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塞姆帕(Francis. P. Sempa)为马汉的《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撰写导言时就警告美国人:中国有一天会成为一个逐渐强大的势力,对现存的国际体系提出挑战。[9]1898年4月25日,美西战争爆发,菲律宾控制权随之易主,马汉认为,夺取菲律宾给了“美国进入中国的跳板”,从历史上看,这个“跳板”确实成为美国近百年来插手控制东亚地区的重要支点。

斯皮克曼在1942年指出,地理是美国外交政策最根本和永恒的因素
斯皮克曼对东亚形势的判断完全继承了马汉,他指出,一个拥有 4.5 亿人口且现代的、有活力的、军事化的中国,不仅是日本的一大威胁,也挑战着西方列强在亚洲地中海的地位。[10]20世纪以来,美国为扶持日本成为区域性的大国也不遗余力。1905年日俄战争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因调停日俄和谈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会谈期间,他建议日本外交代表、枢密顾问金子坚太郎将“门罗主义”挪用至亚洲,其意图是让日本宣告亚洲实行门罗主义。日俄战争后,日本精英知识阶层将“门罗主义”的法理架构与“大亚洲主义”的地缘构想嵌合,在东亚经营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霸权秩序,到1940年时,日本已占领大半个中国,其主导下“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在全球占据一席之地。
斯皮克曼对东亚形势的判断完全继承了马汉,他指出,一个拥有 4.5 亿人口且现代的、有活力的、军事化的中国,不仅是日本的一大威胁,也挑战着西方列强在亚洲地中海的地位。
在日本最为强盛之时,甚至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前,斯皮克曼仍认为中国才是美国最大威胁。正如他所指出的,“历史上的天朝大国拥有的力量潜能比樱花大国要大得多……中国未来将发展成为一个国土广袤且控制着中部海域大部分海岸线的国家。它的地理位置与美国相对于美洲地中海的位置相似。中国一旦崛起,它现在对亚洲的经济渗透肯定会表现到政治方面。”[11]

20世纪以来,美国为扶持日本成为区域性的大国不遗余力
“中国的地理位置与美国相似”,这是斯皮克曼判断又一新颖之处。如前文所说,美国地理位置对处于发展进程的国家而言当然是优越的:独处美洲,周边无威胁自己的大国,既有海洋作为安全屏障,可建立强大海上军队,又有安全且广阔的美洲大陆作为领土资源基地,也可以组建规模庞大的陆军。按照有机体国家理论看来,“海陆双元有机体”恐怕是当年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和丧失海权的俄国人梦寐以求的。但在发展完成后,当美国意欲成为统治性的“世界帝国”,原本优越的地理位置由于远离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反倒成为其走向世界帝国的劣势。为实现对欧亚大陆的控制,美军围绕其边缘地带布置大量军事和经济力量,但这一行为代价高昂。
斯皮克曼所说的地理相似,可能指的是中国拥有与美国一样“海陆双元”的地理优势。在他们看来,与美国相比,中国是所有世界大国中陆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逐步迈向“崛起”,“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势必与众多的陆上邻国发生争端,而当它要发展海洋力量,也必然造成海洋邻国的边界紧张。按照他们的思路,较之美国,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遭受的地缘政治空间的钳制极为严峻:东面有美操纵的双重岛链捆绑,西南有新兴发展中的印度随时呼应,东南有“陆地框架破碎”的越南、印尼等国环伺,中国地缘位置处于腹背受敌的棋局。但辩证地看,一旦中国真正实现崛起目标,这一地理位置也让它更容易将影响力辐射到“心脏地带”。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通过基础建设和资金储备渗透亚欧大陆核心地区,打造以海外港口、洲际铁路、输气管道等为主动脉的欧亚大陆经济共同体,中国向欧亚大陆地缘力量投射要比美国更直接、更有渗透力。[12]
1943年,斯皮克曼去世。3年后,凯南化名“X”在《外交》季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1950年,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的凯南说道:“在我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安全都一直有赖于英国的地位;加拿大尤其是我国与英帝国始终保持良好关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人质;英国的地位则有赖于能否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如同对英国一样确保没有任何单一强国统治欧亚大陆。”[13]美国地缘政治学家从英国老牌地理政治学家那里习得地缘战略,即旨在防止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一个有单极支配力的政治力量。斯皮克曼和凯南点破了美对日战略布置意图: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在其国家走向扩张之时,可能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最大敌手,在战争失败后,要将其改造成遏制欧亚大陆的重要棋子。
“二战”让美国联手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战胜了德国与日本,在构筑战后新地缘政治秩序时,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安插”了两只“离岸平衡手”:一只是传统海权国家英国,它在大西洋起到“搅乱”欧洲旧大陆诸势力的功能,另一只则是具有巨大海权潜力的日本,它在亚洲充当英国的角色,以便美国控制西太平洋。与其说目前美国地缘政治的核心是“遏制中国”,不如说,战后美国一直沿着斯皮克曼等地缘政治学家制定的地缘战略行事,其目标仍是建立庞大的陆海边缘国家联盟,从而钳制欧亚大陆。
斯皮克曼和凯南点破了美对日战略布置意图: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在其国家走向扩张之时,可能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最大敌手,在战争失败后,要将其改造成遏制欧亚大陆的重要棋子。
如何看待“地缘政治”?
需要肯定的是,我国对外话语对“地缘政治”的批驳和拒斥是明智的,[14]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地理因素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对不同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会产生极大的制约作用,但他们始终没有将地理因素对政治的影响提高到绝对地位,换言之,“地理决定论”并不“科学”。我们也应该了解,地缘政治学曾与德意志第三帝国有千丝万缕联系,“正统”学科领域都对其“讳莫如深”,更有学者警告此学说乃是“一剂毒药”。
对于正在走向“和平崛起”的中国而言,首先,我们要防范西方话语体系利用“地缘政治”炮制的“中国威胁论”话语陷阱。如今,“地缘政治”越发成为欧美西方国家用于干涉另一国家主权内政的意识形态工具,他们一方面将“遏制理论”包装成“均势理论”或“和平地理学”,另一方面将日益走向复兴的国家贴上“不正义的扩张”的标签。
我们同样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外交决策层依然深受地缘政治思维影响,国际话语体系中“地缘政治”作为对外沟通的一个重要概念仍不容忽视。
其次,我们同样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外交决策层依然深受地缘政治思维影响,国际话语体系中“地缘政治”作为对外沟通的一个重要概念仍不容忽视。诚然,大国崛起必然触及国际秩序建构,要避免历史上成长的大国与守成大国间冲突与对抗的怪圈,中国必须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要超越地缘政治,还需结合时代的新变化与中国自身的特点来考察“地缘政治”本身。有必要以和平与繁荣为目标,充分研究和吸收其规律,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学”。
注释:
* 本文系国家社科规划基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研究”(批准号:21BKS161)阶段性成果。
[1] 艾利森:《中国能赢得地缘政治竞赛的金牌吗?》,观察者网,2021年8月5日。
[2] 滕建群:《三种地缘政治学说与“一带一路”倡议》,载《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5期。
[3] 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另参见图南德:《为了新世纪的瑞典-德国地缘政治学:契伦的〈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方旭译,载娄林主编:《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
[4] 拉采尔:《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袁剑译,载张世明、王济东、牛昢昢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133页。也有学者认为,拉采尔受到达尔文主义影响是其学生辛普森的以讹传讹。参斯托詹诺斯:《地缘政治学与拉采尔:驳拉采尔地理决定论的神话》,金海波等译,华夏出版社,即出。
[5] 张晓林、刘一健:《马汉与〈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载《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6]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3页。
[7] 刘小枫:《美国“遏制中国”论的地缘政治学探源》,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0期。
[8] [10] [11] 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王珊、郭鑫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47页;第444页;第444页。
[9] 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9页。
[12] 麦考伊:《美国全球权力的兴衰》,小毛线译,金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164~168页。
[13] George F. Kennan,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 5.
[14] 杜哲元:《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地缘政治”》,载《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