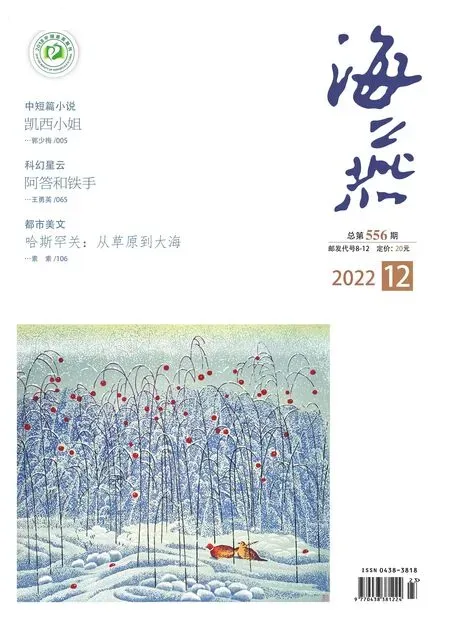那些深爱你的,都没有走远
孟小迷
省城的小雨,如之前的预报,真真地下了一夜,细细的,柔柔的,绵绵的。早晨打开窗子,一股小风夹着巨量的负氧离子直冲鼻腔,我有种恍惚感,若梦若仙。
窗子注定是不舍得马上关合了,甚至连同另半扇鹅黄色的窗纱我也一起拉开。我就这样痴痴地站在窗口,定睛品赏着这风、这雨和这丝丝滑滑、温温柔柔的气象。马路对面的淡灰色楼宇,那一扇扇白色的窗格前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出现绰约的身影,与细雨清风遥相呼应。可我已经顾不上看对面的女人是在忙碌还是在梳妆,只觉得这雨丝真的与牛毛一样细,一阵小风吹过,它竟然还会和着风扭上一扭,那笔直的身板儿,顷刻间有了微微的弧度,像极了婀娜的美人在躬身致谢。
多么神奇的一切呀,让你在感受它的时候,都是温文尔雅且心生欢喜的。此刻,得意忘形的我,特别想自制一个词汇重新形容一下这雨丝的形态,但费尽了心思也没有成功。只能是牛毛细雨了。牛毛这两个字用得简直太贴切,太传神。对,就是又细、又柔、又密、又长、又耐烦、又有个性的那一种。你说马毛、羊毛都不合适。
在这样一个传神的日子里,十分适合写下一些万物互应的奇妙故事。我来了兴致,为了把气氛拉满,进书房前,还特意从柜子里取下了一瓶红酒,倒入高脚杯,呷了两口,算是提了提精神,也壮了壮胆。
今天笔下的故事,确实很神。如果我不是亲历者,断然是不敢相信的。这里有人物、有动物、有植物,还有桌椅板凳。把他(它)们放在一起琢磨,我竟然哭得泪眼婆娑。深深的爱,原来都是那么醇,那么透明,又那么谦卑。
常说天地一体,万物有灵,连同日月星辰,连同猫狗牛羊,连同桌椅板凳,你若与之真心相处,都会产生挚爱,产生交流。也许我们不能精确地翻译出它们的语言,但它们的行为,你一定可以读懂。
初秋的清晨,我依着之前的计划,去离家很远的一个特大路边早市采风购物。结果,刚刚迈入市场,就在一个日杂摊位上,一眼看到那几个崭新的接油小盒。这个意外的发现,令我十分惊喜。在过往的认知中,这种大型家电的配件,只能出现在生产车间,最次是专营店里。
大约五六年前,我家抽油烟机的接油盒,擦洗时被我不慎摔裂个小缝儿,我幼稚地以为,要换这个小盒,需要翻山越岭去找厂家,那实在是太过麻烦。于是,为了省事,就决定用胶水粘上。别说,粘得很好,严丝合缝,毫无破绽。安上后继续用,也没有出现任何妨碍。从此,我再没有管过它,我们就这样相忘于江湖。
如果不是那天在早市上看到这个可以替换它的小盒,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继续恪守自己的职责,依然在岗,但是,这世上没有如果。
自从看到与我家一样的小盒后,我一路上都在兴奋,心想,这回终于可以换掉旧的了,而且还不用翻山越岭。可终因时间久远,我一时记不起到底是盒子坏了,还是其他什么坏了,便决定回家确认后再买,反正可以随时买到,弃旧换新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我的脑子像计算机一样缜密运行,并将这个程序完整地输入到心灵的系统里。
非常遗憾,我一回到家,便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晚上做饭时都没有想起,哪怕是一点点。就在我刚把锅放到炉盘上,还没打开抽油烟机,只听“啪”的一声,小油盒自己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摔在两锅中间,没有坏掉我的一锅汤,只是已经粉身碎骨。
在我没看到新油盒之前,它安安稳稳地陪着我,甜日子、富日子都没有言声,苦日子、穷日子都没有抱怨。这会儿,它竟然动起了脾气。难道这是已经知道要被抛弃,而先自绝了生命吗?
都说万物有灵,都说心有一念震动十方,这回我是真的信了。那些深爱我们的人或物,曾经是多么的投入,多么的忘我无私,以至于在离别的时刻,都舍不得让你心生自责与愧疚。
“我已经碎到不能复原,扔掉我时,主人请你别难过哟。”小盒子深谙主人的心思。它知道主人舍不得扔掉的肯定不是一个物件或那个物件背后的价码,而是陪她太久的一段感情、一个习惯、一份信任。
那些用起来非常顺手的东西,就像一个为你竭尽忠诚以至于逆来顺受的老仆人。
而这个“老仆人”还有所不知,在它的主人没有能力接纳残缺时,曾一度还想换掉整个油烟机。这个愚蠢的主人,也不过是刚刚才知道,不小心划破了一根手指,是不用放弃全身的。
“老仆人”终于知道自己就要光荣下岗了,又怕主人自责,便主动粉碎了自己。这毅然决然的大义之举,也仿佛在对我开示:成住坏空乃自然之律,来了的,就双手奉迎;走了的,就让它走得清净。
与小盒一样无私忘我深明大义的,还有多年前我替他人代养的芦荟。别人托付我时特别介绍,这是一棵独株,只长高,不分叉。可是,这个家伙到了我家后,叉分得像雌鱼甩籽,乌泱乌泱的。就算丢片叶子都能活下去,插到石头缝里也不干枯,一改之前的娇气,既不挑盆,也不挑土,皮实得跟天养的一样。最多时分出12个盆,每盆又都有十几株。它们以它们的善良在讨好我,撒着欢儿地回报着我的认真。
眼见着快泛滥成灾,有一天,我站在花房跟它们叨咕:可别再生叉发芽了,为娘实在是养不了太多,花盆也买不起了。并在心里悄悄决定:周六打理时,必须要扔掉几盆。结果到了周六,我再去花房,不过几天的工夫,架子上的一排芦荟一下子死了七盆,且都是不可救药的枯死烂掉。它们曾经因为我长时间出差而缺过水,缺过光,甚至缺过空气,但都顽强地活了下来,这回仅仅因为我有了嫌弃它们的念头而集体自杀。
万物果真有灵呀!你爱它,它知道,它确定以及肯定地知道。
它们低下头,只是为了让你赢。它们躬下身,只是为了让你赢得足够体面。所有深爱我们的人与物,都是甘愿放下自己的身段,为你的一切决定让路。
真爱你的人,不忍心在你面前趾高气扬,飞扬跋扈。不忍心与你争高论低,逞一时之能。不忍心因为自己的光芒而让你陷于尘埃。它们化泥成灰,只是为了让你赢得痛快。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在一家外资上市公司任职,因工作需要,公司为我们配备了一辆当年新款的林肯车。车从天津港保税区提出,因为免税,海关只给了我们一把钥匙。
那个年代,这种牌子的车,马路上极少见到。而我正年少轻狂,何况车子确实又太漂亮,很难把持住锦衣夜行的低调。车首先开进我们军区大院,一阵嘚瑟,引来许多熟人围观。结果乐极生悲,下车时,竟然忘记拔出钥匙。厚重的车门,“嘭”的一声被朋友随手关上。
我的心脏仿佛一下子被门挤碎。
林肯车的密闭性,无需妄加设想,连空气都灌不进去。而当时我的城市还没有一家专营店。我望着这个一动不动趴在院子中央的大家伙,一筹莫展。围观的一二十人,出了一二百个主意,也没有办法撬开车门或是车窗。几乎绝望的我,猛然想起家里柜子上的那把头带黑柄、总长只有林肯车钥匙三分之一的小钥匙。
这把小钥匙原属于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已经被偷走了两年,可这把小钥匙却被我一直放在柜子上没舍得扔。身患重度整理癖与洁癖的我,一百次地想扔掉它,又一百次地把它从垃圾桶里捡回来,擦擦干净又重新放到柜子上,且放在明面处。不知为什么,每每要扔掉它或准备收入抽屉时,心里总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好像它就该这么光芒万丈地躺在这里,并有一天在这里显灵。
也许是我的诚心,真的寄附在它的身上了。两年间,我与它有过上百次的对话,可能彼此早已心有灵犀。
我向围观的一位朋友借了辆自行车,风一样地骑回家。拖鞋都没有换,直冲柜子而去,拿起小钥匙,连忙揣进了裤兜,再风一样地往现场赶。
嘘!我没敢吱声,怕人家笑话。小钥匙那么短,怎么可能打开这个厚重的车门?我决定悄悄地、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干。这时正好有人提议敲碎挡风玻璃,于是,大家凑到了车前,我则将小钥匙偷偷插进了左后门的锁孔。我屏住呼吸,轻轻一拉,怎么样?见证奇迹的时刻终于到了,门开啦。我激动到泪水喷涌,紧接着翻过驾驶座椅,一把拔下了钥匙。
林肯车安好无恙。
围观的人,怔得像被定住的木头人。待醒过味来,问我是怎么开的?我举着小钥匙说:“就是它。”大家笑到差点把一口老血喷出,纷纷让我再试试。我高呼着小钥匙万岁,可这个理应万岁的功臣,此刻却在我的挥舞中被甩到了路旁的草丛。
我很想留下它做个纪念,众人帮我翻遍草丛,最终也没有找到。
它的使命终结了,不再需要我的奉养。于是,挥挥手,躬身退下,不留一点念想。它决意不让我为它再费心思,以至于连以后凭吊的机会都不给我留。
小钥匙,好一个大君子啊!
深爱你的,都那么谦卑,那么无私,那么慷慨,那么恩重如山。
有人说,“所有的逢凶化吉,都是平日攒下的人品。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帮你,连老天都讲论功行赏。上天将我们平日积下的善缘统统记在账上,只为将来的某一时刻,救我们于危急。”我也愿意这样相信,这是德行的回馈,否则,谁还想当好人呢?
初中的时候,我养过一只橘猫。别人送给我时,它才出生五天。放在我的手心上,像个绒绒的小毛团,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咪咪。
当时我家住在中华路一个小院里,房子是日式的二层小楼。每天放学回来,一进小院大门,我就对着天空喊:咪咪——它的耳朵像装了雷达一样灵敏,不一会儿工夫,只见它从院外的楼顶飞奔而来,一路飞檐走壁,虎虎生风,疾如迅雷,猛如虎豹;可一旦趴到我的后背上,又乖得跟个小可怜包似的。
我天生不近海产品,却情愿为它手撕鱼片。它为了回报主人,常常带着战利品向我表功,三天两头还会带上对象和一帮狐朋狗友回来,我也是好吃好喝供着。但咪咪不受我父亲的喜欢。父亲是位老军人,他刻板地认为一切萌宠都会令我玩物丧志,于是多次要处理它。那天晚上,咪咪如常趴在我的脚下,收起了以往的恣意,温柔得有点楚楚可怜。我跟它说:“以后别惹我爸爸,我可不想难为你们任何一个。”
第二天,我照常上学。可等我放学回来,再喊它时,那个风一样的身影却没有出现。我找了三天,方圆几里,反反复复地找。最后,一位认得它的老伯说:“姑娘,别找了,好猫是不会死在家里的。”
我没有勇气见它最后一面,我宁愿相信它只是又玩疯了,忘记了回家。但眼泪还是不争气地噼里啪啦往下淌。
咪咪真的听懂了头天晚上我说的那些话吗?但是,它不想让我为难这一点,我确实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之前我不让它总带对象回来,它真的就不再带了,偶尔带,也是背着我,匆匆来且匆匆去。
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些深爱你的,会是多么地深爱,深爱到多么地乖顺。
我的母亲,是一位坚强乐观善良的女性,我信赖我的母亲,除了血缘上的牵系外,还有人格上的深深崇敬。爱与敬的叠加,构成了我对母亲这个伟大称谓的由衷热爱。
母亲躬身养育了我们,也躬身与我们做了告别。
母亲生命的最后十天,我们兄妹安葬了一年前仙逝的父亲。从那一刻起,母亲的生命也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望着母亲日渐孱弱的身体,我有强烈的预感,这株美丽而优雅的老茉莉花,终到了要凋谢的时刻。我交待好工作,请好了假,日夜陪伴在母亲身旁。
立冬时节的东北特别地冷,冷得彻骨透心,那是我有生以来最为寒冷的十天。昔日母亲那盏通明火热的油灯,总能为我们点亮一切幽暗,驱散所有的荒凉。而今这盏油灯正在逐渐熄灭,仅剩的那一缕光亮,已不足以对抗我内心对别离的恐惧。
我深深知道,母亲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她为了我们,一直在咬着牙、忍着痛坚持。她每迎来的一个黎明,都充满着对人世的眷恋。
倒数第七天时,我内心的挣扎已近崩溃的临界点。我不知道决定这个大限到来的权利,是应该交给上天,还是交给子女,还是交给母亲自己。这个艰难的抉择,是世上最痛苦的考题。
最后,我用掷骰子的办法将权利还给了母亲。稻盛和夫说:“当你无力选择时,就向苍天投上一枚硬币,之后相信它就是天意。”
母亲是个心里有数、认知层次很高的女人。我直接问:“妈妈,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治疗?”母亲淡定地摇摇头表示拒绝。之前,母亲的身体有些异样,她是愿意积极配合医治的。我问:“那就这样了吗?”母亲从容地点点头。
母亲视死如归的凛然里,透着一股所向披靡的气势,那淡若清风的语调中,爆发出石破天惊的力量。母亲给了我吞下泪水迎接死亡的勇气,那一刻,她已注定成为我余生路上一盏最伟大的明灯。
相聚的日子谁都会过,分别的痛苦强人都难以承受,我懂得母亲在告诉我什么。
这是母亲为我们也是为她自己做的最后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为我遮住了满天乌云。之后的七天,母亲基本不再进食,意识偶尔清醒,偶尔糊涂。清醒时,她将自己最后的话都留给了我,那里有她不曾透露的心思,还有她孩童一般的恐惧,及一个慈母的殷殷嘱托。
我十分感谢母亲的信任,也庆幸有缘可以陪伴至爱的妈妈最后一段时光,并藉由对生死离别的亲身体会,而生出对每一个生灵的真切悲悯与爱护。
母亲是个不流泪的菩萨,她的眼泪很值钱。她的泪水早已化成大海,只为了容纳我们的脆弱与不明。母亲直至最后一刻也没落泪,一滴都没有。她用非凡的毅力,将泪水吞到心底,又在心底将一颗颗泪珠化成慈悲,为我们堵住了那痛不欲生鲜血喷流的创口。
她爱我们时,堪称世上最尽职最温良的母亲;她告别我们时,堪称世上最完美最果敢的英雄。
母亲终在父亲去世后第364天的那个夜里,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惊扰他人。那天正好是农历十月初一,传说是给先人寄寒衣的日子,那一天又恰好是父亲的周年祭。
三日合一,算不算是母亲的精心安排?如果母亲可以回答,她一定会说:凑在一起好,省得让你们多操心。
那些深爱你的,都是为你考虑最多、最不露痕迹的。
那一年,我痛失了双亲。世界上那两个最爱我的人,都走了。之后,我用十年的时间去消化这份思念,也慢慢懂得,理解一份深爱,需要太长太长的时间。
窗外的小雨还在下着,柔柔的,绵绵的,像在诉说,也像在哭泣,那凄婉的落雨声,一滴一滴敲打着我的回忆。原来,那些深爱过我的人,都没有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