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与栖居
——京杭大运河济宁段的百年兴衰
吴士新 孙德皓
“南船北马”的商运文化
自元代全线贯通以来,京杭大运河静静流淌了700 多年。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担负着维系古代中国大一统局面的重要角色。运河沿线崛起了以山东济宁为代表的因漕运而兴的人类聚落。大运河山东段恰置全线中段,尤以山东济宁段“居运道之中”,且运河全线地势最高处地处济宁市所辖之南旺,有“水脊”之称。山东济宁自元代起逐渐成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亦是漕河管理中心与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
在特殊的地形地势与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下,济宁在京杭大运河的运转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城市的发展也随着大运河历史命运的变化而经历了四个阶段:元代至明前期的快速发展阶段、明中期至清中期的繁荣阶段、清末之后的衰落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再利用阶段。明代中叶,海禁甚剧,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南北货物往来的命脉,济宁的发展也随之进入繁荣期。明清两朝,管理京杭大运河治理、运输的总理河道衙门皆设于济宁。“江南之材,从河入漕;山西之材,从沁东下,由济、濮故渠入漕……”四方货物往来,依托运河而以济宁为中枢,济宁成为了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城。明人王通有诗云:“朝天势涌晴天雪,动地声轰白昼雷。万国舟艘皆入贡,五云北望是蓬莱。”彼时济宁商贸、漕运之繁盛可见一斑。随着近代国门洞开,以海洋起家的现代西方文明携坚船利器鱼贯而入,席卷了古老的农耕文化。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在社会生产方式的急速发展变化中,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动荡分裂中,繁荣一时无两的大运河漕运事业在现代航海与陆运的冲击下,渐渐失去其地位。曾经千里无波的京杭大运河河道,也因缺乏修缮而日趋拥堵残破,灾害频仍。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运河的治理才揭开了新篇章。按照排灌、航运综合利用的原则,结合周围天然水域条件,运河很快恢复了航运,并逐渐呈现出新的面貌,发挥起新的功能。
济宁与大运河的命运休戚与共,因运河而兴的商贸、漕运行业孕育出了这座古城所特有的运河文化,并催生出了此地居民世代绵延的独特风气和精神。与孔孟故里曲阜、邹城毗邻,济宁地处齐鲁儒家文化的核心区域,但自大运河开通以来,此地文化风俗便渐渐与儒家文化重义轻利、重耕读轻商贾的传统相迥异。大运河贯通南北,济宁位居其中,“南船北马,百货萃集”,发达的漕运与贸易使明清时期的济宁在城南码头一带形成了长达32 里的发达商业带,店铺鳞次栉比,货品荟萃南北。发达的商业贸易不仅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更使济宁的民风深深浸染了商业气息,在周边儒家文化与农耕生产的包夹中展现出“不贱商贾”的特殊气质。济宁因大运河而产生的这种特殊性,深刻反映在城市人口构成、居民生活方式以及民风民俗等诸多方面。

20 世纪50年代济宁古运河旧照

济宁老城门旧照

济宁竹竿巷旧照
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紧紧拴牢在耕地上,而运河畔以漕运为生的居民,生活则呈现出一定的流动性。与耕种相异的生产方式,使他们沿着运河,或迁徙、或栖居,从而创造了运河两岸丰富灿烂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在农耕文明的大背景中独树一帜。
大运河给济宁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更因人口的流动,让济宁成为不同地域文化的荟萃之地。在建筑方面,明清时期涌现于济宁的各地会馆,将山西、湖南、江淮、浙江等地的建筑风格带进齐鲁大地。制售江南竹器的竹竿巷更以南方样式的粉墙黛瓦,给人以身处姑苏的错觉;在饮食方面,运河之水馈赠的物产、自五湖四海而来的食材、商业经济带来的“食不厌精”的享乐意识、因人口交融而形成的口味融合,以及因漕河运输行业的劳动特点而形成的规律习惯,构成了济宁本地极为丰富的饮食形态。“老鳖靠河涯”等将珍贵水产以复杂工艺烹制的“大菜”,诠释了济宁人“靠水吃水”的幸福;融南方技艺与北方口味于一坛的玉堂酱菜和将沿运河而来的南方大米与北方粗豪的炖肉碰撞出馥郁香气的甏肉干饭,是据地利之便的济宁人味蕾的“特权”;而食用便捷、暖身饱腹的糁汤油饼、托板热豆腐等小吃,不仅为济宁的漕运、码头、商贸、手工业的运转提供着能量,更以独特的吃法记载着历史长河中运河畔的劳动者们在奔忙间对“味”的追寻与对“胃”的犒赏。
自元代起,济宁往来的商贾多非本地人士。大运河上的船帆将来自各地的服食器用、特色物产汇集于济宁,将济宁本地的矿产、粮食、蔬果、棉花等物产经由运河转运至各地,更使来自各地的商人随贸易与运输,或往来奔忙、或扎根于此,进而深刻影响了济宁的人口构成,影响了济宁人的性格与生活方式。与周边如曲阜、邹城人的勤俭、质朴相比,生活在运河两岸、与各地商人长期融合而“不贱商贾”的济宁人,在性格上多了一些因商业文化与人口流动交融而生的灵活、机敏、包容,甚至还带有一丝“狡黠”。而看似“重利”的性格背后,恰恰是流动的大运河与具有流动性的生活方式赋予济宁人的智慧、勇气与活力。迁徙与栖居,构成了大运河沿岸居民的生活状态,而在大运河百年来的兴衰更替与功能转变中,也见证着沿岸居民的生活变迁。
酱园的味道
经营了三百年的中国老字号“玉堂酱园”,是济宁大运河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来自姑苏的戴氏船户,结束了在大运河上贩运行商的生涯,于济宁南门外运河南岸街开设“姑苏戴玉堂”,专售姑苏口味的酱菜。大运河将大量来自南方的商人带往济宁,济宁城繁盛的商业贸易与利于行商的风气,使众多南方商人们迁徙而来,买房置地,栖居于此。戴氏或许正是在济宁的人口流动中看到了苏式酱菜的商机,姑苏的风味可以犒慰在鲁地谋生的南方商人们味蕾上的乡愁,于是,吴地的鲜活滋味随运河而来,留在了萃集南北的济宁。
姑苏戴玉堂的酱菜多是自苏州“潘万成酱园”进货,乘漕运之便,将纯正的江南风味销向栖居于济宁的南方商人的餐桌。但偏鲜甜的口味毕竟难以与北方人的饮食习惯相适应,加之苛捐杂税的负担,使酱园的经营渐趋艰难。地处“南北冲要”之地,姑苏戴玉堂注定要以南北兼蓄的方式在济宁继续发展。1807年,戴氏传人将延续近百年的酱园公开拍卖,济宁本地大药材商冷长连与官宦世家的孙玉庭联手买下酱园,更名为“姑苏玉堂”,开始了冷、孙两家的联合经营。身为药商的冷长连不仅资金雄厚,而且对酿造之道颇有研究。孙玉庭本人则曾官居湖广、两江总督,其所在的孙氏家族更是济宁极为显赫的名门大族。本地富商与显贵的联手,使酱园在经营上占尽地利。而真正使玉堂酱园名动京省、味压江南的奥秘,则在于融汇南北风味之优长、荟集南北物产之特色的酱菜本身。
玉堂酱菜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冷长连潜心深入的研制,更有赖于贴身伙计梁圣铭几十年间对酱菜口味的开拓创新。梁圣铭在冷长连的支持下,致力于南北风味的融合和酱菜式样的开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梁圣铭吸收江南酱菜制作考究精良之长,加之广泛走访学习、研究琢磨,使南方酱菜的精要与济宁口味的地方特色尽入玉堂。在玉堂酱菜融合南北的口味中,既牵动着各方迁徙之人的乡愁缕缕,又蕴藏着结束漂泊而栖居于运河两岸的人们对当下与未来生活的盼望与重塑。通达南北的大运河赋予了酱菜在口味上兼容并蓄的条件;运河商业文化“重利”的灵活精明,与济宁地处儒家文化核心区而根植在济宁人血液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重义”精神相交融,所产生的儒商观念,则建构了玉堂酱园得以长久经营的坚固根基。玉堂酱园生意虽大,本质上却是“一个制钱的买卖,便利于民”。其生存发展之道正是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和优质的产品而成为济宁人味蕾上难舍的情结。也正因为如此,在北洋时期军阀混战、运河阻断的风雨飘摇中,玉堂酱园仍能维系经营,不致衰颓,并在如今盛日中继续生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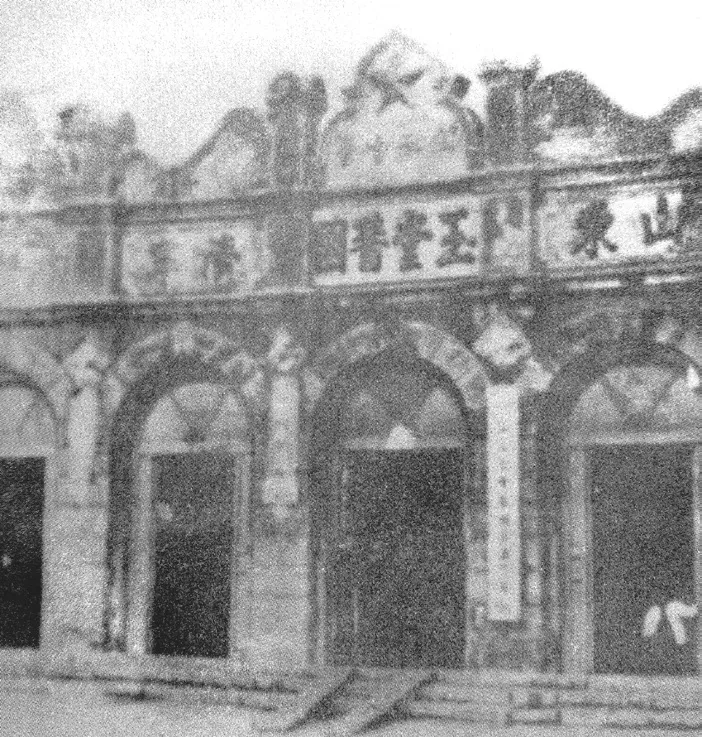
济宁玉堂酱园旧照
“南门外,买卖忙,生意兴隆数玉堂。”济宁民谣中玉堂酱园“生意兴隆”的背后,是济宁人寄托在这座酱园中对大运河文化深挚的情感。300年的玉堂史里,体现着济宁城、运河畔人口构成、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开放和交融,这一切也都诠释着这条大运河与人之间深刻的联系。
孙家的变迁
居住在运河畔的济宁市民孙留成,一直乐于向子侄们讲述他们的家族与大运河之间的渊源与故事。他的姓氏与经营玉堂酱园、在济宁历史上极为煊赫的孙氏家族并无关联,只是众多沿大运河外迁而来、命运随大运河而沉浮的普通人家之一。清道光年间,时值大运河漕运繁忙、济宁商贸兴旺之际,原本世代居于扬州的孙氏“允”字辈兄弟三人,以乘船沿大运河北上贩卖茶叶为生,济宁是他们商贾之行重要的中转之地。彼时已渐趋动荡的社会环境,给兄弟三人带来了意外的灾难。他们的商船在济宁南门外停泊时遭到歹人洗劫并纵火焚毁,幸而逃生的三兄弟失去了生计。或许是不舍昼夜地流动的运河水塑造了他们坚韧的性格与灵活的处事方式,抑或是繁荣的济宁商业环境带给他们重整旗鼓的希望,兄弟三人在挫折中振奋起在济宁图生存谋发展的豪气,与众多迁徙至济宁的商人一样,开始了在运河畔的栖居。具有流动性、包容性的大运河文化总能给善于经营的人更多的机会,孙家三兄弟或经商、或行医,在运河畔各展其才,落地生根。“允宝世延昌,宏德泽厚光,学仁兴广远,诗书传家长。”这是孙家“允”字辈儿三兄弟在扎根济宁后为子孙后代所作的家族排辈,此后,孙家在运河水的滋养下开枝散叶,延续着在大运河畔迁徙与栖居的故事。
孙家在运河畔繁衍至第四代,即“延”字辈时,大运河的发展已由盛转衰。晚清之后,长期的分裂与战乱,一方面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与市场繁荣;另一方面使当局无力对大运河维持有效的管理,河道日渐淤堵残破。此时已在济宁栖居数代的孙家,与众多将命运紧紧系于大运河的济宁人一样,依然凭借着坚韧与勤奋,尽力维持着乱世中的生存。“延”字辈有兄弟二人,兄长颇有经济头脑,在钱庄中供职;弟弟身强体健,在大运河边的坝口粮行从事粮食生意,他的子侄们也多跟着他在粮行中谋生。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剧变,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消解,但大运河仍肩负着中国南北之间粮食运输、中转的古老而沉重的责任。动荡的时局下,大运河带给济宁商业贸易的鼎盛虽已不复当年,但“民以食为天”依然是迟暮英雄般的大运河所坚守的信念。大运河的河道如同衰老的骨架,运河之水如同骨架间饱含着不甘而奔流不息的血液,那些漂泊于运河水面的粮船中、奔忙于运河两岸码头上的人们,则是大运河的细胞,是大运河生命力量之所在。
孙留成是孙家迁徙至济宁后的第六代人,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运河紧紧相依。孙留成本姓崔,他的先祖从中国西部迁徙至济宁,父辈在济宁运河西岸堤口的粮行谋生。1954年,由于家庭变故,母亲无力抚养三个孩子长大,便将仅仅三个月大的孙留成托付给了同院邻居,也就是孙家。孙家不辞生计艰难,视孙留成为己出,他在仁爱的家风与大运河水共同的滋养下度过了运河畔的童年。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运河,在疏浚治理下,河水清澈见底,鱼虾成群。冬夏两季便是运河人家的孩子们最快乐的时节,严冬冰上起舞,酷暑水中激泳,在尚未懂得何为生计的时光中,大运河便在他的心中生出依眷。1972年,摆在孙留成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投身建设兵团,二是招工。命运在冥冥之中为他选择了本来机会渺茫的第二条路。孙留成进入济宁港老码头从事装卸工作,自此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大运河紧密相连。济宁港老码头本身历史悠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重视水利、发展航运建设,1967年,在原址基础上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可进行粮食、木材、钢铁等货物机械化运输的码头。在京杭大运河发展的新纪元里,在众多如孙留成这样的职工的汗水灌沃下,古老的大运河重新迸发出勃勃生机,继续维系着人们在运河畔的栖居。
改革开放后,孙留成所在的码头实现了公司化改革。围绕着大运河的生产工作,与此时整个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一样,涌动着盎然春意。在运河码头的装卸工作岗位上奋斗多年的孙留成,因运河得以安身立命,又因大运河而得遇姻缘。孙留成的妻子与他同在一个公司,也出身于传统的运河人家,住处与孙家隔河而望,父亲曾是参加过革命的运河码头工人。在这对“运河伉俪”身上能看到代代栖居运河畔的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与发展。孙留成在而立之年担任了公司经理与党支部书记,与大运河深切的情感羁绊使孙留成夫妇将振兴运河码头的事业视为人生的信仰与目标。与数百年来大运河发展状况所不同的是,新时期大运河的复兴,其发展成果真切地惠及了“运河人”。从住房等物质条件的落实到社会地位的提升,为运河发展而奋斗的劳动者们拥有了安定富足的生活与前所未有的尊严。孙留成夫妇所代表的新一代“运河人”用半生的拼搏抒写了人们在运河畔新的栖居方式。
随着大运河功能的转型,新的运河河道穿济宁城西而过,担负起水利灌沃、防洪除涝、输水送水等现代功能。曾为济宁带来数百年商贸繁荣的大运河古河道,即济宁人们口中的古越河,其实用功能渐渐消解。此时的孙家人以及无数普通的运河人家,随着大运河发展方向的转变,有的投身于新时期的大运河事业,如孙留成夫妇;有的则随着时代的浪潮,踏上了迁徙之路,这种迁徙对他们来说陌生而又熟悉。他们的先祖多是由外地迁徙而来,在各自宿命般的因缘际会下,以一段段人生建构了济宁与大运河的700年浮沉。例如孙延润之子孙苓昌,是孙家在济宁出生的第五代人。他的童年见证了古越河担负运河功能的最后阶段。河面上的桨声灯影,码头上的往来奔忙,那些跨越半个中国而来的人与物,在他的童年记忆中洒下余晖。1950年,16岁的孙苓昌经过济宁市招干,前往江苏徐州矿务局工作,投入到矿业建设生产中。1966年调往江苏镇江,回到了孙家先辈迁往济宁之前的那片故土。孙家人在扎根济宁的百年后,再次开始了他们的迁徙。直到1975年,孙苓昌为照顾远在济宁的父母,将工作调往临近济宁的兖州矿务局。对他出生在江苏的子女们来说,从镇江到济宁,便是从一个故乡向另一个故乡的迁徙。他们在古运河畔的栖居,已经成为记忆中留下的一道剪影,伴随着百年来家族与大运河的羁绊,在迁徙他乡的岁月中记录着几许温存。
济宁城内的那段老运河河道,载着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依然参与着济宁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建构。与孙苓昌的少小离家不同,他的侄子孙新民、孙建民兄弟自幼生长在济宁,延续着孙家在运河畔的栖居。提起大运河,兄弟二人无法对它的相关数据和历史上的各个发展阶段如数家珍,更多的是一些碎片化的记忆,这些记忆片段也无不与柴米油盐的生活琐碎相关。计划经济时期,食材种类有限,四个小碟分别盛放着青豆、生菜、莲藕、花生米,这是他们春节餐桌上必备的菜品。“清白生财”“通透清廉”的寓意,是大运河两岸商业文化的“利”与儒家文化的“义”交织而成的观念在济宁人生活细节中的投射。这样的习惯被保留到今天,济宁特色的“馓子”被掰碎拌进生菜中,“馓子”仿佛金丝一般的形象与生菜“生财”的谐音配合成一道简单而不可替代的菜肴。每逢春节,它便和另外那三样小菜一起被端上孙家人的餐桌,曾经难得一尝的珍馐在今天已经索然无味,反而是这些小菜的老滋味经得起反复品味,而它们承载的寓意,也被兄弟二人年复一年地向后辈们提及。
记忆的乡愁
如今的大运河古河道,早已卸下了贯通南北漕运商贸往来的社会功能,它为济宁缔造的繁华也在世事变迁中历经沧海桑田。大运河在济宁中留下的物质痕迹,除了古老的河道,就是一些零星的遗存,沿河居民旧日在运河畔的生产生活亦如同隔世。但在世世代代的迁徙与栖居中,机敏与忠厚并存的性格、眷恋乡土又不畏征途的观念、融汇南北的饮食习惯、无数运河人家中代代流传并延续着的家族故事以及家风,这些都是大运河的赋予,形成了穿透时空阻隔的力量,建构着济宁人的精神生活。大运河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文脉,700年来形成的运河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了济宁城古今之间的纽带。曾经商业重镇的繁华与地位带给当代济宁人以骄傲,深厚的历史底蕴更使当代济宁人拥有享受当下与开拓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济宁城中大运河古河道,如同城市精神的纪念碑,它是恒久的,又是流动的;它古老的躯体镌刻着颠扑不破的史实与记忆,同时又因时代发展而不断地变化与生成。当代济宁人对运河文化的开发可谓不遗余力,这既是出于对经济发展的考量,也是决策者对城市文脉自觉地承继。对竹竿巷、太白楼、东大寺、铁塔寺、玉堂酱园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宣传几乎贯穿了济宁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在国家开发“线性文化遗产”和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战略下,济宁对大运河的开发从文化遗产保护、河道水系治理、生态环境修复和文化旅游发展等诸多方面齐头并进。“运河记忆”文化街区、运河水上旅游等项目如火如荼。明清时期设立在济宁的河道总督府,是济宁历史上最大的官府,也是济宁成为“运河之都”的一大标志,在其遗址上建立的河道总督府遗址博物馆即将开放。同时,今天的济宁人也仍然执着于运河畔的商业开发,曾经繁华无两的码头商埠虽已不存,但原址上依然矗立着现代的商业实体。运河古河道当然已经不再是现代商业的命脉,但它所象征的商业精神,成为济宁人现代化建设征程中无法忽略的地标。这种现象体现在众多像济宁一样拥有辉煌历史与特殊城市“符号”的老城中。历史上运河沿线的重镇,比如北京通州、江苏淮安、浙江嘉兴,等等,时至今日亦如济宁一样割舍不下运河文化的情结,进而大力挖掘大运河对当代城市发展的现实意义。相比这些地方,运河文化对于济宁城的影响更具特殊性,它在历史上直接塑造了济宁人的性格与生活习惯,并在当下仍然参与着济宁人精神世界的建构。
京杭大运河作为人工开凿的生产资料,它的发展与命运都与人息息相关。自元代全线贯通以来,700 多年的大运河史,不仅仅是冰冷的文本资料或物质遗存,也是一代代人围绕着运河迁徙与栖居而书写的故事。人开凿了运河,运河承载了人的生活,而人的生活历程则赋予大运河以生命温度。文本中的寥寥数语便能概括近百年来大运河发展的兴衰沉浮,而透过宏大的历史叙事,细微处是人们在大运河畔漫长的朝朝暮暮。今日的古运河河道,不仅是穿城而过的水域,更是一片面向济宁市民的、活态的公共空间。一方面,古河道见证着济宁因运而兴的历史,承载着济宁一脉相承的城市精神;另一方面,古河道凝聚着沿岸居民的运河情结,记载着他们围绕运河的生活记忆。对于生长在运河人家的人们来说,那条流淌在他们记忆中的运河,与他们过去的人生经历相交织;这条留存在身边的河道,则象征着滚滚时代浪潮下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当下生活。面前的河道与心中的运河,一条由当下流向未来,一条从眼前流进记忆深处,编织成济宁人的现实空间与精神世界。他们碗中的甏肉干饭和酱菜还是运河畔的老味道,抬起头,这座城市以及他们的生活,正在日新月异地向前推进。运河文化的延续就如同这条古河道,融进人们平凡的生活,既因眷恋而连接过去,又因发展而通向未来;既在恢弘的战略项目中踏步向前,又在琐碎的人间烟火中生生不息。对于济宁运河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或许还有一些启示,就藏在沿河居民世代迁徙与栖居的故事里,藏在今天生活在运河畔的济宁人柴米油盐的生活细节里,也藏在迁徙至他乡的人们因运河而牵动着的乡愁里。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土生土长、乡音不改的老济宁人乔羽先生,乘火车途经长江时收获灵感,写下《我的祖国》里这句经典的歌词。他最初将这首歌词定名为《一条大河》,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条大河”在心中流淌,这条“大河”不仅是象征着民族的长江黄河,也是故乡家门口的一条小河。老家济宁的运河,便是他心中的“一条大河”。这条河载着岁月挪转而南去,在百年间的兴衰更替中,看惯了人们迁徙与栖居间的生活变迁。而今运河畔的人们,或怀揣记忆与希冀依旧栖居于此,或带着水声中的乡愁,踏上新的迁徙之路。而旧貌换新颜的古运河,又因割舍不断的文脉和与时俱进的功能,吸引着更多的人,将生活与事业寄于大运河的水光潋滟中。
注释:
[1](明)于慎行编: 《风土志》,《兖州府志》卷四,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