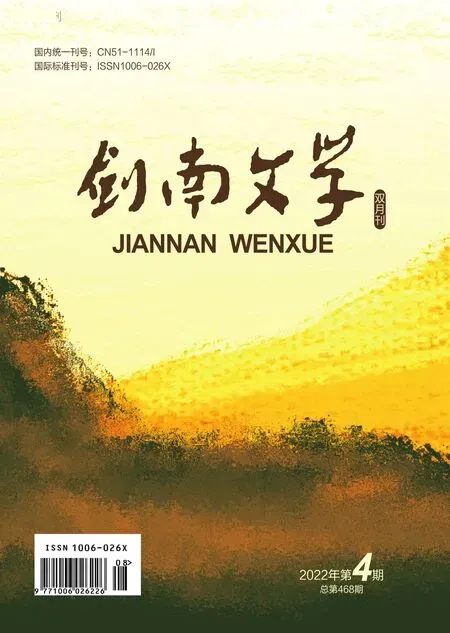石滓:一个狭小地区的备忘录
□彭成刚
一、是不是越小的世界里,人的生活目标越清晰?
或许,这就是我们的童年常常在成年之后出现在梦中的原因,同时也是在我们日益充满重要事务的中年偶尔得以回忆起一些无关紧要的童年场景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最近几年,我越来越愿意把童年的许多事物交给石滓,仿佛它是一座记忆的仓库,至少有几千个熟悉或陌生的人仍然在守护着。然而,我真正想回忆的事物在距离石滓大约七八公里的陈家沟——通常意义上被称为老家的另一个地方。这两者在地图上几乎无法分辨,这一带没有什么重要的工厂和设施,也不是什么交通要道,历史上或将来也没有什么重要人物诞生——没有任何公共标记大概是对它们最好的待遇。
比如出生在陈家沟的人如果不走出陈家沟的话,一定会把陈家沟视为宇宙的中心。根据肉眼观察,陈家沟确实具有成为宇宙中心的种种客观条件。在念小学之前,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小孩子能够轻而易举地感受到在人类久远的年代里那些聪明人所拥有的骄傲和荣耀——地理位置上狭隘和逼仄在给人的生存提供安全感之余,通常也提供了成为宇宙中心的全部物质资源。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天似穹庐(更似厨房里的锅盖),星辰如山路行人手里摇晃的马灯。夜里的星辰米粒般沉落在水井之中,从未有人在井水之外能够获取一丁点儿星光。太阳东升西沉,绕着陈家沟的上油坊湾的几座破烂的房子转,从未因为刮风下雨改变过这种方式,这至少说明了陈家沟的几座老房子有一种吸引宇宙物质的能力。
最奇妙的是春天和秋天的傍晚,月亮从麦田和稻草之后的山丘升起来,然后跟着山丘回家的人逐渐下沉,到了沿河的平地,牛羊的影子几乎贴着河滩,小孩子不用抬头,月亮就落在肩头上了。小孩子惊慌失措,一奔跑,月亮也奔跑。一暂停,月亮也暂停。在河里洗干净裤腿上的泥浆的成年人不慌不忙地走路,月亮也不慌不忙地走路。
一个小孩子为月亮和自己的影子发怔了。
二、为何月亮不放过乡下的任何一个好奇的小孩子?
一路狂奔回家,紧闭门窗,一个小孩子才获得相对的安全感。若是一个院子成为宇宙的中心,一条峡谷自然也是宇宙的中心,而相隔七八公里的石滓却不是宇宙的中心。这个秘密要等到我背着行李包到镇中学读初中之后才发现:石滓的沦陷几乎是陈家沟的沦陷,一个小孩子的人生也是在沦陷之中开始成长的。
在石滓,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够代表宇宙中心的事物,这一伟大发现在引起我私人的一阵失望之后,又引起我私人的一阵狂喜和欣慰。在靠近镇东南方的场镇口子上,一口名叫御河井的沙井曾给予我极为甘甜的味觉。在自来水出现之前,每一口井都带着天然的特征。
首先是位置,要么在岩石底下,要么在稻田中央,要么干脆在河岸。每口井的井水的味道都各不相同,有的带着土腥味,有的带着砂砾味,有的带着青蛙和蚯蚓、癞蛤蟆味。御河井的井口全是黄色的沙粒,井水仿佛是从众多的沙粒中渗透到地表上来的。
上世纪70 年代,御河井里有好心人丢了一柄木瓢,那木瓢一直漂在水面,走路口渴得不得了的人便俯下身子,捡起木瓢舀起一瓢水咕噜咕噜往肚子里灌,直到五脏六腑都极舒服才赞不绝口地离开。下一个人又来了,如法炮制,久了便成为御河井的一大风俗。然而,我喝的第一口御河井的水却是在一个大人的手掌里盛着的,记不清那人是谁了,反正那人没拿到水瓢,直接用手掌掬水,掬的力气足,喝的力气也足,饮水的声音增添了御河井的风俗味。
御河井是石滓的一个点,可能与石滓的地名有一定的关系。石滓的通俗说法就叫石滓滩,在大洪河和东河交汇处,据说水深两丈,船夫用竹竿撑不到河底。这里不仅水深,而且水域宽广,波光粼粼,蔓延至两岸,则是金黄色的松软平细的沙滩。石滓,即砾石被水磨而不灭形成的浩如星海的细沙世界也。从地质构造来说,御河井与石滓滩都是广义的石滓,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一致,品相一致。只是我们对滓的联想不大美好,总是容易想起渣滓这个意思,后来改为石子,大家便觉心安理得。而石滓滩的名义,则落到大洪河下游的邻水县的某个地区的老百姓去享受了。
现在,我们不得不以一个孩子的视角面对一条大河。俗名叫石滓大河、长河,而书名十分伟大,叫大洪河。另外,它还有一个雅称:御临河。其得名估计与某个皇帝有关,但落到老百姓口中,又是一个俗气的名字:玉麟河。
我在想,如果石滓没有紧邻这么一条河,也许我们的记忆之中就少了一个重要的坐标了,许多事物也无法记录下来。相对于御河井,御临河就是一个广泛展开的记忆平面,有关它的许多事物可以无穷无尽地演绎下去。我相信某些词语就像人的干细胞一样可以产生巨大的繁殖能力。在童年,石滓就算是其中的一个。
1975 年左右,石滓所在区域发生比较严重的旱灾,大洪河的两岸耸立起了无数巨型的生铁水管,还有专门用于安置抽水泵的小房子,那是我们童年用以辨识石滓镇的最重要的标记物。巨大的生铁水管直插大洪河底,像一个神秘莫测的水生怪兽,而它的赤裸裸的脊背和骨骼是光滑而温顺的。我们双手抱住它,小心翼翼地翻越而过,然后才放心大胆地抚摸它,察觉它具有豢养动物的习性。
在靠近石滓镇的河岸高处,一只银灰色的变压器缠绕着众多铜线的瓷壶,它构成了我童年时期最为神秘的工业制造和生产的意象,然而,它不属于石滓,它只是把石滓变成世界的无知的边缘,引起我内心的惊悸和恐慌。直到那个时刻,我还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物质叫电,一种抽象得无法理解和想象的事物。在石滓下游的高洞电站,蓄水坝蓄积的水像巨大的玻璃镜子横亘在大洪河上,它像是大洪河的一个奇怪的化身,没有人亲自看见电是怎样从水变成的。只是水坝下轰鸣的瀑布声像蛮不讲理吵架的农妇一样干扰了我们的可笑的思考,而水坝旁边更是有银灰色的变压器和缠绕着铜线的纯洁无比的瓷壶重复了电在石滓隐没的奇迹和疑惑。
1978 年,我和表叔一起到区供销社和区公所的楼房里去与几十个人一起挤着看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第一次知道了电视里也有新闻,与桉树上颤抖的高音喇叭一样,连乐曲也是一模一样的。
1980 年代,我背着行李包来到石滓,作为全区优选的两百个学生就读区中学。九月的第一个周末,我迫不及待往家里奔跑,在御河井旁边的沙地上遇见表叔在扯花生,我便打着帮忙的旗号一边从沙地里扯花生,一边摘生花生吃,不一会儿,肚子胀鼓鼓的,就觉得花生没那么好吃了,帮忙也没什么意思。表叔说:吃了生花生,不要喝御河井的生水哈,不然,屁股会打标枪的哟。我不相信,硬生生喝了半瓢御河井的水,然后借故回家,一路奔跑一路胃里哐当哐当是御河井的水在晃荡,一路打标枪,回家时,早已是腿软头晕了。
三、入学第一周,我仿佛提前过完了我在石滓的一生
秋高气爽的石滓滩,砖瓦房围聚而成的一所学校燥热无比,尤其是宿舍和食堂,两个最拥挤的场所,一个陌生人靠近的感觉就像一个摄氏四十度高温的天气。十人一桌分一面盆蒸饭,饭的表面有一层硬壳,号称水碱,我猜那是大洪河的杰作了。硬壳当然是不能吃的了,用筷子挑到潲水桶,碗里只剩了少半米饭。而米饭里有一种红色的豆子,蒸熟了,豆子像伤口一样流出鲜艳的血液来。我捧着碗,蹲在墙脚,一边吃,一边掉眼泪。我在想陈家沟里吃的饭,红苕、南瓜为主,米饭只有几粒,仅仅是装饰用的。然而,学校的米饭再多,我也没兴趣吃,每天只是想回家。比如,我端着一碗红苕,红苕不好吃,我就狠狠地掀一个在尘土里,家里的猛犬立即欣喜若狂地扑上去,也顾不了发烫,一骨碌吞到了肚子里。一碗南瓜饭也是,鸡吃一口,鸭吃一嘴,狗咬一下,哪怕是苍蝇也嗡嗡嗡嗡跟着嚷嚷。我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吃饭场景,学校里吃饭的人太严肃了,好像做数学题,必须有一个标准答案。
好在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街上店铺蜡烛和手电筒不够供应,我们的大多数夜晚是坐在教室里胡思乱想,有时候老师觉得我们太无聊了,便放我们回寝室睡觉,这样,我就可以在梦中高高兴兴回家了。下午的时候,我们端着搪瓷盆,到大洪河端水回宿舍洗脸洗脚,水里有绒绒的、滑腻腻的苔丝,有时候还缠绕着死鱼烂虾,水里漂浮着河蚌的腥臭味,但并没见到河蚌的尸体,这就奇怪了。
有个晚上,我们几个同学对御河井特别感兴趣,便偷偷拿了面盆去舀,结果碰到表叔和他的小伙伴到街上看电视回家,相互之间先是发生口角,接下来又是肢体冲突。表叔打赢了,他们趁着地形熟悉,一溜烟跑了。我的一个同学的兄长是学校的老师,在全校借了十来根手电筒,晃荡晃荡,去找村民算账。其实,不过是虚张声势,把许多院子里的狗惊动了,许多乘凉的农民弄醒了,一个打人的孩子也没找到。表叔说,他打了招呼,不然,我要被打惨。也许,这就是亲戚和熟人的好处。
我到石滓的第一周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返回陈家沟,家里人都喜欢听我讲新闻,而对我的学习成绩反倒没怎么关心。我用从学校捡回来的两节旧电池,加上私下去供销社买的一颗两分钱的小灯泡,以及在学校教室的角落捡来的电线,一个下午,一个晚上,我一直在尝试着亲自设计一个手电筒,我要让手电筒在陈家沟里发光。在家人带着我讲的新闻入梦之后,我偷偷摸摸还在做一个让灯泡发光的实验,终于,在夜半时分,实验成功了。
在陈家沟的土墙房子里,在九月的炎热天气里,那个曾经给予我宇宙中心印象的陈家沟竟然会因为一颗灯泡发光的问题让我陷入手忙脚乱的状态。陈家沟也不是没有电,它拥有的电是天然的——转瞬即逝且不可控制——带着极大毁灭力量的震耳欲聋的事物只能令人望而生畏。从这个角度而言,石滓镇的电给予人的感觉是安全的——比如我安静地坐在土墙下倒腾了大半夜才把一颗小小的灯泡弄亮了——我的父母对我的学习是极为放心的(可以想象区中学的电所释放的光也会让我安静地看书做作业),他们劝我不要太用功了。在过去的无数个夏夜,陈家沟漫天飞舞的萤火虫也让我对电这种事物浮想联翩,萤火虫屁股闪闪烁烁的光线暗中仿佛连接着一个神秘的世界——夏天电闪雷鸣的天气或秋天夜空中幽暗不明的浮动的光明,然而,它们到底还是有着天然与人工的巨大鸿沟。
四、宇宙的中心应该是人工的还是天然的呢?
在陈家沟,我虽然小小年纪但已经体验到了人工的种种艰辛,而那时候,我以为天然的才是最符合人类心理需求因而也是最符合宇宙运行规律的。
比如,在陈家沟的大坡寨半坡上,有一块巨石突然遭到雷劈,像房子那么大的石头竟然一分为二,整整齐齐,仿佛斧头劈开的一样。只有亲眼一睹,才会惊叹雷劈石不是随意的偶然的人类事件,而应该是代表着某种不可克服的力量在执行强大意志的行为。然而,由于认知手段和视野的局限,人类永远也无法知道其中的奥秘。
1974 年,吉星公社邻峰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社员们在盅盅坡参加集体劳动的时候,在地边搁着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里面播放着断断续续的噪音,偶尔混杂着一段清晰的东方红乐曲。作为儿童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把收音机的外壳给拆了,但收音机依旧在咿咿呀呀地唱歌。生产队的一位老太婆坚持认为有人躲在收音机里唱歌——直至我把收音机拆到不发出任何声音为止——她的观点不能被任何人改变。是的,电确实是在以不同的介质执行某种力量和意志,老太婆相信收音机里躲着一个人唱歌,这种观念比不相信里面有人要好得多——至少不会有私自拆毁收音机的行为发生,作为儿童,采取行为也许正是深信不疑的一种必然趋势。
等到我们习以为常或者懂得了电的原理,我们把收音机当成收音机,这才是可怕的一个局面。
我的童年是在震耳欲聋的雷声中度过的,陈家沟的电量可真充足得很哪——我的耳朵——我的肉身第一次遭受这来自宇宙深处的力量的冲击,我获得的听觉有着比人工声音清晰和强大一百万倍不止的记录——不过,由于声音的局限,这些记录转瞬即逝——仿佛它们并不存在或从未发生过一样。当我经历了太多的声音,尤其是人工的声音——锅碗瓢盆吃喝拉撒喜怒哀乐这些俗世的信息一次又一次重复——它们从老生常谈变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声音的空壳,我的听觉自然衰退了不少。
在石滓,人工的电花样繁多,比如收录机——就是一盘孱弱的磁带周而复始地转动,一个人的声音便释放出了繁殖的欲望——满世界都是这个人的声音。第一次,在最初的工业化场景之中,我们产生了一种非常富饶的幻觉——我们生活在一个声音的海洋里,声音的海浪把我们贫乏的灵魂和营养不良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冲刷向花团锦簇的形而上世界里——歌曲是这样平衡我们的肉身和灵魂的,声音只是在形而下的世界里进行声势浩大的运动,而词语则在形而上的世界里象征永恒。
石滓的空间狭小而肮脏,从教室到公厕、宿舍再到食堂,每个角落里,我们的身体都因为发育和生长而自我膨胀。低矮的屋顶,密不透风的四壁,散发着霉臭味和尿骚味的走廊,永远有一股潲水味的食堂——没有洗澡的地方——我们的身体自然带着一股汗馊味。到了春天三四月间,宿舍里到处是瘙痒的声音,抓破皮肤的感觉比抓破窗户玻璃还难受——一种极端的异痒——有人说,这让人昼夜难眠的玩意儿是一种传染病。
不到一个月,整个学校的男生都感染上了一种名叫疥疮的皮肤病。在不断升温的四五月,疥疮之痒如烈火烹油之势在石滓蔓延——我的个天哪,连我最敬爱的老师也患上了疥疮——上课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瘙痒。我最敬爱的老师充满了正义感,他经常抨击社会上那些不正之风,后来,他又扩展到对历史上那些丑恶现象的抨击,遇到无可抨击的内容了,他开始抨击全人类的问题了——我以为这个疥疮对他的授课方式是一种完美的助攻——每每说到激动之处,他便毫无顾忌地在讲台上伸手瘙痒了,而一大群纯洁无比的孩子对此浑然不觉。
五、疥疮嘛,于我心有戚戚焉
我本来是个痴迷于读小说的贪玩学生,没想到也感染上了疥疮。疥疮的痒不在白昼,不在人多处,恰好发生在人烟稀少的时刻——比如我听数学课不认真,老师突然点我的名——数学难题折磨我的时候,疥疮的痒便是火上浇油了。
我的同桌挥舞着圆规,用最尖锐的一端猛刺自己的额头,一时间鲜血淋漓,只见他呻吟着,嚎叫着,突然间他大笑起来,原来,他把答案弄出来了。有些时候,他也不是那么夸张的,他只是小心翼翼用圆规的针尖把疥疮溃烂结痂的部分剔除,没有痛苦,只有恐惧——他瞪大了眼睛,注视着结痂部分脱落之后新生的皮肤——像婴儿一般红晕,他有些痛苦了。继续用圆规的针尖挑,新生的皮肤破了,一层血珠子沁到手指上,红艳艳的,像握着一簇花。又过了一些时刻,血珠子凝固,他又继续用圆规的针尖挑,居然挑出一层皮,这次没有流血了。这种惊心动魄的场景让我把人的身体想象得像一枚藠头或一颗洋葱,从外到内都是一层一层的皮裹在一起的。然而,数学的学习是没有止境的,而人的皮肤层数是有止境的。
医生说,必须注射治疗,不然,会有较大的麻烦。我请了假,每天三次到区医院注射一种杀菌的液体——不知道这种注射治疗有没有效果——我只是注意到了那个硕大无朋的针头,那可是给一头水牛注射使用的呀,我的小小的身体,我的小小的血管,不堪一击。可谁也没想到,端午之后,全校的男生疥疮奇迹般地消失了。
端午之后,大洪河进入汛期。洪水一次又一次让大洪河名副其实——波澜壮阔又深不可测。我的体育老师是个二杆子,我们在太阳底下上什么体育课嘛——女生站在树下吹凉风,男生站在太阳光里瘙痒——鲜血淋漓,痛中有快,体育老师直呼爽爽爽,然后,他脑洞大开,突发奇想:老子们何不去大洪河游泳?他这一说让男生们如脱缰的野马,一窝蜂狂奔到了大洪河。哐哧哐哧,哐哧哐哧,哐哧,哐哧……男生们一个个变成了青蛙,直接飞进了大洪河,好不舒服呀!
作为一个旱鸭子,在众人的激励之下,我也哐哧一声,直接蹦进了大洪河——在洪水的冲刷下,在砂砾和泥浆的裹挟之中,疥疮的痒实在算不了什么——我踮着脚,在河边的浅底上一跳一跳,毫不费力地遨游着,欢呼着,全然不知道即将发生的危险。大洪河的河边是不规则的砂土,细细的,柔柔的,简直像虚无的云团——我一脚踏空,一下子沉入一个深坑——屏住呼吸,我才浮上水面,然而,我一慌张,竟然又重新跌进深坑,这一下子,我没法再屏住呼吸往水面浮了,而是大口大口喝了一肚子浑水。一着急,我拼命招手,但见同学们个个笑逐颜开,似乎在为我精彩的表演摇旗呐喊。我只得拼命挣扎,竟不知道是怎么攀附上岸边的一个大石头,用尽全力爬了上去才脱离险情的。我瘫坐在砂土上,肚子胀鼓鼓的,想把刚才灌进胃里的脏水吐出来,但实在吐不出来。另一方面,我的耳朵也灌水了。我的二杆子体育老师依旧和他的幸运的学生们在大洪河里嬉戏游玩,完全忘掉了疥疮的痒。
六、在一群幸运的傻子之中,我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
就在大洪河中这么惊险一游,我的疥疮就消失了。
我们班的男生的疥疮也消失了。不久,全校的男生的疥疮也消失了。
我最敬爱的抨击社会不公的那个老师的疥疮也消失了。
然后,石滓的学校发布了一个公告:严禁师生私自下河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