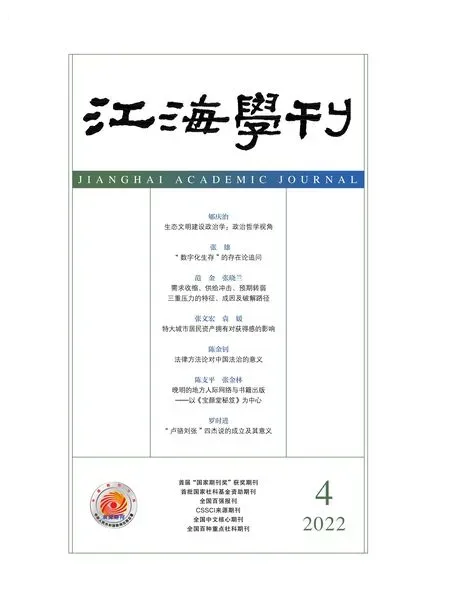孔门传经弟子的形象重塑与清代经学转型*
——以子夏为中心
赵四方
在明清学术思想转型的过程中,汉唐经师渐为儒者所推崇,与汉唐经学有着内在传承渊源的荀子的地位也发生明显改观。长期以来,围绕荀学复兴及其与清代经学之间的关系,学界已积累了较为可观的成果,(1)参见马积高:《荀学源流》第十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田富美:《清代荀子学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康廷山:《清代荀学史略》,中华书局2020年版;孔定芳、朱冉琦:《荀学复兴与清代学术转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9期等。但倘若由荀子而上溯,我们会发现孔门传经弟子在清代的形象变化,一直是一个缺乏足够关注的重要课题。作为孔门传经弟子的最主要代表,子夏在清儒笔下反复出现并受到大力尊崇。以子夏为中心来考察孔门传经弟子的形象重塑,或可从一个侧面揭示清代经学的特征与底色。
重建孔门“学统”:清初推尊“七十子”的思潮
清代初年,治学以朱子为宗的江南儒者陆世仪在回答弟子“道统”之问时说:“道统重闻知,不重见知。”(2)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二九《诸儒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0页。以他之见,孔门弟子虽亲见孔子,但从道统而论,这些“见知”者实不可与“闻知”者孟子相提并论。陆氏所谓闻知,乃是“无师传而有开辟之功者”。(3)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三〇《诸儒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第280页。在他看来,这一渊源于《孟子》末章的说法正是道统论的思想根基。钱穆称陆世仪为“宋明道统殿军”,(4)钱穆:《陆桴亭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正是从这一论述着眼。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正处于深刻转型时期,总体来看,陆世仪的观点与当时的主流趋势颇有疏离。从其他学者言说“道统”的语境来看,该词的涵义正在趋于泛化。阎若璩说:“韩文公之婿李汉为文公作集序,止称门人而不称婿;朱文公之婿黄榦为文公作行状,止称门人而不称婿。古人重道统而轻私亲如此。”(5)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第393页。这实际是在讨论传统所言的“学统”,而并非“道统”。理学名臣熊赐履重构先秦至明末的儒林谱系,虽极力捍卫自孔、颜至程、朱的道脉,却以“学统”命名其书。其弟子对此解释说:“道之存亡系乎统,统之绝续系乎学。学统即道统也。”(6)熊赐履:《学统》附周铭跋,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页。表明狭义的“道统”观念正在受到“学统”的渗透。另外,据近来学者研究,朱彝尊笔下的“道统”也绝非程朱理学之说,而是近于“以六艺为中心的学统”。(7)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中国文化》2010年第32期。因而可以说,“道统”在清初儒者心中已逐渐变为一种较宽泛的学术传承关系,它原来所特指的那种以道自任者“不由师传,遥接圣脉”的意涵正在消逝。
这一观念领域的变化可以追溯至晚明。(8)参见邓志峰:《王学与晚明师道复兴运动》(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3—236页。《续文献通考》的撰者王圻提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此道,则斯道之统不可一日而无传。”(9)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九八《道统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在这一思路下,汉唐经师自不必论,身处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孔门弟子也获得了被重新审视的契机。王圻在《道统考》中就明确将孔门诸子列为“翼统先贤”,并较详细地考察了其中数十位的生平言行。大致同时的钟天完,更是以孔门弟子来质疑孟子在道统中的合法性,他说:“夫谓孔子传之孟轲,则孔子时亲受业诸贤,若颜之四勿、曾之一贯、子贡之超悟、子思之精微,岂皆不得与孟氏埒乎?即他如仲弓、闵子、南容、子贱……岂其皆出孟子下乎?……此七十余纵不皆颜、曾,岂不人人关闽而濂洛哉?”(10)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七《道学》,《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68册,第144页。钟氏将七十子与孟子对举,认为前者非但在传孔子之道上不亚于后者,而且比宋代的道统传人更具有亲见圣人的天然优势。若以前文陆世仪所说的“见知”“闻知”之别而论,钟天完显然认为“见知”重于“闻知”。置于明清思想转向的背景中,这一论调可以说是清儒以“孔门学统”质疑并挑战“孔孟道统”的学术先声。
既然道统观念已走向衰退,那么何处是道?重新回到孔门是否为一条可能的通途?七十子的话题之所以在清初逐渐由隐及显,应当说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背景。朱彝尊是清初学者中推崇汉唐经师最力的学者之一,同时也是考证孔门弟子最主要的开风气者。朱氏曾撰《孔子弟子考》,通过博采群籍,共考得98人,详列姓名、籍贯及历代封号。在其观念中,弟子谱系的完整性居于首位,因而在标准上宁宽毋漏。例如前代多认为申枨、申党只是转写之异,但朱氏力辨二者并非一人。再如公伯寮长期以来饱受非议,朱氏却说:“后儒以(寮)愬子路一事,断为非圣人之徒。然《论语》圣门六十人所记,公是公非,有过未尝少隐,即宰我、冉有、陈亢过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尽掩其生平也。子长引孔子之言‘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寮盖其一矣。”(11)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六《孔子弟子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第277—278页。朱氏还在《经义考》中述《承师》五卷,专考经学史上的师承关系,他批评前人论述经学传承往往“挹其流而未探夫源”,而真正的起点正应是“自仲尼之徒始”。(12)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八一《承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0册,第600页。
除《孔子弟子考》外,朱彝尊还特撰《孔子门人考》。朱氏认同欧阳修所说的“受业者为弟子,受业于弟子者为门人”,并据《论语》文本中的多处“门人”予以论证。《门人考》共录孔子再传弟子31人,在标准上亦略显宽松。如朱氏怀疑公祈哀即公皙哀,但又认为“《广韵注》既列孔子弟子公皙哀于前,又列孔子门人公祈哀于后,则别是一人,未可臆决也”。(13)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七《孔子门人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第289页。尽管未能考定,仍列入门人之中。另需注意的是,不论《弟子考》《门人考》有何缺陷,在朱氏以后,至少有惠栋、全祖望、王鸣盛、赵佑、郑珍、陈澧等一大批学者,都参与到门人究竟是弟子还是再传弟子的讨论中来。他们无一例外地以朱氏之说作为讨论的基点,表明朱氏确实提出了一个相当能反映时代学风的话题,而且影响非常深远。(14)除惠栋外,其他诸人均反驳朱氏之说,认为门人与弟子所指相同。不过从这一问题的反复辩难也可以看出,清代学者尤为关注师承关系。这本身就是学统观念复兴的一个表现。
以史学著称的万斯同是可以说明这一思想动向的另一个例子。《儒林宗派》将孔子至明末的学派传承以史表予以呈现,其中在孔子之后谱列弟子84人,唯载名、字与籍贯。与朱彝尊考订“门人”的做法类似,万氏还谱列“诸儒传考”三十余人,以展现孔门后学的发展状况。(15)万斯同:《儒林宗派》卷一《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第521—525页。对于该书的撰作因由,四库馆臣说:“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流毒无穷。斯同目击其弊,因著此书。”(1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史部传记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28页。万氏以“学统”取代“道统”,不仅注重汉唐经师授受源流,而且肯认了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重要地位。与万氏大致同时,史学家马骕在《绎史》中专设一卷考察“孔门诸子言行”,(17)马骕:《绎史》卷九五《孔门诸子言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67册,第137页。表明在清代学者看来,七十子作为一个群体在上古至秦代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清初广东学者陈遇夫对七十子及其后学的关注与此不尽相同。他并未详考孔门弟子的具体情况,而是从汉唐经师渊源的角度进行讨论,因而在方向上与朱、万、马三人殊途同归。陈氏《正学续》旨在“续正学”进而“续道”,但刻意避开道统谱系,不录孔孟与宋儒,只录由汉至唐的27位经师。至于从汉代开始的原因,陈氏说:“自七十子之徒以至思、孟,以迄于秦……其时以六经为学者,如檀弓之《礼》,左氏、公羊氏、谷梁氏之《春秋》,及公明仪、乐正子春之属,见于著论,学士家类能言之。若其行事,皆不可得而考也,故叙述诸儒,特自汉始。”(18)陈遇夫:《正学续》卷首《论略》,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陈氏深晓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的重要意义,只是由于文献不够翔实,才从汉儒开始“续正学”。康熙年间的陈启源则从《诗经》学角度提出,时代先后应是检验经义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他认为魏晋隋唐“去古稍远”,“宋元迄今,去古益远”。(19)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册,第334页。汉儒之所以需要特别重视,就是因为他们学有师承:“汉世近古,先王礼教犹存,诸儒皆七十子之徒,渊源有自。”(20)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二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册,第645页。这种通过师授渊源而将七十子与汉儒相连接的做法,代表了清初很重要的一种学术取向。
在推尊七十子方面,蜀中儒者费密也许是立论最为深刻系统的一位学者。较上述诸人更为激进,费密公然对道统进行批判:“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门人亦未言,百余岁后孟轲、荀卿诸儒亦未言也……流传至南宋,遂私立道统。”(21)费密:《弘道书》卷上《统典论》,《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46册,第6页。以相当决绝的态度揭示道统只是出于宋儒的私见。对于孟子,费氏更是大加质疑:“孔子传七十子,承以曾申……曰孔子传之孟轲,七十子与曾申诸贤将不堪比数耶?”(22)费密:《弘道书》卷上《道脉谱论》,《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46册,第16页。与前引钟天完的主张如出一辙。但费氏不仅批判道统、质疑孟子,同时也质疑曾子、子思,说:“圣人于道,未尝有所谓教外别传也,七十子共传之……曾氏独得其宗,古今安有是言?《大学》非曾氏所述,子思、孟轲远不相及,无所授受。”(23)费密:《弘道书》卷中《先师位次旧制议》,《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46册,第31—32页。可以说,费氏深入系统地质疑了韩愈、宋儒建立的道统谱系。
费密对曾子、孟子的质疑,实际上是为表彰七十子张本。依费氏看来,孔子将道传至七十子,其后传至汉唐儒者,“如父于子,子于孙……悠久至今,成为道脉”。(24)费密:《弘道书》卷上《道脉谱论》,《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46册,第12页。不同时代儒者间的关系就如同树木之根、枝、叶,“后世之儒,条叶丰茂而已。非根不深,非本不成,非柯非枝不盛。受雨露而滋养者,条叶也”。(25)费密:《弘道书》卷上《统典论》,《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46册,第6页。准此而论,即使宋明儒者“条叶丰茂”,离开七十子也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费氏还将七十子视作大国齐、晋,后世之儒只堪比滕、薛。上述种种观念都指向七十子较后儒更具权威性,而其根基就在于“七十子身事圣人也,见全经也,三代典制存也”。(26)费密:《弘道书》卷上《道脉谱论》,《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46册,第17页。正是因此,费密不仅提出孔庙应祀全部七十子,而且主张“七十子之后,士大夫宜奏访其嫡派苗裔,充五经博士之典”。(27)费密:《弘道书》卷中《七十子为后一例议》,《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46册,第34页。在晚明以降的学术史上,费密对七十子的推崇可以说达到了前所罕见的一种高度。
大致而言,理学背景愈深厚者,思想中保留道统论孑遗愈多,如陆世仪、熊赐履、汤斌、张伯行的著作皆可体现。但即使如此,清初理学家也多会面临如何定位七十子及其后学的问题,由此正可觇见当时的学术风气。熊赐履将颜、曾、思、孟列于“正统”,将闵子骞、冉雍、子贡、有子、子游、子夏列于“翼统”,而将其他十数位孔门弟子归至“附统”,代表了最为接近宋明儒的一种意见。但熊氏十分肯定子夏及公羊高、谷梁赤的传经之功。稍晚的李光地提出,孔庙应专立“及门之祠”与“传经之祠”,前者祀七十子,后者祀历代经师。(28)李光地:《榕村集》卷二一《文庙配享私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4册,第822页。表明官方理学家也特为关注七十子及传经之儒。此外,潜居不仕的理学家应谦提出,两汉、魏晋及唐皆有“道统”可循,他在叙述七十子至汉初的经典传承时说:“六经之垂亘于天地,当未立学官之时,数百年间,无在上者荣以利禄,而诸儒笃信而死守之。师承渊源,不忘所自,今除湮灭不可考外,载之于篇,以示不忘先农先炊之意。”(29)应谦:《性理大中》卷二《传经诸儒》,《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49册,第403页。表明学统观念在朝野理学家那里都已露出了端倪,这与对七十子及历代经师的重新认识有着很深的关系。
从“得其一体”到“圣学正宗”:孔门传经弟子在清初的形象重塑
这股推尊七十子思潮之所以在清初产生,有一个直接动因,即学者不满当时的孔庙祀典,而寻求合理的更革方案。自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祀典更定后,一批原先从祀孔庙的儒者或遭到罢祀,或改祀于乡。从增减状况而言,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确立了传道之儒的地位,同时“贬斥(甚至否定)汉唐的传经之儒”。(30)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及至清初,伴随学统观念的兴起以及对汉唐经师的重新认识,这一孔庙祀典引来了巨大反动效应。顾炎武依据贞观年间以左丘明、子夏等二十二人从祀之事,批评嘉靖祀典更革是“弃汉儒保残守缺之功,而奖末流论性谈天之学”,并慨叹“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顾氏原注说:“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创业者也。二十二经师,助其垂统者也。”(31)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四《嘉靖更定从祀》,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770页。这一声音代表了当时遍及朝野的讨论意向。
在孔庙祀典上,清初学者的努力方向之一正是重新恢复七十子整体的从祀地位。这也就可以解释朱彝尊等人何以那么在意孔门弟子谱系的完整性。朱氏曾有一组题为《斋中读书》的诗,其中说:“后儒不晓事,吹毛务求疵……云何七十子,一眚罢其祠?何年复旧典,俎豆敕有司。”(32)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二一《斋中读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7册,第630页。明斥嘉靖更定祀典之人太过严苛,求全责备。对于秦冉、颜何等孔门弟子,明儒疑为附会而罢祀,朱氏据《仲尼弟子列传》反驳说:“生数千载之后,安见二子必无其人?”(33)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六《孔子弟子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第278页。阎若璩也提出,孔庙中不仅应复祀秦冉、颜何,而且要增祀《孔子家语》中的县亶,“如是而孔子所谓受业身通者皆全具矣”。(34)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册,第514页。费密力主“七十子中论罢与汉唐先儒已祀者,皆不可废”,(35)费密:《弘道书》卷中《从祀旧制议》,《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46册,第39页。甚至理学名臣陆陇其也认为,议定从祀原则时应从宽不从严:“孔门弟子亦有不能无疵者,岂可以一眚掩大德乎?”(36)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三《灵寿志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5册,第30页。
与明儒正相反,清初学者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传经之儒上,除汉唐经师之外,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七十子中的传经弟子。梁启超曾概括说,孔门弟子可分为以子夏为代表的传经之儒与以曾子为代表的传道之儒,前者重“外观的典章文物”,后者重“内省的身心修养”。(37)梁启超:《梁启超论儒家哲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26页。若从孔门四科而论,大致相当于文学与德行之别,“文学之儒,皆务经学传承,以师法自居……德行科诸儒则能向内探求,悟自得之趣”。(38)邓秉元:《孟子章句讲疏》卷三《公孙丑章句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112页。如果说宋明儒主要取径于曾子、孟子,那么清儒在对理学进行反思与批驳的同时,则尤为关注子夏。实际上,在清初复祀七十子的思潮中,形象变化最大的也正是以子夏为中心的传经弟子。
朱彝尊曾撰有《文水县卜子祠堂记》,文中反映出清初学术思想的明显异动。朱氏说:
孔子既没,曾子之学,群弟子或未之笃信,独以有若为似圣人。而子夏居西河,西河之人亦疑之于孔子。若二子者,将不得为具体者与?……盖自六经删述之后,《诗》《易》俱传自子夏,夫子又称其可与言《诗》,《仪礼》则有《丧服传》一篇,又尝与魏文侯言乐。郑康成谓“《论语》为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赞一辞,夫子则曰“《春秋》属商”。其后公羊、谷梁二子皆子夏之门人。盖文章可得闻者,子夏无不传之。文章传,性与天道亦传也,是则子夏之功大矣!(39)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五《文水县卜子祠堂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第371—372页。
宋明时期,子夏等人的形象多以《孟子·公孙丑》中的如下一段话为根基:“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朱注说:“一体,犹一肢也。具体而微,谓有其全体,但未广大耳。”(4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7页。正是因此,较之颜、曾,子夏等人在理学范畴中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特别是南宋以降,曾子作为“四配”之一获得配享资格。(41)参见朱维铮:《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6页。但朱彝尊此处话锋所向,直指孟子与宋儒。在他看来,子夏不仅在六经的传承上至关重要,而且即使以“性与天道”论也堪称居功至伟。朱氏还指出,既然有子与子夏皆被当时人比作孔子,那么何以不能有“具体者”之称呢?
为传经弟子争地位的思路贯穿于朱彝尊的许多文字中。他说:“孔子之道著乎六经。传其业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开之习《书》、传《礼》,子舆之述《孝经》,子贡之问《乐》,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之撰《论语》,发明大义,不越数子而已。”(42)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〇《孺悲当从祀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第316页。此处所列孔门弟子,皆从传经角度着眼。子夏兼通六经,实际上被赋予了最权威的地位,而尤需注意的是,颜渊因未传经而无与于此,曾子之功也主要在于述《孝经》而非传《大学》。联系清初已有陈确、毛奇龄、费密等多人怀疑《大学》非曾子所作,进而提出《大学》应回归《礼记》,则不难推知曾子此时地位走向之大概。(43)参见石立善:《〈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历程及其经典地位的下降》,成中英、梁涛编:《极高明而道中庸:〈四书〉的思想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164页。
朱彝尊对孔门传经弟子的重视,还表现于特别关注孺悲。历来儒者多因“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论语·阳货》)而弃之于孔门之外,但朱氏提出:
互乡、阙党之童子,未尝无诲,何独悲之学礼,以君命临之,反绝之已甚乎?……悲一学礼而《士丧礼》之书传,其功岂小也哉?且既授之礼,则为弟子。礼,六艺之一,悲身通之。学者毋徒泥《论语》之文,谓悲不在弟子之列,必合《杂记》论之,而悲当配食于孔子之庑可信已。(44)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〇《孺悲当从祀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第317页。
前文已经论及,朱氏在孔门弟子的认定上,标准往往从宽。这其实为孺悲等人留出了足够空间,在“文章传,性与天道亦传”的观念下,传经弟子本身就具有更多的传承孔子之道的优先权。
在推尊传经弟子方面,费密与朱彝尊堪称同道。费氏也从“具体”“一体”之说出发,但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看法:
自孟轲以来称七十子……未尝以“具体”称曾子,其称曾子与子夏并。孟轲论道甚严,笔于书如此。具体、一体虽有异,非七十子尽劣于颜渊,独颜、闵数人始能传圣人之道,可以教后世也。孟轲于七十子未尝有所去取,后世之儒何所见,以意尽为芟除,独许曾氏欤?(45)费密:《弘道书》卷上《圣人取人定法论》,《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46册,第28—29页。
费氏主张,对于孔门七十子“不可过为分别”,但此处对颜、闵、曾的质疑,恰恰说明他反对的是宋明儒的“过为分别”。他认为曾子不应有“具体”之称,颜渊也不优于其他七十子,这实际上是在为抬升子夏等人的地位铺平道路。费氏说:“圣门具体诸贤,未闻传人。子夏、子游、子贡……各有授业。曾申、孔伋、公明高……其传不绝,或显或不显尔。”(46)费密:《弘道书》卷上《原教》,《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46册,第24页。从传经视角而论,“具体”诸儒尚不如其他人,由此可知“不可过为分别”只是门面语,推崇传经弟子才是费氏真正的思想底色。
费密还绘制了一份以传经弟子为核心的《七十子传人表》,并解释说:
七十子传人见于汉国史者止四人,子夏、子贡、左丘明、商瞿。子贡之传为《公羊春秋》,公羊高事子贡,亦事子夏……子夏之传有二。谷梁赤传为《谷梁春秋》……曾申、李克传《诗》……左丘明传为《左氏春秋》……商瞿传《易》……汉徐防奏云:“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则《礼》《乐》《诗》《书》,皆子夏之分宗世绪也。此七十子之正传嫡系,古经赖四家门徒而得存,三代典章赖四家门徒而不散,至今二千余年,王道如日中天。(47)费密:《弘道书》卷上《七十子传人表》,《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46册,第19页。
此处将子夏、子贡、左丘明、商瞿定位为“七十子之正传嫡系”,还原的是孔门至汉初的经学授受源流,消解的则是颜、曾、思、孟的道统权威。费氏极力表彰子夏等四人,而其一瓣心香,要在子夏,甚至谓“《礼》《乐》《诗》《书》,皆子夏之分宗世绪”。另据章学诚转述,费密“自推其学,出于子夏七十二传”。(48)章学诚撰,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二《书贯道堂文集后》,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65页。在费氏心中,子夏已经完全成为孔门正宗。也正是因此,朱、费二氏的做法实际上是在道统之外另立了一种学统,在这一更新了的孔门谱系中,居核心地位的是子夏,居次核心地位的是商瞿、子贡、有子、子游等,甚至此前不被认可的孺悲也获得了重要一席,而颜、闵、曾等人则被移至相对边缘的位置。宋明儒所理解的孔门正统谱系被完全打破,在经过重塑的孔门结构中,原先“得圣人一体”的传经弟子成了新的“圣学正宗”。
更能反映此时学术风气的是,即使在理学积淀较深的学者那里,子夏的形象也渐有与颜、曾可以分庭抗礼的迹象。康熙初年,理学名臣魏裔介为其弟魏裔慤所辑《卜子夏集》作序,序中说:“当春秋之终,战国之始,斯道绝续之关,子夏氏独留其统于西河之上,其有功于洙泗岂浅鲜哉?”评价该著的纂辑可使子夏“伯仲于颜、曾、思、孟”,文献价值堪比“鲁壁之再见”。(49)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三《先贤卜子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2册,第698页。魏氏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也说道:“或谓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弟独以为颜子之治心、曾子之敬身、卜子之传经,皆圣学嫡传也。”(50)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九《与郝雪海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2册,第822页。可证序文所说并非完全出于虚饰。魏裔介将颜、曾与子夏平等视之,实际上肯定了后者的传经之功。虽然魏氏仍是清初维护道统观念的一员主将,但在他这里,子夏确实得到了理学范畴中并不多见的一种定位。
此外,清初也有从专经方面来评述子夏之功者。康熙年间的福建学者蔡衍鎤勤治《诗经》,自名书斋“尊卜轩”,认为“说《诗》当以西河为主”,(51)蔡衍鎤:《操斋集》文部卷七《诗经尊卜自序》,《四库未收书辑刊》集部第9辑第20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不可因朱子之怀疑而废《诗序》。他说:
子夏之言《诗》也,在《论语》止一见,而即为夫子所与。是当年所序三百余篇,无一不见与于夫子可知也。夫子之美子夏也,在《论语》亦止此一见,而所美者即为其称说逸《诗》,是当年欲删一诗,未尝不谋及子夏可知也。《记》言“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赞一辞”。夫惟《春秋》不能赞,其余必有赞之者矣。(52)蔡衍鎤:《操斋集》文部卷一〇《诗经尊卜跋》,《四库未收书辑刊》集部第9辑第20册,第348页。
蔡氏此处由某一证据而推测全貌,实不乏武断之处,但其推尊子夏之意清晰可见。特别是他将《诗序》溯源于子夏,代表了清初学者的一大共识。顾炎武的弟子潘耒有一首诗说:“孔辙不到晋,西河遗泽长……髫年受《诗序》,不敢薄毛苌。”(53)潘耒:《遂初堂诗集》卷二《子夏祠》,《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17册,第189页。同样是因为《诗序》由子夏传至毛公,故而不敢轻视。甚至连理学背景较深的汤斌也发现,《诗序》之说“往往与《左传》合”,“子夏、左氏皆亲见圣人而闻其笔削之意,岂尽无据乎?”(54)汤斌:《汤子遗书》卷六《十三经注疏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2册,第543页。大体而言,清初长于《诗经》的学者多有重回《诗序》的倾向,而对于子夏与《诗序》的关系则多不否认。以子夏为代表的传经弟子,正在得到清初学者有意识地推尊。他们在孔门的地位由边缘走向中心,这一方向性的变化开启了乾嘉时期以“汉学”推尊子夏的学术先声。
“汉学”复兴与清儒对子夏的重新诠释
虽然清初学者已将视野转向汉唐经学,并有意识地推崇七十子以降的传经之儒,但无论是顾炎武、阎若璩,还是朱彝尊、陈启源,实际上都处于“汉学”的草创时期,并未有学术进路上的根本转折。真正力扬汉帜而形成系统者,当首推苏州四世传经的惠氏家族。从惠有声、惠周惕至惠士奇、惠栋,汉学意识逐渐凸显,特别是惠栋于雍乾之际撰写《九经古义》《后汉书补注》等,在经史研究的互动中重新揭橥了汉儒最重视的“家法”观念。此后,伴随汉学思潮的愈演愈烈,清儒对于子夏的理解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惠栋对子夏的重新定位,与家法观念的自觉密切相关。在惠氏那里,汉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经义由孔门后学一代代传承下来。他说:“孔子殁后至东汉末,其间八百年,经师授受,咸有家法……由两汉而溯三代,沿波讨源,家法犹存。”(55)惠栋:《松崖文钞》卷一《韵补序》,漆永祥点校:《东吴三惠诗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308页。惠氏尤其推尊孔门文学科诸弟子,将其视作家法观念的源头:“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家法之祖也。各自成家,各守其法,至汉犹然。”(56)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整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辛壬稿卷三《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9页。关于子张与文学科的关系,阎若璩的意见值得重视。阎氏主张,孔庙在颜、曾、思、孟“四配”之外,应立“十二哲”。他据《论语》提出公西华“政事之才实与由、求并”,据《孟子》提出子张“属文学”,再加上王应麟“有若盖在言语之科”的见解,就形成了孔门四科各有三位弟子的结构。钱大昕认为此说“确不可易”。惠栋将子张同子游、子夏一起视为“家法之祖”,应当与阎若璩同一思路。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册,第515页;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八《阎先生若璩传》,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602页。作为吴派经学大师,惠栋实际上将汉学的源头追溯至孔门传经弟子。这一定位奠定了此后清代学者对子夏的认识根基。
在家法观念下,《论语》中的“述而不作”被吴派学者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在惠栋看来,“述而不作”乃孔门精义,不仅受到孔子称许,而且还能与先秦其他典籍相印证。(57)惠栋:《九经古义》卷一六《论语古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1册,第502页。而在孔门之中,文学科的特质恰在于传经与解经,在“述而不作”方面显然较其他诸科为长。受惠栋影响甚深的王鸣盛注意到,对于《礼记》中的“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唐儒就解释为“述者,子游、子夏是也”。(58)王鸣盛撰,单远慕校证:《十七史商榷校证》卷一〇〇《缀言二》,三晋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3页。王鸣盛援此而自命“述者”,而且同惠栋一样,批评宋儒乃是“不知而作”。此外,钱大昕也将汉儒家法上推至七十子,认为:“诂训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59)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第365页。
这种以家法观念尊崇子夏的做法,一直持续至晚清。今文学家皮锡瑞从家法视角分析了子夏在经学史上的地位,据其所述,自“儒分为八”以后,“诸儒所传,今皆亡佚,不复能考其家法”,而子夏是孔门兼通六经的翘楚,故“考经学家法,当以先儒卜子为首”。(60)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潘斌选编:《皮锡瑞儒学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286页。皮氏与惠栋所见略同,都以“家法之祖”许子夏。唯其如此,他在叙述“经学传于孔门”时,(61)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8页。首先论及的便是子夏的授受渊源。与皮锡瑞同处晚清的盐城学者陈玉澍撰有《卜子年谱》二卷,作为晚清以前唯一一部专门研究子夏的著作,该著不仅考证了子夏的生平,而且对其评价极高。陈氏认为,从经学视角而言,子夏之功绝不在曾子、孟子之下。他说:
无曾子则无宋儒之道学,无卜子则无汉儒之经学。宋儒之言道学者,必由子思、孟子而溯源于曾子;汉儒之言经学者,必由荀、毛、公、谷而溯源于卜子。是孔子为宋学、汉学之始祖,而曾子、卜子为宋学、汉学之大宗也。(62)陈玉澍:《卜子年谱·自叙》,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89页。
子夏作为汉学的宗主,与宋学宗主曾子得到了平分秋色的定位。由惠栋至皮锡瑞、陈玉澍,子夏的“家法之祖”与“汉学大宗”形象可以说一脉相承,而这一形象背后所潜藏的,正是清儒对自身学统的深刻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晚清出现的《卜子年谱》未尝不可视作清儒对自身学术源头的一种回视。
清儒对子夏的重新诠释,还包括重建由子夏到荀子的经学脉络。深于荀学研究的汪中指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而“荀卿之学实出于子夏、仲弓”。(63)汪中:《述学》补遗《荀卿子通论》,《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65册,第415页。如果说荀学是清代的一种显学,那么子夏作为其源头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以校勘著称的卢文弨总结说:“经十有三,而不由子夏氏之门所传授者,盖仅二三而已。”(64)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吴槎客子夏易传义疏序》,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页。肯定了子夏兼通群经的重要地位。丁晏则从《诗经》学着眼,认为荀子上承子夏,下启毛公,因而《毛诗》“渊源子夏,其所传述,盖西河授受之绪言也”。(65)丁晏:《毛郑诗释》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71册,第366页。皮锡瑞更是一再强调,“先贤卜子之后,传经最有功者惟荀卿子”,“圣门诸经犹能流传至今绵延不绝者,卜子之后,以荀子为最著”。(66)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皮锡瑞儒学论集》,第286、287页。乾嘉以降的学者推崇子夏、荀子传经之功的风气由此可见一斑。
若论从学理上考察子夏、荀子关系者,惠栋应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惠氏撰有《荀子微言》,不仅深于荀学,而且常常表彰子夏。他在《荀子微言》的第一处按语中,建立起二者的礼学渊源:
自子夏论《诗》,有“礼后”之说,而夫子与之,故其徒皆传其学。五传至荀子,其言曰:“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又曰:“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盖先王治定制礼,夫子训伯鱼,先《诗》后礼。论成人,兼备众才,而终文之以礼乐。是知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君臣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此子夏“礼后”之说为不可易也。厥后朱子解《论语》“绘事后素”,废郑氏之义,以“礼后”之“礼”为礼之仪文,于是荀子之所以述子夏者,后儒亦不知其义之精矣。(67)惠栋:《荀子微言》不分卷,《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32册,第464页。
惠氏由《论语》“绘事后素”章发论,认为“礼后”正是强调礼学之重要,对照荀子《劝学》所言,可谓前后一贯。原朱熹注文之意,认为素近于质而似忠信,绘近于文而可喻礼,所以将“后素”解释为“后于素”,强调“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6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3页。惠栋显然不同意此说,他依托郑义,力主绘事之后须依“素功”来达成,犹如一切美质均应进于礼方有所成。
惠栋之说有其渊源,其父惠士奇就认为:“忠而无礼则愿也,信而无礼则谅也……不学礼而忠信丧其美也。是故画绘以素成,忠信以礼成。”(69)惠栋:《荀子微言》不分卷,《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32册,第464页。父子之说基本一致。学者曾对此解释说:“惠氏之意,荀子‘隆礼’思想继承子夏‘礼后’之说,继孔子圣言,荀子为孔学传承之正统。”(70)王应宪:《清代吴派学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这一观察是相当精准的。惠氏父子正是希望通过将荀子思想与子夏之说进行沟通,为子夏、荀子一系的礼学思想争地位。而与此可并观的是,戴震也认为,子夏所言“礼后”正是“重礼而非轻礼”,其本意是“凡美质皆宜进之以礼”,绝非“后礼而先忠信”。(71)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仁义礼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50页。凌廷堪在这一问题上也与惠、戴观点相近,认为“五性必待礼而后有节,犹之五色必待素而后成文”。(72)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一六《论语礼后说》,《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80册,第221页。三者的解释反映了清儒对礼学的特殊重视,较之朱熹之说无疑更符合“古义”,而且对于子夏、荀子的学术渊源而言,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究。
在汉学风潮下,乾嘉学者还有一种学术倾向值得重视,即他们对早期典籍及宋儒所塑造的子夏某些“负面”形象,纷纷进行辩解与再认识。如子夏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一语,宋儒认为“意圆而语滞”,“惟圣人则无此病”。(7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27页。在钱大昕看来,这正是一种偏见:
宋儒说《论语》者,于诸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贬抑。然细绎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闻之言,初无一语自造……孔子曰:“大道之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又曰:“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横渠张氏《西铭》云“民吾同胞”,即四海皆兄弟之说也。子夏所闻,即孔子之绪论,又何语病之有?(74)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九《答问六》,《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第135—136页。
据钱氏分析,“四海皆兄弟”只是转述,不仅与其他典籍中孔子之语作合,而且张载所见也与之略同。既如此,宋儒的负面意见只能算是一种苛求。这种“有意贬抑”的做法,为钱氏所不取。
《礼记·檀弓》所记载的子夏哭子丧明一事,也是一个常见于清儒著作的话题。曾子因此事而面斥子夏“三罪”,宋儒多赞同曾子而批评子夏。但治经尤尊汉学的王鸣盛,力辩其事不可信。他说:
子夏少夫子四十四岁,曾子少夫子四十六岁,然二岁之长,亦长也,况本父之朋友乎!有过相规,其言亦宜稍孙。乃《檀弓》载子夏丧明,曾子责数其罪,直呼其名曰商;就其所责三事,亦属太苛。恐未可信。(75)王鸣盛:《蛾术编》卷五四《说人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770页。
在此之前,清初孙奇逢曾留意此事,虽认为“不妨子夏之贤”,(76)孙奇逢:《孙征君日谱录存》卷一三,《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8册,第835页。但对其可信度并未质疑。王鸣盛指出,曾子的做法不仅从年齿、辈分而言有失礼之嫌,而且所责难之事也近乎苛求,故而此事缺乏真实性。受汉学影响的另一位乾嘉士人赵佑也沿袭这一思路,列举出此事诸多不合情理之处,并讥弹宋儒“读书无识而好轻议古人之短长”。(77)赵佑:《四书温故录·论语一》,《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166册,第464页。直至治学折衷汉宋的简朝亮,在清末民初仍旧为子夏辩护,认为“皆《檀弓》传闻之失也”。(78)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卷六《颜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3页。可知在汉学思潮影响下,《檀弓》中这一“哭子丧明”的子夏形象已鲜为清代学者所接受。
被纳入清儒视野中的还有子夏“心战”之事。据《韩非子·喻老》,子夏说自己在“先王之义”与“富贵之乐”间心战不已,最终“自胜”而选择前者。从德行存养而论,子夏确实不如颜、曾坚毅,朱熹就批评其“为人不及,其质亦弱”。(79)朱熹:《朱子语类》卷四九《论语三十一》,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4页。清儒对此事进行辩解者,以沈钦韩为代表。沈氏认为,《韩诗外传》所记闵子骞事与此大同小异,皆有附会之嫌。他提出:
愚谓此皆浅之乎测大贤者也。后汉郭泰以人伦师道自任,童子魏昭曰:“经师易遇,人师难求。”入供洒扫,三进粥,遭呵叱而无愠色。彼魏昭以为舍泰无他慕也,则闵子、子夏亦为舍圣人无他慕也,岂其志不若一童子哉?周末诸子著书,多诬古人为谈柄,俗儒信之,愚矣。(80)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七《古今人表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266册,第224页。
此处所引魏昭事见袁宏《后汉纪》。沈氏的“考证”并无直接证据,只是据魏昭之例来推测“心战”不实,但他为子夏极力辩解的心态颇堪玩味。近来有学者提出,乾嘉学者对荀子若干形象的辩解是一种“集体的有意识的行为”。(81)康廷山:《清代荀学史略》,第129页。我们由以上多例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子夏“负面”形象的洗刷与辩解,同样也不限于一时一人。考虑到乾嘉以降对子夏传经之功的肯定以及“家法之祖”的评价,可知清儒已不愿子夏以早期典籍及宋儒所理解的那种“负面”形象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代学者对子夏形象的重塑过程,实际上蕴含了对汉学学统进行重构与清理的学术诉求。
结 语
清初对七十子的推尊,主要源于道统观念的衰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学统回溯。在这一过程中,在宋明理学那里绝非圣学正脉的孔门传经弟子逐渐由学术话语的边缘趋近中心,并在从理学到汉学的思潮演变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由“得其一体”到“圣学正宗”,传经弟子的形象重塑不仅是对孔门结构的再次调整,而且也为经学进路的根本更新提供了助力。
子夏、荀子一系的学问在清代走向复活与兴盛。倘若说宋明儒是颜、曾、思、孟的思想裔孙,那么清儒无疑是子夏、荀子一系的正宗法嗣。从顾炎武以“日知”名书,到惠栋提倡治学重积累,再到钱大昕以“驽马十驾”自许,倘若追溯其义,无疑都源自子夏、荀子。而清代学者中以“抱经”“拜经”“揅经”“味经”等自命者不一而足,更是体现了“以经为师”的基本信念。这与子夏等传经诸儒的学术特质是完全相符的。在这个意义上,清代学者将子夏奉为“家法之祖”与“汉学之源”,既是对宋明理学的一种“反动”,更是对自身学术来源与路径的精神自觉。
在清代经学的“范式”重建中,先秦两汉许多儒者的形象都得到了重新塑造。这些更新了的形象往往体现出清代学者的基本关怀与价值倾向。本文所论子夏等孔门传经弟子只是这一问题的一端,有关其他学人形象的重塑及其与清代经学的关系,尚留待我们不断反思与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