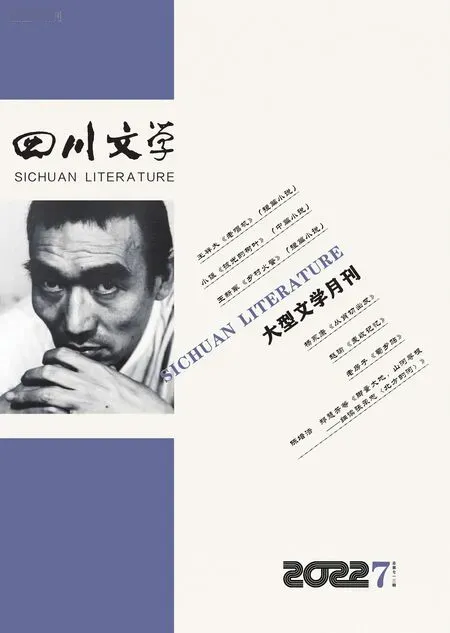长河岸
□文/虞雅岚
父亲在城墙根旁开了一家客栈,取名叫做长河岸,大概是因他总能酿得很好的酒,几十年来长河岸的生意一直不差。
十八岁以前我也在客栈里帮忙,客栈不大,两层楼,但每天擦拭的桌椅都目睹过人来人往的沧桑。来住店的人很杂,说书的经商的、普通老百姓、做官的、走江湖的、从江湖中走出来……有偶尔来住上个三两天天天大鱼大肉的,也有长期占一两间房住着不走,每天只吃咸菜下米饭、小酌一两杯的。
客栈里的基本陈设多年来都没翻新过,虽然陈旧但是干净整洁,桌椅间鲜少积得有灰尘,刀剑划痕更是从未有过。父亲说那种桌椅碗筷都用人血洗过,一言不合就亮家伙,刀光剑影哪怕是良辰美景也沾染了匪气,明明腌得有上好的牛羊肉只因来客不懂道上的规矩就拿白肉来随意糊弄,三教九流碰上头,不问高低只想着要拼个输赢,那样的店是黑店,我开店不开黑店,黑店太脏。
几十年来也遇到过喝醉酒叫板不服气的,要将江湖规矩搬来论理,父亲只出过两次手,从此道上的歪门邪气再没进过长河岸的门。江湖规矩在店里是行不通的,我一直只当是因父亲是从江湖里走出来的人,深知那规矩害人,所以不认那规矩。后来偶然听他说起:“世人如今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那还有什么规矩可言,不过是冷眼看人心浮躁罢了。”我才明白他没有别人估计的那么多心思,不过是到了如今眼里再容不下沙子而已。
客栈里的人来来去去走走停停从无定数,遇到过的怪人不少,风月刀也是一个。我第一次见到他大概是三年前的冬至,那天风极大,天还没亮就开始飘雪了,大雪盖住了路,积得厚厚的,雪深处一脚踩下去直没膝盖,我拿了扫把想去门前扫开一条路,父亲止住我,我不解,他从柜台下取出用了多年的紫砂酒壶灌上一壶酒说:“今天我只温一壶酒,不接四方客,只待有缘人。”他话说完便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起来,我们都知道江湖习气是不应该带到生意上的,否则就只剩下眼前路再无身后路了,但今日不同,今日店里只有我们两人,面子里子都过得去。
雪一直没有停,还越下越大,黄昏之前店里都没有来人,这个季节天黑得早,太阳还没完全落下去,弥漫得凶猛的雾气已全成了橙黄色,我瞧着远近都点了灯,便拿了木叉到门口去取挂在屋檐上的灯笼,想着今天早点把灯笼燃起来,在这雪雾里晕成一团,远远地瞧着一定很好看。我刚燃起一只,红彤彤的光很是晃眼睛,这个时候我听见了踏雪声,嗡嗡的声响由远及近。伸头一瞧,一个挺拔的身影正在走近。他穿青色的袍子背上背着一把剑,没有戴雪披,发髻上都是零星的未化的雪片,棱角分明的脸或许是因为寒冷而显得苍白,两弯眉如漆刷,一双眼射寒星,高鼻薄唇,长相清俊,堂堂七尺,眉宇间却少了几分英气多了几分阴柔。“温一壶酒,烧一只鸡,再酥一盘下酒的花生。”他说着抖落身上的雪片,进门去了。我将他要的酒端去给他,见他的长剑就摆在桌上,剑身剑鞘都用布包着,只露出一截剑柄,剑柄上的雕花十分精巧。
“学武的?”我问他。
“是。”他抿了一口酒。
“武林嘛,”我边说着边为他斟上酒,“一条腰带一口气,上了这条腰带就是练武之人,往后就要凭这口气做人。”他听闻抬起头来,露出笑意:“你也是学武的?”我摇头:“皮毛而已。”
后来雪停了。再后来冬天也过了。他倒是常常来喝酒。我渐渐知道他的名字叫风月刀。我觉得这名字挺滑稽可笑,一听就是名号而非真名。我问他为何会叫这么个名字?他大概是喝多了,指手画脚却只说了一句清楚话:“我早早料得这浮生一片草,风月如刀。”对于他的解释,我不太懂。风月刀来的日子没有规律,有些时候天天来,有些时候大半年才来一次,但每年冬至,风雪最狂的那一天他一定会来,我不明白也不感兴趣。
他说他十岁学拳,为了找到服气的宗师四处奔走。“我曾经一个人破浪而行,历经千帆漂泊无依。”他说得很真诚,“我十岁学拳,至今见过丘陵,没有遇见高山。”他有些无奈。我听了他的故事。在彼此的故事中,我们的面孔如此陌生,擦肩而过却无从把握一个武者的内心。我问他:“打了一辈子石头,才知道这世界有沙袋,但当他出世诡异地强悍,算是宗师吗?”
“不!”他回答得斩钉截铁,“那是愚人,不是高山。”我不解:“那什么才是高山?”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他的拳法众人佩服,他的名号令天下群雄服气。”他回答得轻描淡写毫不犹豫,看来这个定义一早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有一年初秋,我正拿了扫帚在后院,用簸箕将满院落花拾起埋在院墙西处一棵种了多年的梧桐树下。
“舍不得落红成泥碾作尘吗?”我吓了一跳,抬头见风月刀噙着笑迈步向园子里来了。
“你来这里做什么?”我问他。
“你父亲说来这里能找得到你。”风月刀说着就在我对面围廊的木栏杆上坐了。
“找我做什么?”我放下簸箕,斜眼瞅着他,想着他好像是有一阵子没来了。
“我接了镖,南下去了一阵子。”他自顾自说了下去。我想他是要跟我讲讲他的江湖际遇了,拾起簸箕将花瓣铺在刚翻好的泥土间,准备听听他的故事。
“我见过你练剑。”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我吓了一跳,簸箕掉在地上,红粉的花瓣全洒在了我的鞋上和地上。“什么时候?”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大概觉得我的反应大得有些可笑,神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你的剑法不错,如若你愿意入道,在这江湖上立块招牌是绰绰有余的了。”
“不感兴趣。”我撇了撇嘴。
“我搞不懂你,你是做江湖菜的人,为何对这江湖如此没有好脾气?”
“我不过是个厨子,”我说着将头发拢起来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四处找寻着平日里搁在墙角的一把小扫帚,寻思着要用它把满地落花扫个干净,“我做菜给客人们吃,客人心里担了恩怨,吃的饭菜也变成了江湖菜,其实不过是寻常的饭菜罢了。”
他听我说着,眉宇间起了褶皱:“告诉我,你是败过,所以不愿意再出手?”
“败过也胜过。”我弯下腰,捧了梧桐树下的碎泥盖了落花:“不过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先拳后腿次擒拿,内家兵器五合一。江湖那么大,门里门外一招一式都难以激起什么风浪。从前总以为功夫是纤毫之争,只论高下不论生死,后来遇见过高山才明白。所谓江湖,真正计较的不过是几套拳法的事,没什么意思。”
“高山?”风月刀苦笑了一声,“高山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不一样的概念,”我打断他的话,“我从前与你说过的高山,都不过是眼前的高山,上山下山一样难;现在我要说的,是命里的高山,上山容易,下山难。”
他笑了起来,似乎欲言又止,这个话题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你知道我的,不是谁的镖都接,难得去一次南方,给你带了些东西。”他伸出手,示意我把手给他。“知道你心诚,在中旬停留了几天,给你求了一枚平安扣。”一枚雕刻精致的平安扣落在我的掌心上,琥珀做的,我一看就知道是上好的血珀。
“按你出生的时辰,贴身戴的护身符血珀是最好的。”
我吓了一跳,忙说:“这礼太重,我收不得!”我挡了回去。他并不言语,掰开我的手,“礼是很重,但是还是希望你能收。”我瞧着手里的平安扣,心里止不住地打鼓,叹了口气:“我不走江湖,只怕是用不上这个,倒是你,现在做了镖人做了侠客,这风里雨里的才是该好好求个平安。”我把平安扣攒了起来,算是收了这个礼,“我不想求平安,但求心安。”
他笑了起来,他笑起来一向好看。
我没有说话,伸手将平安扣上拴着的红色编带解下来,抬起他的左腕,系了上去:“这样的话,希望你能明白,平安心安都在这条绳上了。”我避开他的视线,脸上辣辣地烫,“好了,你该去喝酒了。”我将那条红绳打成一个死结,抬头对上他的眼。我们相视而笑,我引他向前厅去了。
第二年春天,雪化后不久的一个夜里他突然来了。他只裹了一层单薄的汗衫,那时天还很寒。我将他的枣红马牵到马棚里,见着父亲领他进了西厢房。他向来是剑不离身的,那天他来却没有带剑。
早上约莫有六点钟了,我起身去点灯。城西有名的镖队几天前托人捎来消息说今天一早要打长河岸过,要了够七个人分量的烧酒。与镖队有关的买卖我一向很上心,不只是因为镖队的头领是父亲旧友的大弟子,私交颇善,镖队人是生意人,更是江湖势力的一个轴心,黑白两道都有交集,而现在的长河岸想要抽身江湖之外除了不惹恩怨,镖队便是头一个得罪不起的。
镖队的人马打着大旗,接了江河间的酒菜,从城墙根东面的木门拐出城去了。我站在客栈门口。天还没全亮,大概是起了雾,远近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对面的店铺只有一两家卖早点吃食的卷了帘,街上也没什么车马,我瞧着镖队红色的大旗只觉得刺眼。护镖的人一旦接了镖就同请镖人上了一条船,对方的是非恩怨镖人都要照单全收,而请镖的人,尤其是请这样大型镖队的人,他们身上往来的执念都相当锋利。作为镖人刀不离手弓不离身,但最要紧的是暗箭难防,既然暗箭难防,还竖什么大旗?那么多条人命。我也曾劝过镖队的头领:“师兄,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你功夫好我知道,但言必称三,手必成圈,还竖什么大旗列什么马队?”我唤他师兄,他长我五岁,从小领着我长大,无关辈分但我习惯了唤他一声师兄。师兄却说:“我上得了九龙台,下得了青石长阶万里河,大旗不为招风只为定人心。”我明白他的意思,却不敢再响应。大旗在雾气中变得模糊了,或许还在猎猎飘着,或许没有了,或许根本没有风吹,不过是我自己心不平静。
我原本计划着要去赶个早集,走时路过后院的围栏,看见西厢房的灯还亮着,糊在窗户上的糙纸映出端坐的两个人影,我便知道他们谈了一夜。我为他们灭了灯盏,到厨房泡了父亲爱吃的早茶煎了几味茶点,端去给他们醒神。我推门进去,他们依旧精神,大概还算是谈得投机。我跪坐在父亲身旁,预备为他们沏上一壶茶。“熙儿,你先出去,我们再谈点要紧的事。”父亲的神色甚是严肃,眼神却分明带了笑意。我收拾起碗筷,将用热水浸过的帕子递给他们,起身出门去,耳边他们的谈话只响了几句:“你可是想好了?”父亲问道,声音很是严肃。
“今天我来可没带剑。”风月刀回答得倒很肯定。
“我的剑可是沾过血的。”风月刀打断父亲,“但是系上了熙儿这条红绳,我愿意折了我的剑。”
紧接着是一阵急促的沉默。
“我是过来人,知道路不好走,因此才决不让她上道。”父亲说时叹了口气:“如若你真的想好了的话……”
“您不用再问这个问题了。”
“为何?”
“因为我已经在折剑了。”
“你不是又领镖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比我更懂。不过我答应过你的事,我一定会兑现。”我赶快蹲下身子,生怕被他们发现。
那天过后,春天也过了,夏天来了,六月伏天见过人人摇扇,七月流火,后来又见了枇杷金黄,再后来下了第一场雪,日子一天一天过着,又下了很多场雪,这一年也快完了,风月刀一直没再来过。我想着他或许是不会再来了。走江湖的人到哪里都有江湖菜吃,又或许他已经死了,来不了了。有时候看看脖子上系着的平安扣也会想起他和他的长剑,我知道他心诚也有慧根,又或许他已经遁入空门,出家去了。
又到了一年年关。年关凶猛,这一阵子客栈里的红灯笼都是从早燃到晚,红色嘛,可以辟邪。
那一天是冬至,同往年一样,这天的风雪最大、最狂。大雪是从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下了的,风整整吼了一天,到了傍晚才稍有收敛。住店的人不多,但也有那么十来个。我煮了两锅饺子准备送去,冬至嘛,吃饺子,图个吉利。
天暗得早,门口的路是早就被雪盖牢了的。我拿了扫帚,想着还是要将门口挡路的雪堆扫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个道理我从小就知道。
“温一壶酒,烧一只鸡,再酥一盘下酒的花生。”
我吓了一跳,连扫帚也掉在了地上。瞧着我,风月刀堆满笑意的脸,觉得有些陌生又很是纳闷。不知道是我耳聋了,还是他确实功力深厚,那么厚的雪堆,踏雪声我这回竟是一声也没听见。
“我以为你不来了?”我把他要的酒菜端到桌前。
“怎么?”他正擦拭着他的长剑,“江湖是条河,我以为长河岸是江湖的头,会不会是我的岸?”
我对上他的眼睛,那里有些东西我至今说不清。
“我是有一阵子没来了,有些事要办。”他搁下他的长剑,“不过,这阵子我办的事都是为了心安。”
“有一件事我不太懂,”我为他斟上酒:“你来的日子一向没有规律,但是为什么,每年冬至,风雪不管多大,你却一定要来?”
他哈哈大笑起来。许久未见,我都忘了他笑起来一向好看。他笑道:“你那么懂我,却不明白这个?”我摇头,他叹了一口气:“是啊,这风大雪大的。”他从我手中接过酒壶,从托盘中翻起一只瓷杯,斟上酒,“这风大雪大,因此我才要来看看叶底是否还能藏花?”他将酒杯高高举起,递到我的身旁。我看见他露出的手腕上系着的红绳分外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