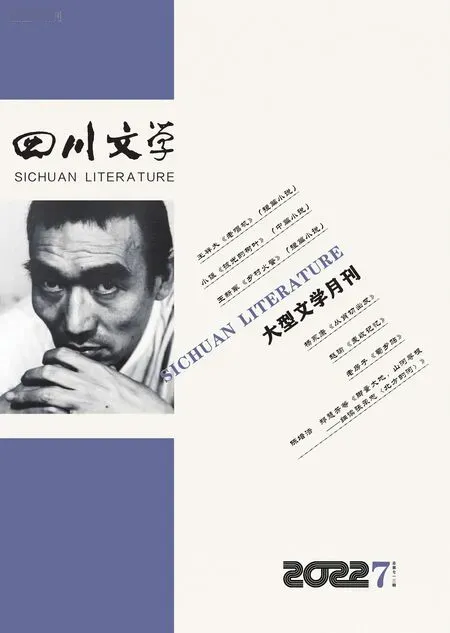课桌上的星巴克
□文/王忆
晚上十点之后,终日喧嚣的酒店大厅总算安静下来。真正开始热闹的,应该是一天准备扫尾工作的后厨,七八个油腻大褂,穿梭在洗洁剂和白瓷盘之间。余文霜在最里边,双手泡在水槽里,如机械般一个接一个洗刷这没完没了的白瓷盘。离她约有两米开外的李勤自己忙活手上的事,突然转过身对她大声说了一句什么话,余文霜丝毫没听见。不只她没听见,就算是离他很近的人也不见得能听清他说的每一个字。后厨的环境远比想象中要嘈杂,别说是相互之间说一句话了,哪怕你就是吼起来,别人也不会太过在意。他们必须在十二点前结束所有的工作,快要洗完最后一波时,余文霜还是不小心把水槽里的洗洁剂溅入了眼睛里,她没法用手去擦拭,只好歪头将眼睛在肩膀干净的地方蹭。李勤从两米开外跑过来,托起她的头,掏出一叠干纸巾让她别动。李勤实在不明白,她明明在餐厅替人收盘子收得好好的,最近为什么要主动请缨调来后厨刷盘子?十二点后,后厨喧闹逐渐散退,其他人纷纷挥去满身油烟与疲惫离开。余文霜动作比他人缓慢一些,这几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李勤其实早就忙好了自己的事,他又套上橡皮手套打算取下余文霜手里的盘子,让她歇会儿。她不肯,说一会就弄好了。他斜着身子倚靠在瓷砖柱边,看着她终于关掉水龙头,脱下外冷内热的手套,然后反复搓了搓看起来都有些麻木的手。李勤转着眼珠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有意识把手揣进裤子口袋里肆意摸索,果然一支护手霜就变了出来。他不解地叹气,问她是怎么想的?在餐厅那么体面舒服的活不做,非到后厨凑啥热闹。余文霜呼出一口气,累坏了般坐到背靠冰柜的凳子上,眼皮耷拉下来,打了哈欠说不早了,回去睡吧。
看她累得没精打采,李勤从旁边冰箱里取出一盒做好的甜品塞给她。她盯着这盒甜品大惊失色,下意识左右张望着,吓得嗫起声音责备李勤,这是干吗呀?让人发现你又偷着藏东西工作还要不要了?李勤不以为然露齿一笑,笑她胆小如鼠的样,说怕什么,工作不要就不要了呗,反正也不耽误给你做甜品。她向来拿他这种无赖行为没办法,只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别弄了。只不过,李勤还是没弄明白,她为什么突然要来后厨刷盘子。
抹茶拿铁这个名字,早在两年前从某写作网站横空出世,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做网络写手,这步骤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注册一个ID可以是一个人,注册几个ID也可以是一个人。如今但凡会打字上网的,谁还没个发言权呢。但是很多网络写手都是从默默无声做起,有的人在这里面摸爬滚打了好几年也不过是个无人问津的菜鸟。真的,有时候别以为有一腔热忱,有几分文学天赋就能随时随地发光发热,想通过网络码字有朝一日名声大振,对任何人而言几乎都是天方夜谭的话。当然话是不能说得太满,有些事碰到机缘巧合往往就是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气。抹茶拿铁不就赶上好运气了吗,尽管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能这么顺利在茫茫网海中脱颖而出。不仅如此,人家在两年内不仅在网络文学中人气大增,还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唯一令人疑惑的是,很少有人见过她本尊,在网络上见不到也属正常,在现实中文学圈里也没有人知道她的真面目。她几乎不参加文学活动,也不与人打交道,甚至连作家群也不加。她想的是,为什么要加群,写作不是个人的事吗?这两年作协真正和她有过密切接触的也只有一次,作协人要她去领会员证,她在电话里用并不甜美的嗓音回复道:不好意思,老师。我现在不方便去拿证,能不能麻烦您给我快递到家里。
然而,最近她更帖小说的网站,不断有人开始在下面抱怨:
抹茶拿铁最近干吗了?怎么都不准时更新了?
就是。抹茶拿铁怎么回事?这是要弃坑断更吗?不带这样的,有没有职业素质了!
这就是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差别,在网上写小说,你假如每天不更新几帖,光是催更就能灌上好几页的水。再说,读者选择追看你的帖,不仅是因为你写得合胃口,关键你总不能把别人胃口吊起来,又突然不给下文了呀。但是这几年长久追随抹茶拿铁的读者应当都明白,这不是随随便便断更的人,否则她这几年的上千万字岂不是白码了?谁还没个特殊事儿。还不错,一连刷了两三页总算有人说了句良心话。万幸,这天大约半夜两三点钟,抹茶拿铁在帖子第八百三十七页更新了最后两帖,并留言:十分抱歉,让各位久等。今日更新最后两帖,此小说已完结。感谢大家长久的追逐与等待。此情可待,江湖再见!
退出界面,关闭电脑,她从巴掌大的床底下拖出半旧不新的行李箱,呼一声吹去上面持久不散的灰尘,似乎是在为一场并不遥远的旅行而预备。
她这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中午,好不容易睁开眼看看时间,吓得一个猛子弹跳着坐了起来,直愣愣想了一会儿,又一阵沉下心喘息:今天不用赶那么早,都还来得及。没错,她今天要拖着那只许久不见光的行李箱出门了。是出门,不是出远门。在这之前她决定好好地梳洗一番。松散开日复一日绑的马尾,从淘宝特价淘回来囤了半年的化妆包,这会儿是时候拿出来发挥作用了。眉毛画一下,假睫毛也可以接一下,口红就用姨妈色的。她不喜欢太亮太艳的色彩。今天得有仪式感出门,伸手套上浅灰色呢外套时,她下意识从手机翻出短信通知:网络作家培训班,11月8日下午三点国泰会议中心报到。
国泰会议中心?她站在原地显得有些犹豫,没过一会儿又不假思索,翻箱倒柜找出一架墨镜顺势戴上。至于为什么给自己起抹茶拿铁笔名,这好像也完全是一种随意的巧合。几年前一个下午,当她决定开始在网上码字,注册用户名时,恰巧手边有半杯已经冷掉的星巴克咖啡。她专注地盯着屏幕,抬手喝了一口,味蕾像开了花似的甜蜜。啊,这是什么口味的热饮?香甜又不腻味,还带着些许清新口感。抹茶拿铁。这个味道真不错,就叫这个名字好了。
这是她第一次以一个作家身份,从网络来到现实。这是一件对她来说十分庄重的事情,也许她一亮出抹茶拿铁的身份就会有许多慕名者围追堵截她,他们会追着她问这问那,他们会好奇她网络写手背后的身份。想到这些,她突然心头一紧,又潜藏期待。无论怎么说,她现在的身份是一名持证作家。滴滴快车将她一路驰骋送到了会议中心正门口,她正给司机支付路费,酒店门童就提前为她拉开了车门。她被这一举动惊着了,隔着墨镜与门童的满脸笑意对上一眼,迅速撤离,随后尽量避免再与他眼神对视。按照大厅指示牌提示,她找到培训班签到处,根据会务人员指引到酒店前台办理住宿房卡。她在几米开外对前台方向望去,办理入住的人排成了两排,办理房卡的是两个面容青涩的女孩。她推了推脸上的墨镜,行李箱在地面上跟随她滚动。排到她的时候,服务生要求出示身份证,她迟疑地点了点头,从单肩包里笨拙翻出,犹犹豫豫递到服务生手中,她有些生怯,像是没见过大世面似的低着头。服务生拿身份证做了登记,对她说:“请摘下墨镜!”摘墨镜?她显得有些差异,而后看到服务生举着摄像头,才恍惚明白,完事又立刻戴上。都说写作的人喜欢僻静,她有些庆幸,拿到109,位置较为偏僻,而且就在一层的房间。走进房间,手还停留在门把上,从里边探出头去看并没有人。长长舒了一口气往里去,环顾四周,干净宽敞的房间,三点多钟阳光懒洋洋地撒在两张单人床上。她总算可以放下一切包袱,摘下墨色“面具”,直到很晚的时候,才从洗手间门缝里发散出具有品牌意识的沐浴露香味。
李勤是酒店专门做糕点的甜品师。无论怎么说,他毕竟是一米八的大高个,每天把力气消耗在烘焙上,实在不是一个男人应该追求的。就像在这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今后的工作竟然是做这个,而这只是因为余文霜来到这里工作。这几天,李勤陆续接到余文霜父亲打来的电话,绕来绕去,只想通过李勤这儿问问余文霜元旦回不回家。余文霜耻笑父亲肚里的花花肠,即使是当李勤面也不会留情面地拆穿自己的父亲,他是想问我元旦能带多少钱回去。余文霜的母亲走得早,起初两年她和父亲生活在一个家里。母亲刚走那会儿,父亲每周给母亲烧七,周年时还请了法师回来为母亲念经超度。第二年因为忘了买纸钱,父亲心里愧疚得很。总说,活着的时候没能让母亲享到福。然而没过多久,父亲经常日落出门,到半夜三更才偷摸开门回家。有一天余文霜坐在堂屋等父亲回家,等到天亮了,父亲才蹑手蹑脚进门。她问父亲,这是去干什么了?父亲觉得也没必要隐瞒了,索性全盘托出。他跟北村一个寡妇好上了,也不打算结婚,想就这么好着,做个伴。余文霜要是乐意他就接回来同住,要是不乐意他就两头跑,权当锻炼身体。她对父亲心里的算盘很不屑地一阵冷笑,什么做个伴,也不知道该说这老东西是贼心不死,还是色心不改。她想,你愿意接回来就接回来吧,权当雇个人回来替我照顾你。反正我也不打算在这家待了。
李勤劝慰她别这么胡思乱想,叔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容易。夜晚更深露重,后厨不再嘈杂,他想送她回去,余文霜摇头不肯。她脱下袖套,解开黑色塑料围裙,捋了捋挡住视线的碎发。说,你先走吧,我歇会就走。李勤又劝她,明天去跟领导说说,还是回餐厅吧。她好一会儿没作声,头仰靠后墙冰冷的瓷砖,闭了一会儿眼朝他摆摆手,说你回去吧,我一会儿就走。
第二天培训班正式开班。抹茶拿铁没想到开班仪式会这么隆重正式,会场设立在三楼万泉厅,这是一个足以容纳几百号人的大厅,平常是可以用于举行婚宴的宴会厅。而现在容纳的应该也有上百人的规格,因为座位排列很清楚,总共有三列培训班,一列青年读书班,一列高级研修班,还有一列,最靠南边门的就是网络文学培训班。透过深蓝色墨镜,抹茶拿铁找到自己的席卡,是在倒数第四排靠边第二的位置,她很满意这个位置,因为不是那么显眼。她特别注意了前后左右的铭牌,有真名有网名,但她对他们几乎都不熟,她也希望他们对她也不是那么熟悉。坐到位置上,翻看学员手册,在导师名单中她找到了想找到的名字。吴华星。没错,是他。
开班仪式只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三个培训班便各归各位,被分到不同的教室,这样每个班只剩下三十几人,大部分人都有要好的伴,可以自由组合座位。她呢,天生的孤僻人,怎么选择只会靠后选。前座的同学回头与她打招呼,她只得笑笑应对。一想到要在这种大环境里朝九晚五待上七八天,她就感到内心堵得慌。不过,吴华星,她还是蛮期待见到的,为此等上三五天,还是可以忍耐的。至少,她很早就习惯了等待的滋味。至于这个吴华星是谁?她为什么期待见到他,这得从好多年前说起,假如用抹茶拿铁自己的话说,这似乎好像上辈子的事一样,仿佛不可能再见到,又似乎迟早都会见到。一天课结束,五点半下课,人人都往餐厅冲。上培训班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平时生活不规律的作家借这几天上课时间调整好作息。但是,她下课是坚决不往餐厅冲的,自助餐对她丝毫没有吸引力,这大概是因为下午星巴克咖啡已经喝得足够饱了吧。说来也奇怪,自从开始上课,每天下午她的课桌左上角总会放上一杯星巴克咖啡,而且是大杯的那种。有人问她,咦,附近好像没看到有星巴克门店,你在哪儿买的咖啡?她把杯子盖掀开一小口,推了推墨镜简单回答:中午散步,顺道坐地铁出去买的。自从几年前喝过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半杯冷咖啡,她就一直对抹茶的清香念念不忘。其实也对,没有一个长期彻夜码字的人,会有下午不困的道理,咖啡对他们来说是个白天拿来续命的好东西。她一直在思考,过两天等到吴华星来讲课,她该怎么面对他?要不要主动上前跟他握手打声招呼,还是他会主动认出她是谁?他会对自己成为一名所谓的作家感到欣喜,或是惊讶吗?在这之前,她假设过很多种与他再见的场景,这貌似是最意料之外的一种。
余文霜还是坚持每晚十点之后来到后厨刷盘子。李勤边盘点今天没售完的甜品,边盯着余文霜的脸看。旁边一起工作的小伙对李勤痴迷的眼神直发笑,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天天看都不够啊!还真别说,余文霜虽然最近天天熬夜刷盘子,但是脸上的气色却是越来越红润亮泽,一眼看上去两面脸颊粉扑扑的,靠近一些,还会嗅到淡淡的清香。李勤忍不住多看了两眼,面庞羞涩地低语问她,你今天是化了妆吗?怎么这么好看。被拧开的水龙头持续直泻而下,噼里啪啦砸在白瓷盘上,她压根听不清李勤说了什么,只觉他笑得有些怪异。她有些急躁奇怪地皱眉,声音高过水冲下来的音量对他说,啊?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李勤没再说更多,只望着她笑笑摇头。
他们正准备收拾东西下班,李勤的手机响了。他递到余文霜面前,给她看一眼,她打算拿过来接,一时又被李勤快速收了回去。他对她做“嘘”的手势:我先接。余文霜用一种既懊恼又厌恶的表情听着李勤和电话那头对话,她心想,这真是个麻烦。接电话两分钟下来,只听得李勤态度温和地对电话里说:挺好的挺好的,您放心吧。您别着急,回头把您卡的号码告诉我,我给您打一些过去……余文霜看出他的表情几度尴尬,她知道电话那头说的准没好事,实在没法再控制住情绪,从李勤耳朵边果断抽出手机,愤怒到无所顾忌对电话那头臭烘烘地嚷道:你老给人家李勤打电话算怎么回事?跟我要不到钱,都开始伸手向李勤要了!你怎么开得了口?她紧锁眉头,满心的不爽真是不言而喻。电话那头当然也不服输,以老子的口吻数落已经一年多不回家的余文霜:我怎么开不了口,李勤也不是外人。你在外边挣了钱快活,就不管不顾你老子的死活了?家,家你不回;电话,电话不接;钱,钱你也不给,你还养不养你老子了?她实在不想再说下去,一提到钱她这老子是永远挂不了电话的,除非她答应给钱。不是没给过,只不过给了钱他不但开销了自己的吃喝拉撒,还得管跟他同居寡妇的吃喝拉撒。要真是这样,她也就认了。最令余文霜愤恨的一点,是他喜欢去赌钱,赌一次输一次,赌十次输十次,他是越赌越输,越输越想赌,好像就图个心里快活。开始余文霜也想不明白,后来她一想也对,反正老子赌的是她给的钱,他自己那点低保也够他存到老了。原本指望找回个寡妇能替她把老子收了,结果人家儿女一召唤,寡妇二话不说抬腿走人。这不能怪人家,寡妇毕竟不是余文霜她妈,到死都能忍受他的恶习。
她老子话没说完,余文霜瞬间就把电话掐了。不仅如此,也没经过李勤允许,她手指利索地把这串号码从他手机里拉黑了。李勤一时间虽然被这父女俩搞得很无语,半天才憋出一句,其实没事,叔就是要点钱,我能给……
你能给多少?你以为你那点工资能赔得上他欠的赌债?她满口火气说着,以后不许你跟他联系,他的事跟你扯不上关系。
怎么扯不上关系?以后总归要成为一家人的。李勤说话声逐渐变小,害怕余文霜听见。
抹茶拿铁今天换上一套黑色带豹纹边的卫衣,脸颊雪白粉嫩,两片嘴唇依然是颜色暗淡的姨妈红。除了墨镜之外,她今天还戴了一顶与卫衣搭配好的豹纹鸭舌帽,帽舌被压得很低。她坐在教室最后双手交叉握紧,握到双手青筋都已暴露在外。桌角上的咖啡还没喝一口,就凉得很快。她的眼球在墨镜内焦虑打转,最不安分的是她今天的心脏,从坐下那一刻就如锣鼓喧天般在身体里狂跳不止。是的,她一直期待已久的吴华星,还有几分钟就要出现了。
中午她坐了八九站地铁去买咖啡,地下的黑暗扫过她忧虑的神情。李勤突然在这个时候打来了电话,告诉她说,他今天感觉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调成了下午的班,晚上就不能陪你了。他停顿了几秒,又说了一句,我刚刚经过酒店大厅看到一个戴鸭舌帽的女孩,似乎很像是你,就是穿着打扮跟你不是一个风格。她握紧手机,眉头微皱,心头猛然一紧,结巴地说,怎……怎么可能是我呢,我这会还没出门呢。李勤在电话里控制不住咳嗽了一声,自嘲说,对啊,我想也不可能是你。看来我今天真是头晕眼花了,不仅把你看错了,还看错另外一个。她松了口气问,谁啊?李勤歇了半晌才出声,有点像那个衣冠楚楚的禽兽!但是应该不可能会是他,没那么巧的事情。余文霜知道他说的是谁,是他那个快十年没见面的父亲。李勤的父母在十多年前就分开了,他父亲当年为了奔更好的前程,不惜抛妻弃子一个人去了大城市,李勤懂事开始就暗自发誓,这辈子绝不认他这个父亲。
很快一个声音从教室最前方传来,让我们欢迎吴华星教授为大家授课。随之,周围掌声四起。没有人注意到此刻那副墨镜后面,一汪泉水正在沸腾。那一下午的课,是她这几天以来听得最入神的课,换句话来说,这是她回忆最入神的一下午。
那年,她还是扎着两束乌黑羊角辫的时候,有一天上课铃打了许久,教室里鸦雀无声,只有她在教室门外徘徊,因为和家里发生了矛盾,挨了父亲的打,以至于上课迟到。她不敢走到教室门口喊报告,却又没地方可以去,只能可怜兮兮蹲在窗户下面等待老师下课。这时候隔壁班的青年老师吴华星正巧经过,看到这么一个小女孩蹲在那里,以为是犯了错,被老师撵出来罚站。她眼睛红红地对他说,我迟到了,不敢喊报告进班,害怕老师批评我。吴华星说,你这样旷课就不怕老师批评你了?他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余文霜。他想起这个名字好像最近在哪儿才听过,这下让他原本严肃的脸变得温和了一些,他把她带回办公室。她站在办公桌前不敢动弹,也不知道怎么就跟着他来了办公室,但是学校老师的话,她总不敢不听。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叫她搬过来坐下。接着从一摞作业本里翻出一本作文本,她认得很清楚,那是她上周交的作文本。他翻开本子,递到她面前,突然展开笑颜说:你的作文写得不错,你们语文老师给我看了,我正准备拿到我们班上去借鉴一下。然后他问,你今天是怎么了?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在一段黄昏下,他们交往多了一些。他觉得,十五六岁的孩子作文里能写出一些有关哲理的东西是不简单的,一个人的悟性如果能体现在她的文字语言里,那必然是不可多得的。吴华星对她的态度越发亲切温柔,似乎已经超出了对他自己班学生的关怀。放学路上,吴华星推着自行车,余文霜小心翼翼地走在他身边。她会问吴华星,老师,您觉得我以后能考上大学吗?他特别笃定地回答她,能啊!你怎么会考不上大学呢?如果你以后成为一名作家就更好了。她放慢脚步害羞地笑了笑,小声呢喃着,我要是在您的课堂上就好了。十几年前,她感觉前方就像背后的黄昏一样充满无限希望。她的脸又一次被照得通红。
她坐在最后一排,望着吴华星在讲台后面讲解分析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说这是圆形写作手法。她悄声拿起桌角上冷掉的咖啡,想他说得没错,万物其实都是圆形的轮回。然而,她那年终究没能考上大学。人生往往总是祸不单行的,她没考上大学,除了她自己,家里并不觉得可惜。将来出去打工是父亲早就给她定好的命运,用她父亲的话说,你就这命,考大学,还想当作家,你数数脚趾头也明白是痴人说梦。母亲去世后,余文霜大笑父亲还知道痴人说梦这么文雅的词。余文霜说,她未必是痴人,可父亲必然是做梦。
她和吴华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毕业典礼上,她坐在礼堂最后一排,吴华星发言结束后,绕场半圈坐到她旁边。真的就这么放弃了?他问。她眼神发痴,不一会儿泪眼婆娑。他把手谨小慎微一点点移到她的手背上,不到一刻工夫,余文霜冰凉凉的眼泪一滴滴落到了吴华星的手背。
此刻,她正痴痴望着吴华星在仅离自己一米讲台上侃侃而谈。他老了,眼袋下垂了,应该也有些许白发。一阵热烈答谢掌声后,前面的那些人稀疏散去。她缓缓起身,桌角上留下大半杯没喝完的咖啡。她取下鸭舌帽,摘下墨镜,静静悄悄迈出庄重的步伐,向低头收拾讲义的吴华星走去。他恍惚抬头注意到她豹纹边的卫衣,她终于与他四目相对,一双热泪眼看就要溢出。
这时,外面一阵推车闲杂声逐步逼近,李勤和一起打扫教室的服务生说笑着走了进来。忽然之间,他们几人面面相觑,李勤睁大眼睛吃惊不已叫道:文霜?另一边吴华星喜出望外脱口而出: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