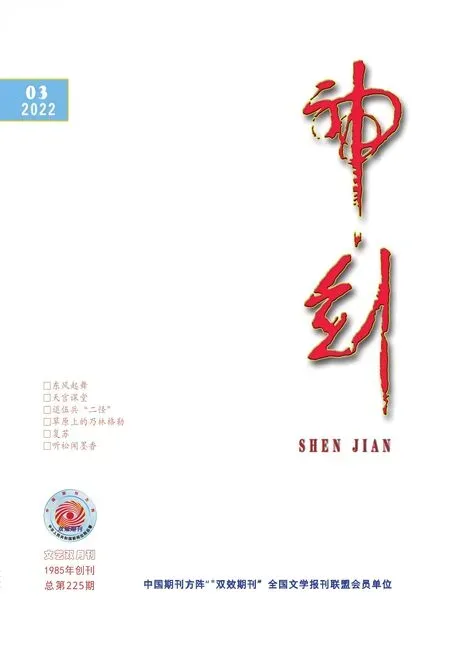退伍兵“二怪”
□李 芳

陈拐弯村不大,但村里的退伍兵却不少。在村里这一堆退伍兵中,最牛的人就数陈铁棒,退伍回村后,竟然当上了市委宣传部的部长,混成了处级干部。村里人都知道他在部队会写文章,他退伍回来后,被招聘到乡里当通讯员,慢慢地就混出名堂来了。还有,陈小二在部队是个喂猪的,回来后办起了养猪场,现在混得也不错。那个陈六一,在部队是个烧火做饭的,现在都成了县“白金汉宫大酒店”里的大厨了,据说一个月工资三万多块。还有王一横、刘一撇等,虽然事干得不太大,承包鱼塘,租地种草莓,一年收入也十分可观,在这些退伍军人中,唯独有一个人,除了拿点政府给的补助外,啥事都不干,就守着自己的几亩薄地,只要撑不死,饿不坏,就十分满足了。这人叫宁忠实,村里人都叫他“二怪”,让人几乎都想不起他是退伍军人了。
这个退伍军人宁忠实,可是陈拐弯村出了名的“二怪”。说是“二怪”,其实,三怪,四怪都不止,村庄的名字听上去都有些怪怪的,在皖北一带,村名多以“营”“庄”而取。比如:张营,张庄等,哪个姓氏人多,就把姓氏放在前边。如果张庄多,咋办?前张庄,后张庄,张大庄,张小庄。村子带拐弯却不多,怪村出个怪人也不稀奇。据传,原来这个村有一户陈姓人家,从山东枣庄迁徙而来,走到安徽境内的阜阳县地界,忽然眼前一亮,发现了一块风水宝地。前边有一条河,一打听,原来这条河叫沙河,据说发源于河南桐柏山,一路奔来,流经安徽。住在下游的人家,都称这条河为颍河或沙颍河。在沙河段的拐弯处有一开阔的浅滩,中间隆起,平坦而呈梯形,正适合居住,于是,陈姓人家便安顿下来。因最先居住在这里的人姓陈,村庄的名字就依照沙河的流向而得,陈拐弯村就因此有了烟火人家。一代人又一代人在这里繁衍生息,陈姓成了大户,也不知过了多少代,后来,中国命运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阶级成分划分,陈姓多地主。之前,因种地需要雇工,这里有了杂姓。宁、王、刘等姓氏的出现,让陈拐弯村这里更加热闹纷繁,人际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宁忠实的爷爷那一辈逃难来这里给人种地,落户陈拐弯村,而宁忠实就是从陈拐弯当兵走出去的。可他当了几年兵后,又回到了农村,由于生活方式改变了,村里人都说他当兵当怪了。人们最初说他怪,只是从生活习惯说起。那个时候,村里就一口井,全村人几乎都从这口井里挑水吃。宁忠实刚回来那会儿,经常在早晨脖子上挂一条雪白的毛巾,上边还印着红字。村里的老人多不识字,就问小学生,那个当兵的,毛巾上
一行红字写的是啥?学生告诉说,将革命进行到底。老人嗯了一下,就不再言语了。宁忠实搭条毛巾,嘴里还哼着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嘴里哼着歌儿,手里端一只盆,还提着一只小桶,来到井边,眼睛清澈地把小桶慢慢放进水井里,水桶碰着井壁,发出叮咚声,在井里产生着回音。站在井边的宁忠实,轻轻晃动系在水桶上绳子的一端,然后往下用力一趸,正在摇晃的水桶翻了个底朝天,把井绳快速往上一提,灌满一桶水。在土井里打水,那是需要技巧的,自幼在农村长大的宁忠实,当了几年兵,这点儿技巧是不会生疏的。宁忠实把盛满水的水桶放在井沿,然后从盆里拿出一只绿色牙缸,舀出刚打上来的井水,还带着清凉的味道,然后,他又把牙刷捏在手里,摸出一管牙膏,挤出豆粒大小,摊在牙刷上,有人说还没有小虫意(小鸟)屙的屎多。慢慢腾腾,多有一袋烟工夫,才蹲在井边,左左右右地歪头刷牙,弄得一嘴白沫,难看死了。村民看不惯他这种做派,说他是作洋怪。那个时候,全村人刷牙的不多,也就是上海下放知青和退伍兵有这些毛病,村里人把习惯说成毛病,有厌恶之意。宁忠实还有一怪就是一年四季,离不开棉衣。三伏天,别人热得恨不得扒下一层皮,他还穿着一件老式的从部队带回来的“光屁股”对襟军用棉袄,跟电影《创业》里石油工人穿的那种棉衣一样。村里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说,暑天里穿棉袄是有说头的。说,过去后庄有个叫刘老赞的地主家,家里雇的一名长工,三伏天就穿着一件“光屁股”薄棉袄下地锄秫秫(给高粱除草)。暑天里钻进高粱地里干活是啥滋味?真能把人热毁。可是,长工身上的棉袄,成了降温解暑的“宝贝”。锄完一趟子地,他把浸透汗的棉袄脱下来,拧干浸在棉衣里的汗水,再穿时身上就凉飕飕的,得劲哩很。那是干活的长工,可“二怪”三伏天干不干活都不会出汗,棉袄成了他的“贴身铠甲”。再一怪就是常年不剃头,说穿了,他头上根本就没有毛可剃。当兵回来那年,还一头黑发,渐渐地,他头发越来越少,最后都成了一个锃亮的大“灯泡”了。
有人问他:“‘二怪’,也没听你说过你当兵时在部队到底干啥工作,看你弄得像个啥?一年到头就跟你这身棉袄有缘,舍不得脱。头秃不说,你也干点啥嘛。人家往当场一偎,只要一说自己当年在部队,一个比一个能吹。王一横说起他们部队会餐,从连长到小兵子,都是用碗喝,东北兵嫌碗不过瘾,干脆把酒瓶盖用牙咬开,嘴对“嘴”就灌起来了。说连队包饺子,用啤酒瓶擀面片,供一个班的人包。那包饺子的速度,饺子都像是从手里往外扔一样快。刘一撇说他在连队养猪,都是用哨子唤它们吃食。更邪乎的是,有一天,说他正在猪圈打扫卫生,他们军长在师团干部的陪同下,到连队视察,竟然提出要参观一下养猪场。因为军长当兵时在连队养了一年半的猪,所以,他每到一个基层连队,看养猪场是必须的。之后,军长还会和饲养员一起合影留念。那次,刘一撇在参观他的养猪场时,被军长问住了,憋了个大红脸,也没能回答出军长提出的问题。军长问道,小鬼,你知道母猪都长几个奶头吗?谁没事研究母猪长几个奶头呢?军长就研究过。见刘一撇站着发窘,就拍了拍他的脑袋说:“记住,小鬼。一般情况下,母猪都长七对奶头。”在场的师长、团长都笑了,可刘一撇也把村上的人说笑了,都说,要不是刘一撇在部队上养猪,村里人一辈子都弄不清楚母猪长几对奶头。村里人常说,没吃过猪肉,还没有见过猪走吗?这是说一个人没有见过世面。可多数人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就是不知道母猪长几对奶头。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见过外面的大世界。“二怪”就不像他们了,根本就没有见过猪走,看来猪肉吃得也不多。村里人对他说,像咱庄的王一横,养猪,刘一撇,烧饭,陈铁棒,连队文书,就你的嘴跟贴了封条一样,从来都没有说过部队上的事。“二怪”眼一瞪,反问道:“管我当兵干啥哩,还非得让你知道?你又不是部队首长。”更怪的事就有点涉嫌“二怪”的个人隐私了。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子嗣,有人说怪他老婆,那几年,他老婆中药可没有少吃,跟人在一起,身上的中药味儿都往外窜,生产队里没有人愿意跟她一起干活。真是吃不少苦,不见肚子鼓。后来,又有人说怪“二怪”,是他没有后。啥叫没后,就是没有生育能力呗,传说与他当兵有很大关系,真假不知道,估计这一点是胡说八道了。
村里退伍兵中,有人拿定补,一季度好几千块,说是带病回乡的补助。定补的钱也是最近几年才翻倍地往上涨的,前些年,一个月才百十来块钱。不管钱多钱少,“二怪”没有这种定补,他拿的是另外一种政府补贴,叫特种部队退役军人生活补助,但这种生活补助也是近年来政府才发文给的,也不过七八年的时间。如果不是有人在民政部门看到他的册子,谁也不知道当年的宁忠实在特种部队当兵。什么样的部队才是特种部队呢?村里人不知道,都知道他在一个大山窝子里,从当兵走一直到回来,家里就收到过他一封信,下边也没有个地址。当兵前村里人还都喊他宁忠实,回来后,身上一年四季都罩着军用棉袄,都觉得他是一个怪人,哪里还像一个退伍兵?更怪的一件事,让村民无法理解。上个世纪电视还没有进入普通人家,一个村有一台黑白电视,几乎成了全村人的露天“电影院”。一次,电视新闻里播放一条我国又成功发射一颗卫星的新闻,挤在人群中看电视的宁“二怪”,居然站起来,对着电视机举手敬礼,直到新闻播放完他才坐下来。有人说,那是电视机,你给它敬个啥礼?“二怪”也不解释,就说,我想敬礼了呗。他的这一举动,又让村民看到了宁忠实的怪。
土地承包后,民风就开始有点变了,一些人只往“钱眼”里钻,横着膀子走路的人越来越多了。民选村长,有人推荐宁“二怪”,说他是退伍军人,性情耿直,这样的人当村长,身上有正气,能镇住那些“二不赖”。虽然没当上村长,他还是进班子成为民兵营长。当上村干部,他只对带兵参加县人武部组织的基干民兵训练感兴趣。每次带队参训,不管是队列会操还是打靶射击,每个项目的第一都被陈拐弯村的民兵拿下。县人武部领导,军分区领导都看重宁忠实这位民兵营长,建议配他当村书记。可是,宁忠实却在跟村民要提留时一点都不上心。其他干部都是上门催,有的甚至“逼”,他对于那些没有钱的村民,给出缓交时间,谁知,这一缓都没个期限。每次乡里兑现提留款,他们村都是倒数第一。村长每次挨批,都在乡长面前给“二怪”上“烂药”,当过兵的宁“二怪”,不受这窝囊气,他干脆辞职不干。村民对他自动辞职村干部还是有点看法的,说这个“二怪”,干部不想当,还想干啥?别人都挤破头地往里钻,他却说不干就不干了,要知道,村干部虽然小,多少还是有点“油水”的,大小当个官,强似卖纸烟嘛。从村级领导位置辞职下来的宁忠实,本想到镇上去卖包子、稀饭或炸烧饼、油条,可他起早摸黑身子吃不消,也就打消了做生意的念头。于是,他就窝在家里种自己的二亩地。好在他当过兵,头脑还算灵活,麦地里套种菠菜,一开春就卖好价;玉米地里套种豆角,一亩地比别人多收好几百块。再养几只羊,几头毛驴,也有小钱赚,日子过得不算差。悠闲自在的“二怪”,没事的时候,也喜欢哼哼歌曲。当然,他唱得那些歌曲都是老掉牙革命历史歌曲。不是《打靶归来》就是《我是一个兵》,有些歌曲他连词儿都记不全,但他却唱得很认真,尽管唱着唱着跑调儿,或者串了调儿,自我感觉良好,反正是一个人哼哼呗,又不是上《星光大道》。后来,又出了一首新歌叫《咱当兵的人》,“二怪”最爱听的就是这首歌,他只会前几句: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头顶着边关明月,脚踏着雨雪风霜。他在唱时,把脚唱成“足”,把风霜唱成“风箱”。因为词儿不准,调也唱走了样,会唱这首歌的人,听了就想笑。
“二怪”在部队到底干啥工作成为村民心里的一个谜,越来越吊起一部分村民的好奇心。他的那个特种部队,总让人觉得有些神秘。
有一次,村里有两个人抬杠打赌,一个说,你要是能从“二怪”嘴里掏出来他在部队干啥工作,他能跟你吐出半个字,你去哪里吃,我就在哪里请你,饭店里的菜,尽你点。
真的?
一言为定!
且看这两个打赌的鸟货到底用啥办法从“二怪”嘴里掏出真话。
请他吃饭,把“二怪”灌到二八盅上,这办法根本不行,因为,“二怪”不喜欢喝酒,即使喝点酒,也是抿一小口,雨过地皮湿,从来就没见他醉过酒。
“二怪”养驴最上心,每头毛驴都是他的“心尖子”,几乎他每天都给几头驴梳毛。驴子也怪,如果哪一天“二怪”不给它们梳毛了,几头驴会高一声低一声地“昂叽昂叽”的叫唤,像是在叫“二怪”来给它们梳毛。有的毛驴是犟脾气,如果有陌生人靠近,就会尥蹶子踢人。不管几头毛驴有多犟,只要“二怪”一来,用竹扫把在它们身上从前往后呼啦几下子,每一头毛驴都低头顺耳地打着响鼻,表现出十分亲昵的样子来。有一天晚上,突然刮起了大风,把“二怪”饲养棚的木门拍得直响,几只吊着的电灯,也明明灭灭地晃动着,几只羊也惊得咩咩叫,槽上拴着的几头毛驴也惊恐不安起来。“二怪”过来,随手抄起一根棍子,指着惊恐的毛驴们说:“刮一阵怪风,有啥可怕的?又不是把你们牵卖了,都给我老实些,谁给我把绳弄开了,就先把谁卖掉。”几头毛驴似乎听懂了“二怪”的话,一头比一头老实,没有谁再乱踢乱动了。重新把门关紧,“二怪”就回屋睡觉了。他的一举一动,被远处一双眼睛牢牢地盯着,这个人,就是试图想从“二怪”嘴里掏出他当兵时在部队做啥工作的打赌人。
“二怪”躺下刚想闭眼休息,他突然感觉像要发生什么事,就有点睡不着了。这时,他又听到驴棚里有异响,人还没有坐起来,只听一声“哎哟”,像是有人被什么东西磕碰到了,声音还有点痛。“二怪”几乎是从床上跳下来,那个麻利哟,哪像是一个夏天棉衣人庄稼汉?只有在部队搞过夜间紧急集合的人,才有如此身手。
去年冬天,应该是一个暖冬,可是,突然就冷了起来,冷到令人就没有思想准备,甚至有人责怪电视台播报天气不准。这一冷不要紧,手套、耳捂子以及电热毯,凡是能够御寒的商品,从小到耳捂子,大到鸭绒被,很让商家在短时间内大赚了一把。当然,气温骤降,水面结冰,这给乡村孩子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溜冰场。老一辈人说,早些年的时候,至于早多些年,反正都很遥远。那时有多冷,对于地球正在变暖的今天,毫不夸张地说,过去都是草房子,房檐上都挂满一排排冰柱子。雪停天晴,太阳照在房顶的积雪上,融化的雪水,顺着冰柱往下淌,雪水还没有淌下来,又被冻结住,冰柱也由细变粗,由短变长,调皮的孩子用棍子横向一敲,哗啦啦的脆响,像是断弦的琴声,尖锐刺耳。
现在,池塘猛然结冰,孩子们用棍子敲击冰面,像是把棍子打在石头上,连一个印子都没有凿出来,有人试着在上面走了走,冰层很厚很结实,人走上去一点事都没有。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开始下到结冰的坑塘里溜起冰来。这口结冰的坑塘,面积很大,也很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有人在承包地上建窑场时取土挖成的大塘。当然,现在不允许再乱挖可耕地烧窑了,烧砖的窑被取缔拆掉了,但土地被挖成了大坑,永远都不能恢复了。“二怪”那天去镇上给他的毛驴买饲料,天冷,人要吃好,驴要吃饱,经常在粗饲料中加点精饲料,这样,驴长膘,过了年,能卖个好价钱。经过坑塘时,“二怪”看到好多孩子都在溜冰。他小时候也在冬天溜过冰,还在冰面上打过陀螺,推过铁环,现在很少有孩子玩这些了。正在他一边骑着车子,嘴里一边哼着《我是一个兵》的歌:我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革命战争培育了我,立场更坚定。哎嗨两个字还没哎出来,他就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了。这个“二怪”就是怪,别看他嘴里不停地哼着歌,耳朵还能听到其他声音。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丝冰面裂纹的声音,他脚下用劲,把车子蹬得飞快,一手扶把,一手朝孩子们挥动,大声喊道:“快趴倒”!孩子们都玩得痛快尽兴,根本就没有听见他的喊声。这时,只听咔嚓一声,冰面破裂,孩子们都向岸边跑,但还是有两个孩子跌进了冰窟窿里。
“二怪”扔了车子,他三两个箭步飞奔过去,甩掉军大衣,里面的棉衣顾不上脱去,就跳进冰冷的坑塘。活脱脱上演了一场悲壮而又感人的中国式罗盛教勇救落水儿童的故事。
天寒地冻,冰层也有点厚,而破碎的冰块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把“二怪”的衣服划破,皮肤也刺出了血,他每向前游动一米,身后都有一片殷红的血,染红的池水像一条红色的带子紧紧地把“二怪”拴住,生怕他滑入冰窟出不来。棉衣浸泡冷水后,像厚重的铠甲裹在身上,“二怪”在冰水里艰难救人。开始他还奋力向前游去,越向前游越感到呼吸困难,像有石头绑在身上,身子渐渐在往下沉。第一个孩子被救出来时,“二怪”冻得下巴壳子打着哆嗦,浑身已经没有了力气。有人在上面喊,还有一个呢。另一个孩子离他很近,往前再游一点,就能抓住孩子的衣服,可是,“二怪”像是被孙悟空施了魔法给定住了,感觉自己已经坠落万丈深渊,又像有万枚钢针在猛刺着自己的肌肤。他几乎被冻成冰人,想往外吐口热气,嘴巴都张不开。他已经感觉不出刺痛,似乎身子轻飘飘的,他这是麻木了。冥冥之中,他又看到了身边的战友,班长、排长都在喊他:宁忠实,你不能睡着了,你要坚持住,坚决完成任务。“二怪”不知从哪里迸发出一股力量,他用力向冰层下的小孩子靠近,伸手抓住了孩子的衣襟,紧紧抓住不放。等村里救援的人跑来,把孩子连同他一起救了上来。那次救人,“二怪”又留下了膝关节疼痛的毛病,他说,这跟部队没有关系。也就是他宁愿自己忍受疼痛,苦自己一点,也不给政府添乱的原因之一。其实,没有那次破冰救人,“二怪”的身体健康状况与一般人比起来,还是差了些。体质差的人往往意志是坚强的,关键时候,当兵人的那种果敢与顽强,是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这就是军队熔炉铸造出的钢筋铁骨。
睡不着的“二怪”强迫自己眯上眼睛,有一种开门的声音从夜色深处钻进了他的耳朵,他警惕地翻身坐起。这时,他听到驴棚里传来一声“哎哟”,不好,有人要偷他的毛驴。他跳下床,冲出屋就往驴棚跑去,这时,他看到一个黑影,朝院外逃窜而去。别看“二怪”有些腿疼,他跑起来,依然像流星一样划将过去。当然,被追的那个黑影也快如闪电,“二怪”终究撵不上他,也许是那个黑影活该栽在“二怪”手里,本来,“二怪”就放弃追赶了,正要放慢脚步时,只听“扑腾”一声,黑影像一只沉重的布袋被摔在了地上,“二怪”几步跨过去,举起铁锨,正要猛劈下去,只听一声:“姐夫,别打,是我”。掏出打火机擦亮火光一照,“二怪”大吃一惊,气不打一处来,喝道:“猫油,怎么会是你?”
原来,被“二怪”生擒的这个人就是他的小孩二舅子。他当然知道“二怪”腿脚不好,根本撵不上他,即使把他给逮住了,也不会把他怎么样。这就是他敢打赌的理由,要不是念在本村人的情面上,“二怪”就是不打他,也要把他送到镇派出所。
这深更半夜地,你给我搞什么鬼?
他看坐在地上的猫油,手一直捂着头,“二怪”就问他,你捂着头干啥?
猫油说,我的脑袋被驴给踢了。
骂一个做事迂腐的人,常用你脑袋被驴踢了这句话讥讽,看来,现实生活中,还真有人的脑袋被驴踢了。猫油不就是嘛。
“二怪”心想,这不是找活该吗?但他没有说出来。
当猫油跟他说出事情的真相时,“二怪”哭笑不得,说,你们真是无聊透顶。打赌掏我嘴里话,居然大半夜地牵我的驴,我还以为这是偷盗呢。跟你说,我要是出手狠一点,手里拿的这个家伙,说着,他晃了一下手中的铁锨,已经从地上爬起来的猫油,头往一边歪了下,还真怕“二怪”给他一铲子。“二怪”接着说,我是在特种部队练过武的人,万一把你弄个好歹,你这辈子算是废了。我就是一个当兵的,没有你们想的那样悬乎。特种部队自有特种部队的规矩,我不能破坏部队的规矩。能让你们知道的,我也可以云里雾里吹嘘一番,不该我说的,你就是把我用热油炸了,从我嘴里也难掏出半个字。从那以后,姐夫半夜捉小舅子的笑话在就村里传开了,说,一个当兵的,这么神秘兮兮的。越传,“二怪”就越怪了,都把“二怪”传神了。
“二怪”没有孩子,哪来的小孩二舅子?
原来,陈拐弯村杂姓多,村里人通婚是很自然的事。宁忠实的媳妇就跟他一个村,还是当年双双老人给定的娃娃亲呢。两人不是不生育吗?“二怪”曾抱养过一个孩子,是邻村他旁门小姨子家的男孩。也就是说,这个小姨子跟宁忠实的媳妇是堂姊妹。一个不生,一个生多养不起,就送了他。当然,孩子长七八岁,已经很懂事了,小学3年级,可能因为“二怪”对他学习管太紧,考试成绩差,打了他几次,孩子赌气又找他亲爹亲娘去了。有人说,这“二怪”,孩子不是亲生的,下手狠,自己不生,抱养一个,也被他打跑了。“二怪”也去跟孩子沟通过几次,孩子就是坚决不回来,这让“二怪”自责了好久。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关乎孩子跟父母的亲密度,当过兵的宁忠实,自然没有很好的教育方法,更没有很好的教育手段。好在孩子大了,还经常回来看看,当个亲戚走了。
关于“二怪”,还有呢。每年的“八一”建军节,退伍兵都喜欢参加战友聚会,可“二怪”好像就没有战友,跟没当过兵一样。可有一年建军节,有看见“二怪”自己一个人,把收藏的军装又翻箱倒柜地找出来,重新缀上领章和帽徽,穿得周周正正,在自家院子里,一会儿跑步,一会儿又踢又跺脚的,嘴里还喊着“一、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口令。自己一个人过起了建军节,看见的人都说,这“二怪”又在弄景致呢。有人猜测,“二怪”在部队怕是受过啥处分,不敢见战友,都说新光棍怕老邻居,万一有人揭他的老底,那不是更没脸见人了吗?所以,回来几十年,他一次战友聚会都没有过。之前,也有战友来找过他,要他参加一次去北京的上访活动,说是维权。当然,这个找他上访的战友,是“二怪”在街上卖菜时认识的,也不是同年兵。后来,“二怪”怀疑他是不是真正当过兵。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与退役军人明显不同。“二怪”不是春卖菠菜秋卖豆角吗?那次他用一辆人力三轮,装满一车斗菠菜来到菜市,正好旁边也有一个卖红芋的人,两个人互为“邻居”,一边卖菜一边叙话,咋恁好,两个人都是退伍兵。既然都是当兵人,两个人越叙话越多,末了,“二怪”说,兄弟,没事的时候,到我家里坐坐。也不知道“二怪”当时客气呢还是真心话,战友可当真了。没有多长时间,那个人还真找到了“二怪”家。进屋坐下来话还没几句,他就要求“二怪”跟他一起去上访,说他已经联系好几名战友了。“二怪”问道,他们都愿意跟你一起去吗?那人回答说,十个有八个不愿意去。“二怪”有点不悦地道,你咋就知道我愿意参加?那个战友听“二怪”这样回答,立马笑着说,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
那人也是一个“硬头钉”, 坚持要维什么权,“二怪”劝说不听,被“二怪”给赶跑了。对他怒喝道:“你不要给我们退伍兵丢脸抹黑,我就怀疑你有点冒充,下次再敢到我这里来,我就拧断你的腿!”那人灰头土脸地走了,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拉他一起上访的战友来过。知道他的人,说“二怪”始终是军人本色,主持正义和公道,不知道的人,还说他没有战友情呢。“二怪”就是“二怪”,他可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怪呢,反正,这也怪出名了。宣传部长陈铁棒对他的看法一直很好,也非常尊重他,每次回乡都找“二怪”啦啦呱。就有人问铁棒部长,你跟“二怪”又不是战友,比他还早当几年兵,咋就跟他近乎?
陈铁棒说,你们有所不知,宁忠实是位功臣,搁在过去就是忠臣,他可没有取错名字,忠臣首先要忠实,只有忠实的人,才能配当功臣。在部队立过二等功的他,本来是可以安排工作的,因为和平时期,国家有规定,退役军人,平时二等功,战时三等功,政府给安排工作。他是家里的长子,那个时候,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在上学,忠实的父亲是个瘸子,一家人全靠母亲一个人挣工分养活,太累了。忠实是个孝子,退伍那年,他主动放弃政府给他安排的工作,自愿回乡当了农民。
有人就说,就他那老实巴交的熊样,还能立功?铁棒部长说,忠实居功不自傲啊,不管家里有多困难,他从来都没有跟政府摆过谱,也没有向组织伸过手。后来国家出台政策,像他们这些为我国卫星发射做出过特别突出贡献的老兵,才有了政府发给的特殊补贴。
乖乖,这个“二怪”原来搞卫星发射的啊,咋就没有听他说过呢?
陈铁棒说,军人只要从事过特殊职业,都有纪律要求,有些事,就是烂在肚子里,连半个字都不能往外说。像忠实这种人,即使退伍了,也得有十到二十年的脱密期。怪不得宁“二怪”从来不提他当兵的事,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功臣。
去年,村里来了一个白净的老头,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年轻,一老一少,一前一后,进村见人就问,村里有叫宁忠实的人没有。
这老头身板硬朗,目光有神,走路步子迈得跟别人都不一样,那派头像是从哪里来的大干部,见人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让人感到很亲切。这一老一少,见从村里出来一个骑电动摩托的年轻人,老头非常和善地问眼前这个烫一头红毛的年轻人。摩托没有熄火,年轻人一只脚点在踏板上,另一只脚撑着地,非常认真地对他摇头说不知道。老头又说,他以前当过兵。年轻人回答,我知道俺们村当兵的人多,有的不在家,在家的几个人,没有谁叫宁忠实。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走过来说,不就是“二怪”嘛。
听到这话,老头很兴奋,连连拱手对提供信息的人说:“太感谢你了,能不能带我们去他家?”那人说,我这里还有点事,说着,他往不远处一个宅院指了指,对老头说,离这不远,看见没有,就那个带门楼的小院子,门口栽着一棵皂角树的那家就是,你一喊“二怪”他就开门了,一般他不会到哪里去。
一老一少按照那人指点,很快就找到了“二怪”家。院子不小,但大门没有锁,一扇关着,一扇半开,从院子里飘出一股股的驴屎蛋子的粪便味。现在养驴的人少了,“二怪”养驴也有了经验,驴肉在市场上价格攀高,驴肉火烧店天天客满。因此,养驴是“二怪”的一项副业,也是主业。以前农村治安环境不好,有人专偷两条腿的鸡鸭,四条腿的牛、羊、驴,自从那次他追赶猫油之后,说要不是本村熟人,他一铲子下去,就削了他的半个脑袋,“二怪”也因此成了传奇式人物,一般人不敢打他的主意。这时,闻到呛鼻子的驴粪味道的年轻人耸了耸鼻子,往后缩了缩,老头就一脚跨进了门槛。老头进了门来,没有看到人,他先问道:有人吗?
没有人应。接着又问:这家院子里有人吗?
虽然没有人应,可槽上的一头驴抬起头来,昂昂地叫了几声,像是在告诉这个老头,有的,有的。
听到驴叫,这时,从驴槽底下钻出一个人来,光秃秃的脑袋,松垮垮的眼皮,像一只半风干的老倭瓜;一件军用棉袄上粘着几片柴草,一肩高一肩低。“二怪”看到自家院子里站着一老一少两个陌生人,愣了半天,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那老头眼睛紧紧盯着“二怪”,仿佛在看外星人一般,他们两个相互间谁也不认识谁。还是那老头说了一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像是当年地下工作者接头暗号一样,这话一出口,“二怪”眼泪出来了,两人同时都看出对方是谁了。“二怪”把手里抱着的扫把扔在了地上,上前一步,人才到跟前,眼泪就刹不住车地往下流,他紧紧地抱住老头的膀子,委屈得像一个孩子,嘴里一个劲地叫着“班长,班长,你咋会在这里,这不是做梦吗?班长,我可想你了啊,做梦都在想你”。原来,眼前这白净的老头曾是“二怪”的班长,比“二怪”早当两年兵。只是“二怪”超期服役一年退伍了,之后,跟部队多年都没有了联系,班长却成为一个军区的司令员。他寻找宁忠实多年,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但他只知道宁忠实是安徽阜阳县人,至于阜阳县哪个公社大队,他就记不起了。由于行政区划,阜阳县早已从省、市地图上消失。阜阳市划为三个区,宁忠实所在的村庄是颍泉区最偏远的地方。他退休前借机到安徽省军区检查工作,通过军分区人武部系统,终于找到了宁忠实本人,这时的宁忠实,已经年近七旬。
放开老头的肩膀,“二怪”说,老班长,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你咋找到我这里的?
旁边一直站着的年轻人,看到两位老人如此亲昵,他也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这时,从外边进来一位提篮子的老太太,满头白发,篮子里是刚从地里薅回来的青菜。她见院子里来了两个陌生人,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还是老头反应快,就问宁忠实:“我没猜不错的话,这位就是弟妹了?”
宁忠实这才缓过神来,笑着把老婆介绍给老班长。
听说是忠实的班长,看着比自己两口子还年轻的白净老头,“二怪”老婆放下篮子,说:“叫我嫂子吧。”
别站着说话,快到屋里坐。老太太礼让着说。
这时,站在一边的小年轻提醒道:“首长,到时间了。”首长?“二怪”惊讶了。
在一旁的“二怪”媳妇对年轻人嗔怪道:“这孩子,上午说啥都不能提走的事,忠实夜里做梦都喊班长班长的,几十年没见面了,喝口热茶也算是在俺家吃饭了。”
不一会儿,一辆军车停在了“二怪”家的门口,跟在军车后面的是刚才那个骑摩托车的“红毛”小伙子,他走进了院里,对宁忠实喊道:“俺宁大爹,你原来是部队上的人啊,咋没听说你当过兵呢?我出门的时候,就遇上这两个人,向我打听,我只知道你的外号,哪知道你叫这名啊!”说得一旁的人都笑了。
老头固然是不会在“二怪”家里吃饭的,知道了班长的身份后,“二怪”反而有些紧张了,也不敢跟老头握手了。他只是微笑着说:“班长,咱部队上的事,我从来都没有对外人说过,我们干的是惊天动地事嘛,得为党和国家保一辈子的密。”
班长对“二怪”说道,忠实,哪天想部队了,你就跟我说,带你再回去看看,那口老发射井还保留着呢,你在地道里站了4年岗,现在从地下室观察口里还能看到远处的发射架。
哦,村里人明白了,一个朝天上放卫星的地方,在地下室站了4年岗的士兵,估计他知道的事也不是太多,当年那个地方就是不被外界知道。卫星发射,在当年是一个充满神秘而又无人知晓的事业,一名站岗的士兵,退伍几十年,还这样一直都在为党和国家严守着秘密。俗话说,猪嘴好捆,人嘴难捆,意思是说,让人保密难。可是,“二怪”就是对自己当年在部队经历的事守口如瓶,想从他嘴里得到一点信息,你就是用起子撬开他的嘴,也休想让他透露半个字。
司令员姓甚名谁?“二怪”不说,没有人知道。至于他为什么要微服私访,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说多都是废话,与故事无关。司令员走后,“二怪”家里发生了变化,每年的建军节和春节,军分区和区人武部领导都来慰问“二怪”,称他为“宁老”。问他家里有啥困难需要帮助的,宁“二怪”头摇得拨浪鼓似的,然后只提了一个要求,说,他家的门头上,还差一块“光荣之家”的牌子!

马踏祥云(摄影)/玉 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