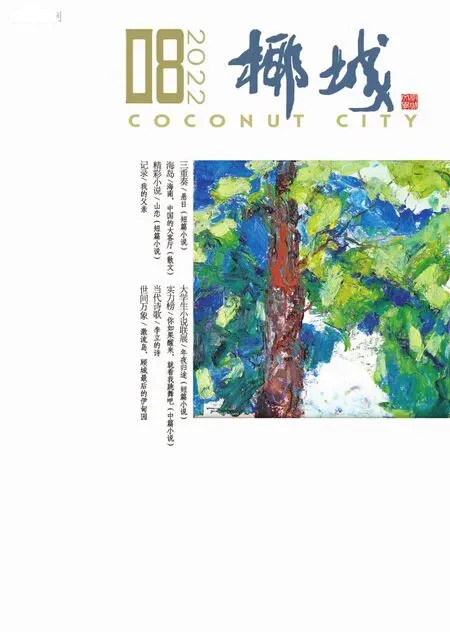悬日(短篇小说)
◎向 南
一
外公又病了。这种事若放在平常人家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家里人肯定都急急忙忙地往回赶了,而我却对此一点感觉都没有。
看着刚刚挂了电话的手机屏幕,上面显示的日期是2022年1月27日,心想:快要过年了,怪不得又有事了。
一月的桂林,风总是像泥鳅似的,你一定要穿裹严实,否则它就会从任何一个被你忽视的缝隙钻进去,在你的皮肤上游走,往毛孔里钻,直到袭入你的骨骼中,将骨髓都吸食干净才肯罢休。我骑着小电驴,慢悠悠地往家里开。天空下着小雪,我穿戴着黑色的冷帽,黑色的羽绒服,黑色的裤子,就跟那种开袋即食的芝麻丸在糖霜里滚一样。这条街的枫树早在上周就落完了所有叶子,只剩下它秃了的枝头,在夜幕的映衬下,发出一声又一声怪叫。
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冷了,也许是在为今年冬奥会造势也说不定。我顶着一头冷气回到家,刚踏进家门就看见老妈在那里收拾明天回永福老家的衣物。店里刚刚卤出来的卤货、卤水和刚刚炸出的锅烧都放在桌子上,靠近她房间那边的门口摆着一只半开的行李箱,里面装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件红色的外套,这肯定是为营造温馨的团圆而准备的。“你怎么才回来啊?慢吞吞的和你爸一样,赶紧收拾你的衣服,明早八点的车啊!”老妈还不等我坐下,就对我发令。“那你收拾呗,我刚刚电话里不是说了我不回去吗?”我反问她。老妈总是如此,只要自己认定了,便默认她身边所有人也同意了。
“你少磨唧,你外公他这次这么严重,医生又下病危通知了,不是开玩笑的。”
晕,又来了。
你一定觉得我很冷血吧,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医生都已经下病危通知了,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去看看老人,你作为他的后辈,都是应该的呀”之类的声音呢?
说实话,我也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件事情上一直这么轴。
“别磨磨唧唧的,你像不像一个男人啊?”
晕,又是这句。
也许是从小我的性格更贴近大众认知里的“女孩子”,所以老妈一直试图将我改造成她心目中的“男生”。为此我们俩经常不定期爆发注定没有结果的战争,最后也大多都是以我们俩的摔门回房结束。
不过那天,我罕见地没有因这句话顶嘴,只是把包放下,拿着换下的鞋子走到阳台,我想安静一会儿。
也是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会羡慕那些烟鬼、酒鬼,毕竟他们好歹还有一支烟或者一瓶酒来让自己或放空,或逃避。
我和外公家断开联系应该有六七年的样子,大约是在我高二的那一年吧,具体我已经不太清楚了,只知道那天回家时也特别冷,家里静得很,老爸也不在家,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妈,以为她睡着了。可任由我的喊声在家里晃荡了一圈又一圈,也没见有回应,当时我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打电话给老妈,说来也很好笑,我老爸的电话,那么多年我都还记不住,而老妈的电话,即使是在睡梦中,我也可以依靠本能拨出去。平日里,大多数情况下,她都会在铃声没有响完一轮时就接起电话,而今天,电话那头传来的只有一阵冰凉的嘟嘟的声音。
老妈是不会突然消失的,自我有记忆起,从来没有过。期间我每隔半个小时便给她手机打一个电话,在老爸回来时我问他知不知道老妈去哪了。“我怎么知道你妈去哪了。”他撂下这句话后就回房间去了。
真不知道当初老妈是看上了他哪一点嫁给他的。
直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我的手机才接到她的回电。“喂妈?你在哪里呀?”我问她,而听筒对面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说:“阿辰啊,妈现在在永福,你二姨这,明天我就回去了。”
“你去二姨那干嘛啊?”这两天是什么大日子吗?她回老家做什么?我心里嘀咕着,而当时的我还没有发现她虚弱声音里藏着的信息,只是觉得奇怪,她怎么没有住在外婆那?
“怎么没住在外婆那?”
“你别管啦,回去再说。”
我当时也没多想,老妈说完后不等我继续询问就挂了电话。可等第二天放学回到家看见老妈时,我才发现这事儿不简单。她躺在床上,面色惨白,根本看不清她的嘴唇在哪里,头发跟前几天相比枯燥了不少,在头顶中间的那一圈的发根生了白。她半眯着,黑眼圈将眼袋和眼睛一起围起来,上眼皮肿涨着,脸颊上的肉也凹了进去,本身凸出的颧骨显得更高了,嘴角还受了伤,紫了一块。“妈?你回来了?”我轻声试探着,期望得到回应,又怕吵醒她。
“回来啦。”她听见我的声音以后,艰难地撑起身子,说:“今天妈妈做不了饭了,你自己把冰箱里的饭菜热一下吃了吧。”
“妈,你这是?”不等我问出来,她就摆了摆手,打断我,说:“吃完饭再说吧。”
我将热好的菜端上桌时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后了,我朝房间里喊了两声都没有反应。我急忙过去看,事到如此,我更加确信这两天一定发生了些什么。“阿辰啊,扶妈妈起来。”似乎怕我担心,老妈用左手撑起身,一边又从自己虚弱的喉腔里断续挤出几个字来。我连忙将她扶回床上,说:“我给你把饭打过来,你就在这里吃吧。”她叹了口气,说:“也行。”
可当我将饭菜端过来时,她也只是吃了两口便将饭碗放在旁边,说:“儿子啊,妈妈和你说个事儿啊。”我愣了愣,坐到旁边的椅子上,脑子里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平时雷厉风行的老妈变成这副模样。
“你要记住啊,就算是妈妈以后死了,你也要记着把永福家里那套房子要回来。那是妈妈留给你的。你舅舅、外婆那些人都不得好死!”她咬牙切齿的样子是我从来没有在见过的,觉得陌生得很,我背后发凉,额角的汗水也顺着流下来,仿佛眼前的不是老妈,而是一只面目狰狞的孤狼,眼睛里闪着绿光,绿光里包裹着要将对方脖颈咬断的杀意。
我这辈子都忘不掉老妈这天的模样。
提到这事,就要回到二十多年前。老妈家里一共兄弟姊妹四个,我妈是家里的大女儿,往下老二又是一个女孩,老三是舅舅,而老四则是外公外婆忘记戴避孕套的产物。外公他特别看中家里小孩的成绩,可最后考上大学的就只有我妈,老二在半路辍学了,排行老三的舅舅皮得很,但得益于外公外婆的疼爱,走关系勉勉强强读完高中。
老四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时刚好赶上外公外婆经营的陶瓷厂破产,家中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还债,才让外公免除了牢狱之灾。这件事过后,家里再没有余力供养老四了,只得由着她与甘蔗田一同长大。
“阿烨啊,现在家里没有什么钱了,连房子都没有了,家里实在是困难,你看这……”外婆打电话给老妈,当时老妈已经工作,是一个效益还不错的单位,几年下来手头上也有了些积蓄。“妈,要不然我看看附近周围有没有转卖房子的,我出钱买一套下来先给你们住着中转一下。”老妈当时想也没想就开始四处联系,用自己的积蓄加上向同学借来的一些钱一起买下了现在他们住的那栋房子。
当时房价没有现在这么火热,加上当时的房主急着出手,所以价格还算是可以接受,几万块钱就拿了下来。可是谁也不知道,当时用来过渡的房子,在二十年以后会是一枚定时炸弹。
我好不容易将老妈安慰好,让她躺下,我看着闭上眼睛的她,红肿的眼皮颤得厉害,大概还沉浸在刚刚的场景里没有出来。说实话,我也还没有从刚刚老妈给我的描述里完全脱身。“妈,你先躺会儿,我给你去熬一点红糖水喝。”我那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能说什么,只能选择让自己的手不要空闲下来。
我在厨房里一边熬着糖水,将红枣和桂圆剪碎,放进锅里,一边搅拌,一边由着水蒸气爬上我的眼镜,右手机械式地用勺子在锅里画着圈,看着锅里面被汤勺画出的圈,我才慢慢地从老妈刚刚的话梳理出信息来。
二
起因是昨天在老家的朋友和老妈聊天,那位朋友告诉我妈:“阿烨啊,你们家好福气哦,住的那条街道说要道路规划,要重新翻修,政府还帮出钱。你们家赚了哦!”
我妈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个反应便是要和外婆确认,可打电话给外婆时,那边言语之间却躲闪得厉害。由于那套房子是老妈买给二老住的,可当年因为一些历史的问题,房产证上没有写老妈的名字,而当初老妈对于自己的母亲也是信任的,于是便同意先暂时只写了外婆的名字。老妈理应知道这件事,毕竟这房子在事实上也是她付全款买的,为此还背上了一笔小债务,几年后才还清。只是没想到昨天回去的时候才发现,房产证上没有她的名字,除了外婆外,竟然还有舅舅的名字。
老妈得知后气不打一处来,后来我听邻居伯娘告诉我说:“你妈那天中午到家里,看见房子都拆得乱七八糟,就和你外婆吵起来了。我那时刚刚吃完饭,听见吵闹声。你外婆也真是的,自己女儿啊!唉,这么狠……”而具体细节我也没办法求证,只知道老妈这两天恰好在例假期,和外婆争吵时急火攻心,本来身体就不好,推拉间不注意就大出血了。当时不接我的电话也是因为这,那会儿她还在昏迷当中。好在还有邻居伯娘帮打了救护车,还将她搀扶到自己家里休息一下,联系同在老家的二妹来照顾,才让老妈躲过一劫。
自那以后,老妈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她变得爱叹气了,身材也由于大出血之后需要吃药和静养变得发福起来,我帮她擦药酒时发现她的身体变得肿胀乳房却干瘪了,白头发也开始侵蚀她的头顶。她变得不再爱穿裙子和高跟鞋,时常挂在嘴边的也多是哀叹之类。她开始不再爱和外人交往,我们家也几乎和外婆家断了联系,还有联系的姊妹也只有二姨。
直到我高考之后,她与我爸离婚时,在桂林的房子也因为父亲的耍赖,老妈只能将房子都让了出来才换得了自由身。老妈走投无路了,加上还对外婆外公抱有一些期待,便拉我一起回她老家,希望他们能念在我当时还小、念大学还需要钱的份上,能从娘家那讨来些资源。此外,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安身的地方。
那时候新房子刚刚竣工不久,外婆外公他们也是刚刚住进去。我回去时看见这才完工的五层洋房,和眼前陌生的外婆外公,我还是没办法将这两年发生的事儿联系起来,即使距离发生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新房子装修得很规整,从外面看,和左右邻居的样式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不是外婆站在门外,我定是分辨不出哪家是哪家。
“阿辰,你先上楼一下,喝杯水。”我知道老妈只是为了将我支开,她不忍心让我看到接下来的画面。我只能应了一声后,乖乖上楼去。我来到三楼,遇见了舅舅,他在客厅里和一位师傅说话,似乎是在交待着什么。我站在门外,看见了刚刚布置好的客厅里放着两台还未拆封的空调。他也发现了上来的我,说实话,当时我从进门时便开始恍惚,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这房子里的所有人。
我忙挤出一点笑容向他打招呼:“舅舅好。”我知道自己当时脸上很僵,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做,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我妈,我都要这样做。
他似乎也不太敢对视我的眼睛,眼神总是在往左右两边飘,只有嘴里在不断重复着:“现在天气太热了,按个空调,让老人家们好过一点。”我想他应该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语气都是颤的。
“来,阿辰,舅舅给你个红包,要好好读书啊。”边说着,边打开钱包,抽出六百块钱塞进我的手里,然后便匆匆离开了。我看着他的背影,这感觉像极了刚刚做错事的孩子逃离“犯罪现场”的样子。
如果是现在的我,这么点钱完全不够让我的心情产生什么变化。可在当时,我是读不懂他那陌生的背影,只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乞丐。
太阳透过玻璃把我的脸晒得通红,汗水流过,烧得我生疼。我楞在原地,不知道那么大的房子,我应该去哪间。这里已经不是我熟悉的地方了。我望着房间里的家具出神,在脑子里检索着它们,想看看哪些是新添置的,哪些还是我熟悉的。
“辰!吃饭了!”我听见老妈的声音从楼下传来,我应了一声后,将钱揣进兜里,下到厨房去。
因为是才住进来,厨房里只简单的装饰了一下,里边倒是挺大的,前面是灶台,水池,旁边是那几把原先跟了外婆几十年的刀具。后面有一个小隔间,还是空的,不知道以后会在里面填些什么。中间摆了一张圆桌,是新买的原木桌,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凳子也是新的,碗、筷子都是新的。桌上摆着我喜欢的菜:蒸鱼、扣肉、糯米饭、白切鸡,还炒了些时令的青菜,若不是如今的状况,我想我会和以前一样,一边啃着鸡腿,一边和外婆外公说我在学校发生的事儿,高考考得怎么样,还有我要学什么专业的事情,就像我十二岁小学毕业和十五岁初中毕业那样。
而今天我只能低着头,不敢发出多余的声音,自己吃着自己的。就连一根鸡翅都吃了很久,从它的翅尖开始,一个关节,一个关节地吸着,我将咀嚼的动作尽可能地放慢,甚至连关节之间的软骨都没有放过,都用牙齿细细地一点点剔出来吃掉。我不敢说,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只能让食物在我的嘴里停留得久一些,尽量填满我的嘴,好让它显得自己是不方便说话的。
我不敢看桌子上的外公和外婆,那样子的他们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外公坐在我对面,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手里端着一碗稀饭,偶尔夹一筷子菜,伴着稀饭喝下去,也不说话,他的眼睛一直是半眯着的,上下眼皮之间仅留了一条小缝,不知道在盘算些什么,也不知道是在看着对面桌的我们还是置身事外,把自己只当做一位看客。在我的记忆里,过去每到暑假回来时,总会向外公要他编竹虫给我玩儿,编那东西很麻烦,但是他还是会在每年这时候去山上砍竹子回来给我编,完后就会和我一起在一楼的大厅那逗弄着这些玩意儿一下午。而现在眼前这老头,我甚至不确定如果自己和他说话,他会不会搭理我。
此时,我们四个人坐在餐桌上各吃着自己的,谁也不理谁,而率先打破沉默的是我妈。她声音虚得很,试探道:“妈,这房子……”话还没说完,外婆就将碗摔在桌子上说:“之前已经讲过,没得商量,这个房子是我们留给阿洋的!”
“妈,这事情你们做得不厚道啦!”老妈也把碗丢在桌子上,语气不再如先前温缓:“先前讲好是我买下来孝敬自己父母的,当时也说好是我以后给我阿辰的,怎么就成要给阿洋了?没得道理啊!”
母女俩在餐桌上谁也不让谁,外婆任我妈怎么哭叫都没有任何动摇,铁了心一般不打算让步。
“谁说了?有谁听见了?当时你是说送给我和你阿爹的,那就是我们的了。我们的房子,我们怎么不能处置?”外婆叉着腰,指着我妈骂道。
我一边吃,一边用余光看着坐在我对面的外公,和外婆那边不同的是,他一直在那里瘟瘟的,就由着外婆和老妈在闹,也不说话,就是手里端着杯水,靠在椅子上这么看着。就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呗,我当时想,心里骂道。
后来,见我妈哭得没力气了,她又对我妈说到:“阿烨啊,你看你,带阿辰来掺合这个事情做什么?”语气听起来苦口婆心地,随后又转向对我说:“阿辰啊,你看啊,大人那一辈的事情就留在他们那一辈,别让这事情影响你们这一辈的关系,你看你阿姐,她就从来没管过这事情。你就安心读书,以后读出来好好孝敬你爸妈……”我当时已经分不清自己是被气笑了的,还是被逗笑了的了。心里嘲笑到:“姐姐自然是不需要亲自出来的呀,你们一家四五个人都在帮衬着,她何必要出来做这个坏人呢?”
我妈听到这里便更加坐不住了,从椅子上弹起来,指着外公说:“你们这就是过河拆桥啊,平时都让阿妈冲在前面,坏主意都是你在背后出的,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时,外公将水杯缓缓放下,说:“是啊,反正我们也已经过河啦,我肯定不用再管这条桥啦!你这个人都是我们生的,你用什么报答我们?你的就是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语气越来越冷。
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说话这么大声过。
后来我也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回到桂林的,兴许是餐桌上的那段记忆太过浓烈,让在它前后发生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事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那之后,我便读了现在的大学,转眼七年过去了,期间的日子磕磕绊绊地过着,而我再没去过。后面外公生了几场大病,好几次都到鬼门关外了。老妈也因为这事,回去了几趟,再加上在这两年里有几个比较近的亲戚都离开了,母亲和外公外婆家那边才慢慢地开始恢复了走动。
此后,老妈几次劝说我回去见他们一面,可我始终都没有再回去。再后来,我听母亲说,外婆许诺给她那栋楼中的一层房。期间我不知道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我无数次向老妈表明我不相信那老太太有这么好心。可在那之后,老妈催促我回去的次数便多了起来,但我仍然没有回去的打算。
真的原谅了?我不确定,但我想这里面多多少少和那许诺了的一层房有关系。可每当我试着问她时,她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唉,都那么大年纪了。”
真的好想骂醒她,可我又不忍心。
三
“阿辰,呆着干嘛,还不快去收拾东西。”老妈催促着,走进来,手里还拿着刚刚吹好的袜子和内裤。她额前吊了两缕头发,花白的,眼神也暗淡了好多,这些年我只有放假才能回家,即使回来,但也很少会仔细看看老妈。原来她已经憔悴了这么多了。
“妈,我真不愿去。”窗外的雨好像下得更大了,雨水拍打这雨棚的声音都快要把我的声音淹没。“你怎么总是这样扭扭捏捏的,他再怎么样也是你外公。”说完,她就直定定地望着我,而我却不敢直视她,我开始躲闪她的眼神,我偏过头去找了个灯泡,好让自己的视线落脚,“如果我说,这几年都没有让我从那件事走出来,你信吗?”
“你这孩子就是又轴又倔。”
“可是你真的确定她们会给你他们许诺的那一层吗?”我朝她喊到,我要叫醒她。说实话,我真的不相信他们会这么做。我担心老妈到那时更加受不住打击,七年前老妈才刚刚五十左右,那时候就已经半条命在那儿了,这要是换做现在,后果我根本不敢想。那一年,他们已经把话说尽了,事也做绝了,难保以后还会不会做出什么来。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老妈叹了口气说:“妈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妈也知道你在乎的不是那一层房子。”她慢慢坐回床边,接着说:“说实在的,妈也不是完全相信,毕竟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这事儿就连法律都管不着了。”
“那你怎么……”还没等我话说出口,老妈就紧接着对我说:“你就回去一趟吧,就当陪妈妈一起去看看好不好?你也好多年没有回去了。”
我望着老妈,看着她逐渐变形的身体,生怕她哪天再病倒。仔细想想,或许她现在硬是要拉我回去,也是想给自己讨个安心吧。
最后,我还是没拗过她,答应了今年一起回去过年。
回想起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是七年前的事儿了。那天,当我们坐的大巴车驶进县城里时,说实话,它和我之前印象里边的永福县城没有什么两样,街道两旁的布置也都大同小异,如果说市中心有那么一点点微小的变化的话,我想也只有店铺与店铺之间的简单更新吧。当车越往内深入,我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也并没有让这里有什么改变,依旧坑坑洼洼是巷子路,乱搭的电线,就连过去每家每户在门口种的植物都跟我印象里一模一样。直到眼前出现了一栋没有见过的新式五层小洋楼时,老妈拍了拍我的肩膀,提醒到:“阿辰,到了。”
我望向窗外,看见门口有一个老太太在那站着,才反应过来,到外婆那儿了。只是对站在面前的这栋楼,我没什么印象。
由于晕车实在是严重,胃里早就翻天了,闹得我脑袋沉得很。我艰难地下车,看见外婆就守在门口。她同我的记忆里相比变了许多。她比七年前瘦了两大圈,原本花白的头发,如今都变成雪白的了,眼神里已经没有了曾经的锐利,泛着好像慈祥的目光。她眼神微眯,似乎在确认着下车的人是不是我。
老妈随后下来便跟她打招呼。我则先是用微信给司机付了款,随后便从车的后备箱拿出行李,低着头,径直往里走,老妈见我如此,拍了拍我提醒到,我这才勉强地向那人问了一声:“外婆好。”

插图作者:曹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