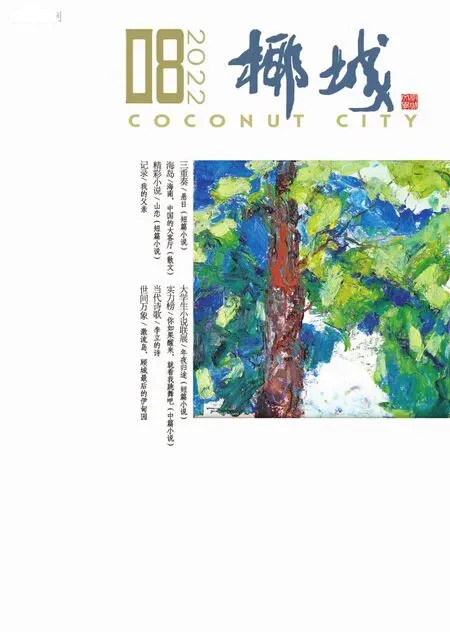我的父亲
◎唐炳超
父亲离世的样子安详得让人感到意外。那天傍晚,四川北部的天空一如既往的晦暗沉闷,小镇里寥落的灯火在暮色四合的夜空若隐若现,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一想到那个傍晚,我就会浮现出鲁迅先生在《祝福》中描写的灰蒙蒙而又带有神秘恐怖色彩的鲁镇。其实那天没有一点不祥之兆,上午他年轻时的一位“结拜兄弟”专门赶来看他,在他们的对话中我还听见他发出一声浅浅的轻笑,可到了下午他就昏迷不醒。我爬上床搂着他的头,他半仰着躺在我的怀里像睡着了一样,脸上没有一丝痛苦。那时我才注意到他右手打着点滴的“白蛋白”已经停止滴注。姑父转身从隔壁房间拿来一根灯草放在他的鼻孔前,那根轻如鸿毛的灯草最终一丝未动,全家人自此才相信父亲的生命之灯已经熄灭,顿时哭声四起,闻讯赶来的乡邻们也饱含泪水轻轻呼叫着他的名字。全屋子的人唯有见过无数生死场面的母亲格外镇静,她先吩咐我把父亲的遗体从床上抱起平放在地面的一张草席上,以免血液停止致使身体僵硬变形。接着,母亲关上门独自为父亲擦洗干净了身体,换上了寿衣,又叫人从屋后抬出棺木,按照当地的习俗将父亲安然入殓。就在棺盖即将合上的那一刻,母亲才安排全家人肃立在父亲的棺木前,她趴在父亲的头上轻轻呼唤他的名字,泪水涟涟。
父亲的葬礼很隆重,出殡那天为他送葬的人挤满了小镇的街头巷尾。很多年之后,我才自我慰藉地感到,我的父亲其实走得很安祥。
在我模糊狭促的童年记忆里,父亲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这是因为,我出生不到一个月就被同住在镇上的一位隔房舅父“抱”走了。父母一生养育了八个儿女,我排行老四,是父亲的第三个儿子。我出生那年,父亲同时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和肝病,家庭处境极为艰难。但父亲是个硬汉子,“有人生无人养”对自尊心极强的父亲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因此,当舅父缠着要抱养我的时候,父亲没有一点商量余地一口回绝。舅父无奈,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从后门翻墙而入,为我而做了一回“梁上君子”。从睡梦中惊醒后的父亲歇斯底里地大喊捉贼,趿起鞋子一直追到舅父的家门口。舅父姓张,膝下无子,他隔着门缝指着父亲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张家屋里抱得娃儿与你何干?你是狗撵耗子多管闲事。这句话戳到了父亲的痛处。父亲是入赘到母亲家的,父母成婚那年,父亲家境一败涂地,上无片瓦,下无卓锥。而母亲就不同了,母亲是镇上一户小殷人家的掌上明珠且是独生女。在我们那一带的婚嫁习俗中入赘是低人一等的。舅父就以此说父亲空手来到张家就是想霸占那座祖传的大瓦房,现在在张家生的娃儿到底姓张姓唐不是父亲说了算。舅父强词夺理,父亲理屈词穷,只有带着一腔的愤懑默默地回到家里,一手按住剧痛的肝部一手端着粗糙的青花土碗借酒浇愁。
我成为舅父的养子就这样既成事实,但对那个“抱”字父亲一直耿耿于怀,一辈子也没承认过。对父亲最初的记忆应该是6岁那年,一直任性顽皮的我对上学读书强烈抵触,最后还是舅父用一个麻饼哄着我走进了学堂。可在回来的路上,父亲和舅父相遇了。父亲似乎有所预谋,他很蛮横地扯过我的书包,掏出学校新发的书本,看见舅父用张家子辈为我取的名字郝然写在作业本的封面上,瞬间暴跳如雷。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父亲最为暴烈抑或说是英武的一次,他先是一个耳光煽在我的脸上,说我忘祖忘宗改名换姓,接着就用手指着舅父的鼻子大吼大叫,甚至摆出一副要动手的架势。一向强势的舅父被父亲震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有面向前来看热闹的人要大家评理,说在张家养大的娃儿不姓张跟谁姓?已经失去理智的父亲什么理也听不进,只是将满地的书本重新收拾起装进书包怒冲冲地回了家。当天晚上他就托人将远在十多公里外当小学教师的姑父叫到家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和已经成年的哥哥姐姐一起为我取了现在的名字。第二天父亲又赶去学校,将在花名册上已经登记好的名字重新改了过来。从那天起,我才懵懵懂懂地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尽管在后来的成长岁月里,面对舅父无数次的恐吓和诱惑,我也始终没改我的姓名,直到现在。
老实说,从小长大,父亲在我的心中都无足轻重,发生在他身上的很多事我并不引以为意。多年以后,当父亲的有些举动被时间过滤,我才在年岁的沉积之中读懂了他。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我被舅父“抱”走不到两个月,镇上的一位邻居突然暴卒而死,留下一个左手残疾的孤儿,小名叫青波。那时全镇的合作商业刚成立不久,母亲是经理,老有所养,幼有所教是母亲对大家的承诺。也许是长期受医道仁心的浸染,在一家中药店当“头儿”的父亲对这一承诺妇唱夫随。因此,当母亲为逝者操持完后事,父亲就将这个孤苦伶仃的残疾孩子带回了家,从此,青波就这样代替我成为了父母的第五个孩子。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对她的八个亲生儿女是格外严厉的,却对青波呵护有加。1970年舅父病故,我回到父亲身边,对这个取代了我位置的“哥哥”恨之入骨。那时被舅父宠坏了的我格外刁蛮,这个残疾的编外“哥哥”给我带来不少麻烦,我的儿时伙伴常常学着他“爪手”的样子讥讽我,使我的自尊心无数次受到伤害。一次吃饭的时候,青波不慎用了舅父留给我专用的一双铜筷,我横蛮地将一碗很烫的南瓜汤泼在他身上。父亲看见后怒不可遏,“啪”的一声将一双竹筷重重地砸在桌子上,然后操起桌边一把扫帚对着我就是一顿狠揍。从那以后,我再不敢在青波面前颐指气使。再后来,父亲不仅将青波带在身边教会了司药手艺,让他能自食其力,而且和母亲一起,费劲周折,为青波讨了老婆,并养育了一儿一女。
作为一介布衣,忠实于自己的职业是父亲一生的唯一。在我的记忆里有一张底片格外清晰:十米见方的中药店里,穿着白色圆领衫的父亲一手按着钝痛的肝部,一手抓着中药来来回回,汗珠挂在他并不宽阔的额头上。父亲八岁起就在镇上大户人家开的中药铺里当学徒,几十年下来,自然浅涉医道,背得一些汤头。那些年但凡遇到乡下那些吃不起药的人,他都会自己出钱给他们抓几副中草药,药普通,效果却神奇,日子久了,大家都信他,说他心肠好。一次,青波用党参代替人参骗了一位乡下大娘,父亲知道后不问青红皂白对着青波就是几个耳光,气急败坏地骂道:娃儿,给老子记住了,这种钱是不能赚的!这钱为什么不能赚,直到他退休后发生的一件家事,父亲的内心秘密才得到诠释。记得父亲是76年因为身体原因提前病退的。父亲病退不到两年,小镇发生了深刻变化,全镇所有的集体商业几乎是一夜之间门可罗雀,仅有中药店在勉强维持,30多号人发不出工资。为此,身为经理的母亲陷入从未有过的困局,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对父亲说:你熟人熟手,回去操持一下。父亲就是在那时又重新回到了中药店。借助父亲的名义中药店又开始兴隆起来,每遇逢场天店里店外人头攒动,一路路乡下人不但找他“抓药”,而且还讨“方子”。父亲不是正式医生,可他开出的“方子”人们都信而且都起作用了,一传十,十传百,父亲简直就成了悬壶济世的神医下凡。
在县川剧团吹小号的大哥就是在那时看见了商机,很快策划出一个方案,打着父亲的牌子在自家开中药店,那无疑是一个赚大钱的行当。我那时十分理解作为长子的大哥的良苦用心,并和他很快结成“联盟”。大哥的打算就当时来讲很超前,大哥计划建一家“唐氏中药材总公司”,在全县设立三个连锁店,聘请县甚至市里的知名医生星期天坐诊。这一系列策划加上父亲的牌子,大哥说这是我们唐氏家族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大哥很快通过各种关系办好了手续,并谈定了坐诊医生,可没想到这件事却受到父母的断然拒绝,特别是父亲,他几乎是哭丧着脸对大哥说:不能搞那事呀。大哥赌气地问:大家都在搞我为啥子不能搞?父亲第一次在大哥面前低三下四。父亲说:那钱不能赚,你看,胡家,我八岁起给他家当学徒,多兴盛,半截子街都是他的;父亲说,不是啥子钱都可以赚的,赚昧心钱要遭报应;父亲说,后来胡家财产全被没收,还有人进了班房。深陷在父亲意识里“因果报应”对大哥来说只不过是一句梦呓,记得那是一个西北风夹着黄沙打旋儿的冬日的黄昏,大哥几经周折,一切准备就绪,就待第二天开业,可父亲却突然失踪,不知去向。面对这一绝情的打击,血性的大哥发疯似地砸碎了牌匾,撕碎了执照,然后扬长而去。在后来的一年里,没回过家,没和父亲说过话,直到后来父亲患老年性肺结核住院,大哥才勉强去了医院,站在病房的门口木然地望着他。

作者(右一)与他的父亲(右二)
父亲走后我估摸他去了姑姑家,我踏着崎岖的山路赶到姑姑所在的那个小山村已是暮色苍茫,远远的,我就看见父亲独自一人蹲在姑姑的家门口,形影枯槁,像一支风中残烛。父亲那年59岁,再过一年就届满花甲,长时间在病痛阴影中生存的父亲一直看重那个生命的节点。我曾在1986年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爸爸活满花甲》,小说里的“父亲”是一个贪婪、自私、狡黠、市侩的文学形象。1986年5月,我在中国新闻学院重庆分院读书时,第一次收到《四川文学》手书的回函决定刊发我的作品。《四川文学》那时叫《现代作家》,每期仅发一个中篇且是头条,但苦等一个月之后却大失所望,那期刊物发表的是一位知名作家反映农村改革题材的中篇。凝聚着我和父亲心血的那部小说就这样无疾而终,这件事我一直没敢向父亲提起,那时我已初为人父,多少有些感觉我和大哥其实是父亲身上的一只“俾虱”,无情地吸取着他的精气和骨血,一个为利,一个为名。再者,小说中的“父亲”早已在我的笔下抑郁而死,尽管是文学作品,但对父亲来说我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一种罪恶感。就这样,一个死了和一个活着的父亲同时并存在那个时代,那些真实和虚构交织的情节长时间成为父亲在我心中定位的依据。直到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人生磨砺,甚至在父亲驾鹤西去的二十多年里,我才在一次又一次的思念之中重新复活了一个灵魂的父亲。
大哥开店赚钱的梦想就这样被父亲“扼杀”,这件事一直是我解不开的一个心结。90年代初,我南下海南,对父亲的记忆逐渐模糊。那时的海南大特区到处弥漫着金钱的气味,一夜暴富屡见不鲜,浮华和喧嚣足以使每个追随者的价值观潜移默化。1997年6月,由于发财心切,我贸然拿出所有积蓄去“炒股”而最终血本无归。那是一段必须自我承担和接受日子,迷惘之中才又想起父亲和父亲说过的一些话。也就在那时我接到七弟的电话,七弟说,父亲的肝病最终转化为肝癌而且已经扩散。那是一个日丽风清的上午,在红绿数字闪烁的股市交易大厅我掩面而泣。第二天我就请假从海南回到父亲身边,父亲大限已至,这是全家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那些天我一直守护在父亲的病床旁,面对一天一天走向死亡的父亲,我下意识地想起那篇《爸爸活满花甲》。小说中的“父亲”早已死了,而现实的父亲不但活满花甲活过古稀还直奔杖朝,他们之间隐匿着何种玄机我不得而知。住院20多天后,对父亲的病医生已无力回天,建议我们回家准备后事,从来没问过自己病情的父亲似乎有所预感。那天下午他把我叫到床边旧事重提,断断续续说了这样一段话:老四……你是知书达理的人……说句老实话……钱,谁不想赚……瞎子见了还眼开呢……那年我们要开了那个店……集体的就要关门……那是30多人的饭碗……都是街坊邻居的……抹不下那个脸啊……合作商业成立那阵你妈就当了经理……几十号人的生老病死都指望她……当初她是指天发誓给大家保证了的呀……父亲说完就一声叹息,而我却受到如雷轰顶般的震撼。我绝然不会想到我的市民父亲在灯枯油尽的最后一息会说出这些话,我绝然不会想到在他卑微甚至愚钝的内心世界却深藏着一方人情,我趴在他的床上紧攥着他枯瘦如柴的手任泪水恣肆,第一次发出内心深处的呼喊: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