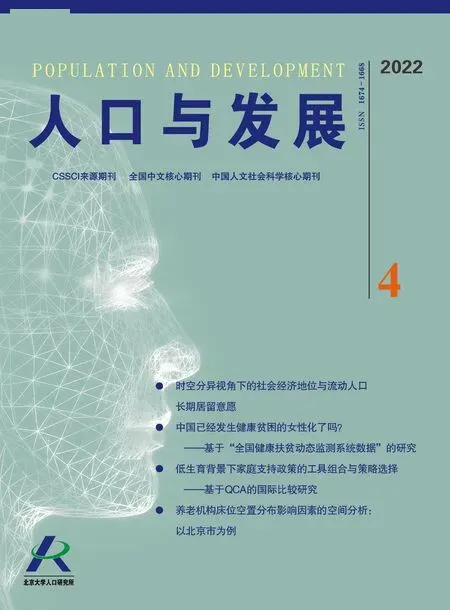跨越户籍界限的“绿卡”:居住证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
林龙飞,陈传波
1 引言
作为我国户籍改革的核心举措之一,居住证被赋予摊薄城市户籍福利、实现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重大使命(谢宝富、袁倩,2019)。居住证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它主要借鉴西方“绿卡”制度而创立的,并最终成为中国的“绿卡”制度(刘丽,2015)。2015年10月21日国务院第109次常务会议通过《居住证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居住证制度,并于2016年1月1日正式施行。宣告了自1951年起实施的户籍管理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统一规定了城市户口登记制度。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一个全国性户籍法规。1958年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正式形成。,标志着中国打破城乡户籍藩篱、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居住证施行以来,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肯定其积极意义。《条例》赋予持有居住证的农村流动人口拥有“六大服务”和“七项便利”(2)六大服务分别是: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国家规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七项便利分别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出入境证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机动车登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申请授予职业资格;办理生育服务登记和其他计划生育证明材料;国家规定的其他便利。,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鸿沟”(孙伟、夏锋,2018),推进了户籍与福利的脱钩(陈鹏,2018),摒弃了以往暂住证隐含的身份歧视(姚先国等,2015),使得持证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就业、教育、社保、住房保障等方面享有基本权益,有助于跨域户籍界限为流动人口提供当地市民化待遇,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实现“市民梦”的重要举措(杨富平,2017)。
但也有学者直言其存在的问题。居住证是一种施舍性的制度,某种程度上是户籍制度的“改良”,其核心是在维持现有户籍居民福利规模和水平不变的前提下,逐渐增加和改善对居住证持有者的公共资源与福利的供给水平(杨菊华,2017)。《条例》赋予居住证的清单中夹杂着“充数”的权利选项,无法实质性增进农村流动人口城市权利(邹湘江、吴丹,2020),通过“累积赋权”配置社会福利资源仍带有明显的区隔性(王春蕊,2015),居住证可能会降低中小城市流动人口享受当地福利的门槛,但同时也给特(超)大城市将外来人口拒之门外提供了一柄“尚方宝剑”,为地方排斥流动人口、尤其是低端流动人口提供了政策上的便利和支持(杨菊华,2017)。
融入城市是市民化的重要取向。流动人口虽然户籍在农村,但大多数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就业,对融入城市有着强烈的期盼。作为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招,居住证持有无疑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持有居住证意味着跨越了城乡户籍界限,可以获得与当地居民相当的城市权益,是流动人口落脚城市并深入融入城市的重要阶梯;另一方面,如果附着在居住证上的权益只是“充数”的权利选项,对于特(超)大城市反而异化为将外来流动人口拒之门的一柄“尚方宝剑”,那么持有居住证可能并不能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
本研究的兴趣和疑问是,政策初衷旨在摊薄城市户籍福利、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居住证究竟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有怎样的影响?迄今为止,居住证制度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和本文主题相近的文献是梁土坤(2020)的研究,他利用2017年珠三角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探讨了居住证制度、生命历程与新生代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关系,发现居住证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心理融入有显著影响。这篇文献极具参考价值,但他并未考虑实证方法上的因果内生性问题,同时也忽略了不同城市等级中持有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异质影响。而中国当前更普遍的一个现实是,随着城市等级规模越高,居住证含金量也会越高,但与此同时,以居住证为依托的落户、社保、教育等也均有相应更高的门槛设置。这意味着在中国不同城市等级中持有居住证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效应会有明显的差异。
本文拟作进一步的推进。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居住证持有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过程中,为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Roodman(2009)提出的工具变量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MP)进行回归,并进一步使用Rosenbaum等(1985)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造反事实框架,最终得出居住证持有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正向效应,且随着城市规模等级的逐次上升,居住证的城市融入效应亦在上升的结论。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数据、变量及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城市异质效应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2 文献综述
居住证制度与城市融入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研究主题。居住证实施以来,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居住证的基本功能、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未来居住证改革方向上(杨富平,2017;孙伟、夏锋,2018;原新利,2019)。居住证避免了“一个国家、两种待遇”的刚性身份区隔,可以使持有居住证的农民均等化享有当地基本公共服务,进而有助于进城农民市民化(谢宝富、袁倩,2019)。居住证对社会和个人的根本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城乡户籍藩篱,使微观农民在流入地就业、教育、社保、住房保障等方面享有基本权益,是助力农村流动人口扎根城市和融入城市的利好制度(姚先国等,2015)。
尽管居住证对农村流动人口扎根城市意义重大,但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一种“过渡性”举措,居住证目前还存在诸多问题(许经勇,2020)。最大问题在于居住证并未触及到户籍制度背后福利共享的本质,某种程度上只是户籍制度作出的局部性改良,居住证虽然赋予农村流动人口准市民身份,但居住证里面包含着“充数”的权利,无法实质性增进流动人口城市权利(杨菊华,2017;邹湘江、吴丹,2020)。因而,进一步破冰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固化(杨菊华,2017)、增强赋权的普惠性(王春蕊,2015)、降低城市准入门槛(李世美、沈丽,2018)是未来居住证制度改革和完善的重要方向。
“融入”一词最早源于西方国家外来移民研究,旨在探讨不同文化、不同地域背景下外来移民如何消减文化差异,适应流入地生产生活,进而达成文化和身份共识(Gordon,1964)。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城市融入实际时对国外社会融合理论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先后提出了“再造社会化说”(田凯,1995)、“三阶段理论”(童星、马西恒,2008)、“五阶段理论”(杨菊华,2009)等。融入是一个多维度概念,通常指农业人口在城市不断适应及融合的过程。有学者认为心理融入是城市融入的最高级,是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的体现(崔岩,2012),也有学者认为城市融入是心理、身份、文化多方面融入的过程(钱泽森、朱嘉晔,2018),还有学者强调城市融入是心理和行为两方面的体现(唐跃文等,2021)。
目前进入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处于“半融入”或“半城市化”状态(蔡昉,2001)。Robert and Ernest(1921)提出的“社会融合理论”强调,融入是一个同化和相互渗透的过程,外来移民进入到新的社会环境中,会呈现非同质化的区隔,而摆脱非同质化区隔并最终融入当地的关键是适应流入地的制度规范。中国农村流动人口进城既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摆脱“乡土性”的进程(田凯,1995),进入城市新情境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制度规范方面通常面临着再适应和再融合的挑战。而作为我国户籍改革的核心举措之一,居住证可以赋予农村流动人口拥有“六大服务”和“七项便利”,帮助农村流动人口消除城乡户籍鸿沟,提供当地市民待遇(杨富平,2017),摆脱进入城市的非同质化区隔,最终实现城市融入。
现有研究多关注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如户籍分割(王晓峰、张幸福,2019;黎红,2021)、个体性别、年龄特征(钱泽森、朱嘉晔,2018)、人力资本特征(赵建国、周德水,2018)、婚姻家庭特征(林龙飞、陈传波,2021)、住房和流动特征(王子成、郭沐蓉,2020;王晓峰、张幸福,2019)等。此外,不同城市等级持有居住证“含金量”可能不同,通常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持有居住证“含金量”会更高(杨菊华,2017)。倪超军(2021)实证发现,不同城市等级持有居住证具有不同效应,持有居住证对Ⅱ型大城市、Ⅰ型大城市和特大超大城市农民工的福利水平提升均有积极推动效应,其中特大超大城市的作用效应最大。
目前同时将居住证制度与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关联起来的实证文献极少。在有限的实证文献中,袁方等(2016)运用2009—2010年上海农民工调研数据,基于OLS方法发现居住证制度会显著改善了农民工的总福利水平。吕明阳、陆蒙华(2020)基于上海市居住证微观调查数据,发现居住证持有对流动人口留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钱雪亚等(2017)同样以上海市为例,运用CFPS2010-2012年数据估算了农民工的居住证积分水平,但发现农民工当前居住证积分水平较低,市民化程度并不高。梁土坤(2020)利用2017年珠三角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运用0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发现居住证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心理融入有显著影响。
上述实证研究极具参考价值,但现有研究依然存在进一步推进的空间:一方面,现有研究多将居住证制度与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分开讨论,缺乏将居住证和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特别聚焦居住证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更鲜有研究关注中国不同城市等级中持有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异质影响;另一方面,囿于数据的可得性,现有研究通常在方法上多采用简单线性回归,缺乏较为严谨和多样的稳健估计方法,从而造成理论分析上的缺陷以及实证估计结果的偏误。
区别于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是:第一,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将居住证与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为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居住证与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第二,利用工具变量条件混合估计法进行回归,并进一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造反事实框架,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有一般性;第三,研究进一步细致考察了不同城市等级中持有居住证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异质性影响。
3 数据、变量及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进行实证分析(3)感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支持。。CMDS数据基于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样本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32个省级行政单位,调查对象为15~59周岁的流动人口。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流动人口,因此仅保留户籍为农村户口的样本。同时,根据外出流动原因,仅保留务工、经商样本,删除婚姻嫁娶、投靠亲友、拆迁搬家等其他原因流动的样本。此外,考虑到居住证办理条件一般需在流入地半年及以上,本研究仅保留在流入地生活半年及以上的样本。剔除其余变量的缺失值和错误值后,本文最终识别有效样本为86460个。
3.2 变量描述
被解释变量——城市融入。目前对城市融入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有学者认为心理融入是城市融入的最高表现(崔岩,2012),也有学者强调心理、文化、身份融入是城市融入的重要维度(钱泽森、朱嘉晔,2018),还有学者强调城市融入是心理和行为两方面的体现(唐跃文等,2021)。同时,测度城市融入的方法也存在不同,有的学者使用单一指标测度,有的学者使用综合指标测度。本文采用综合指标测度法,在测度城市融入上侧重考察农村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融入。原因在于,真正意义上的融入是建立在高度心理认同基础上的(崔岩,2012)。朱力(2002)发现,城市融入有经济、社会和心理3个依次递进的层级,杨菊华(2009)认为心理认同是社会融入的最高级。以心理融入表征城市或社会融入的研究也普遍见于其他文献中。
结合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指标的可得性,本文分别选取“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地方”、“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地方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4个问题作为城市融入的代理变量,4个问题的答案均是“1完全不同意 2不同意 3基本同意 4完全同意”。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主成分分析系统自动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1个因子,对因子分析的适应性进行检验,提取出的因子方差贡献率为67.40%,KMO达到0.7865,因此认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借鉴杨金龙等(2020)的做法,本文采用正向极值法将提取因子转换为0~1之间的标准化值,转换后的城市融入为连续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居住证持有状况。问卷向被访者询问了“您是否办理了居住证?”,答案为“已经办理;没办,没听说过;没办,但听说过;不清楚”,本研究将回答“不清楚”的样本做删除处理,同时将“没办,没听说过”和“没办,但听说过”归并为一个答案。本文将持有居住证样本赋值为1,共60162人,占比69.58%;将未持有居住证样本赋值为0,共26298人,占比30.42%。
通常而言,男性适应能力更强,更容易融入城市;低年龄、高学历的流动人口因技能水平和年龄的优势更容易融入城市;家庭人口数、家庭负担比和家属随迁状况是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一般家庭人口数越少、家庭负担比越轻、有家属随迁的流动人口更容易融入城市;在城市拥有住房、社保、从事高职业层次的流动人口更容易融入城市;经济收入越高城市融入越容易;在熟人社会情境下,省内流动通常比省外流动更容易在流入地扎根;通常在流入地留居时间越久、流动经历越丰富,越有助于流动人口城市融入。
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可能会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故本文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对地区效应进行控制(4)本文以虚拟变量形式控制问卷中31个省份。,以弱化回归分析中可能引起的偏误。表1列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3.3 模型设定
基准模型——最小二乘线性模型(OLS)。被解释变量城市融入是连续变量,本研究采用最小二乘线性模型分析居住证持有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构建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Integration=αi+βresidencePermiti+φZi+εi
(1)
上式中,Integration为被解释变量城市融入,residencePermiti为核心解释变量居住证持有状况,Zi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其他变量,αi为截距项,β、φ代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ε为随机干扰项。
准实验法——倾向得分匹配(PSM)。本文采用Rosenbaum et al(1985)提出的倾向匹配法,通过构造反事实框架来纠正因样本自选择而产生的潜在选择性偏误问题。目前这一方法已普遍用于纠正潜在自选偏误问题(祝仲坤,2017)。本文重点将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划为处理组,将未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划为对照组,然后通过多样匹配方法获得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2)
(2)式中,ATT为准实验估计量,N为处理组样本个数,yai和ybi分别表示匹配前与匹配后的样本差异。
内生性讨论——工具变量条件混合估计法(CMP)。除可能存在的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还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由于本文中衡量居住证持有状况的变量为二值虚拟变量,常规两阶段的工具变量法难以处理(Angrist,2001)。本文采用Roodman(2009)提出的工具变量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CMP)进行回归,以进一步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目前这一方法在国内已得到普遍应用(祝仲坤,2017;刘启超,2020)。工具变量条件混合估计法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将联立方程当作一个系统进行估计,第一阶段寻找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将工具变量代入模型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参数的外生性,进而获得一致估计。
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的数据采集工作对普查数据质量至关重要,要抓好普查数据采集、普查表填写、数据录入和汇总上报等各环节的质量控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普查员自审自验。
4 实证结果
4.1 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基于OLS模型的回归结果。方程(1)纳入核心解释变量,结论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居住证持有正向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方程(2)在方程(1)的基础上,继续加入其它主要控制变量,结论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显示居住证有助于提升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方程(3)在方程(2)的基础上,继续控制地区效应,结论仍然显示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正向效应。具体从方程(3)来看,持有居住证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系数为0.015。主要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与预期基本一致,但由于控制变量并不是本文的核心关切,同时简单的线性回归也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在此对主要控制变量不做过多引申探讨。

表2 居住证持有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
4.2 倾向得分匹配法
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可能是自选择的结果,即居住证持有流动人口可能并不满足随机指派原则,直接回归存在自选择性偏误。为纠正潜在自选偏误问题,依照Rosenbaum(1985)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法,本文将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处理组)和未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控制组)进行倾向值匹配,以弱化匹配前样本间存在的显著性差异。


表3 不同匹配方法ATT结果
4.3 内生性讨论
除潜在样本选择性偏误之外,本文还可能反向因果的潜在内生性问题。由于本文中衡量居住证持有状况的变量为二值虚拟变量,常规两阶段的工具变量法难以处理(Angrist,2001)。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祝仲坤,2017;刘启超,2020),本研究采用Roodman(2009)提出的工具变量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MP),以克服实证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择“流入地中除本人以外其他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的均值”作为个体持有居住证的工具变量。从相关性来看,同一流入区域内的流动人口容易相互模仿和学习,产生行为上的“同群效应”。已有文献发现,农民在城市中往往呈现出“同乡同业”的行为特征(孙九霞、李怡飞,2020)。同一流入区域内其他流动人口是否办理居住证会对该流动人口是否办理居住证产生决策上的影响。但从外生性来看,同一流入区域内其他流动人口是否办理或持有居住证对该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并无直接关系。这种工具变量的选取思路也常见于其他文献中(何安华、孔祥智,2014)。
根据表4回归结果可知,CMP方法的第一阶段回归显示,工具变量对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本文的工具变量选取合适。进一步看,CMP方法回归的第二阶段,居住证持有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基准回归OLS的结论一致,进一步证实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同时,CMP方法的内生性参数Atanhrho-12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本文基准模型中并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表4 内生性讨论—CMP方法结果
4.4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回归结果稳健不变,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一是调整因变量。考虑到已有文献中常用落户意愿和留居意愿衡量城市融入。本文分别用问卷中“您是否打算落户?”和“您今后是否愿意继续留居?”两个问题替换基准模型中的因变量,两个问题的答案均是“打算(愿意)、不打算(不愿意)、没想清楚”三分类变量。本文用oprobit模型重新回归,居住证持有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正向效应仍然显著。二是增加控制变量。考虑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与户籍地土地、宅基地和村集体分红权益密切相关,本文将“您户籍地是否有土地?”、“您户籍地是否有宅基地?”和“您是否有村里分配的集体分红?”3个问题作为控制变量,重新纳入基准模型回归,回归结论仍然稳健不变。各稳健性检验结果详见表5。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5 拓展性分析:不同城市等级的异质影响
前文已经证实,居住证持有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正向影响。但这一结论只是全样本的平均效应,并未考虑不同城市等级中持有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异质影响(5)根据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并借鉴孙迪等(2020)对城市行政级别和经济发展的考虑,本文将样本城市划分为特大城市、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4类。特大城市包括北京市、广州市、深圳市、上海市。一线城市包括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南京、郑州、长沙、东莞、沈阳、青岛、合肥、佛山。二线城市包括厦门、福州、无锡、昆明、哈尔滨、济南、长春、温州、石家庄、南宁、常州、泉州、南昌、贵阳、太原、金华、珠海、惠州、徐州、烟台、嘉兴、南通、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绍兴、中山、台州、兰州、海口。其余城市均囊括为三线及以下城市。。中国当前更现实的情况是,随着城市规模等级的上升,公共服务的含金量也越高,同时附着在居住证上的福利也越好,但随着城市规模等级的上升,城市融入的难度也在加大,以居住证为依托的落户、社保、教育等均有更高的门槛设置。本部分进一步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不同城市等级中持有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异质影响;二是不同城市等级中持有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级差规律。
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MP)分析不同城市等级的异质影响,借鉴温兴祥、程超(2017)的估计思路,首先分样本分别估计不同城市等级中流动人口持有居住证的城市融入效应,然后在全样本下估计居住证持有状况和城市等级规模的交互项系数,以此检验不同城市等级中持有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如表6所示,总体来看,从列(4)到列(7)均显示,持有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正向影响,这与前文基准OLS回归结论一致,进一步证明文本核心结论的稳健。其中列(4)特大城市中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水平最高,影响系数为0.083;列(7)三线及以下城市中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水平最低,影响系数为0.016。这说明当前以跨越户籍界限为目的“绿卡”——居住证确实是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重要阶梯。同时,列(8)中结果显示,城市等级变量在统计显著性上存在差异,居住证和城市等级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即不同城市等级中持有居住证的融入效应差异,该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为 0.008,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不同城市等级中流动人口持有居住证的城市融入效应确实存在差异。同时,进一步具体来看,随着城市规模等级的逐次递减(特大城市→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居住证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系数也在递减(8.3%→8.0%→2.4%→1.6%),这说明居住证助力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明显的级差效应,即城市等级越高,居住证城市融入效应越大。

表6 异质性分析结果
6 结论与讨论
融入城市是中国城镇化下半场的重要主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3.76亿,数量庞大的农村流动人口,既是未来在城生活的主体也是融城艰难的弱势群体。尽管经过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制度障碍的消除,农村流动人口已先后取得“退出权”、“流动权”和“进入权”(蔡昉,2017),但“进入”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却依旧难以融入城市,这其中主要的梗阻原因在于户籍制度(王晓峰、张幸福,2019;黎红,2021)。以往的研究大多就户籍制度本身谈户籍制度改革,鲜有研究专门聚焦居住证制度。而居住证制度作为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破冰举措,它的变革性意义在于,跨越了城乡户籍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因城乡不同户籍而产生的公共福利享有的差异,使得外来农村流动人口可以与本地居民均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推动数以亿计的农村流动人口扎根与融入城市。
本文的实证研究佐证了居住证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正向效应,发现具有“绿卡”属性的居住证在中国的普遍推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因城乡不同户籍而产生的公共福利享有的差异,进而有助于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具体而言,文章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了居住证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居住证持有会显著提升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在加入主要控制变量、地区虚拟变量后,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为克服实证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和选择性偏误,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MP)进行回归,并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构造反事实框架纠正可能的选择性偏误,所得结果依然支持居住证持有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正向效应。第三,分样本估计显示,随着城市规模等级的逐次上升,居住证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效应亦在上升。
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府应考虑居住证制度和农村流动人口的联动关系,要以居住证制度为抓手,推进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在居住证下一轮改革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是,给予居住证加载更多的福利和权限,实行弹性化的居住证办理门槛,提升居住证的含金量和覆盖面,特别是在特大城市和一二线重点城市,需逐步将基本公共福利与户口性质相脱离,淡化积分在获取相关公共服务和福利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要以居住证制度为重要载体,稳步推进对农村流动人口城镇义务教育、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就业服务、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的进一步获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