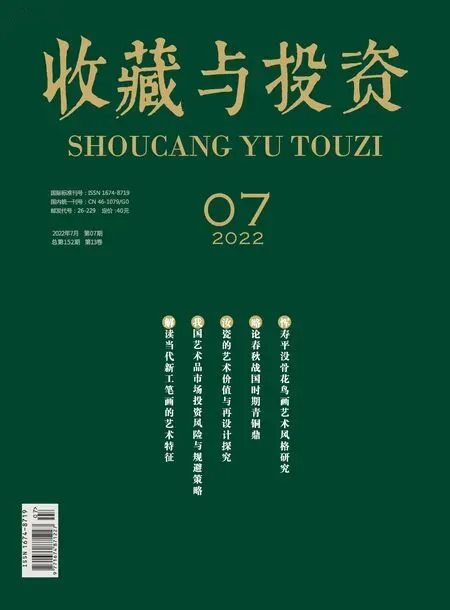民国油画中的现代主义倾向
——以刘海粟为例
魏 力(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说到刘海粟的艺术,首先想到的是一系列感性的词汇——“崇高”“热烈”“率直”“粗犷”“生命的表现”等。著名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对刘海粟的艺术十分赏识,他认为后者的艺术完全是凭借由大自然引发的纯挚情感与其自身的独特个性相结合而生发的。他对于线条和色彩的表达极为敏感:线条语言粗拙厚重,色彩上则擅用对比强烈的两种调子来提升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刘海粟艺术风格的成型可以通过如下三个阶段来分析。
一、艺术生涯早期
刘海粟1896年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儿时即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8岁习画,在临摹古画时常常表现出不拘泥于传统的、叛逆的精神。刘海粟14岁前往上海,进入周湘创办的“布景画传习所”,并开始正式接受西洋画实践的训练。此后,他在“虽发”“普鲁华”等书店购得戈雅、委拉斯凯兹以及塞尚、马蒂斯等艺术家的画册,并加以精研。这些珍贵的学习经历与视觉图像初步打开了刘海粟的艺术眼界。除此之外,他还在漆店购置各种色粉来研磨、调制颜料,在花旗布上作画。颜料与画布品质的低劣,使得刘海粟在这段时期鲜有留存下来的作品。
通过对现有材料的整理可知,刘海粟最早的油画作品绘制于1919年左右,如《披狐皮的女孩》。此作整体感觉较为平淡,艺术家以规矩的大笔触与稍嫌窒闷的灰色调来表现人物形象。根植于其脑中的中国传统绘画的淡雅色泽和理想中的后印象派作品的鲜明色彩之间的冲突;逸笔草草却无不贴合结构的委拉斯凯兹与莫奈式的笔法、独立自觉的现代主义笔触之间的冲突和表情抒意与塑性建构之间的冲突……这些内在的犹豫似乎对于初涉油画,尤其是拥有传统绘画功底的中国学生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让人想起塞尚早期的“古典之心”与笨拙手法斗争而产生的那类有着古怪浪漫主义气息的最初作品。除此之外,这幅描绘了一位时髦的都市女郎在繁密枝叶所形成的暗绿背景前为华丽的狐皮披肩代言的画作,似乎还受到流行一时的月份牌绘画的影响。

图1 刘海粟《西泠斜阳》,布面油画,1919年,刘海粟美术馆藏
好在艺术家天生的自信不会让这种情形维持太久。画于同年的《西泠斜阳》(图1)已然展现出刘海粟日后成熟风格的雏形。正如他的偶像,后印象主义画家凡·高善用饱满的情感、响亮的色彩、挥砍般的笔触,用点、线和夸张的形来释放自然中一花一树的灵魂那般,刘海粟亦用能够与之对应的、奔放的中国式写意笔触与强烈的色彩来表现一位红衣女子斜倚美人靠,静览宅院即景的抒情一瞬。当时惯见庸俗时装美人广告画的人均认为此画作风“粗鄙”,但艺术家正是藉着这“粗鄙”来打破事物的表象,表现那深层情感的真实。刘海粟深谙西方的“移情说”这一美学理论,他将内心的热情“投射”至眼前的亭台、草木与佳人之上,绘就此幅极具感染力的迷人作品。
观者从这幅色泽稠丽且创造了一个织锦般玄想世界的画作中可以看出:刘海粟深知,东西方绘画虽然源于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但并非无法相互融合。他所取法的西方早期现代主义风格对西方传统绘画的突破,在美学上即是“绘画的中国画化”。具体到这张画上,无论是“线的雄辩”(如亭栏与树影的勾勒)、色彩的铺陈(浓烈的红绿与黄紫色之碰撞),还是空间的架构(景深的谨慎缩小),均体现出中西艺术的综合影响。刘海粟“一生以师法后期印象派自居,以凡·高、塞尚为偶像”,这种艺术取向是在对上述观念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二、日本之行至欧游前
1919年10月,刘海粟一行人在日本西洋画家石井柏亭的鼓动下东渡日本,考察了当时日本的一些主要展览会。其中,二科会美展充分地展现了日本艺术的多元生态,令年轻的刘海粟激动不已。刘海粟评论说,与官办的、束缚艺术家个性的“帝国美术院展览会”不同,二科展中的大部分西洋画作品(主要倾向于后印象主义),都是通过艺术家的个性与敏锐的感觉,并凭借灵活的手法创作出来的。他们虽然既不模仿古人,亦不甘落眼下的各种主义之窠臼而勇于创新,但依旧是从对真实自然的感悟出发,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而非空假想象,无中生有。此次日本之行,令刘海粟对后印象主义的兴趣更加浓厚了。但从上述评论可知,他所主张的“个性”“表现而非再现”等观念,均是建立在对真实自然的观察之上的。这种内在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他随后的欧游之旅中对欧洲绘画的态度即可体现出来。

图2 刘海粟《北京前门》,布面油画,1922年,刘海粟美术馆藏
1921年年底,蔡元培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养病,彼时正在北大讲学的刘海粟常常去医院拜会蔡元培,并将自己创作的写生作品送呈后者请其指导。蔡元培发现了刘海粟这批写生作品的不足之处:虽然画作中洋溢着真挚的情感,但感性的宣泄多于理性的控制,不利于艺术家内心美学观念的准确表达。他送给刘海粟一本《塞尚选集》,望他关注塞尚画作中稳固的秩序感,弥补自己作品的弱处。
在创作于1922年的《北京前门》(图2)一画中,刘海粟不再像印象主义者那样,将传统绘画中清晰的轮廓线消解为雾状的色斑,将恒定的色彩击碎为律动的色点。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对实景进行感性观察的基础上,运用理性于画面中建立起恒定的秩序。此幅作品色彩艳丽,光照下的中黄色楼身,与钴蓝含紫的天空形成鲜明的对比;画面下方小面积的红、橙、蓝之点缀,丰富而不凌乱,凸显了前门那纪念碑式的坚实结构;经过提炼的楼身造型更添画面的稳固之感。画面前景那喧嚣闹市的缤纷人流与垂直竖起的根根竹竿和简洁的楼身形成了极富韵律的点、线、面节奏关系。那粗拙的轮廓线与概括成几何体的造型叫人体会到刘海粟特有的“力”与“大”之感,虽受到后印象主义与野兽主义的影响,但全无模仿的痕迹。刘海粟用手中的画笔将百年前的北京一日凝结成永恒,保留在画布与人们的记忆之中。
三、欧游至新中国成立前
刘海粟在1929—1935年期间有两次欧洲游学之旅。“有关刘海粟‘观看’西方艺术的方式与立场……需要明确的一个前提,即画家是携带着自身的经验积累与精神诉求与西方相遇的”。因而,彼时的刘海粟抱着的是平等交流的心态,而非艺术朝圣者的膜拜心理。他继续强调要重视创作者的主体精神及其所引发的独特创造力。由此,他发现了从内部串联西方艺术史上的一众大师——自米开朗基罗、提香、委拉斯凯兹,直到塞尚、马蒂斯等艺术家的一根逻辑隐线。但值得注意的是,刘海粟对彼时的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严格来说止于野兽派。

图3 刘海粟《峇厘舞女》,布面油画,1940年,刘海粟美术馆藏
经蔡元培的提点,刘海粟的艺术由此前单纯依赖直觉转变为理性与感性并重。这种新的艺术面貌是由艺术家的个性糅合后印象主义和野兽主义的某些特征后产生的。塞尚以几何形概括物象的思维、凡·高的色彩表现力、德朗回归传统后的画面构成手法,均被刘海粟以自己的方式加以吸纳和综合运用。此外,他还着重在画面中凸显中国画家特有的、倾向于抒情写意的审美趣味。刘海粟在此期间创作的油画作品有百余幅,如《巴黎圣母院夕照》(1930年)、《威士敏斯达落日》(1935年)、《雨后比利时鲁汶圣彼得教堂》(1930年)等均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画作。
刘海粟自欧洲归国后,在勤奋的绘画实践中努力消化所学的知识。抗战时期,他离开上海而暂居南洋,并于1940年在印尼举办赈灾展览。展品中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峇厘舞女》(1940年)(图3)一画。此画的运笔、施色、结构以及色块间的并置方式,均由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所支配,并且融入了画家自身的个性特质。在色彩的表现上,中黄草绿、深黄翠绿的并置对比,响亮而和谐,使得整个画面极具跃动的生机。高更式的平面化与装饰化的表达,更使此画洋溢着一股浓烈的热带气息。这种形而上的性灵活力,准确地体现了谢赫“六法论”中的最高要义——“气韵生动”的内涵。
当时的刘海粟已经对野兽主义的造型原理与画面构成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个人的油画创作风格趋于成熟。以这幅作品来说,刘海粟对画中两位异域女子的造型进行了适度夸张和变形,与现实中的女子形象拉开了距离。这正是野兽主义者马蒂斯努力用自己的作品证明的。一幅油画,只是画家用饱蘸颜料的画笔,于画布上摆放、堆砌而成的、自我完善的物件。它完全可以自成独立系统,没有暗示或再现现实世界的义务。他所表现的人或物,只是试验形体与色彩的载体而已。苏轼亦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但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这说明,一幅画中若无形似,韵味便无从谈起。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叙述在刘海粟的《峇厘舞女》中找到了契合之处,如果把握不住“似与不似”、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平衡,刘海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刘海粟在民国时期的油画创作中,始终重视自身情感的直率表现,亦不忽略画面形式的理性建构,且着重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手法(包括书写性的笔触与饱和的色彩)以及东方精神内蕴的融入,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尽管刘海粟的油画作品往往由于追求拙朴与粗犷的画味,而牺牲了细节处的雕琢,但这也正是他个人所欲达到的“粗拙”与“率朴”的艺术境界。刘海粟以其独树一帜的艺术面貌,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油画界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在整个中国近现代美术中,他亦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宗师。
①周湘(1871—1933),字印侯,号隐庵,上海嘉定黄渡镇人。中国近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工山水、仕女人物,兼擅书法、治印。
②布景画传习所:由画家、美术教育家、洋画运动先驱周湘于1911年7月19日在上海创办。近代中国早期的西洋画传播与教学机构之一。
③移情说,由德国美学家废肖尔在“移情”理论的概念基础上提出的美学术语,主张人可以将自身的情感赋予对象,使其具备某种审美色彩。此理论广泛应用于20世纪初西方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的创作实践中。
④李安源:刘海粟与蔡元培,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⑤石井柏亭(1882—1958),原名满吉。日本著名西洋画家,擅长油画、水彩画,兼及日本画。其画作风格偏向写实。
⑥莫艾:《接受的限度—论刘海粟首度欧游阶段对西方艺术的解读与反思》,《文艺研究》,2013年第12期137-144页。
⑦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96,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