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友爱”
——一种共享式的共在
张云翼
在《存在与时间》中,“此在之存在”(Sein des Daseins)的基本样式是“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并分别展现为“寓居于用具世界”(Bei der Zeugwelt sein)、“共在”(Mitsein)和“自身存在”(Selbstsein)。就理论构成而言,“自身存在”更为基础,并且是“此在之存在”的本真性得以成立的根基;而“共在”和“寓居于用具世界”则多体现为奠基于本真性的日常状态。虽然我们确实也能找到关于本真的共在样式及其实现的条件的相关论述(1)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2006, S. 124, 298.下引该书以缩写SuZ加页码形式随文夹注。,但这些只言片语还难以成为共在之本真性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承认共在具有本真性,但却难以说明:在本真性中,共在与自身存在对“此在之存在”的构建作用有何差异?它揭示出了一种怎样的此在的存在实情?

一、基础存在论中的共在及其疑难
在《存在与时间》第25-28节中,海德格尔引入了共在问题,并且通过对“共同”(mit)和“也”(auch)的阐释初步勾画了共在之图景。具体来看,“共同是一个此在式的共同”(SuZ, 118)。“此在式”(daseinsmäβig)规定了此在这类存在者的存在性质。因而,“共同”属于“此在之存在”构成要素;关于“也”,海德格尔认为“‘也’意味着存在的一致;这种存在即是寻视着的-操劳着的在世存在”(3)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S. 118.译文有改动。。也就是说,“我(此在)”与“其他此在”没有决然的区别。“其他此在”并不是除我之外的所有人,而恰恰是与我一致,具有同样的在世存在样式(操劳)。综上,海德格尔认为“由于这种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SuZ, 118)。在此,“共同”和“也”都说明了此在与其他此在都具有在世存在。
但这一章节的主题并不是“共在源始性”,而是“日常状态中此在为谁”(SuZ, 114),即此在的自身性问题。在澄清了共在的基本样式“操持”(Fürsorge)后,海德格尔立马转而讨论起“常人”(das Man)。总的来说,常人不是某个特殊的此在,而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常人是一种生存论环节并作为源始现象而属于此在之积极建构”(SuZ, 129);同时,它也是操持的极限状况“代庖”(Einspringen),如大众媒体对个人生活全方位地“越俎代庖”。相比之下,在操持中具有本真性的“作出表率”(Vorausspringen)却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当然,我们可以根据其规定性——“这种操持有助于他人在他的操心中把自身看透并使他自己为操心而自由”(SuZ, 122)——去构想一个合适的情境,如导师让学生自主选择研究课题。但是,这类实例要以本真共在理论上的明晰为前提。
可事实是,海德格尔一笔带过了“作出表率”。这并不是在回避问题,而是受限于基础存在论逐步构建进程。在此章节中,他也无法澄清本真共在:日常状态是“此在之存在”的一个特殊样式,而不是其全貌,而“常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过渡。它的出现恰恰强调了对“在之中”(In-sein)之一般结构分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那么,我们能否通过“此在之存在”的本真性来澄清本真的共在?这是一个理论疑难。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分别通过“畏”(Angst)(面向本真和整全的此在之存在的可能性)(SuZ, 184)、“向死而在”(Sein zum Tode)(此在领会自身界限的可能性)(SuZ, 258-259)和“决断”(Entschlossenheit)(此之展开的整体性)(SuZ, 301)来逐步勾勒出了本真存在,而且,在决断中,海德格尔也确实说明了本真共在的“实现条件”:“让一道存在着的他人在他们自己最本己的能在中去‘存在’,而在率先解放的操持中把他们的能在一道开展出来……本真的共处,唯源出于决断中的本真的自身存在……”(SuZ, 298)
显然,共在之本真性基于“自身存在”和此在的“个别化”(Vereinzelung)。通过个别化,日常状态中的“寓居于用具世界”和“与他人的共在”都失效了。对此在而言,这个“个别化了的存在”才是其本真存在。在此基础上,共在之本真性似乎就变得“理所当然”:在本真性中,此在仅仅根据其“为其之故”(Worum-willen)进行操劳和操持。这样的此在既不会受他人所制,亦不会试图去掌控他人。这似乎便是作出表率的实现。但是,“一同在此”不仅是存在论的规定,同时也要在此在的实际存在中得到实现,而“其他此在的自身实现”似乎并不能直接从“此在之存在”中得出。这之间还缺乏澄清共在之“共”的关键环节。对此,我们不妨暂且放下这一问题,先把目光转到海德格尔非常重视的亚氏哲学。
二、友爱:善的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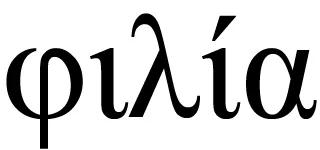
从性质和作用(1155a8-21)(5)Aristoteles, Nikomachische Ethik, übersetzt von Eugen Rolfes, hrsg. Günther Bien,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5.下引该书以贝克码随文夹注。此外,关于友爱的基本性质和作用,还可参见《优台谟伦理学》的相关内容(1262b7f, 1280b36-39)。(Cf. Aristotle, Works of Aristotle, ed. by W. D. Ross, M.A., Hon.LL.D.,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30.)来看,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章开篇中,亚里士多德开宗明义地将友爱理解为一种德性(1155a2-3)。德性与人的实现自身幸福(善)的活动息息相关,友爱亦是如此:无论是提供善举还是接受他人之助,都是促进个人完善的方式;同时,不同于灵魂之善这类“最恰当意义上的、最真实的善”(1098b15),友爱是一种必要之善,毕竟“即使享有所有其他的善,也没有人愿意过没有朋友的生活”(1155a5)。这种“有朋友的生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来,友爱是一种天性,是同种群的成员之内在联系的体现,二来,它还是维系城邦的纽带。稍加对比即可发现,“个人”“种群”“城邦”恰好对应着实践智慧的三个维度:伦理学、家政学和政治学。由于实践智慧本就是一种灵魂之善,所以,友爱不是某种情感的名称,而是善的实现,更准确地说,它作为对善的保全和成全,是现实着的善。

虽然友爱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朋友之间总是互相“因对方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1156b8),但这种“为他人着想”的根基仍在于个人追求自身之善的实现,即“一个人对邻人的友善,以及我们用来规定友爱的那些特征,似乎都产生于他对他自身的关系”(1166a1-2)。那么,“因他人之故”在何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因其自身之故”呢?在友爱中,“为他人着想”体现为,某人通过对朋友的关爱,成全对方的自身之故,例如:让朋友根据自身兴趣来选择专业。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善的自足性,一个拥有善的人,他的“为他人着想”亦是一种出于自身的善行,而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有用”或“欢愉”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为他人着想”是基于“实现着自身之善”的一个样式,而且“着想”的内容也是善的,因为一个善的行为无法包含“不善”的内容。由此,友爱作为“因他人之故而希望他好”归根结底亦是“爱友者”的自身实现。
但是,“因他人之故而希望他好”并不意味一种“传递性”,如某个拥有善的人通过其善举把另一个人带入友爱,进而让他也能拥有善。作为善,友爱是一种拥有善、或类似德性、亦或相同目的的人们之间的共处关系。不仅如此,对于关系中的具体的人而言,这种关系具有先行性。更准确地说,它是亚里士多德以“友爱”(伦理学)之名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对“善”的实现:对亚氏而言,善不是柏拉图式的理念;善类似于形式(Form),它不仅是普遍且现实的,还随着个别实体一同展现。对“好人”而言,“拥有善”是其自身的实现,正如个别实体拥有其形式一样;但对于另一个好人的自身实现,他就无能为力,只能让另一个人也因其自身之故地实现自身。这种“让”不是消极地“自扫门前雪”。毋宁说,它在确保个人自身之实现的独立性的同时,还凸显着诸个别者间对其共有本质的分享。潘格尔也认同这一“分享”:“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好的生活同时也是最能够被分享的生活。”(6)L.S. Pangle, Aristotle and the Philosophy of Friendship, p.191.在此,“被分享之物”并不是个人身上的某种特质或目的,而是其本性(或德性);而“分享”也不意味着某人拿出对方所没有的东西,以供对方使用。只有友爱双方都是“基于自身之故而实现自身之人”,换而言之,两者都是好人或拥有同类德性,他俩才有可能共同享有善或同类德性。这也正是应了那句俗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基于友爱之“分享”特性,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何亚里士多德把它视为比公正更好的维系城邦的方式了。那么,我们可否认定,海氏哲学中基于自身存在的共在就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呢?不,这一相似性仅依托于文本内容的对比。如要进一步揭示两者的亲缘关系,我们还得深入它们各自的基础(“此在之存在”与“善”)及关联。



四、话语的共享和“道出自身”、共在的困难

就结构而言,话语包括“所谈之事”(Beredete)、“话语之所云”(Geredete)、“传达”(Mitteilung)和“公布”(Bekundung)(SuZ, 162)。具体来看,“所谈之事”是某次具体言谈的主题。例如,当我说“这张椅子太硬了”时,“这张椅子”就是言谈的主题;它源于说者的“为其之故”。更准确地说,“为其之故”限定了“所谈之事”。相比“所谈”,“所云”更加丰富,因为它是对言谈之“为其之故”的完整展示。在上述例子中,我正是通过“太硬”来展示“谈论这张椅子”的目的。此目的还可进一步被形式化:“太硬”说出了这张椅子(坐的用具)的不适宜。根据海德格尔对日常事物的阐释(SuZ, 67-71),他将用具视为上手事物;而用具之为用具源自上手性,也就是用具(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因此,“所云”展示了“所谈”中所涉之存在者(椅子)的存在方式(用于坐)的实际存在状况(太硬)。除了“所谈”和“所云”,话语还有“传达”和“公布”的功能。“公布”不难理解,它正是逻各斯的“显明”(SuZ, 32),即把某存在者展示为“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而“传达”则是处理共在问题的关键。
海德格尔认为,“传达活动从来不是把某些体验(例如某些意见与愿望)从这一主体内部传输到那一主体内部这类事情”(SuZ, 162)。“Mitteilung”是一个合成词,“Teilung”源于动词“Teilen”(分享、共有(11)当然,“Teilen”还有“分开、分裂、除”等含义,但与此处文本意思不符,暂且不论。);而理解该术语的关键就在于其前缀“Mit”。在“Mit”的众多含义中,与“Teilen”形成搭配的含义主要是“一起,共同(12)虽然海德格尔的用词非常别出心裁,但词义选择非常严谨,在讨论共在、共同此在等相关概念时,他就把“Mit”解读为“一起、共同”。(SuZ, 118)”。因此,“Mitteilen”也可以翻译为“共同享有”。当然,“传达”与“共同享有”并不矛盾,毕竟“传达”似乎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让……共同享有”。但这种作为言谈结果(对话题的共享)显然不是该词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且“传达”一词也确实容易造成以上引文中所说的误解。在言谈中,说者和听者皆是此在。作为“能够领会其存在方式”的存在者,听者不仅听到了“所谈”(存在者),还一并在“所云”中获悉了这一存在者所处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通过“所云”,说者实现了与听者对言谈目的的共同享有。这亦是一种共在的实现:“共在本质上已经在共同现身和共同领会中公开了。在话语中,共在以形诸言词的方式被分享着,也就是说,共在已经存在,只不过它原先没有作为被把捉被占有的共在而得到分享罢了。”(SuZ, 162)
这不就是一种此在间的共在吗?不,以上阐释还缺让言谈双方都能够展现其自身的关键环节,即“道出自身”(Sichaussprechen)(SuZ, 162)。谁在道出自身?此在。由于此在的自身存在是其本真存在的根基,因而“道出自身”也意味着“在道出中让自身存在”。回到凳子的例子,无论我如何表达我对凳子的观感,都得遵循一个“完备之在”(Fertigsein),即我总已对凳子(上手事物)的存在方式(上手性)有所领会。在相应的“道出”(“这张凳子太硬了”)中,被道出的是“我与凳子的存在联系”。虽然这一“道出”述说着我的某具体的存在方式,但同时也隐含着更为基础的东西,即我(此在)的自身存在。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具体的“道出”之中,我(此在)总已先行地对我(作为此在)的“自身存在”有所领会——我总已经道出了自身。因此,在某一具体言谈开展之际,言谈双方总已对各自(甚至是对方)作为此在式存在者所具有的特性“能够言谈”(13)海德格尔的这一规定类似于亚氏对人的定义,即“拥有逻各斯(会说话)的动物”(GA18, 45)。有所理解。任何一个具体的“所云”之传达的成立,恰好必须建立在双方所共有的“能说话”的基础之上。
在亚氏的友爱中,好人总是因其自身之故(目的因在自身之内),而坏人追求着不定的欲望(目的因在自身之外),两者无法结成共享式的友爱。好人之所以为好,正是需要其自身之善的实现。完善的友爱的基础正是对善或类似德性的共享。但是,在“道出自身”为基础的言谈中,我们如何才能像澄清“友爱双方对善的共享”那样,找到“诸此在对‘此在之存在’的共享”的理论依据,进而将共在视为对“此在之存在”的保全呢?
五、在情绪中的共享式共在
仅凭基础存在论,恐怕难以说明这个问题,但我们的讨论仍须由其开始。从目标而言,这一理论框架以此在的“自身存在”为基础来构建“此在之存在”的开显,为的是从“此在对其存在之领会”展现“存在领悟”(Seinsverständnis);就方法而论,它致力于通过时间化(Zeitigung)来展现“此在存在着”这一实情(可能性的实际起效);从结果来看,海氏确实通过“此在之存在”重新阐释了本体概念的多重含义(GA18, 21-35),并借由时态性(Temporalität)揭示了此在的存在(运动)内核“超越”(Transzendenz);基于此,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存在本就超越着(transzendierend)。同时,“此在之存在”也展示了此在特有的“整全”,即此在的“自身存在”、以及奠基于其上的“与用具世界和他人的存在关联”。当然,“奠基于”并不是说,此在能够规定其他事物的存在,而仅仅是强调,“存在者之存在”的成立归根结底源于其自身存在,成于存在者的自身显现(实际存在着)。因此,当某些存在者展现为用具或他人时,更准确地说,当我们称其为存在者时,我们早就已然默认了他们的存在。这一预设本不是问题,但此在与它们(用具和他人)的存在联系还不能等同于它们各自的自身存在,因为无论是用具性,还是他人的存在,都要源于此在自身的“为其之故”。这恐怕就是基础存在论中共在问题的核心所在。
此在确实是特殊的存在者,但不是某个特定的存在者,如:决定芸芸众生的神,而且海德格尔也并未声称“此在之存在”决定了其他存在者的存在。但是,“存在者存在着”这一实情确实需要一种“存在者的整全状态”。在此,“整全”意味着存在者成为“在其存在中存在着的存在者(das in seinem Sein seiende Seiende)”;这一“整全”不是某存在者所给予,而是存在本身敞开中所呈现,而且它也不是某一存在者的“整全”,而是一切能被称为存在者的事物所共有的。因此,如若存在本身具有超越性,它就还必须对“存在者之整全”(das Seiende im Ganzen)(14)“存在者之整全”是理解海德格尔思想转向之关键。方向红和丁耘都准确指出了此概念对基础存在论的完善性作用。不同的是,方向红更强调与此概念所对应的“元存在论”(Metontologie)与基础存在论的对立,亦即形而上学二重性之间的张力。丁耘则通过对马里翁还原思想的批判,呈现了“存在者之整全”中所蕴含的“一”与“多”的统一及其与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之渊源,指出“存在者整体不仅是转折后所谓存在论差异的核心,甚至就是‘转折’(Kehre)本身的要义”。考虑到此概念的复杂性,在此笔者仅处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内容。此外,对“Metontologie”之翻译,笔者沿用丁耘的译法“超存在论”。(参见方向红:《试论海德格尔元存在论概念的出现及其意义》,《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丁耘:《论现象学的神学与科学转向》,《世界哲学》2019年第6期。)进行超越。一般而言,“im Ganzen”多被译为“整体”。但笔者认为,此概念应该包含了存在者的“整”与“全”:从“整”来说,它指代“完整的存在者”,亦即一种现实着、并在其存在中完满地实现自身的存在者,例如亚氏哲学中的“神”;就“全”而言,它亦是一种“诸存在者之大全”。由于神的完满性影响世间万物,“诸存在者存在着”实际上是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共享。与此相应的超越就得具备两方面内容:1.对完满的存在者(存在着的存在者)而言,存在本身是超越的。这对应了《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海德格尔通过畏展现了“无之无化”对“脱落着的存在者之整全”的拒绝着的指引(15)Martin Heidegger, Wegmarken,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6, S. 114.。无不能“是”脱落着的存在者之整全;2.对统摄着一切存在者的东西(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言,存在本身亦是超越的,因为它不能“是”统摄诸存在者的最存在者(Seiendste)。这对应着《形而上学基本概念》中海德格尔通过深度无聊(tiefe Langeweile)呈现了“存在者之整全的自身拒绝”对“存在者存在着”的开显作用(16)Martin Heidegger, Grundbegriffe der Metaphysik,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3, S. 210-211.下引该书以缩写GA29-30加页码形式随文夹注。。“存在者之整全”的统摄性作用关系着对共在问题的澄清,而如何理解深度无聊,则是此处的关键。
深度无聊开启了“一种特殊的无关紧要状态”(eine merkwürdige Gleichgültigkeit)(GA29-30, 207-208),使得此在无法通过某一具体的方式把握其他存在者。在深度无聊中,一切其他存在者陷入了“没有(kein)”,更准确地说,作为存在者,它们拒绝着(versagend)任何具体的把握方式(GA29-30, 207);同时,“人称化”的此在也宣告无效。综上,无关紧要状态中的“剩余”也就只有最为基本的“存在者存在着”(dass das Seiende ist)。这难道不是与《存在与时间》中的畏功能类似吗?
确实,畏是一种“让此在直面在世存在本身”的可能性(SuZ, 187),而且这一“直面”也是此在实现自身的必要途径。但是,无论是“畏在世”,还是“畏即畏死”(SuZ, 265-266),其目的都在于澄清“此在之存在”。这是基础存在论的基本任务。但在深度无聊中,海德格尔并未借助无关紧要状态重回“本真的自身存在”。相反,他让此在逗留于无聊之中,更准确地说,他让此在无关紧要地逗留于那表现为“自身拒绝着的存在者之整全”(das sich versagende Seiende im Ganzen)的深度无聊之中(17)“Langeweile”源于动词“langweilen”,“lang”指“长时间的”,“weilen”指正是“逗留”,由此“langweilen”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存在者的运动方式。在这种“长时间逗留”中,存在者才能“存在着”。,并以此来展现一切(此在式或非此在式)存在者的存在实情(存在着)。在这个意义下,“此在之存在”确实依旧能够被理解为“向死(界限、终结)而在”或“在世存在”,但深度无聊中的存在者之整全却不从“此在之存在”出发来解读“存在着”这一适用于所有存在者的实情,即便“此在之存在”是通向存在本身的可能道路。
在此,我们还可以结合“在世存在”来进一步推进讨论:从理论结构来看,作为此在的存在建构,“在世存在”揭示了此在(存在者)与世界的联系(SuZ, 53),进而厘定了“此在之存在”的基本样式,即“向……而在”;从功用而言,“在世存在”作为此在的“存在着”,保证了此在的实际存在。也就是说,“在世存在”成就了此在之整全。但是,在《形而上学基本概念》中,海德格尔对世界的阐释已不再聚焦于此在的存在活动。通过“世界的弄权”“筹划中,世界弄权着”等这一系列世界对存在者(包括此在)的弄权(Walten)(GA29-30, 514-515, 530),海氏反倒彰显了“存在者之整全”对诸存在者的普遍性。
在无关紧要状态中,“在世存在”不再是从此在的“第一人称视角”出发的存在活动。此在之逗留揭示了它的存在实情:作为存在者,它在整全之中。不仅如此,由于无关紧要状态公开的是“作为无人称的此在驻足于其他无法以具体方式把握的存在者之间”(18)W.Y. Cheung, Stimmung und Zeit in Heideggers Deutung der Seinsfrage, Nordhausen: Verlag Traugott Bautz GmbH, 2020, S.161,166,191.,而且这种“驻足于……之间(inmitten des... stehen)”不是从一个以此在的个别化为基础、进而勾连其他存在者的此在式生存(在世存在),因此,无关紧要状态不单呈示了此在式存在者的整全,而且是一切存在者的整全。换言之,此在与其他存在者共享着“存在者的整全”。在这个意义上,无关紧要状态就揭示了一种诸存在者的共在,一个诸存在者皆由自身的存在出发、却又共享着“存在者存在着”的存在实情,“情绪并不是一个在灵魂中作为体验到场的存在者,而是我们共同此在的如何”(19)Martin Heidegger, Grundbegriffe der Metaphysik, S.100.译文有改动。(GA29-30, 100)。不同于基础存在论中此在的个别化的奠基性,在无关紧要状态中,我们尚无须区分此在与非此在式存在者各自的存在。
还需注意的是,在深度无聊中所展现的“诸存在者存在着”的存在实情与“此在之存在”关系依旧甚密。如果没有此在分析及其时间化,“此在”这一特殊的存在者的整全都无法澄清,一般意义上的“存在者的整全”就更无从谈起。因而深度无聊还有另一维度,即“此之在”发生的视域。在此,海德格尔又重回基础存在论中的决断、时间性、当下即是等关键性概念(GA29-30, 211-217, 222-228)。也就是说,如果说基础存在论通过“存在问题的时间化阐释”为我们带来了“此在之存在”的整全以及澄清“存在者之整全”的必要性,那么通过深度无聊所揭示的“诸存在者对其存在性质的共享”恰好实现了基础存在论中对共在在的预设;而以“存在者之整全”为核心的超存在论也不是用于替换基础存在论的新系统。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基础存在论和超存在论之统一构建了形而上学的概念”(20)Martin Heidegger, Metaphysiche Anfangsgründe der Logik im Ausgang von Leibniz,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8, S. 202.。
六、结 语
情绪概念的发展对存在问题之阐释具有完善性作用。在深度无聊中,诸存在者对其整全状态(“存在着”)之共享得以呈现。这种基于“存在者之整全”的诸存在者之共在正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保全”。在这个意义上,基础存在论中以“作出表率”为本真样式的共在才是可理解的。这正是对《存在与时间》中“共在何以可能”的补充和完善。也只有这样,本真的共在与亚氏友爱的相似之处才真正得到了澄清;同时我们亦能理解海德格尔在基础存在论中未提及友爱的原因之所在(21)实际上,在1927-1930年间,海德格尔也未论及友爱问题。在1928年的莱布尼茨讲座后,他开始系统地进入德国古典哲学,其兴趣也明显转至德国古典哲学。。不过《存在与时间》毕竟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基础存在论受其理论本身构建进程的限制,诸如共在这类概念无法充分展开也是有理可寻。因此,在批判海德格尔的同时,我们亦可将其放至更为广阔和深厚的理论背景中,并通过海氏诸文本之联系,找寻完善其思想发展图景的可能径路。这亦是阐释者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