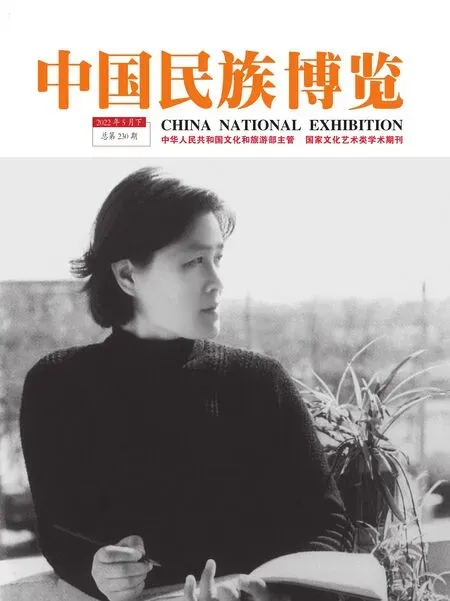身份焦虑与重构
——论鲁巴伊巴勒斯坦难民小说
柳源清 南北宝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00)
1948年以色列建国并发动战争,将近70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地区被占领,史称“Nakba”(النكبة,劫难)。大批巴勒斯坦人沦落为难民,此站役成为现代巴勒斯坦史上的分水岭,国土沦丧、国民出逃引发的创伤记忆成为巴勒斯坦当代文学的“奠基神话”(艾仁贵,2013)。流落海外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用文字治愈民族创伤,追忆祖国美好过去,深思与残酷现实格格不入的困境。这些知识分子兼有圈外人与圈内人的双重视角,这种游移、混杂的地理位置使他们对文化、对祖国的认识更为深刻。
巴勒斯坦难民小说聚焦“后Nakba时期”,以巴勒斯坦难民生活状况为主题,是“巴勒斯坦文学”的一部分(周顺贤,1994)。“巴勒斯坦难民小说”注重写实,刻画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细节,反映社会现象和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感情,表达巴勒斯坦难民在国外的真实生活和对祖国的强烈思念。通过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或荒谬、或悲惨的故事,建构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


一、现实主义:鲁巴伊难民小说的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要包括:1.真实地反映生活,是现实主义的目的和原则,是核心层次;2.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刻画性格,塑造典型形象,实现上述“目的”的方法和途径,是中间层次;3.按生活本来的样子描绘生活,实现上述“方法和途径”的手段,是表面层次。
《命运:大屠杀与大劫难的协奏曲》(以下简称《命运》)与《来自特拉维夫的女人》(以下简称《女人》)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主题、人物和故事情节上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以瓦利德·达赫曼为线索展开情节,刻画了母亲、朱莉等鲜活而真实的人物,展现了巴勒斯坦难民的现实形象。
(一)巴勒斯坦难民的复杂和矛盾形象
1.瓦利德·达赫曼:第一代难民的矛盾形象
瓦利德的思乡之痛、离别之苦蔓延了38年,他渴望摆脱“难民”身份。在“是否要继续回家的路上”,他产生过动摇。但是,当得知“英国护照”可以从“VIP通道”过,他的个人尊严得到了满足,那种兴奋和喜悦一下跃于眉宇间(鲁巴伊·马德洪,2013)。
这种矛盾形象真实体现了以瓦利德为代表的漂泊在发达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群体。叶落归根回到祖国成为他们魂牵梦绕的愿望,当真正踏上祖国的领土,却无法接受现实的残酷。
2.朱莉·达赫曼:第二代难民的纠结形象
朱莉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葬回家乡,回到阿卡。朱莉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因为对于家乡和Nakaba的记忆来源于母亲的口述。
她内心对祖国所有的记忆都是虚幻的,她感到恐惧害怕。(鲁巴伊·马德洪,2013)
居住海外的巴勒斯坦二代难民接受西方教育,对家乡的认知限于口述史,缺乏具象的记忆和联系,祖国只是虚化的情感寄托,随时可以产生或者消亡。时过境迁,二代难民难以将现实与父辈回忆挂钩,更像观光客,对祖国的好奇感远远大于对祖国的眷恋感。
(二)鲁巴伊难民小说中的典型细节
1.丧失尊严的安检
第二次阿拉伯大起义之前,以色列人频繁地遭受恐怖袭击,检查站是受攻击的“重灾区”。因此,以色列军人与来往的阿拉伯平民之间相互警惕。
又等了好几个小时检查站才开始放行……士兵看都没看他一眼,就把瓦利德的护照拿走了。(鲁巴伊·马德洪,2013)
鲁巴伊描写了大量安检站的细节,巴勒斯坦人“双眼像被粘住了”、以色列士兵“把护照往桌子上一扔”等,任何接受检查的人员都是“可疑的”。为了安全抵达目的地,巴勒斯坦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忍受着。
2.穷追不舍的轰炸
《命运》与《女人》两部作品真实地再现难民的日常生活。瓦利德的母亲是无辜的,这些普通的巴勒斯坦百姓只希望和平、安定,但是,如此简单的梦想,却惨遭蹂躏。
我(瓦利德的母亲)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纳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呼啸着朝我们飞来。我非常着急地对着他们大喊:“你们在干呀,孩子?!……一旦你们躲进居民区,他们会对我们开火的呀!”(鲁巴伊·马德洪,2015)
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巴勒斯坦人都是“威胁犹太人安全的危险分子”。面对强大的敌人,巴勒斯坦人只得忍气吞声,赔上全部的尊严等画面展现在读者眼前,让人不得不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遭遇。
(三)鲁巴伊难民小说中的典型意义
(1)久居海外的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后对故乡不能适应
瓦利德在新的环境中闯出一片天地,对祖国的依恋促使他踏上了返乡的旅程。当他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时,却无所适从。
一个热心的巴勒斯坦青年察觉到了这个“外地人”的困惑,“嘿,他不是本地人!”(鲁巴伊·马德洪,2015)
流散的巴勒斯坦人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因乡愁引发的巨大痛楚与可怕孤独是不可弥合的,他们对美好的过去无法释怀,对现状却又格格不入,游移、兼具、混杂在圈外人(outsider)与圈内人(insider)中。个人与故乡、自我与其真正家园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对于流散的哀伤永远也无法克服。
(2)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难民面对以色列的辛酸奋斗
对儿子的思念是瓦利德母亲生活的全部动力,她坚守在饱经战火摧残的难民营中守候儿子归来。尽管有时,她面对现实很无奈。
“每天早晨,她都会问自己,我儿子会在我死之前回来看我么?我还有没有机会告诉他这一切背后的故事?他会怎么回应我?(鲁巴伊·马德洪,2015)
面对悬殊的军事和经济差距,母亲内心的愤怒无处宣泄。但为了亲人,母亲甘愿忍受种种委屈,甚至勇敢地反击。平凡而弱小的难民用尽毕生力量捍卫家园。
二、身份认同危机:鲁巴伊难民小说的叙事视角
身份认同(Identity,具有“本体及相同性、一致性”等含义)是个人或者集体界定自身处于某一特定语境中自我身份的标志(张莹等,2014)。在全球一体化语境的现代社会中,大规模的移民使身份认同失去了原本的稳固性和明确性,导致个体产生观念、心理、和行为的焦虑、缺失。因此,这些个体和集体需要对身份进行重构。
(一)巴勒斯坦难民身份认同的焦虑
在新的环境中,难民的民族身份意识在持续的现代化追求中逐趋模糊,甚至“丧失”(李如春、肖井泉,2012),巴勒斯坦难民对身份的焦虑不断滋生,个人的身份逐渐模糊,形成“身份认同的焦虑”。
我担心有谁过来,喊道“巴勒斯坦人,这个男的是巴勒斯坦人。”(鲁巴伊·马德洪,2013)
瓦利德在两种身份认同中徘徊,“英国化”现实身份表象之下,瓦利德在心理构成上倾向于巴勒斯坦原生身份。但在文化形象建构上,身份取决于外部环境对主体的认同,即他人的评价和选择。在西方人眼里:他是可以亲近的阿拉伯人。但巴勒斯坦文化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在巴勒斯坦同胞眼里,他俨然是一个西方人。
(二)巴勒斯坦二代难民身份认同缺失
由于多重文化交汇,原生身份认同建构过程呈片段化,第二代巴勒斯坦难民的身份认同表层出现缺失和断裂。“家乡”是历史与记忆紧密联系的身份认同空间,“二代难民”长期接受西方教育与文化价值观输入,但是,由于缺乏与祖国产生亲密的空间认知,朱莉对“巴勒斯坦”的感情更多是“好奇”。
朱莉诧异于母亲临终遗愿是将骨灰带回“祖国”安葬。但“祖国”与父母描述的完全不一样,她感受到害怕。“二代难民”初来“祖国”的真实感情在朱莉身上得到诠释,她对“祖国”身份认同的缺失彻底暴露。“二代难民”的生活环境与祖国完全不同,形成了对世界、文化等方面的认知不平衡,从而导致了他们对原生身份认知的缺失。
(三)难民群体的身份重构
瓦利德如愿获得看似“更高贵”的英国合法公民身份,没有得到心心念念的蜕变。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身份还是“英国人”身份都无法轻易抛去。反而随着年龄增长,对祖国、母亲的思念越发深沉,内心的焦虑逐渐褪去,身份认同焦虑得到化解,他选择现实,做“巴勒斯坦裔的英国人”。
以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来看,东西方文化不存在所谓的绝对力量对比和冲突,而是存在彼此协商对话的空间。作者通过刻画人物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迷失、追寻,进而构建真正属于他们的身份认同。
三、祖国情怀:鲁巴伊难民小说的主题凸显
主题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部分,是集中对个别主题、母题做追溯探源的工作,探究作者是如何利用主题反映时代和凸显小说的情感(王春荣,2006)。本论文将借用“主题研究”,分析鲁巴伊在《女人》和《命运》两本小说中如何反映时代、表达感情。
(一)“小宅子”——母亲在祖国永远的家
在作者笔下,独自生活的母亲是柔软、坚强的。在母亲眼里,小宅子是除儿子瓦利德外,世界上最亲近的“家人”。
她对着小宅子自言自语,用手指摩挲着最靠近她的那面墙,就像是在爱抚亲爱的恋人、爱抚她的孩子。(鲁巴伊·马德洪,2013)
与此同时,任何船坚炮利都无法击垮母亲的意志,几十年的小宅子被多次炸毁,她每次都坚强地拾起一砖一瓦,重新搭起房子。
辛辛苦苦修缮好的房子还没有住满6个月,又被以色列的阿帕奇直升机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击垮。(鲁巴伊·马德洪,2013)
“小宅子”是积极的信号、希望的象征、艰难夹缝中的希望,信念被摧残但从未摧垮。有别于以往小说,鲁巴伊着重凸显巴勒斯坦难民生活的困难,和抨击以色列政府的丑恶嘴脸,试图展示巴勒斯坦难民——苦难面前不服输、不低头的品格。通过对“小宅子”一系列情节深入地刻画,更多的人关注巴勒斯坦难民的积极与乐观,而不仅仅是怨天尤人。
(二)“父母爱情”——瓦利德在祖国的根
年迈母亲婆娑的泪眼,使在外漂泊38年的瓦利德愧疚不已。但每当提起“小宅子”,母亲仿佛年轻了几十岁,与丈夫刻骨铭心的爱情使她坚信一切值得。苦涩但温馨的画面浮现在鲁巴伊笔下,难民营里的爱情是纯粹的、干净的。
瓦利德他爸,你走了,没有其他男人可以走进我的心了。(鲁巴伊·马德洪,2013)
整部小说将废墟中有荒凉,有爱情,更有希望,有着人间最美好的主题刻画得淋漓尽致,鼓励无论是生活在巴勒斯坦亦或是流散的难民同胞重拾生活的信心。虽然仍有炮火,仍有苦难,但是希望是最有穿透力的情感。
四、结语
依托瓦利德对身份认同的焦虑,朱莉对身份认同的缺失,寄托母亲牵挂的“小宅子”和“父母阴阳两隔的爱情”,巴勒斯坦难民小说家鲁巴伊将是巴勒斯坦人永远无法抹去的祖国情怀展现给读者。时过境迁,“巴勒斯坦人”或“难民”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鲁巴伊将亲身经历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融入写作中,作品风格现实,感情刻画细腻,文字表达更趋近与东方与西方都能够接受的风格,引发读者思考巴勒斯坦问题背后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