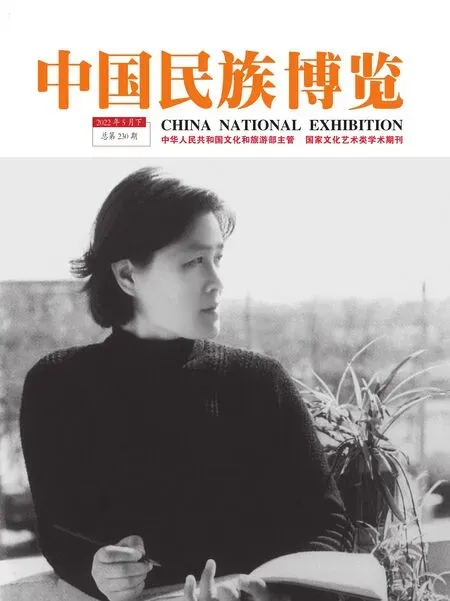共时分布与历时演变:土家族摆手舞的舞蹈身体语言变迁
任栗苇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上海 200000)
摆手舞,是土家族的代表性民族民间舞,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至2008年,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申请的土家族摆手舞、湖北省来凤县申请的恩施摆手舞、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申请的酉阳摆手舞,分别列入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摆手舞主要分布在我国湖北、湖南、川渝、云贵等山林地区,并且在这一地域内较为普及。清代《永顺府志》《湖广通志》等方志文献中均有对土家族摆手舞的记载。另外,清代土家诗人彭勇行、彭勇功兄弟,以及他们的侄子彭施铎均在多篇《竹枝词》中,有过关于“摆手舞”的相关描述。例如,彭勇行在诗句这样写道,“摆手堂前艳会多,姑娘联袂缓行歌。咚咚鼓杂喃喃语,女弱女弱余音荷曰荷。新春上庙敬彭公,唯有土家磊不同。各地也荷同摆手,歌声又伴呆呆嘟。”彭勇功也在诗句中写道,“山叠绣屏屏尾拖,滩悬石鼓鼓声和。土王宫里人如海,宛转缠绵摆手歌。新春摆手庵年华,尽是当年老土家。”又如,彭施铎所写的“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
土家族主要分布于我国武陵山山脉以及余脉山区,跨越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界地区。土家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所以起源众说纷纭。颜勇在《土家族族源新探》中提出土家族的“多源”说。他认为从目前的分布与民族历史迁徙看,土家族是巴人、濮人、楚人的后裔。因手臂在身体的前、旁、后做大幅度和小幅度各类摆手动作配合多走山路形成起伏动律,而得名“摆手舞”。土家语将小摆手称为“舍巴日”,大摆手的土家语为“麦则嘿”。小摆手动作幅度较小,生活形式轻快活泼;大摆手因摆动幅度较大,多用于祭祀祖先。从舞蹈的发生来看,“舞蹈最先发动于身体的表达行为,即驱除恶灵的创作行为;而后才能有身体的‘文本’行为;最后才能有身体的接受行为,即部落村民观看后的释然”。所以摆手舞的发生来自于祖先祭祀、生产劳作,而后形成现在的表演形式。从舞蹈身体语言的共时性分布看,因不同地域特点与和其他民族不同互动生发了不同地域的摆手舞特征;从舞蹈身体语言的历时演变来看,摆手舞也因为时代的变化与更迭而变化,其语义和语用与古代已经截然不同。
一、摆手舞的共时分布
(一)地域空间
在语言学的方法论中,“索绪尔明确强调了‘共时的方面显然胜过历时的方面’,因为只有抽象的共时最能反映语言的自然关系。舞蹈身体语言同理。”对于摆手舞而言,身体母语来自于原始发生时候的语言形态。随着民族迁徙与通婚,摆手舞目前分布在鄂、湘、渝、贵等地,土家族与地域原住民和其他多民族发生互融关系后,形成了摆手舞一体多元的身体“方言”形态。如湖北地区的恩施摆手舞,先抬手臂,在向下摆手臂时配合颤膝的动律,基本动律为向“下”重拍。这一动律做手臂的大摆、小摆、屈臂摆和抬腿颤、踢腿颤等,多以表现农作生活、抒情达意。讲究韵律性。与湖北地区不同的是,以酉阳摆手舞为代表的川渝地区摆手舞,先做屈膝,在站直的过程中向上摆臂,整体动律为向“上”重拍。除此之外,以川渝地区摆手舞的舞蹈结构多以戏剧性为主,有时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都与土家族的生活相关。从共时分布来看,湖北地区和川渝地区摆手舞虽然都是以复杂的摆手、摆臂配合步伐舞蹈,但是动律随着历时演变呈现相反的节奏。这也正是“历时线性被共时呈现所体现”。尽管各地“方言”有所不同,我们也可以从“历时”发展之中找寻其共同特点就是“摆手”的舞蹈语言。如土家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中播种、插秧、打谷子等动作语言都成为了摆手舞动作语汇的基本元素。
(二)形态空间
1.生活形态
舞蹈身体语言学将舞蹈身体语言分为生活形态、规训形态和作品形态。其方法论适用于摆手舞的历时特性。虽然土家族没有文字记载,活态传承的摆手舞与远古时代的摆手舞具有相异性。在当代,受政府和专家们的指导与影响,原生形态的摆手舞几乎不得而知,现存在村落、山寨中的生活形态也因为时代变化而发生着变化。如土家族的“撒叶儿嗬”,仅前后十年的发展,其舞蹈人的心理、形式、过程等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两相对照,已经由邻里乡亲的无偿自发表演,悄然变成了民间专业表演队的有偿商业表演。”不过从人类的发生来看,摆手舞的语言来自于迎战庆功、祖先祭祀、原始宗教、巫术活动、生产劳作、模拟动物等相关内容。与当下生活相关的原生内容发展至今,就演变成了节庆舞蹈、时节舞蹈、自娱舞蹈。这些内容也是规训形态和作品形态的依据来源,即使是舞台的表演,很多时候对于劳动生活的诉说、对动物的模仿、对仪式的再现都脱离不了原生形态的语言来源。
2.规训形态
摆手舞的舞蹈规训性语言与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民族舞蹈还有着一定的区别,它不作为专门的教材以规训“专业民族舞蹈演员”进行使用。在土家族聚集的城区,群众参与摆手舞一般具有两个目的:一是以当地政府命名的各类不同主题的“摆手舞文化艺术节”,节庆欢愉而摆手舞蹈;二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进行“体育操”式的传播。无论是广场上的节庆舞蹈还是社区、学校等地的日常健身活动,都有统一的舞蹈模式进行规训和操练。所以场域空间的不同导致规训下身体语言的根本性不同。在广场上,“舞蹈教师以600元~1000元不等展开为期一年的教学”。在学校里,“龙山县、永顺县等地大部分中小学校都开设了摆手舞课程,学生们穿着民族服装围成圈起舞,动作生动、情绪饱满。”舞蹈身体语言在统一“模式”下被规训成为区别于原生形式语义的新形式。
3.作品形态
“舞蹈身体语言的作品形态包括舞蹈的创作文本、表演文本和接受文本,是进入‘期待’视野中有单位时空限定的艺术舞蹈。它脱离了生活形态的日常功能性和规训形态的技术工具性,就像人工制作的玩偶,不仅被制作出来成为‘产品’,被放进商场成为‘货品’,还要被顾客买给孩子成为‘消费品’,完成这三个过程就成为商品——对于舞蹈而言就叫‘作品’。”根据摆手舞的动作、动律与姿态创作的艺术作品形态很多,它们具有很多舞台民族民间舞的特点——审美、雅化。从舞蹈身体语言的视角看,这是能指与所指的非趋同性。
艺术作品“舞蹈身体语言作品形态的原有的动作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了可变性。不同的能指相连接,或同一能指的时间、空间、力量三要素之一改编,都会使最初的动作的性质发生变化,形成能指与所指重组的新的符号”。如摆手舞中生活形态的“上下摆手”“画圆摆手”“前后摆手”等各类动作相加的语义等于祭祀、狩猎、劳作、生活;而中央民族大学的作品《摆手女儿家》中摆手和各类的舞姿相加的语义等于美丽、优雅。
21世纪初,为适应新经济形式,各地政府大力开发各类旅游项目,旅游演艺应运而生。这时,土家族的摆手舞也因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旗号开始“招客引流”。鄂、湘、川渝、云贵等地的摆手舞演艺现象并非如张潮歌的“印象”系列,宋城集团的“宋城”系列等形成大型的演艺IP,而是在“旅游带经济”的形式下对摆手舞进行“旅游态”发展。如湖北恩施的“土家女儿城”中,用“原生态”和“非遗”的名义将游客招揽进场,并教学互动。从舞蹈身体语言的角度来讲,摆手舞在这一形态下被当作“消费品”实现了两面化的身体语言传播,一方面,是积极的,如他文化对本文化进行的一定程度的认知;另一方面,是消极的,并且是巨大的是,将非原生的语言进行传播而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舞蹈身体语言性来讲,这些动作和舞姿相加的语义的等于收益。
二、摆手舞的历时演变
语言的多样性来自于时间的多样性,维柯将艺术史划分为部落文化、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从这点来看土家族的历史层级,对土家族的族群影响较大的几个历时点为“羁縻制与土司制的实施;改土归流政策的实行;新中国成立;近代文化保护浪潮的复苏。”身体语言中的历时演变,突出表现在部落文化时期;土司制度时期;改土归流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寻根热”浪潮中,虽然经历下来语言形式的发展被限制在“文化框架”中,但我们还需要从土家族在历史中的变化而得知摆手舞的语义变化。
远古时期,土家族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而无法知其原生样貌。但在中国古代,秦岭、淮河以南的地区被称为“蛮夷之地”。相较于“中原”地区,生活在此地域的土家族先民——巴人天性喜爱歌舞,《后汉书》中提到“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乃武王伐纣之歌也。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摆手舞的语言生成来自于巴人喜爱的《巴渝舞》。公元前206年8月至公元前205年6月,汉高祖刘邦经过还定三秦之战,将巴、蜀、汉中三秦之地收入汉军。由此,巴渝舞则成为了汉代宫廷中重要的乐舞,并常常用来设宴群臣、招待贵宾。而到了唐宋时期,巴渝舞则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并且最终从宫廷乐舞中消失。
巴渝舞在宫廷乐舞中的消失,并不能代表着其艺术生命力的彻底完结,而是随着宫廷乐工、舞伎流落民间并广泛传播。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巴渝舞舞蹈语言体系和形式则逐渐过渡成与劳作生活相关的摆手舞。“唐以后巴人受汉人所逼,生存空间急剧紧缩,最后定居在今天武陵山脉,此时‘巴渝舞’不再称之为‘巴渝舞’而是转为“摆手舞”,舞蹈中减少了争战痕迹,增加了生活气息。在土司执政时期,人们跳摆手舞必先祭祀已故土司,同时还有驱邪纳吉、战地竣工以及促进青年男女交往的功能,村民祭祀土王,修建土王庙,祀奉已故土司。”摆手舞的语言变化也因为土家族族群的变化而变化,一是生存空间的变化,二是与唐代以前相比,在土司统治下,巴人的生活由农耕替代了狩猎。所以农作生活式的舞蹈语言逐渐替代了战争式的动作语言。
清代雍正年间,统治者对西南“蛮夷之地”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清代雍正时期统治者开始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施行的相关改革措施,废除了当地民族地区的土司世袭制度,并任命一定期限、可以调动的官员在西南地区开展人口清查、土地丈量、改革赋役等工作。改土归流以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土司不得出境,汉人不得入峒”。所以在土司统治时期,就是在雍正进行“改土归流”以前的土家族与外界、外族的接触甚少。直到改土归流后,因其核心是“废除原有的土司制度,确立朝廷轮流委派行政官员异地做官的制度。”所以将原始的、田野的、具有仪式性气息的“蛮夷地区”的少数民族舞蹈冠以“有伤风化”之名而被禁止。这其中也包括了土家族人民世代相传的摆手舞,历时的演变中,因强制或者非强制等种种原因使其呈现不同面貌,有时是压缩其物理空间,有时是消失绝迹。
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家文化部门到各省市地区地方政府对民族文化高度重视。随着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启动,民族识别、民族文化调查工作也提上日程,到1956年10月,经国家民委的科学识别与文化调查,最终土家族被确定为具有独立文化的单一少数民族。此时的“摆手舞”在被重新放置在重要的文化位置——族群文化的独立,民族身份被认同。1979年12月,湖北省设立了凤土家族自治县,后在1983年8月,撤销随着恩施地区行政公署的撤销,成立了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后在1993年更名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3年,在重庆也设立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而后1984年,湖北宜昌设立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重庆又设立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1986年,贵州铜仁市又设立了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和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前后中国兴起“寻根热”浪潮,政府和学者们开始着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恢复,此时的土家族摆手舞再一次也被重新发现、认识和传播。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打工潮的兴盛,祖辈居住于武陵山区的土家族村民也纷纷来到武汉、长沙、重庆、成都、贵阳,乃至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工。而这一时期土家族年轻群体在城市空间的转移中,致使原生态的摆手舞出现了一个短时期、局部性的断代。
至2001年,重庆酉阳正式被命名为“酉阳—土家摆手舞之乡”,当地土家族人民在参加摆手舞文化艺术活动时获得了报酬、威望以及关注,逐渐产生了民族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而后2006年,湖南湘西土家族摆手舞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后2008年湖北恩施摆手舞和重庆酉阳摆手舞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摆手舞的舞蹈形式、语言、甚至节日庆典能得以恢复,意味着在历时上曾经被禁止,而后被人为恢复;能够得以恢复,也意味着在共时上摆手舞并没有因“改土归流”而完全的消失。所以,这个“传统”来自于对元语言的承载和现代语言的融入。
从土家族的历史层级可以看出“摆手舞”的身体语言来自于远古时期的“巴渝舞”。土司制的建立和“改土归流”,对土家族族群的生活影响巨大。土司执政时期舞蹈身体语言从骁勇的巴渝舞转变为以农作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摆手舞”。从雍正开始,有悖于“男女授受不亲”思想,“摆手舞”被认为有伤风化,而后下令禁止。随后因为新中国成立和“寻根热”浪潮的涌现,摆手舞被“复现”和重新提及在历史的维度上。很大程度上,当时当今的“摆手舞”身体语言的形成与当代人的关系巨大,同时也因为能够被复现,意味着其共时分布的特点与中国古典舞的重建,从戏曲舞蹈中、武术、壁画中挖掘素材寻找规律不具备同理性。
三、对摆手舞共时分布的历时解释
德国语言学家施密特(Schmidt)提出语言的“波形理论”,他认为历时与共时的语言状态可以用“语言波”来描述。“在语言的生成、定型和发展中,既含着一种时间的流程,又含着一种空间的交错,合成一种波状的流动和重合。”共时语言呈现的多样性无论是否合理如何变化,都来自于时间的多样性。从历时的角度来解释共时分布的原因是较为准确的。纵观土家族摆手舞的舞蹈言语也是如此。
如表1、表2所示,经过挖掘后的摆手舞,无论是大摆手、还是小摆手都呈现多种类、多元化的语言体系。在时间因素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摆手舞是原始“巴渝舞”演化而成的结果,也是封建时代“改土归流”和“寻根热潮”留下的时代烙印,但是在后来又因政府和文化部门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形成了“渔猎”“农事”“军事”“生活”这样四类摆手舞舞蹈语言。而在空间因素上,随着巴人的移民、迁徙、融合,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等地的土家族又与汉族、苗族、瑶族、彝族、侗族等民族杂居生活,语形追溯“传统”,实际语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回归到时空因素,作为舞蹈身体语言的摆手舞呈现的各类动作,终究是对生活的隐喻,既包含古代生活也包含现当代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越来越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2017年,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曾经走出武陵山区的土家族人也开始了逐渐走上了回乡创业的道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以土家族摆手舞为纽带的土家族乡村旅游再一次出现了新的发展。

表1 土家族摆手舞舞蹈语言分类

表2 土家族摆手舞大摆手、小摆手舞蹈语言对比
四、结语
摆手舞是土家族人民历经千年,世代相传而来的民族文化和精神财富。在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土家族聚居地区,摆手舞在当地老百姓的心目中的精神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它承载着祭祀、劳动、交际、自娱等多方面的社会功用和精神内涵。本文梳理了土家族摆手舞的历时演变情况,根据历时演变对共时的存在与分布有了较为清晰的解释。因土家族族群经历的几次历史事件,其内部生活和外部空间对摆手舞的语用也产生了变化和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越来越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曾经走出武陵山区的土家族人也开始了逐渐走上了回乡创业的道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以土家族摆手舞为纽带的土家族乡村旅游再一次出现了新的发展。现在,摆手舞一方面在村落的节庆进行,也有旅游演艺性质的形态,更有舞台形式和位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下,其共时分布的语义更不相同。因此,我们从单一体的历时发展看到元语言形成语言波,多样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摆手舞凝结了土家族人民生产、生活、民俗等多方面的民族形态,在未来摆手舞依旧是土家族人民精神娱乐的重要形式,更是旅游文化、乡村振兴中重要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