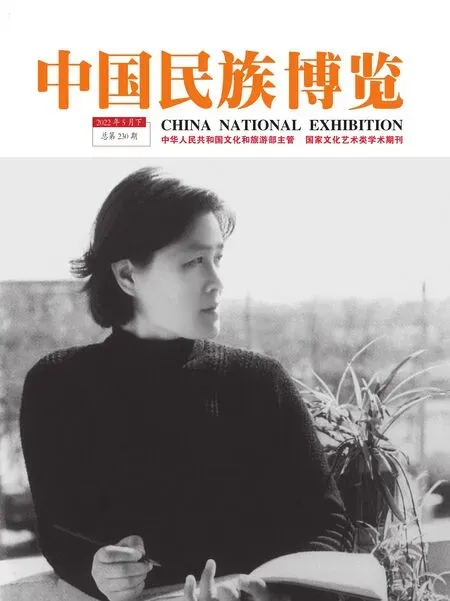骏马扬鞭 茂陵秋风
——西汉霍去病墓石刻赏析
文/赵农
霍去病出生的时候,父亲霍仲孺是平阳县的一名衙役,母亲卫少儿是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的奴婢。那一年大约是公元前140年。但是霍仲孺和卫少儿属于未婚私通,两人最终无奈分手,而霍仲孺离任后归家,另外娶妻,生下了霍光。卫少儿也改嫁陈掌。
卫少儿的妹妹即霍去病的姨母卫子夫,在平阳公主的操持下,送入汉武帝宫中,而且与汉武帝生下了史称“卫太子”、“戾太子”的皇长子刘据,于是卫子夫被立为皇后,舅舅卫青被封为大将军。
霍去病虽然失去父爱,但是在姨母、舅舅的庇护下,并随着卫氏家族的兴盛而茁壮成长。18岁为侍中,追随卫青,西征北伐,横扫大漠,英勇骁战,功勋卓著。曾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为骠骑将军出击匈奴时,寻亲拜见了父亲霍仲孺,并带回了当时只有十余岁的同父异母弟弟霍光。
《汉书》记载:“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上尝欲教之吴孙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
霍去病的丰功伟绩,使当时的匈奴人传唱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也使汉朝收复着河西走廊,拓展着国家实力。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为了彻底消灭匈奴,让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攻打匈奴。霍去病英姿勃发,一鼓作气,北进2000余里,与卫青共俘斩7万余人。
经此激战,左贤王战败溃退,匈奴已经失去了还击能力。霍去病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克鲁伦河之北的地方,封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祭天,禅姑衍山(今蒙古肯特山北)祭地,登临瀚海(今俄罗斯之贝加尔湖)以还。大将军卫青也得胜而归。据统计,霍去病一生四次出击匈奴,都大获全胜。因此,21岁的霍去病就已经功冠汉庭,威震天下。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有着个人的猜忌与盘算,不断地提携奖励霍去病,以至与卫青同等待遇。“自是后,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贵。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辄得官爵”(《汉书》)。目的是两人相互制约,以便自己控制。随着霍去病与卫氏家族的声誉鹊起,也带来了人生的阴影。而卫青也随着姐姐卫子夫的失宠,被汉武帝逐渐冷落。“青仁,喜士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于天下未有称也”(《汉书》)。
事实上,功成名就之后的霍去病与卫青已经产生了隔阂,并随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范蠡语)的惯例,汉武帝也不断利用着卫氏家族的矛盾摩擦,挑拨利用,分解离析,加强自己有效的统治力量。
霍去病突然死了。时间是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只有24岁。而《史记》记载的是“卒”,非常简洁,没有死亡原因。只是隆重地记载“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史记》)。《汉书》只是进一步记载“(嬗)为奉车都尉,从封泰山而薨。无子,国除。”霍去病的后代也基本灭绝了。
西汉时期的史学家褚少孙在《史记·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中补记:“光未死时上书曰:‘臣兄骠骑将军去病从军有功,病死,赐谥景桓侯,绝无后,臣光愿以所封东武阳邑三千五百户分与山。’”这个“病死”,就是对“卒”的补充。
褚少孙是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颖川(治今河南禹县)人。曾经居住在江苏沛县,为司马迁《史记》作过增补。
在《汉书》中,还有一段记载:“(李敢)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票(骠)骑将军去病怨敢伤青,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为讳,云‘鹿触杀之’。居岁余,去病死。”
李广为汉武帝大将,与卫青协同作战,不料迷途失路,力战逃脱后,不甘再被汉武帝追究,受辱身死,自己“引刀自刭”。其子李敢痛击卫青,而卫青心存内疚,不愿计较。但是,李敢是霍去病的部下,霍去病知道后,借射猎之机射杀李敢,一方面是霍去病桀骜不驯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有甥舅之谊的复杂情感。但是最大的收获是汉武帝高超的政治策略,由是功臣自残,而实现江山永固之意。加上元狩六年三月,霍去病竟然上书汉武帝,请立三位皇子为王,以确保皇太子刘据的位置。一介武夫,糊里糊涂地参与政治,于是这年秋天,霍去病就“卒”了。
“居岁余,去病死”,霍去病去世,文字记载太少,留下了太多的悬念。
当时已经40岁的汉武帝“悼之”,沉痛万分,也不乏心中暗喜,于是下诏厚葬霍去病。对待霍去病的儿子,更是“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等待着孩子长大后再能够像霍去病一样为汉室保家卫国。只是又不知什么原因,霍嬗在后来追随汉武帝“从封泰山而薨”了。
卫青也老矣,已经与寡居的平阳公主婚配,霍去病去世后,卫青闲居在家了10年。大约出生在景帝年间的卫青,到了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应该50岁以后了,“卫青围单于后十四岁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这14年是汉武帝元狩四年至元封五年(公元前119年~前106年)的时间。但是“征和中,戾太子败,卫氏遂灭。而霍去病弟光贵盛”(《汉书》)。
汉武帝终于释放了心理压力。纵观汉武帝的一生,杀功臣、杀文人、杀后妃、杀太子,借刀杀人,移花接木,比比皆是,虽说是自家的天下,也是自毁长城的愚蠢之举。而且有意思的是霍去病“卒”在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第二年就是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这个“狩”与“鼎”的差距,也是汉武帝心理的折射。
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面对霍去病的“卒”死,非常地小心谨慎,韬光养晦,终于成为了汉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的一代名臣。许多年后霍光把自己的孙子霍山过继给霍嬗为子,临死前上书宣帝以乞求祭奉霍去病的英灵。而霍光扶持的汉宣帝正是卫子夫儿子、又称“戾太子”刘据的孙子。
后人托名的《古今乐录》记载:“霍将军去病益封万五千户,秩禄与大将军等,于是志得意欢而作歌。按《琴操》又名《霍将军渡河操》,去病所作也。四夷既护,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未央兮。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兮。”也在惋惜霍将军的遭遇,如果霍将军真的能够早知“弓矢藏兮”的道理,也许不会英年早逝。
唐代崔颢《霍将军》诗:“莫言贫贱即可欺,人生富贵自有时。一朝天子赐颜色,世上悠悠应自知”。倒是品出了其中的得失甘苦,亦可知古来人事之艰险,命运之无常。

跃马
元狩六年霍去病去世时,送葬的军阵,黑衣黑甲,车马旌幡,蜿蜒连绵,自长安排至茂陵数十里,堆土为墓,冢为山形,以象征祁连山,由此纪念着霍去病。
霍去病墓在陕西兴平茂陵镇东北五里的土塬上,与卫青墓相衔连,其西南一里即为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冢现存底部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70米。冢高约25米,顶部南北长约15米,东西宽约8米,正视略呈覆斗状,侧看有山形焉。
霍去病墓现存石刻作品16件,有《马踏匈奴》、《卧虎》、《卧马》、《跃马》、《卧牛》、《人与熊》、《怪兽吃羊》、《石人》、《卧象》、《蛙》、《鱼》(一对)、《蟾》、《野猪》以及刻有“左司空”、“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的石料。另外在墓顶及墓下四周,还有巨型花冈岩石料150余件。全组雕像按照石材原有的形状、特质,顺其自然,以关键部位细雕、其他部位略雕的浪漫主义写意方法,突出对象的神态和动感。这些石雕从形式到内容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其中《马踏匈奴》为主题雕像,其余则围绕这一主题,与坟墓所象征的环境结合起来作全面性的烘托:或展现山野川林的荒蛮艰苦,或体现战斗的激烈残酷,或表现西汉军旅的英勇矫健等。
《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前石刻的代表作品,长1.9米,高1.68米,为花岗岩雕凿而成,高大的石马昂首站立,腹下有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的匈奴士兵,做垂死挣扎状态。整个作品采取线雕、圆雕和浮雕结合的手法,整体是圆雕方式,但是在作品的两边分别又雕刻出马匹的三条腿,呈现浮雕感。这匹战马形象被赋予百折不挠,坚定不移威武有力的人格象征,透过造型的表达,它向人们传递着两千多年前汉军严阵以待,维护安定和无坚不摧的信息,使观者感到振奋、壮美,仿佛是对年轻将领的气魄之写照。马下仰卧的人物形象,也雕刻得生动逼真,局部以线刻加以强调,线条疏朗而概括力强。整体看来,作品之上下两部分动静对比鲜明,形成了生动紧张的战争场面,雄健超凡、形神兼备,被誉为纪念碑式的作品。
相传飞将军李广上山打猎,看见草丛有一老虎,箭射过去,才发现是一块巨石,而剪簇已经深入石中。汉代人在自然中能够敏感地发现一些生动形象,不仅仅是误识,还有艺术的想象空间。《卧虎》是一件奇特的作品,洋溢着丰富的意蕴。采取圆雕的手法,加以线刻的局部处理,使整体浑然一体,而不失凝练华贵的感召力。如果把这个石虎放到树林中,更会增加作品的魅力。事实上,现在这些作品的陈列也是工作人员从墓冢上捡回来的,最初也许是翻滚的,或者是斜躺的。因此对于老虎的刻画,是出于一种时代的精神需要,英雄虎胆,虎视眈眈,甚至是一种艺术家超越自身的理想。
汉武帝时代对马匹的渴望,为了国家安全利益,需要西域的汗血马,充实汉朝军队的战斗兵力。于是为了寻找良驹,不惜翻越葱岭,打通丝绸之路,用商业或者战争的方式,获得大量的马匹,提升着国家的力量,保障着国家的安全。于是像《跃马》、《卧马》等作品,将一块大石头略加部分的细节刻画,形成一种轮廓的形象,以石赋形,手法简练,寓雕凿于意象之中,化刚烈以精气之间。《跃马》表现出闻惊而动,将要奔腾而尚未完全跃起的霎时间瞬息动作姿态。由静而动,如箭在弦上,发则风驰电掣,势不可挡的冲劲,这正是骏马雄烈气概的最佳艺术表现。《跃马》最精彩生动的部分是马的颈项,弧度与筋肉紧绷的质感,似乎在调动全身的气力,突出了整体之动势。这样的石马,更能使人联想到青年将领的果敢彪悍威猛英姿。

马踏匈奴

卧虎

石象
而《蛙》、《鱼》、《蟾》等作品,更是巧夺天工,凝聚汉代工匠的心血,一块石材,经过敲敲打打,便雕刻成一件千古不朽的艺术精品。这种生于自然万物,源于内心世界的物我相融的艺术创作过程,就是汉人气质的流露。
在这些作品中,最难理解的是几件有着草原风格的岩画般的作品,如《怪兽吃羊》、《人与熊》等,荒诞怪异,形态奇特,神情夸张。从石材的形体上,利用线雕浮雕结合的手法,赋予野性随意的生命张扬力。只有在游牧民族或者狩猎民族,才可能有与兽激烈搏斗的体会,甚至是逃生的过程,这种你死我活的搏斗,会带来一种深刻的内在记忆,并形成了内心的强烈恐惧。是否有着霍去病遭遇的寓意,也为后世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当然也有安详的《卧象》、《卧牛》、《鱼》等,尤其对于“牛”的刻画,那是一种生活安居乐业的从容自然,对于“象”的表现,也是一种超越时空的闲适优雅。
此外,像刻有“左司空”这样的石料,应是监督机构和管理人员的行为记录。实际上这些石料在墓冢中也许还有,还带有一些采石过程的痕迹,如劈石的凿痕,仍然印证着汉代工匠的辛勤劳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人与熊
霍去病事迹的奇特与复杂,在突然去世的瞬间,会给朝野以及汉武帝带来震动与沉痛,需要用石刻的方式来记功,告慰英灵,也使活者的心灵安适。但是随着工程的浩大,所费财物糜多,加上霍氏、卫氏家族的衰落,帝王的注意力也会慢慢地转移,而“左司空”这样的官员,也会懈怠,以至解散工匠,停止工程。已经运来的巨石,2000年来便散散落落地沉默在墓冢周围的草丛之中。
霍去病墓石刻原有的总数已经无法不可考证,明代嘉靖年间关中大地震,有许多建筑、石碑、石刻倒置或者被掩埋。
中国近代史的衰败过程,也使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中,艰难而倔强地追寻远去的足音。因而在以往的艺术史研究中,过多地强调了霍去病墓石刻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功用,而忽略了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也忽略了其历史文化的意蕴。
汉代在霍去病这些将军的手中,拓展了国土,也延伸了五湖四海的空间意识,丝绸之路从汉武帝时开通,从长安到红海,遥遥数万里,将西方与东方连结,“汉人”成为了一种中国人的代称。汉民族的强盛和先进,使许多欧亚北大陆的游牧民族,携酒赶羊,沿丝绸之路望风而来,定居西域,愿为汉朝郡县。因此,汉代人出现了具体的方位感,如“上朱雀,下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四方概念的形成。
霍去病征战到哪里,那里就是汉朝,而霍去病的军队中有大量收编的匈奴人,也不乏能工巧匠,除了朝廷征派的工匠来修筑霍去病的墓冢,还会有一部分是中亚地区其他民族的工匠。在汉代朝野的观念中,中亚也罢,汉朝也罢,没有绝对的国界区别,也没有后来的自卑感,只有拓展与生存。
开放的观念是国力的强盛,也会形成民族文化交流的意义。因此借助霍去病去世的机缘,不同的工匠表达着自我的特殊情感,也传递着一种汉代人从修养生息到拓展疆域的精神的延伸,也可以看成是不同文化艺术的密切交流。其实从技术层面上讲,这些作品中有农耕文化的风格,如《卧牛》;有草原文化风格的《怪兽吃羊》,两者有着明显的精神区别。因此,像《马踏匈奴》作为一件独立的突出的作品,是一种综合性的表现方式,更多地是记事的结果。
另外,汉代人对石质材料的认识,除了神仙祭祀的需要外,也与草原民族对石材的重视,而获得的启发有关。因为材质的不同,会增加着不同的感染力,早期的泥土雕塑、木质雕塑、陶制材质甚至青铜雕塑的加工,有着加工技术的特殊性,如手塑刀刻,以及翻模技术的运用,但是石材只能是因势赋形,以象寓意。尤其是花岗岩石材的坚硬,加上雕刻工具的限制,往往会制约着大型雕刻的创作过程。
铁器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普遍出现了百炼钢的技术。即将块铁进行多次加热锻打,其韧度和强度不断加大。因此,许多兵器和农具的加工技术的提高,对于中华民族的自信力形成了根本性的保障。尤其是与北方游牧民族长年征战中,铁制兵器成为了制胜的法宝。
汉代大量的铁器出现,也使雕刻工具得以改进,铁器的硬度胜过青铜的硬度,与之坚硬的花岗岩石材也会被选为作品的材料。
相传汉朝有一对石姓兄弟,力大无比,因此汉唐以来,民众也以“石”所向无敌,借此保障安宁。其实石文化的确立,与汉朝早期形成的休养生息的观念中,长生不老的观念也有很大的关系。石质的稳定性,有着与日月同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不是花岗岩石材,霍去病墓石刻也不可能保存到今天。
唐代诗人王维在《出塞》诗中写道:“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回头望去,历史留下了一堆艺术的石头,在咸阳原上祭祀与陪伴着骠骑将军霍去病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