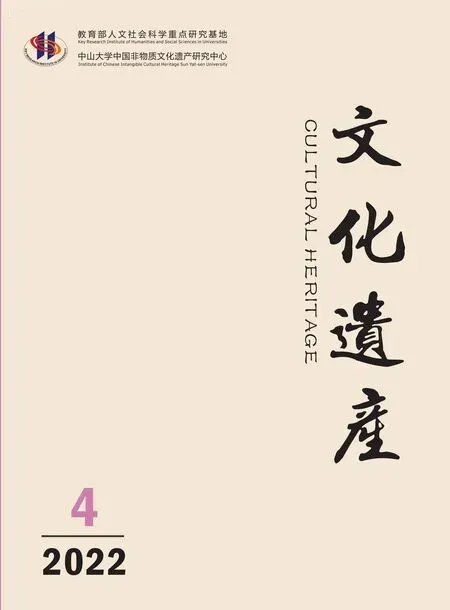图像与科仪:《新见〈西游记〉故事画》论略*
胡 胜 金世玉
西游图像是对西游故事的别样诠释,在图像谱系的艺术传统和表达成规内,演绎着今人或熟悉或陌生的故事。它们有的属于现存百回本小说系统,有的则游离于该系统之外。它们或以刀锥斧锤,或以笔墨丹青,不仅勾画出西游故事的演进轨迹,也和文字一道共同构建起一个立体的、多元的“西游世界”。这类图像包括雕塑、壁画、插图、画册等多种形式,或石、或木、或纸、或棉、或帛,多种材质,不一而足。湖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所出这套“西游”故事画,就是画在生麻片上的,从画中的某些服饰、器物特征推断,似应生成、传播于明代中叶,但其所描述的故事情节,有些明显异于百回本小说系统。它们的出现,一方面使我们进一步相信,西游故事的演进是多轨道的,而非单向度的;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到图画所承载的超越文本之外的特殊意义——祭祀鬼神的超度功能。这一点,与早期具有宗教性质的西游戏、西游宝卷等科仪文本是一致的。
近年来,在中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下,西游图像已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相当体量的独立“谱系”。截止目前,我们所知的西游图像(不包括小说插图),计有王振鹏《西游记画册》、张掖大佛寺壁画为代表的《西游记壁画与玄奘取经图像》、国家博物馆所藏清代画册、无名氏《清彩绘全本西游记》、矶部彰先生所搜集《西游记画三种》(前两种为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全像金字西游记绘本》《通俗西游记》)。其中,元代王振鹏所绘《西游记画册》是公认与百回本小说不同的“另一系统”西游故事,其他除早期少量雕塑、绘画外,举凡多幅成套作品则多与百回本情节相关,应是百回本梓行、流传之后的衍生物。它们尽管是图像,却是以刀锥斧锤或粉墨丹青演绎的同源同径的西游故事。然而,所谓“同源同径”,其实只是一种大概印象,即便一些图像确实以百回本小说为蓝本,也非亦步亦趋地“图解”原著,在事件形态、情节组织、场景呈现等方面,总是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差异,这些差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背后可能存在重要的历史文化动因。本文所论《新见〈西游记〉故事画》在这方面就极具典型意义。
一
本画册原为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所藏,由吴灿、胡彬彬整理出版。整套画册计12幅,纵118cm,横24.5cm,每幅以双线间隔,分为4帧,每帧绘有一个西游故事,共计48个故事。每个故事各有墨书标题(四言、五言不等),故事顺序与百回本小说有所不同。现分次简述如下:
第一幅四帧分别为“五雷击石”“悟空学法”“龙宫得宝”“大闹天宫”,可以对应百回本小说前七回“悟空出世”故事单元,却又与小说文本有些许差别。如“五雷击石”,画面主体是一个背生双翼,鸟喙、鸡足,左手执斧,右手持锤的雷公,左下角山石中露出一猴头,这与百回本小说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所说东胜神洲花果山“有一块仙石……内育仙胞,一日迸裂”,有明显主动、被动之不同。同时,小说描绘的“石猴出世”,并非俗语所谓“从石头里蹦出来”,而是灵石迸裂,生一石卵,见风化成一只石猴。故事画的表现显然更接近俗语的理解。
第二幅分别为“大闹地府”“见佛现掌”“光吕(蕊?)教书”“唐僧下世”,前两帧属于百回本系统;后两帧则属“江流故事”系统,明刊百回本没有专门明写。
第三幅分别为“坐等江流子”“放(访?)亲报冤”“梦斩老龙”“进京见主”,前两帧接续江流故事的大结局,后两帧则是百回本“魏徵斩龙”“太宗还阳”等情节的重述。
第四幅分别为“沙桥见(饯)别”“出山逢虎”“失落乌纱”“到五行山”。其中,第一、二、四帧分别见于百回本小说第十二回、十三回、十四回。“失落乌纱”则画一红发蓬头鬼举刀恫吓,三藏行李担丢在脚下,以袖掩面作惊慄状。不见于百回本故事系统。
第五幅分别为“悟空挑担”“夜被火烧”“失了袈裟”“八戒成亲”,分别对应百回本的第十四回、十六回、十八回。
第六幅分别为“收蚨(蝴)蝶精”“拿乌诡(龟)精”“经女子国”“捕沙和尚”。“收蚨蝶精”为百回本小说所无。按,传统西游故事中无蝴蝶精,唯福建仙游戏《西游记》有“双蝶出洞”,讲金蝶、银蝶二妖变化惑人,为悟空、八戒所擒,此画面或演此情节。“拿乌龟精”同样为百回本所无。不知与元代王振鹏《唐僧取经图册》中的“龟子夫人”是否有关联。“经女子国”可对应百回本小说第五十四回。“捕沙和尚”可对应百回本小说第二十二回,只是此情节百回本中在八戒故事之后。
第七幅分别为“回回引路”“坐相(降?)二孙”“战红孩儿”“收枯骨精”。第一帧“回回引路”不见于百回本小说,戏曲有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回回迎僧”,湘剧高腔《西游记》“回回指路”,演回回师徒接待三藏。第二、三帧分别对应百回本小说第五十八回、第四十一至四十二回。与百回本故事顺序不同。第四帧“枯骨精”或即“白骨精(夫人)”,可对应百回本小说第二十七回。
第八幅分别为“蟒蛇吐毒(雾?)”“大战魔王”“吃水生胎”“追赶西(犀)牛”。“大战魔王”似不见于百回本,第一帧“蟒蛇吐雾”或对应百回本第六十七回七绝山稀屎衕故事,后两帧则分别见于百回本第五十三回、第九十二回。
第九幅分别为“悟空回洞”“变弄宝扇”“玉公点化”“大战魔王”,见小说二十八至三十一回、六十回、六十一回。只是“玉公”不知何指,如接前幅火焰山借扇故事,或指灵吉菩萨。“悟空回洞”,湘剧高腔有“猴王回洞”。
第十幅包括“过火烟(焰?)山”“收鲤鱼精”“收白果精”“乌龟渡江”,分别对应百回本小说第六十二回、第四十七至四十九回、第四十九回,顺序与百回本有很大差异。“收白果精”中,悟空执棒挥向树下两个白色小人,唐僧等三人俯身观看。具体不详,疑其为五庄观人参果。
第十一幅分别为“慈悲引路”“收枯树精”“胃(畏?)见公主”“骆驼现身”。第一帧是百回本《西游记》中较为常见情形:观音云中现化,唐僧、悟空双手合十,八戒、沙僧紧随其后。此处不详具体哪回。第二帧当是荆棘岭故事,见小说第六十四回。第三帧应是天竺国玉兔精故事,见小说第九十三至九十五回。第四帧或是狮驼国降伏白象精,见小说第七十四至七十七回。
第十二幅分别为“私纵采仙桃”“唐僧脱凡”“失落金(兵?)器”“西天见佛”。第一帧百回本小说无此情节;第二帧应是接引祖师凌云渡接引故事,见小说第九十八回;第三帧应是玉华国被盗兵器事,见小说第八十八回;第四帧见小说第九十九至一百回。
二
如果以世德堂本《西游记》小说为核心参照系,这四十八幅图画所展示内容,与现有百回本系统同中有异。相同的是有较为详尽的猴王出身故事(包括学艺、闹龙宫、闹地府、闹天宫),有魏徵斩龙,这说明总体上属于业已相对完整的西游故事系统(前后两大版块有衔接,衔接情节也得到了表现)。同时,“五圣”的组合是齐全的,徒弟有悟空、八戒、沙和尚,以及白龙马,其称谓、样貌也基本是嘉靖朝以后趋于定型的形象,所降妖怪也大都见于百回本。从这个角度说,这套故事画所据应非西游故事的早期形态。
然而,从所涉内容看,画本的故事素材来源不一,并不以百回本小说为唯一蓝本。有些故事非百回本所有;即便与百回本相同者,小说亦只点到为止,图画则作重点描述。如陈光蕊、江流儿故事,在世德堂系统百回本中只是以“虚笔”交代出来的,没有专门独立的情节单元,画本却将其作为“重头戏”呈现,多达四幅。再如“回回引路”“收蚨蝶精”等皆不见于百回本,但可能和戏曲有相合处。“私纵采仙桃”似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入王母池之处”有某些关联,或由此发展而来。此外,还有诸如“失落乌纱”“玉公点化”“收白果精”等目前尚不能完全确认所指的单元。另有部分情节与百回本故事顺序不同,如“大闹地府”(第二幅第一帧)、“捕沙和尚”(第六幅第四帧),一方面可能是既有故事框架原本不同,另一方面也不排除装订顺序有误。还有一些故事尽管和百回本相近,但细节处不同,如第十幅第二帧“收鲤鱼精”,在百回本中观音收的是金鱼精,可在民间一些故事系统中较为常见的是鲤鱼精,像壮族师公经《西游记》通天河一段,即似把鲤鱼精和老鼋合一了。江淮神书里面,出现的则是“洞庭湖收鲤鱼精”,故事发生地洞庭湖恰恰是本地风光,或许不是巧合。第八幅第四帧“追赶犀牛”,画的分明是南方常见的水牛,并非犀牛。
再从形式上来看,这套画本的角色塑造并没有以百回本系统的小说插图为核心模板,而是明显有“戏画”的色彩。多幅画中人物身着戏装,如人物冠插雉尾(第二幅第三帧“光吕教书”,疑为陈光蕊的红袍人;第九幅第二帧“变弄宝扇”、第十幅第一帧“过火焰山”的铁扇公主)、背插靠旗(第八幅第二帧“大战魔王”的疑似青牛精、第九幅第四帧“大战魔王”的牛魔王),女性角色则大多身披云肩(第五幅第四帧“八戒成亲”的女性、第六幅第一帧“收蝴蝶精”的蝴蝶精、第三帧“经女子国”的女子国王、第十一幅第三帧“畏见公主”的公主)。
而在构图和物象呈现方面,又存在与小说插图相近、相通的地方,如“斩老龙”的画面就与李卓吾评本等插图多有近似处。再如猪八戒所使九齿钉钯,与我们熟知的钉钯迥然不同,整理者认为是“镗钯”,为明代俞大猷抗倭所发明,由此判定这套图像不早于16世纪。(下图从左至右分别出自日本广岛市立中央图书馆浅野文库、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李评本《西游记》《新见〈西游记〉画册》):

这些西游戏画与百回本小说存在的“小同大异”,答案如果排除画家的任意挥洒,那就应该只有一个——另有渊源谱系,至少掺杂了不同来源的西游故事。
如陈光蕊故事,从宋元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开始,一直到清初传奇(《江流记》),至今依旧活跃于昆曲舞台(《慈悲愿》)。故事在戏曲文本系统内相当稳定,且传承有序,民间传说更是遍及全国各地,在与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结合后,沉淀于地方戏曲、说唱本子中。基于此,画册大肆渲染“江流故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至今流行于衡阳地区的湘剧高腔“七大本”之一的《西游记》同样可为此作注,内中有多出曲目和画册所述不谋而合,恐不是偶然。如第二本“三王会”中有“围棋斩龙”,第三本“小西天”即包含“沙桥饯别”“回回指路”等关目,而这些恰是百回本所无,画图所有。
更进一步说,这些图画再次以不同的形式说明了西游故事演化传播生态的多样性,整个故事系统是逐渐聚合而来的,又长期处于活跃的裂变、转化、汰洗过程中。它们之中有许多并未被百回本所吸收、整合,因而未能成为小说系统(包括小说插图)的稳定成分,但它们有自己的传播途径,活性(动态)与惰性(静态)并存,惰性使得这类故事情节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一点,民间绘画和民间故事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它们应该是一种伴生关系。这套故事画应该就是这种“伴生”文化的产物。它与明代西游小说的插图有很大差别,更民间化,且与年画颇为相近,粗糙而淳朴,透露出浓重的民间乡土气息。除极少数画面构图品位较高,多数构图空间局促,题图直白,文字错讹(这种“错讹”一方面当然跟传播者的文化教养有关,但也暗示其信息的传播形态——配图讲唱,诉诸视觉的是图像,而非文字,故事是仪式执行者“讲”出来的,被参与者“听”到的。诉诸听觉的内容,落实到纸上,便会出现大量错讹,这是现存的大量讲唱本子可以证实的)。同样是“图像叙事”,却没有更多想象空间,遑论空间分割、布局的营构。也不是伴随情节而生,不受情节演进拘束,表现得十分随意。
三
如果进一步探寻这些图画的来源,颜新元所著《湖湘民间绘画》或可为我们提供另一个参照视角。此书是对湖湘地区民间绘画的收集、整理,第一部分“古今祭祀绘画”中的“吊偈画”部分收有3幅西游故事画,每幅3个故事,共计15个,无题目。
其中,多数情节与前套画图重合,包括“魏徵斩龙”“出山逢虎”“五行山收悟空”“八戒娶亲”“真假悟空”“老鼋摆渡”等,还有一部分画图和此套故事情节恰可相互补充,如前套只有魏徵斩老龙,颜氏所收则有秦叔宝、尉迟恭宫门挡鬼,唐王游冥、返阳等。
当然,不止与西游故事画的内容多有重合,更重要的是对形象的理解和表现逻辑也十分相近。典型者如画册中第八幅第四帧“追赶犀牛”中的牛精都是不折不扣的水牛,而非犀牛;第十一幅第四帧“骆驼现身”中的白象精造型与湖湘画中的骑青牛道祖、骑白象道祖胯下坐骑极为神似;第一幅第四帧“大闹天宫”二郎神手持方天戟(注意,不是三尖两刃刀)的造型,在湖湘画里同样反复出现;仔细观察湖湘木雕神像的符画系列,更能看到与哪吒、沙僧乃至菩提祖师、唐僧相似万分的造型。此外,还有多幅“道教风俗画”(包括悟空、八戒造像;唐僧遇难,观音施救场面)流传于湖湘民间。它们相似的艺术风格,相近的取材特点,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重合不应该仅仅是巧合,这些西游画应同出一源。这些涂抹着浓重地域色彩的画作,同为流传于湘湖间丧葬祭祀仪式所用“鬼神画”中的“吊偈画”。这类“吊偈画”别名众多,“在湘中一些地区习称‘水陆道场画’;在洞庭湖南岸被称为‘功德画’;在沅陵县苗汉民族杂居地区称之为‘道教风俗画’……”尽管名称各异,或名“水陆画”“功德画”“道教风俗画”,或统称为“鬼神画”,但都是水陆法会(原为佛教盛行的一种超度亡灵的宗教活动,后为道教乃至民间宗教广泛借用)法坛祭祀所用,承担着娱神、娱人的实际功能。有趣的是,在湖湘民间,不仅仅局限于水陆法坛,“这种吊偈画有时也被临时挂在地方戏的戏院,用以招徕观者,这时它们应该叫作戏曲画。”这或可解释为何此类画册多具有“戏画”风格。同时也可进一步说明,“吊偈画”的流传是多空间、多场景的,它是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娱人娱神,相得益彰。
这些画作的作者多为民间艺人、道士,他们往往和文人精英话语系统相距较远,他们创作的逻辑建构往往深受地域信仰影响,将沉淀于灵魂深处的神灵信仰流于笔端,诉诸纸帛。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地域风俗,使祭祀科仪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包括“吊偈画”在内的“鬼神画”,伴随着祭祀科仪共生同行,广为流传。“作为祭神与娱神的图画,是要取悦于神明的,自然要有看头。民间画师极尽表现之能事,总是拿出最有意思最受看的画面给神看。他们采用吊偈画的形式,或表现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或描绘生动传奇的西游故事;或把八仙安排于水斗场面;或将神仙与世俗故事混为一体”。可知这些“吊偈画”取材之广。而“取材”的标准——即哪些场面才是最受看的——说到底不在于“神”,而在于“人”,且不在于个体经验和期待,而是集体经验和期待。换言之,用以娱神的图像,总要经过娱人(且是娱乐大众)的“滤镜”,才能够超“凡”入“圣”,俨然起来,堂皇起来。就这一点来说,西游故事在湖湘地区成为民间“吊偈画”取材的热点,与三国故事是一样的,主要在于其热闹好看,即娱乐性、故事性、传奇性。然而,西游故事又有一个其他故事系统不能比拟的优势——它本身就是神魔故事,尤其是故事本身包含的超度元素,使它以更为广泛的艺术形式参与了民间宗教仪式的实践。
西游故事本身的超度功能,在同一地区的西游戏中也有展现,前文所说湘剧高腔《西游记》即以超度泾河老龙做结。这与我们熟知的西游戏结局(往往都是面佛获经,功德圆满)颇为不同。现今我们看到的西天取经缘起,皆因太宗入冥,而太宗入冥是因为许愿救助泾河龙王未果,泾河老龙告至十殿阎君案前,阎君派人拘太宗入冥对质。尽管由于魏征求助判官崔珏,成功使太宗还魂。但地狱的经历还是使太宗许下愿心,不仅要偿还相良的寄库钱,还要举办水陆大会超度亡魂。这是早期西游故事起始的原点。而这个“原点”本身是一个情节序列的组合,其起点序列正是“泾河龙王的故事”。即有学者所指出的:“《西游记》主干故事的动力始发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果暂时卸掉“大闹天宫故事”,单看“西天取经故事”(它本来就是独立发育的),“泾河龙王的故事”确实可以被视作整个故事的“青萍之末”。惜乎百回本实现了“大闹天宫故事”与“西天取经故事”的衔接,后者的“起点”变成了一个“衔接点”,进而被有意无意淡化了。而湘剧高腔《西游记》别具一格的结尾却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戏曲的宗教度化功能。能为这一点做注的是:这一剧目恰恰是酬神许愿时演出的!这与西游故事中的水陆法会产生了某种共鸣:水陆法会是天上地下各路神祇的大聚会,所有超拔的亡魂孽苦最后在仪式中集体获救,往生极乐。这又进一步启发我们去思考:“西天取经故事”的独立发育本来是一个“闭合结构”,以超度亡魂的“动机”起,以超度亡魂的“实践”终,中间的故事只是由“动机”导向“实践”的过程。只不过,在百回本这样由文人写定的小说里,故事系统重组的艺术构思“破坏”了原来的闭合结构,写定者的生花妙笔又尽可能修复“创痕”,使原初结构看上去很模糊,倒是在更具原生态色彩的地方戏曲、说唱本子里,原初结构未被“破坏”,看上去还很清晰。
当然,原初结构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但通过各类文本的比较,起码有一点是可以证明:这些西游“吊偈画”和某些湖湘戏曲一样,承担了超度、祭祀的宗教功能,成为宗教科仪的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出发,回看故事画取材来源的复杂性,一些“想不明白”的问题,或许就说得通了。前文已述,故事画叙述事件多有与百回本不合之处,这其实还是陷在了“百回本中心主义”的逻辑里。百回本作为一部文人小说,其对前代故事的整合、吸纳,主要还是遵循着传统的“寓言”逻辑,依据审美的标准,一些与超度密切相关的人物、事件,或被删削,或被弱化,或竟成为服务于叙事的一个“功能”——斩龙、游冥、进瓜情节蜕化为联结“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两大单元的“钩子”,就是一个突出表现。在许多仪式唱本里,这部分内容才是叙述和描绘的重心(中心)所在。故事画整合、吸纳故事的逻辑则显然不是寓言性的,也不依循审美标准,而是为超度、祭祀等宗教仪式直接服务。哪些故事符合这一要求,就会成为故事画表现的对象。
其实,早已有人指出湖湘一带“吊偈画”中的西游故事是参照当地瑶族师公祭祀的抄本《受生填还宝卷赞》而来(《受生填还宝卷赞》从内容看与《受生宝卷》为同一故事体系的仪式文本,将魏徵斩龙与唐王入冥、三藏西天取经联结成篇——这恰恰也反映着上文提到的故事之原初结构,但演述中心是唐王还阳偿还受生钱)。这无疑为我们探寻这些西游“吊偈画”本来面目掀起了面纱一角。《受生宝卷》由《受生经》发展、衍化而来。《受生经》说的是:人世众生在由冥司转生为人时,都根据自己出生时的属相,在冥司借下了数目不等的注生钱。转世以后,如果能及时偿还,便可福禄寿考;反之则将遭受恶报。所以延请僧道,纳受生钱,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习俗,在民间有广泛影响。至《受生宝卷》则是以《佛说受生经》为蓝本衍生而来的瑜伽道场科仪,为荐亡法会的科仪文本。有趣的是宝卷把西游故事作为框架,把《受生经》嵌入其间,这样一来无疑加大了在民间传播的力度。“西天取经故事”的原初结构是闭合的,又是灵活的、实用的,只要不破坏其闭合性,各种宗教科仪的内容都可以嫁接进来,而“西天取经故事”正是在这种灵活的、实用的宗教实践中,维持其稳定性和传播力的。
如果将目光进一步延展,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仅本文讨论的西游故事“吊偈画”,还有不少学界视野尚未顾及到的西游壁画、石刻,同样具有水陆画的性质,自觉承载宗教科仪超度、教化之功能。如川渝的大足石刻,山西稷县青龙寺腰殿壁画、明代宝宁寺明代壁画等皆有水陆画保存,而这几处水陆画恰恰都包含了西游故事元素,这些水陆画的出现让我们对佛道寺庙(道场)中的西游故事壁画(雕塑)又有了新的认识,与我们既往的惯性认知背道而驰——它们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西游故事传播的反向作用,而是宗教原本功能的自觉辐射。更进一步说,与其它经典故事不同,西游故事的演化传播有一条实用主义路径,那就是民间化、日用化的佛道祭仪借其“背书”,以丰富科仪内容与形式。
以往,我们在讨论西游故事与宗教之关系时,主要聚焦于百回本小说中的角色、名物、事件与佛、道等组织性宗教的关系(更具体地说,是小说内容的宗教来源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是“成书研究”或“原型研究”的衍生物),而大都忽视超文本的故事所承载的宗教功能。其实,西游故事(尤其在早期叙事品位较低的情况下)之所以受到大众欢迎,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故事直接参与民间宗教仪式实践。对于民众而言,“故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无论结构是否完备、情节是否丰满、人物是否立体,“故事”在以亡灵超度为核心的宗教仪式中的实际功能,才是参与仪式的实践者们所关心的,这才是早期西游故事在公共流通领域内始终保持传播活力的根本原因——而非文学批评者一厢情愿地赋予的“审美意义”。这种实用目的,不仅是超文本的,也是跨地域、多民族的。西游故事是吊偈画、石刻雕塑、水陆画等祭祀画的热门题材,南北各地多处出现不是偶然,它们遥相呼应,一方面是西游题材故事影响日益扩大的结果;另一方面西游题材本身和仪文同时成为承载宗教功能的载体,它们和迎神社戏(如莆仙戏《西游记》)、宝卷(如《西游道场》)、江淮神书(《唐僧取经》)、师公经(壮族、瑶族、土家族皆有)等科仪文本一脉相承,而这种内涵的宗教功能却绵延不绝,它们是隐含在西游故事中的内在理路之一,融化在西游故事的血脉中。我们已经习惯于在百回本《西游记》巨大的艺术光晕中讨论故事的审美意义,却忽视了一点:即便百回本小说也生动地保留着宗教仪式实践的痕迹,没有仪式功能这一根本动力,故事就无法在小说、戏曲、说唱、图像等多种媒介系统中自如“转身”,也就不可能成为具有极高艺术品位的案头集大成作品。
具体到图像系统中,这些在艺术上略显稚拙的祭祀画本,与小说插图大异其趣,是“图像叙事”轨道中的另一股力量。
之所以称其为“另一股力量”,首先在于其“文本”属性。以往学界之所以关注小说插图,主要看重其“副文本”属性。尽管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愈来愈多学者指出小说插图具有自己的符号系统和叙述逻辑,不一定与小说“文本”的叙述内容“严丝合缝”,有时甚至大异其趣,但不得不承认:小说插图是“副文本”,它依托“文本”流传,主体内容与文本一致,其目的也在于强化文本的表现力。而如故事画一类“西游图像”却是“文本”。它们不依托小说,甚至根本就不在“集大成作品”的辐射范围内。它们不仅有自己的艺术传统和表现成规,甚至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叙述逻辑和传播渠道:它们以自己的符号系统(即便是高度重合的、刻板化的图像),讲述流传于多地域、多民族中的西游故事,而不是为了“图解”某一部“集大成作品”服务。这就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发现故事演化传播的另外一种可能。上文已列举不少水陆画与百回本小说“同中见异”的内容。这里说“同中见异”只是对现象的客观描述。所谓“同”不代表相似、相近的内容“源出”百回本,更大的可能是它们均指向一个更为古早的故事的“公共形态”,如水陆画与百回本皆有完整连贯的猴王出世故事(包括学艺、闹龙宫、闹地府、闹天宫等核心事件),但整个单元故事不是到了百回本才形成的。而所谓“异”也不能将其理解为对百回本的“改编”,更大的可能是直接继承了当地独立发育的故事系统,如上文提到的“蝴蝶精”“鲤鱼精”等。
而从这类图像生成、传播的实际看,拖曳其前行、推助其转身的也是“另一股力量”,即超度科仪的实际需要,是民众日常宗教实践的需要,而非纯粹审美消费的需要。它们以西游故事为素材,以宣扬宗教思想、强化仪式效果为目的,以更加直观的视觉形象、绘画的表现形式,展现了信徒们所向往的彼岸世界,《西游记》求经佛国,构建极乐世界理想无形中契合了受众信仰,“取经”“游冥”等情节单元也更直接地参与进民间的宗教实践环节。它们和宝卷等案头文本、戏曲等场上排演、民间说唱等口头传播一道构成了立体、多元的西游世界。它们串成了独特的故事链条,挦扯这些百回本小说系统之外的故事链条,也是发掘掩埋在历史尘灰中的原生态遗迹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发现时常带给我们惊喜,而这些令人惊喜的发现,往往能够拉近我们与早期故事演化传播真实生态之间的距离。
可以说,以上两个层面的“另一股力量”,正是这套新见《西游故事画》的独特价值所在:不论这些故事画创作流行时间的早晚,以及与百回本小说的先后,也不论其艺术水准的高低,表现力之高下,其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们揭示了西游画独具的宗教内涵、特质,和百回本系统之外的众多西游故事一道,构建了另一个“西游世界”。这个基于多种可能性而构建起来的“西游世界”,应该更接近故事演化、传播的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