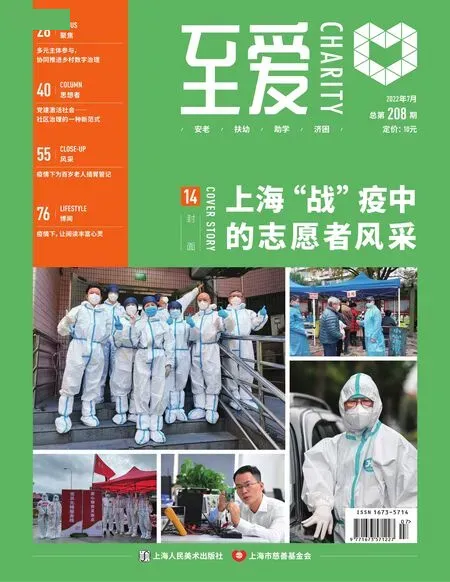“不残缺”的爱
整理|离咲
电影《异类》的主角是一位“星星的孩子”。剧情描述成年的他决定要交女朋友,因而引发一连串的自我改变,连带影响家人与身边的朋友。
或许,有人会认为,《异类》的剧情过于理想化,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要能发展出这样的情感关系非常具有挑战性。在一篇报道里,一位记者曾和一位“星星的孩子”聊天。他告诉记者:“妈妈不反对我交女朋友!但她建议我不要也找“星星的孩子”。主要的原因是,未来如果长期交往,会担心我们两个无法照顾彼此。”
其实爱不只是照顾,因为爱不应该只是交换,爱也可以很纯粹。
有能力才能爱人?被爱一定是被照顾?
其实,每个人都有爱人与被爱的权利!爱人是幸福的,被爱是愉悦的。爱人与被爱不是“普通人”的特权。但为什么对于许多残障人士来说,爱一个人似乎是困难呢?
因为传统的观念教育我们,要有能力才能爱人!这样的观点让“爱”变得过于务实。其实爱是一种感受。爱并不像是我们想得那样简单,爱可以有很多层次,关系也可以有很多形式。你可以爱人,但对方可以不接受!每个人都可能被拒绝,不要因为别人不接受你的爱就全盘否定自己,学习与这样的情绪共处,练习调节与排解这样的状态。
爱,先从每个人的情感教育开始
对于残障人士的情感教育,不同特质的人群有不同需要,举例来说,“星星的孩子”、注意力缺陷过动症,他们会遇到不同的挑战。不论是追求心仪的对象,或是想和他人有进一步的发展,对于“星星的孩子”来说,都需要面对自身社会性互动上的困难。对于绝大多数的中重度残障人士来说,要能建立长期稳定的情感关系,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每个人都需要情感教育,应该教会孩子如何爱人,以及如何回应别人的爱。爱,该从何教起?爱的源头应该是认识自我。当孩子对自我有足够的了解,就有机会知道什么是他渴望的爱,进而有能力分辨、选择以及行动。
很多老师都惯用的方式是让残障孩子从身边取材,让他们练习观察自己的原生家庭,看自己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互动的;或者会鼓励残障孩子吸取他人的经验,让他们反思自己期待建立怎么样的亲密关系。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讨论,让他们能更成熟地思考与面对自己的情感关系。
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教练”
想要锻炼身体,我们会请有经验的专业教练来协助我们,面对情感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懂爱、自爱以及能爱人的“生命教练”教残障孩子学习什么是爱,自己要的爱是什么,该如何付出 爱。
“生命教练”始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富有创意、激发人思考的过程激励客人最大化地展现个人及职业方面的潜能。一位生命经验丰富,平时有意识且有纪律反思与自我整理的“生命教练”,就有机会引领残障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保持稳定地成长,比如教他们写情书给自己喜欢的人,和他们讨论如何邀约比较容易被对方接受,等等。
回归纯粹,不因障碍而去区分爱
爱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就是因为不简单,更要花时间好好学。克莱夫·斯特普尔斯·路易斯在《四种爱》这本书中提到:爱有四种,分别是亲爱、友爱、情爱与大爱。史铁生曾写过这样的文字:“我们有爱情的权利,绝不降低爱情的标准,在爱情上我只接受两个分数,要么100分,要么0分。”事实上,他的爱情确实做到了100分。

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同为残障人士,但与史铁生一样,拥有坚强的意志和对生活的热爱。他们收获了甚至比正常人更甜蜜的爱情。
而在情感关系中本来就混杂着这些不同的爱,每一段关系中不同爱的成分与比例也有所不同。随着时代的改变,网络科技改变人的生活模式,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样的改变是真实的。就像《云端情人》这部电影中让我看见未来的人类或许有可能和计算机谈恋爱,和人工智能发展情感关系,那到底什么是爱呢?我们需要的爱会是什么?对我来说,在“爱”这件事上,残障人士和健全人不应该有所区别,因为那是属于人类最真挚、最宝贵的纯粹。
婚恋之困,亟待解决
不过,婚恋之困是矗立在残障者生活中高高的围墙。据第二次全国残障人士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残障人口中,男性4277万人,占51.55%;女性4019万人,占48.45%。性别比为106.42。残障人口的婚姻状况为,未婚人口982万人,占12.42%;已婚有配偶的人口4811万人,占60.82%;离婚及丧偶人口2116万人,占26.76%。残障人士自身存在身体缺陷和功能障碍以至于在社会和婚姻市场中都处于劣势,部分残障人士贫困与身体残疾相互交织,在婚姻市场中并不占据优势,这样的大环境使得残障人士择偶婚配成为了难题。
要想改变残障人士婚恋的现状,我们还是应从社会、家庭、个人三方面入手,做到三者相互融合、团结协作、互相促进,为实现残障人士婚恋的良性发展,营造残障人士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其中社会的支持是重要基石,家庭的支持是坚强后盾,个人发展是内在动力。外界给予的帮助只能是起助力的作用,追本溯源还是要通过残障人士自身的努力获取资源来解决个人的婚恋问题,才能使整个社会的残障人士婚恋的情况向良性发展。
婚姻是构建家庭的基石,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只有每个家庭幸福和谐,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