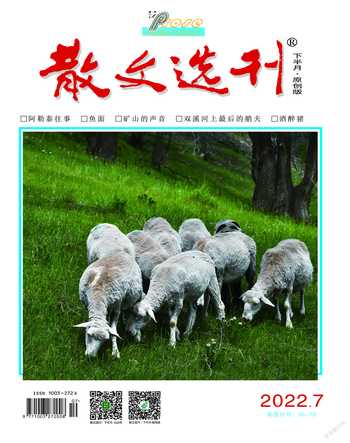明月悄悄拂过山岗
梅苏苏

春天,一个平常的傍晚。夕阳最后的余晖渐渐散去,暮色将至未至。
不远处的田间小路上,走着正欲归栏的牛羊。
少年坐在地上,屁股下垫着草团子。
在他面前堆放着十几根长短不一的竹片,一团麻线和几根铁钉。家中的大黄毛狗懒懒地趴在竹椅边,椅子上斜挂着他的帆布书包。他记得书包最初时是柳条一样鲜嫩的绿色,背了五年,现在却是毫无生气的浅白,背带两侧也起了毛。
少年拿着刀,开始仔细地摆弄竹片,劈、削、剖,动作笨拙而耐心。他要为燕子窝做一个支架。燕子窝在堂屋的房梁那里,正对着大门,海碗大小的模样。燕子窝是今年新建的。不过,他并不清楚燕子妈妈和燕子爸爸到底是从哪天开始建的窝,等到他发现时,不仅燕子窝已经完工,而且还有了小燕子,每天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地叫闹个不停。
“去年,燕子窝掉了下来,两只小燕子摔死了,今年可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想起小燕子软绵绵躺在地上翻着白眼的可怜样子,时隔一年,他心里还是忍不住难受和愧疚。
“可不要太闹,闹腾得厉害,当心这会儿掉下来。”少年默默地祷告着。然后更加仔细地削着竹片,以至于父亲什么时候来到身边也浑然不觉。
父亲腰上拴着柴刀,头发上还沾着灌木的叶子,鲜嫩的,枯黄的,带着山里的气息。
“在做什么?”
“给燕子窝做个支架,免得小燕子又摔下来。”
父亲没说什么,一闪身进了里面的厨房。再回到少年身边时,肩上扛了架长长的竹梯,手上拿着一把小榔头。
“差不多了吗?”
“嗯,好了。”少年举起手中方方正正的支架。父亲用手压了压,随手拿起刀子,在四边又轻轻敲打了几下。
“软了一点。不过,应该能托住燕子窝。”父亲放好梯子,一手托着支架,一手扶着梯子,三下两下爬到了燕子窝前:“里头有四只小燕子!”
“是吗?多大了?”少年抬头问,两手紧紧地扶着梯子底部。
“很小,比刚孵出来的小鸡还小。”
“哦。”少年一边应着,一边在心里极力想象着刚孵化出来的小鸡到底有多大,是什么模样。不过,他实在很难把那些刚孵化出来的黄绒绒、走起路来又摇摇摆摆的小鸡和窝里的小燕子联系起来,一个是天上飞的,一个是地上走的,怎么能拿来比较呢?他想。
但他因此想起了家里的那只大芦花公鸡,每天天蒙蒙亮,就在窝里打鸣。“村子里那么多公鸡,每天都是它第一个打鸣,简直是公鸡中的将军。”想到这里,少年的嘴角情不自禁地扬起一丝得意。
他还想起了挖蚯蚓的情景,就在村溪边的竹林里,风吹竹叶,沙沙作响,泥土松软湿润。他拿着小锄头,在那里找宝似的翻掘,一大群出生不久的小鸭子,一身黄色,或黄黑间杂,或者一身褐色的,毛茸茸,肉嘟嘟,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就围在他锄头边到处乱转,好几次,锄头都差点儿伤到它们。每看到他挖出一条蚯蚓,小鸭子们便哼哼唧唧乱叫着一哄而上。
“妈妈今年还会不会买一些小鸭子回来?如果再买来,我可不会带着它们去挖蚯蚓,那么贪吃,那么强横的小家伙,太难伺候了。”
“也不一定非得挖蚯蚓给它们吃啊,去溪滩里抓一些小鱼小虾不也很好?”
“但春天的溪水还很冷,妈妈一定不会同意的。”
“可以偷偷去啊,就像夏天偷偷去水库里游泳,喊上隔壁的三儿,再带上大黄狗。”
“那,春天的河里有小鱼小虾吗?”
……少年的想象一點点展开,各种可能来到的场景在他脑海里纷至沓来。于是,他的内心也越来越被一种期待和喜悦填满了。
“好了,完工。”竹梯上方突然传来父亲的话。芦花鸡、小鸭子、竹林、春天的溪水……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支架已端端正正地钉在燕子窝下方,大小刚好托住整个燕子窝。
“第一次做,手艺不赖吧?”少年扬着脸问。
“还凑合,但肯定没我小时候做得好。”
“又吹牛,谁知道你那会儿有没有做过这玩意儿呢!”少年在心里嘀咕,不过,他没说什么。他是个讷言安静的孩子。
“记得把地上的东西收拾干净,马上吃饭了。”父亲拍拍手上的灰尘,扛起梯子进了厨房。
少年从门背后拿出扫把,开始默默清理剩下的竹片、麻线、钉子。天色已经暗淡下来,通过眼睛的余光,他瞥见对面的群山,苍茫耸立,迤逦起伏,而村里唯一的那班公交汽车,正缓缓驶过家门口。
除了司机,车上坐着几个七八岁大的孩子——不用说,好心的司机又在村头打开车门,放进了这些蹭车的孩子。
车子将在五六百米外的村尾处停靠过夜,而司机也将被其中的某个孩子带到家里。接下来,憨厚的山里人会像对待远道而来的亲戚,为他奉上一顿笋香满溢的晚餐,还有自酿的米酒,以及天南海北的闲聊。
燕子妈妈回来了。叽叽喳喳,叽叽喳喳,乳燕们鸣叫得更欢了。热烈的啼鸣声里,少年将最后一块竹片,连同它周围的尘土,细细地扫进竹编的畚箕。
厨房里传来腌菜烧毛笋的香味、米饭的香味,一阵一阵,沁人心脾。少年轻轻掩上大门,然后抓起书包,连奔带跳地奔向厨房。这是一天中最芳香温馨的时光。很多年后,当少年已经长大,走出山村,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他会想起妈妈的笑脸,以及爸爸对庄稼、柴火和山村往事的微醺叙述,就像堂屋里的小燕子们互相依偎着,听燕子妈妈絮叨着南方的故事。
明月悄悄拂过山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