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影像化背景下的音乐剧创作
□张诗娴/文
本文以音乐剧影像化创作为研究对象,以理论综合和案例分析为方法,具体探究了音乐剧影像化过程中两个关键戏剧要素的影像化再创作:时空的重构和观演关系的延伸。通过具体实例,阐述了时空重构上幻觉性时空处理和非幻觉性时空处理在影像化创作中所运用的不同观念和技法;以及观演关系中根据音乐剧导演对演员与观众关系的把握,用不同的镜头语言重现这一关系;舞台与观众席的关系延伸到银幕与观众的关系后,加入纪录的元素可以使得音乐剧影像具有审视性。所有这些观念与技法的使用,都是为了一方面“翻译”音乐剧现场演出,另一方面提供给观众不同于戏剧现场的独特审美体验,最终促进音乐剧产业的发展。
1 前言
1.1 戏剧影像化
在现在的多媒体和融媒体时代,“戏剧影像”这一概念早已不是标新立异的说辞,而戏剧和电影这两类艺术的结合也成为了不可回避的趋势。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却依旧有待厘清。笔者纵观前人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戏剧影像”主要有两类所指对象:(1)戏剧中的影像;(2)戏剧的影像化。前者指在现场性的舞台戏剧表演中通过屏幕的运用融入影像的元素,以通过戏剧进行中的影像运用实现多角度叙事和戏剧空间的扩展,如克里斯蒂安·陆帕(Krystian Lupa)导演的《酗酒者莫非》,舞台后方巨大的荧幕放映“电影”,银幕前的舞台上演出戏剧。舞台上的演员在恰当的时机通过幕布上提前开好的小门“走入银幕”,银幕则上放映这一角色后续的行动画面,以此达到一种银幕与舞台互动的效果,最终完成了戏剧空间的扩展。在多角度叙事上,图1莫非与妻子杨花躺在床上,在传统戏剧的舞台调度中,观众只能从一个平视的视角看到舞台上发生的事,而此时后面的银幕以90度的垂直俯拍“窥视”二人的动作,由此实现了叙事角度的多样化,也给观众带去了一种与传统戏剧不同的审美体验。

图1 《酗酒者莫非》剧照
后者“戏剧的影像化”是指通过摄影师、影像导演参与排练,在舞台上及舞台周围提前埋好机位,于戏剧进行的过程中进行多维拍摄,通过影像视听语言的运用完成直播或录播的艺术形式。其本质是以戏剧作为拍摄对象,以影像作为手段和最终呈现方式所进行的“戏剧三度创作”。成为了继传统戏剧由剧作家进行的“一度创作”,演员、舞台美术家、戏剧导演等进行的“二度创作”后一种新兴的戏剧创作方式。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戏剧的影像化”依旧是一种戏剧创作方式而非电影创作方式,是因为从艺术接受层面来说,观众依旧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在“看戏”而非“看电影”。电影的视听语言只是对舞台戏剧内容的承载和再创作。
厘清了“戏剧影像”的两类所指后,本文所论述的“戏剧影像化”的范畴也就清晰起来。
1.2 音乐剧影像化
音乐剧作为兼具艺术性、娱乐性和商业性的戏剧形式,有着比话剧更强烈的传播诉求。相比于话剧艺术面对影像化潮流时展现出的本体地位危机意识,音乐剧则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影像化传播。主要有两类形式:(1)观众在演出过程中拍摄“枪版”(“盗录电影”的借用词)录像,以便自己反复观看或与朋友分享,这样的视频往往机位固定、画质模糊、收声嘈杂。(2)一些音乐剧制作人凭借对市场的敏锐洞察,推出了众多音乐剧“官摄”(“官方拍摄”的简称)。这些“官摄”画面精美,声音质量高,辅以海报等推广形式(如图2、3所示),俨然成为了音乐剧传播的主要途径。

图2 音乐剧影像《真假公主》
音乐剧的影像化既势不可挡又势在必行的。就艺术特性而言,首先,相比于话剧、电影对于情节的依赖性,音乐剧更多的是在故事的基础上完成极致的情感表达。观众在欣赏音乐剧的过程中,对情节的欣赏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整体作品的气氛的感受、对演员表演的感受、对音乐舞蹈等元素的感受等。所以,音乐剧并不担心“剧透”(“透露剧情”的简称),恰恰相反,提前了解大致的情节,对音乐剧的欣赏是大有裨益的。其次,音乐这一艺术形式本身就更能激起观众反复欣赏的欲望,影像化则很好地满足了观众的这一需求。相比于去剧院现场反复观看的高昂成本,对音乐剧影像的反复观看廉价也方便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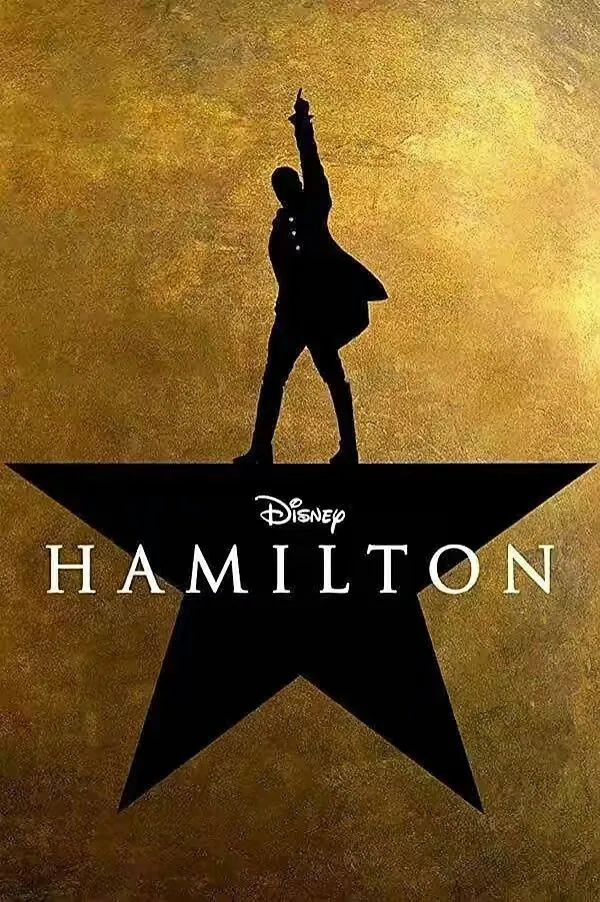
图3 音乐剧影像《汉密尔顿》
就音乐剧的传播需求而言,第一,影像作为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是戏剧作为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戏剧的影响力往往由于语言、剧场实体的限制而局限在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个语言文化圈。而影像传播的便捷性和影视翻译的出现使得戏剧能够打破这诸多限制走得更远,以戏剧影像的形式突破国别、语言、文化的障碍,为世界各地的观众和戏剧研究者带去精美的作品。第二,音乐剧的影像化传播反过来又能进一步拉动线下演出的发展。很多观众会在线上看过“官摄”后成为某一部剧、某一位演员的“粉丝”,在新一轮的演出季购买现场演出的门票,甚至不远万里奔赴上演的城市。第三,音乐剧的影像化能够培养一批音乐剧观众。虽然现场的魅力无法取代,但是吸引观众走入剧场观看第一部音乐剧却不容易,而点开网页宣传进行音乐剧影像的观看就容易很多,由此大大降低了音乐剧的欣赏门槛,最终能够促进音乐剧产业的健康发展。
1.3 音乐剧导演的可为性
虽然有部分外国音乐剧的“官摄”已经具备了较高的艺术水平,但是仍缺乏体系化的理论为音乐剧的影像化创作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就音乐剧影像的创作过程而言,戏剧的主体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影像化需要做的就是以音乐剧演出作为拍摄对象,发挥影像“纪录和再现”的功能,在尊重戏剧导演二度创作的基础上完成“三度创作”。所以,这一“三度创作”是深切地受到二度创作的制约的,故而存在很多不受影像化影响的因素,或者说这些因素是戏剧导演二度创作时就必须考虑的内容,诸如舞台事件、舞台行动、舞台调度等。所以,当谈到音乐剧的影像化创作时,实际是在谈论影像化改变了哪些舞台创作因素。从戏剧属性和影像本质综合来看主要有两点:时空的重构和观演关系的延伸。音乐剧创作者只有深刻体察戏剧与影像在上述两方面的根本区别, 进一步完成时空和观演关系的再创作,才能真正完成音乐剧影像化。
2 时空的重构:从舞台时空到银幕时空
时间与空间是戏剧的载体,一切故事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的,但舞台与银幕的时空构成却迥然不同。舞台时空包括剧场和演出的现实性时空、为戏剧展开而规定的假定性时空和由观众的感觉和印象而产生的感受性时空。其中,假定性时空是戏剧艺术家创作的产物。戏剧的根本属性就是假定性。银幕时空则不同,电影的放映是在平面的幕布上进行的,故而不存在具体的现实性时空,而故事情节展开的时空则是由视听语言、蒙太奇、音乐音响的呈现而形成的。张仲年在其著作《戏剧导演》中就谈到了两者的区别:他认为戏剧的时空特性是“占据”与“显现”,而电影的时空特性是“构成”与“再现”。前者指戏剧通过对具体剧场空间和演出时间的“占据”完成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演员通过表演“显现”出高超的技巧与艺术水平,进而反映出其他舞台艺术创作者的艺术创造。后者指电影通过导演对演员和摄影机的调度,收集创作材料,最终通过蒙太奇的运用“构成”情节开展的时空(这个时空与拍摄时空存在很大差异),“再现”出拍摄过程中的部分真实,进一步反映出其他电影艺术创作者的艺术创造。舞台时空与银幕时空的这一根本区别,使得对音乐剧进行影像化创作时必须慎重处理舞台时空的影像化。
从戏剧的主体地位出发,舞台时空的处理主要有两类:幻觉性时空处理和非幻觉性时空处理。幻觉性时空处理通过为戏剧情节的展开设置具体的地点、场景;为戏剧事件及其发展创造具体环境和细节;设置合理、稳定的空间结构等方法在舞台上创造出“生活的幻觉”,意图使观众在观剧过程中获得对戏剧情节的沉浸感,想人物之所想,感人物之所感,仿佛忘记了自己在看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沉浸在戏剧导演为他们创造的“幻觉”中,故而称为“幻觉性时空处理”。非幻觉时空处理则通过为戏剧情节的展开设置可供演员在表演时随意处理时空转换的空间条件;为舞台调度和舞台节奏创造灵活多变的空间结构;使用抽象的、具有造型美的空间演出形象等方法在舞台上创造出形式精美的戏剧作品,意图使观众在了解戏剧情节的同时,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舞台上的一切,引发观众即时的评价和思考。这类戏剧着重于“打破幻觉”,时时把观众“拉回现实”,故而称为“非幻觉性的时空处理”。由于影像空间“再现”和“构成”的属性的影响,在对戏剧导演的舞台时空处理进行影像化创作时会使用不同的观念和技法。
2.1 幻觉性舞台时空处理的影像化
如前所述,幻觉性的舞台时空处理是为了给观众带去“生活的幻觉”,而这正是叙事类影像所依赖并擅长的工作。银幕是平面的、二维的,却要以此来表现立体的、三维的空间。这样的属性使得影像叙事必须遵守视听语言的“语法”,如此才能交代故事发生的时空、人物关系等重要信息而不至于使观众产生混乱感,在达成这一目标的基础上,才得以承载影像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和评价。所以,当对幻觉性舞台时空处理进行影像化时,创作者也要遵循影像叙事的“语法”,通过视听语言的运用,准确、完整地交代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行动的展开。
音乐剧是以故事情节为基础的戏剧艺术,也需要营造出观众对于舞台上发生情节的幻觉。音乐剧中的幻觉性场面主要有:对白场面、宣叙调场面、和生活化舞蹈场面这三类。对白场面指音乐剧中两个及以上人物通过对白执行舞台行动,推进情节发展,展现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戏剧场面。宣叙调场面指音乐剧中以歌调展开“对话”或推进情节的场面。生活化舞蹈场面指以日常生活动作的夸张化肢体来推进情节、表现人物的场面。这三类场面往往有明确的人物关系和目的清晰的舞台行动,故而在进行音乐剧的影像化创作时,创作者需要通过各种视听语言的运用,将舞台上“全景式”的戏剧场面再创作为符合影像表达要求的蒙太奇画面。具体技法上来说,可以使用诸如平缓的景别组接和镜头运动、非越轴的拍摄机位,符合影像叙事逻辑的视点选择等。音乐剧《一个美国人在巴黎》(An American in Paris)2017年官方影像中,52分16秒开始的对话片段(如图4所示),先通过全景镜头交代人物关系和相对位置,再通过近景正反打镜头展现具体的对白内容和人物反应。

图4 音乐剧影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对白片段
这一场面视听语言的运用就契合了影像叙事的要求。虽然对舞台中后方的舞蹈演员进行了选择性的简略描绘甚至忽略,但对作为舞台焦点的三位人物和他们所依赖的幻觉性时空环境进行了很好地影像化再创作。
2.2 非幻觉性舞台时空处理的影像化
非幻觉性的舞台时空致力于通过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非形象化的概念,诸如情绪情感的外显,剧作者、导演思想的外显等。这类舞台时空呈现出强烈的表现性,强调表现情感、心理和思想。音乐剧音乐和音乐剧舞蹈的表现性,天然就带有这种“非幻觉性”的特征,观众明确地知道在生活中人们并不会在对话时唱起歌来。在这样的场面中,观众并不是为了获得一种“生活的幻觉”而看戏,而是为了欣赏表演艺术的魅力。
音乐剧中的非幻觉性场面主要有:独白场面、咏叹调场面、艺术化舞蹈场面。独白场面指由单一角色通过台词叙述自己的情感、经历等内容的场面;咏叹调场面指以歌调抒发人物情感、表达人物感受的场面;艺术化舞蹈场面指以艺术化的舞蹈动作表达人物情感,阐释思想哲理的场面。这三类场面着重情感和思想的表达而淡化人物行动和人物关系。
所以,对非幻觉性舞台时空处理进行影像化时,创作者需要采用极具表现性的视听语言,最大程度地呈现表演艺术的魅力和创作者的思想情感,如通过越轴的使用,特殊视点、大景别跳切,大幅度的镜头运动等技法再创作非幻觉性场面。音乐剧《来自远方》(Come from Away)2021年官方影像中,女机长贝弗利·巴斯(Beverley Bass)在叙述自己人生历程时唱起《我和天空》(Me and the Sky)。当演员唱到“1986年,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机长”,摄影采用了速度较快的拉镜头(如图5所示),从全景拉到大全景,既是为了配合舞台中后方其他女演员的起立动作,也是人物激动、自豪的心情的外化。

图5 音乐剧影像《来自远方》中咏叹调片段的拉镜头
后半曲唱到“突然,我有了全女性机组人员”,扮演巴斯的演员转身与其他女演员进行肢体交流(如图6所示)。此时镜头从舞台后方的视点向舞台前方拍摄,巴斯成为了站在聚光灯下的英雄,而所有台下的观众仿佛在为巴斯的成就喝彩。这样的镜头调度也形成了一个景深镜头,展现了巴斯与“机组人员”之间强烈的人物关系。

图6 音乐剧影像《来自远方》咏叹调片段的特殊视点镜头
这一曲目中,通过恰当的特殊视点镜头、景深镜头和无契机摄影机运动的运用,人物内心情感和舞台节奏气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还原与再创作。在非幻觉的时空场景中,表演艺术的魅力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3 观演关系的延伸
戏剧观演关系是戏剧中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观演关系的处理是戏剧导演工作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三类关系的处理:演员与角色,演员与观众,舞台与观众席。
在戏剧中,演员承担着“三位一体”的创作使命,即创作材料、创作者、创作作品同时存在于演员一身。演员自己作为戏剧艺术的创作者,运用自己的声音、肢体和表情等作为创作材料,在舞台上成为完整戏剧作品的一部分。戏剧演员的工作体现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接受的统一性,如果艺术家下场,创作随即中止,完整戏剧作品的一部分消失。同时,戏剧表演的这一特点,要求戏剧艺术的接受者必须在“演员的创作现场”才能欣赏戏剧艺术。这就使得观众也成为了完整戏剧艺术的一部分,没有观众的戏剧演出只能是排练。一旦承认了观众是戏剧创作中必须在场的一部分,那观众与演员的互动、产生的相互影响等也就成为了戏剧导演创作的一部分,这就是处理观演关系的重要性和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戏剧观众的戏剧欣赏与戏剧演员的戏剧创作具有同时性、同地性的特点,戏剧观演关系可以概括为“参与”。此处的“参与”是广义上的,尽管有些演出中,演员并不直接用语言、眼神或肢体动作与观众交流,但是观众的“在场”本身就具有交流的属性:观众的凝视、动作、态度,甚至咳嗽、叹气都会影响演员的表演状态和自我评价。
音乐剧的娱乐性和商业性决定了其现场参与感、高昂的“情绪场”的体验对观众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同时又是影像无法代劳的。所以,音乐剧的影像化不能只是简单的纪录,而应一方面尽力还原、“翻译”现场性的戏剧艺术(这主要依赖于从舞台空间到银幕空间的三度创作),另一方面又要给予观众与现场观剧不同的审美体验。
3.1 演员与角色:由二度创作决定
演员与角色的关系指演员在表演中如何处理与所扮演角色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演员运用假使、情绪记忆、内心独白等内部技巧,和台词、形体等外部技巧体验角色进一步“成为”角色的体验派表演;演员通过对生活的观察确定准确的人物动作,在表演时表现动作并保持对角色的评价意识的表现派表演;体验派与表现派交替融合运用的表演。
但这一部分正是前文所提到的,不受影像化影响的部分。由于戏剧在戏剧影像化中的主体地位,故不应出于影像化的需要而干预二度创作,否则戏剧影像化就会失掉戏剧的主体性。演员与角色关系的确定,是由演员与戏剧导演在二度创作中共同确定并加以执行的。
3.2 演员与观众:参与方式从“在场”到“投射”
演员与观众的关系指演员在表演中如何处理与观看自己表演的观众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演员与观众隔绝,不直接与观众进行语言、表情等交流,建立起“第四堵墙”;演员与观众积极融合,各类交流频繁,打破“第四堵墙”;演员与观众时而隔绝、时而交流,如戏曲中的“打背供”。
陈恬教授在《英国国家剧院现场与戏剧剧场的危机》一文中提出“在一个媒介化的时代,观众对‘现场性’的感受从‘身体的现场性’转向‘媒介的现场性’。”这正是参与方式转变的体现。戏剧的参与在于观众的“在场”。正是因为“在场”所以会受演出中情绪和情感“场”的影响。而观看戏剧影像则没有了物理意义上的“在场”,更多是心理层面的是“投射”,也即观众通过获知的声画信息在脑海中还原出戏剧演出,沉浸于幻觉的“现场性”并将自身投射其中。
基于此,戏剧影像化创作要求在处理演员与观众的关系时,要基于戏剧导演二度创作的处理,通过镜头语言的运用模拟出这种关系。若戏剧导演在二度创作中建立起第四堵墙,影像化时则可以运用小景别拍摄细节镜头,客观地表现被摄对象等方法,让银幕前的观众更加生动完整地在心中还原出演出内容。同时,将摄影机的视角隐去,让观众感受不到拍摄者的存在,也是模拟这类关系的方式。音乐剧《唐璜》(Don Juan)2005年的官方影像中《再作停留》(Reste encore)一曲,就通过低角度仰拍大全景表现了人物隔空对话的场景;通过大量近景镜头表现人物情绪;通过特写镜头拍摄水晶球具体展现人物动作(如图7所示)。

图7 音乐剧影像《唐璜》中使用小景别、客观视点的片段
若在戏剧二度创作中打破了第四堵墙,演员直接与台下观众互动,最理想的情况下,应尽力使摄影机位于参与互动的观众旁,以现场观众的视点拍摄演员,或全程或与客观纪录镜头穿插剪辑,最大程度还原这种“交流感”。小剧场音乐剧《不喜欢音乐剧的人》(The Guy Who Didn't Like Muscials)2018年官方影像中,神经质的贺金斯教授(Prof. Hidgens)唱起自己写的音乐剧《走向职场的兄弟们》(Working Boys)有好几处与观众的眼神交流,均由于位置无法从正面拍到,但在全曲戛然而止的时候,扮演贺金斯的演员突然转身,他的眼睛直接看向镜头(如图8所示),这从另一个层面再现了音乐剧导演打破第四堵墙的构思。

图8 音乐剧影像《不喜欢音乐剧的人》贺金斯教授“看向现场观众”与“看向银幕观众”
3.3 从舞台与观众席到银幕与观众:审视的产生
舞台与观众席的关系指在演出中演员表演场地与观众观看场地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舞台与观众席分隔,如镜框式舞台;舞台与观众席融合,如环境戏剧、沉浸式戏剧所用的车库、公园;舞台与观众席既不完全分隔,也不完全融合,如伸出式舞台,日本歌舞伎中花道的使用就是此例。
银幕与观众则不同,既可以认为这二者是“分隔”的,也可以认为这二者是“融合”的。说“分隔”是因为银幕本身与银幕中展示的世界永远无法真正在物理意义上与观众“融合”(当然虚拟现实的发展可能会在感受层面打破这一论断)。说“融合”是因为从艺术接受来看,观众在心理意义上认为银幕中的一切是可听可看甚至可触可感的。正是由于银幕与观众的关系存在这两种特性,使得影像作为一种表达手段和传播媒介天然具有审视性与幻觉的现场性。纪录片正是影像审视性的集中表现,叙事类电影则是幻觉的现场性的集中表现。
戏剧本身的叙事性决定了幻觉的现场性是戏剧影像化必须要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时空的重构,通过准确合理的视听语言的运用,让放映中“所有的位置都是最好的位置”。同时,戏剧影像化创作者对于影像审视性的把握和运用,可以从另一个层面丰富观众观看戏剧影像的审美体验。比如英国国家剧院现场(National Theatre Live,简称NT live)在每部戏开头、中场和结尾处加入了戏剧创作过程的记录,有演员和导演的访谈,也有主持人所做的背景介绍,甚至还有中场时现场观众离场进场的情况。戏剧影像的观众接受了这些内容后再进行戏剧主体的欣赏,会带有一种别样的理解和不同的视角,这也是戏剧影像独特于戏剧现场的审美体验。音乐剧《伊丽莎白》(Elisabeth)2005年的官方影像,在戏剧正片之外,还有一个长达22分43秒的纪录片,讲述了全剧的制作,采访了相关演员(如图9所示)。不过与NT live不同的是,这一纪录片并未与戏剧影像本身嵌入,而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纪录片附在正片之后。

图9 音乐剧影像《伊丽莎白》附带纪录片中画面
4 结语
音乐剧作为集商业性与艺术性于一身的戏剧形式,应积极拥抱戏剧影像化创作。通过创作者对时空的重构和对观演关系的延伸,创作出有吸引力的、有鲜明音乐剧特色的音乐剧影像。
在时空层面,对音乐剧导演二度创作的幻觉性时空处理和非幻觉性时空处理进行区别化再创作。在观演关系层面,通过细节性的、隐藏拍摄者的方式模拟第四堵墙;通过观众的视点镜头模拟第四堵墙的打破;加入纪录性影像以提供审视性等方式,给音乐剧影像的观众带来既有鲜明戏剧特点,又有独特审美体验的音乐剧影像作品。最终,辅以各类宣传方式,拓宽音乐剧的创作手段和传播途径,吸引和培养音乐剧观众。■
引用
[1] 鲍黔明,廖向红,丁如如等.导演学基础教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2] 张仲年.戏剧导演[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3] 费春放.“剧本戏剧”的盛衰与英国“国家剧院现场”[J].戏剧艺术,2017(5):22-29.
[4] 张阳.“拾起电影的拐杖”——NTlive戏剧影像跨媒介生产传播的三个思考纬度[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8(3):117-129.
[5] 陈恬.英国国家剧院现场与戏剧剧场的危机——兼与费春放教授商榷[J].戏剧与影视评论,2018(2):6-18.
[6] 陈晨.延伸的电影:戏剧影像的跨媒介叙事研究[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11):48-57.
[7] 田甜.探索后疫情时代国内数字化演出新业态——以高清戏剧影像为例[J].当代戏剧,2021(5):17-20.
[8] 廖琳达.高清戏剧影像NT Live观察[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20(1):153-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