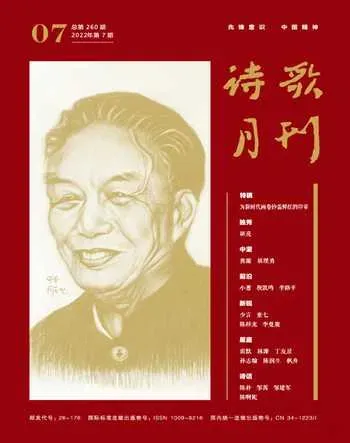笔墨当随时代 歌吟且从内心
——简评“为新时代画卷钤盖鲜红的印章”系列诗歌
陈振华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既是古训,也是当代诗人不可或缺的写作伦理。“为时而著”,亦即笔墨当随时代,歌吟且从内心,从内心的真实感受出发关注当下行进的现实。这既是现实主义诗歌的内在审美要求,也是时代内涵在时间矢量上的审美呈现。特稿“为新时代画卷钤盖鲜红的印章”系列诗歌,铭写新时代气势恢弘的篇章,描摹新时代气象万千的画卷,彰显新时代披荆斩棘的勇气,以富于感性气息的经验、物象、场景、世相、人物、风情,多维度绘制了新时代的“清明上河图”,充分展示了新时代的精神风貌。概而言之,其艺术质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纵笔泼墨绘就色彩斑斓的新时代画卷。这些诗篇既有“新宏大叙事”,也有当下“日常生活”蝶变的原浆书写,以思想的深邃、情感的饱满、视野的开阔、境界的高远以及多样的艺术形式,标识出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现实主义诗歌精神。一些标志性的事物化作诗人笔下跳动的精灵:复兴号、和谐号、宇宙飞船、北斗导航卫星、“.chn”域名、高铁、海底隧道,它们以独特的意象凝定为时代的象征符码。一些地理性坐标,标示出祖国的山南水北。新安江、胶州湾、永兴岛、天井湖、淮河、徽州、石油城,它们各自在诉说成长蜕变的故事。徽墨、宣纸、歙砚、牌坊,它们从历史走向了当下,见证了追梦的新时代……这些诗篇都是新时代的抒情诗,题材广泛,涉及民族复兴、科技创新、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文化自信、中国速度、社稷民生、日常生活、山川风物等诸多方面,诗人满怀豪情纵笔泼墨描绘了气象万千的新时代画卷。
其二,“历史地”而非“历史的”主体性构建。“诗人——同时代人——必须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在此,我并非指罗兰·巴特意义上的诗人与时代的不合适宜,也并非阿甘本意义上的凝视世界的暗淡,而是指诗人,作为“同时代的人”,“准确地感知、捕捉并理解时代之光,从芜杂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这种光芒的特殊价值”。在此基础上,这些诗人们的系列诗篇不是静止地绘制新时代的画卷,展示新时代“历史的”客观进程,而是充分在诗篇中凸显诗人的主体意识,新时代人民的主体意识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激情,他们(诗人和人民)以时代主人翁的姿态“历史地”参与新时代的生成与构形,这种参与、践行是他们自主自觉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动地成为时代/历史的客体,承受被时代/历史裹挟的命运。《皖江赋》描绘八百里皖江奔涌不息的精气神,“每一滴水/都挟带史诗的重量”;《庐州,大科技之城》聚焦科技创新的城与人,这里“有拓荒者滚烫的气血,有大禹的鬼斧神工”。《紫蓬或日出之诗》状写紫气东来的新时代气象“独自御风,紫蓬盛开在春风里/事事新,日日新,气息浩荡”。诗人和人民在“历史地”参与过程中,完成了自身主体性的构建。
其三,个人化的书写和“非个人化”的主题。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多数是“无我”的书写,或者说将“自我”完全融入到时代的“大我”之中,“去我化”的非人格化书写是其基本表征。与那个年代的抒情诗相较,“为新时代画卷钤盖鲜红的印章”系列诗歌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采。它们是“有我的”,诗人将个人对新时代的鲜活感受诉诸个人化的书写、抒情与想象。“我曾坐过开往徽州的列车/车里铺满了鲜花和思念/一直铺到了我的心里/此生不忘”(《开往徽州的列车》),再如“一滴热泪,逼退角落里的寒凉/涌到笔底起波澜的,是一条大江”(《徽墨,在座右铭里散出芬芳》)。系列诗篇以个人的感受性为审美根基,抵达新时代的精神高地,纵情放歌新时代的新气象新创造新使命。尽管这些诗篇的审美书写是基于个人的感受,但诗篇的主题并非是个人性生活的吟咏,更非小资或中产阶级的自恋,而是传达出一种“非个人化”的普遍性主题。当然,这里的“非个人化”主题并不是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歌理论,以放弃诗人的艺术个性,摆脱诗人的个人情感为鹄的,而是将个人的感受、情感融入到新时代的主旋律或标志性的物象、事件、创造中去,做到艺术的辩证统一。
这里所言的笔墨当随时代,歌吟且从内心,主要是指这些抒情诗歌秉持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当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世象中,把握时代的思想脉搏,不做现实亦步亦趋的影子,而是听从内心的询唤。罗杰·加洛蒂有言:“作为现实主义者,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事件、人物的仿制品或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的内在节奏。”在我看来,这些诗篇找准了新时代的节奏,参与了新时代的行动,“模仿”出了新时代的现实能动性,张扬了创造者的主体性,为新时代的斑斓画卷钤盖了鲜红的印章,诗人们则成为时代的优秀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