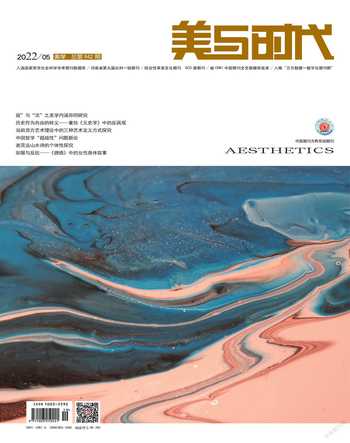论《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沧桑美
摘 要:《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在歌词层面通过“横跳”的时间叙事、遥远的空间叙事,将“沧桑美”构建于叙事时空之中。落实到具体事件时,叙事主体由常见的“牧羊女”变为善良而深情的“牧羊男”;作为另一事件主体的“养蜂女”的隐退,在构造单向叙事的同时,更潜藏着两个事件主体间的“沧桑”张力;作为“沧桑”常见表达方式的颓废肉体的缺席,制造了留白的结局。尽管“沧桑”大多源自消极变化,但其并不指向消极,反而为沧桑者带来不惊与明悟。
关键词: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沧桑美;时空叙事;审美张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极词的空间映射研究”(12BYY120)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1年,为人民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中,《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占据一席。这首歌曲由曾在新疆停留数年的歌手王琪作词、作曲和原唱,发布于2020年5月,经他人翻唱后逐渐流行。在登上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后,该曲再次走红,甚至已有同名电影申请备案[1]。
尽管该曲曾在网络上引发相关讨论,但目前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性成果并不多见。就笔者所见,仅有宏观性文艺评论1篇[2],基于曲艺演唱方式的小品文1篇[3]。本文主要从歌词层面讨论其美学特征及构建机制,试图解释其产生良好审美效果的原因。
一、时空叙事中的“沧桑美”
正如肖炜所言:“迄今为止,以沧桑作为关键词和具体对象进行研究的文章寥寥无几。”[4]11其以宋炜、杨政等人的现代诗歌为例,讨论了关于“沧桑”的诗学问题,认为“沧桑”表现出的状态近乎“心境上的衰老”,带着“对世事的明悟以及明悟后波澜不惊的心态”[4]34。
“心境上”的修饰与限制,提示“沧桑”与较大的年纪并无必然联系。“沧桑”是“沧海桑田的略语”,本义为“大海变成农田,农田变成大海,形容世事变化”,又可形容有生命的个体“饱经沧桑”[5]127。无论是由内而外还是自外向里的“衰老”,线性时间的累积只是一个条件,时间中的空间落实与事件经历,才是其本质原因。虽然这是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从出生到死亡都在经历的,但我们并不认为其中所有的个体都具有“沧桑”的特征。
可见,“沧桑”产生的时空条件及经历的事件、发生的变化具有限定性。时间上的漫长或反复、数量上的繁多、事件的过程与消极结果、变化程度的巨大是几项重要参数。“较大的年纪”作为时间积累的附属,“明悟与波澜不惊”的心态作为事件消极结果的可能的(甚至是少数的)派生结果,或许并非“沧桑”的必需内涵。
因此,审美意义上的“沧桑美”,是指审美主体从审美客体那里感受到的,其经历时间后在具体空间发生的前后变化(往往是巨大的、非积极的)的主观印象。它是一种区别于“壮美”“优美”的美,且不直接属于所谓的“审丑对象”。这一过程自然涉及审美主客体的关系,此处不赘。以下围绕歌词叙事,从时间、空间、事件的角度,分析《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沧桑美”。
二、“横跳”的叙事时间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A-B-B-b式的歌詞结构并不复杂。开头A段4句“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以回忆过往为主;B段13句回到当下,以叙述现状及心理活动为主,复沓1次后,选择性重复B段的后9句。但是,这只是宏观地、粗糙地分析歌曲的时间叙事结构。落实到词汇层面,同一小段内部的时间特征并不相同,“沧桑”则蕴含在“横跳”的叙事时间中。
如果以叙述者的叙事时间作为当下的原点坐标,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时间则为过去,叙述时还未发生或完成的事件的时间则为将来。歌词中显著地表示或标记时间的词汇依次是“那夜”“(陪)着”“仿佛还在”“曾来过”“愿意”“(不辞而别还断绝)了”“(嫁到)了”“又有”“再没人能”“再没有”等。如果再算上少数几个需要语境推导出的具有时间语义的词汇,那么该曲几乎句句都有点明或暗示时间的词汇,句与句之间叙事的时间不同且来回切换,构成“横跳”的叙事时间。
首句中“那夜”必然是过去,远指示代词“那”在首句出现具有较强的“混沌”语义特征,因为被指示的日子并未明确。即是说,“那夜”可能是多年之前的一个夜晚,也可能是半个月前的某个夜晚。第2句“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着”是持续体、进行体的标记,整个小句的时间同样是“混沌”的,既可能是“那夜”,也可能是“那夜”之后的某个甚至是某段时间。第3、4句中“驼铃声仿佛还在”“曾来过这里”表明“驼铃声已经不在”“现在不在”,那么“驼铃声在”“来过”则是过去,“不在”“走了”则是当下的事实。第7句“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的意愿是未实行的计划,它可能是在过去萌生的,也可能是在当下萌生的。第8句中“不辞而别”是既定事实,“断绝了所有消息”发生在其后,同属过去。第10句中“他们说”表明叙述者“我”已经从他者口中获取了“你嫁到了伊犁”的信息,两个事件的时间显然是后者先于前者。在B段将要收尾时,第14句中“又有”驼铃声必定在“你”离开后,可能是过去,可能是当下;第15、16句中“再没人”“再没有”暗示过去曾有,表明现在没有,估计将来也不会有。
因此,对于不同的受众与审美主体,以自身直接或间接经验为基础,构建出不同长度的总体叙事时间——这首以牧羊男子为叙述主体,讲述其与一个美丽姑娘的感情故事(具体故事在文本层面并不明晰)的时间跨度可长可短,这种跨度并不影响“沧桑美”的构建。如前所述,“沧桑”凸出的是前后时间差异在具体空间中的消极性变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中,对坠入爱河的牧羊男而言,从认识女子到爱上女子、再到爱人的离去,这种经历具有巨大的消极结果,对男子的生命境遇和生活状况构成了巨大的变化——体现为撕裂线性时间后的“横跳”叙事。这种叙事同时隐喻叙述者思维的起伏波动,甚至是颠倒颓丧,与“言为心生”的道理具有一致性。
三、遥远的叙事空间
抽象的时间需要依托于具体的空间,这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叙事学上都是成立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中,“横跳”的时间叙事在空间上体现为“遥远”的空间距离,“沧桑”变化包孕其中。
歌词中确定的地点名词有三个,它们在相邻词句依次出现,分别是“可可托海”“伊犁”(二者相距一千多公里)以及“那拉提”。“可可托海”并非“海”,是位于“新疆北部阿尔泰地区富蕴县境内的一个小镇”[6]5;“伊犁”地处新疆西部天山北部的伊犁河谷内;“那拉提”则地处伊犁河谷东端。
从文本语境看,叙述者“我”和美丽姑娘“你”的故事发生在“可可托海”,后者是前者的“心上人”。据歌词可以推导二者相识的过程:在“那夜”之前,双方同处可可托海。姑娘并非土生土长在可可托海,他们初见时,姑娘多半从异地骑着骆驼风尘仆仆而来,否则不会有“你的驼铃”。歌词并未交代二者如何相爱,陡然叙述他们相隔千里雪山、万里隔壁的相离。姑娘“不辞而别”“断绝消息”,不仅让二人的空间距离突然变大,更杜绝了缩小遥远距离的可能性。于是,牧羊男子只能在可可托海毫无希望地等待后者——因为很快他就听说姑娘已经嫁到了伊犁。
但他并不理解或者说不愿理解姑娘离开的原因,只能自欺欺人般地归因于伊犁有可可托海没有的“美丽的那拉提”。但事实是,可可托海本就“水草肥美的天然牧场”,有“壮观的额尔齐斯大峡谷”“高耸连绵的花岗岩山峰”“碧蓝澄清的湖水”以及镶嵌在群山中宛如海蓝宝石一般的伊雷木湖[6]5。曾经,他们就在美丽的可可托海共同生活;如今,却只有“我”一人独在。此时的可可托海依旧美丽,但只能勾起昔日的美好,加重叙述者内心当下的枯涩与萧索。
伴随时间横跳,叙事地点又回到了可可托海——牧羊人居住的毡房外,“驼铃”依旧,物是人非。虽然在文本层面“我”已心如死灰,断定那一定不是“你”,但极大可能是在经历无数次听到驼铃——冲出毡房——失望而归后,才口是心非地说着“不是你”,又忍不住再次走出毡房,或只是在室内偷偷看一眼。
凸显叙事空间中的起点、终点,淡化过程的做法,与凸显伴随时间而发生的变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我”虽然世代在可可托海放牧,但可以为了“你”放弃基业,陪“你”翻山越岭,但“你”不给我任何机会和信息。于是,“时间性变化”落实为“空间距离”,遥远的距离赋予“沧桑”又一层“无奈”“无力”的特征——不是“我”不愿改变现状、恢复原状,而是“我”不知何去何从,只能被动地等在原地。况且,时间不会停滞,当它继续前进而遥远的空间保持不变甚至愈发遥远、不明时,隐喻伴随记忆流逝愈发疏远,“沧桑”随之加重。
四、事件中的兩具身体
时间、空间通常存在于事件及其主体中。《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所述事件的具体情节并不明晰。它并非改编自真实故事,而是词曲作者王琪构思的故事。根据部分媒体对王琪的采访[7],故事梗概为:育有两个孩子且丧夫的养蜂女,在可可托海受到了部分当地人的欺凌,年轻的牧羊男子挺身而出,而后两人相爱。然而,养蜂的女子在一个雨夜毫无征兆地离开,远嫁伊犁,只留下牧羊男子在可可托海苦苦等待爱人。
“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的悲情故事并不特殊,以牧羊人为主角的歌曲也并不罕见,如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新疆民歌《牧羊姑娘》等。那么,《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审美亮点是什么呢?
(一)叙事主体由常见的牧羊女变为善良而深情的牧羊男。相较于同类歌曲中欢快而热烈的情感基调,该曲中牧羊男的情感是压抑而有节制的——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牧羊男子选择了卧听风雨,沉浸回忆,原地等待。在文本层面,没有浓郁的仇怨情感,有的是由悲伤、无奈和些许不甘汇杂而成的“沧桑”。
(二)另一事件主体的隐退构造单向叙事。该曲中,作为事件女主角的养蜂女并未直接出场,只存在于牧羊男子及他者口中——她是牧羊男口中的“心上人”,伴随“驼铃”出场,她唱的歌能够让牧羊男“一醉不起”,他者说她远嫁了伊犁。在牧羊人叙述后,歌曲并没有以对唱的形式给出养蜂女的回应,因此叙事是单向的。这种单向叙事容易让审美主体忽视事件其他主体,当其意识到其他主体也经历了事件、遭遇了变故后,另一股“沧桑”与叙述主体的“沧桑”碰撞,审美心理张力由此生发——作为单亲母亲的养蜂女带着两个孩子独自来到可可托海,母子三人从哪里来?又为何要离开原居住地?她们来到可可托海后,经历了哪些欺凌?又出于何种原因狠心离去?她带着两个孩子是如何走过上千公里的路程去了伊犁?又为何突然再嫁?她在新的婚姻中是否幸福,她的孩子又是否被继父接受?即是说,在牧羊男子面对变故的同时,养蜂女又何尝没有经历变故?甚至她所经历的变故,充满着更多的未知。这一系列审美联想一旦被激发,窒息般的“沧桑”恐怕会席卷审美主体的内心;双向的“沧桑”,恐怕比起文本层面男子单方面的痛苦,更加令人揪心。
(三)颓废肉体的缺席造成留白结局。“肉体”是“沧桑”的另一种表达方式[4]20,经历变故的主体往往以颓废、混沌的肉身对抗自身的遭遇,获得看似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官之乐,这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已有体现。但在《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文本层面,牧羊人并没有因为养蜂女的离去而自暴自弃,也没有沉迷于声色犬马。他去他们曾经去过的山谷,听她曾经唱过的歌曲,一边无奈地等待、一边维持着在她出现之前的放牧生活,甚至为她找了一个离开的理由——伊犁的那拉提的杏花才能酿出她想要的甜蜜。歌词结构的复沓隐喻牧羊人心理活动的重复,直到曲终,叙述者也并未告知两具身体的结局,只留下“无人及你”的唏嘘。
五、结语
“沧桑美”与线性时间中的变故紧密相关,它跨越了生死二分的概念,是一种接近中性的情绪和感受,融合了个人的经验和际遇。尽管“沧桑”大多源自消极变化,但其并不指向消极。与之相反,“沧桑”或许指向一种非典型的积极——承认痛苦或失败,积蓄更大的勇气去继续生活,它激发了这种勇气,可能为经历沧桑的人带来不惊与明悟。
参考文献:
[1]国家电影局.备案公示查询结果[EB/OL].[2021-10-28].http://www.chinafilm.gov.cn/chinafilm/utils/serviceContent.shtml?ID=56653.
[2]胡艺华.百姓为本:《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唱响央视春晚的奥妙所在[EB/OL].[2021-10-28]. http://ex.cssn.cn/zx/bwyc/202102/t20210214_5311801.shtml.
[3]姜昆.在一首流行歌曲里[J].曲艺,2021(5):62.
[4]肖炜.异质的经验与时间:试以“沧桑”作为诗学问题[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9.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骥伏枥.西部秘境可可托海[J].百科知识,2021(8):4-9.
[7]展展,李允浩.他是网版周杰伦,可可托海火上春晚,年轻人却没听过[EB/OL].[2021-10-28]. https://new.qq.com/rain/a/20210312A0CRYE00.
作者简介:赖逸平,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