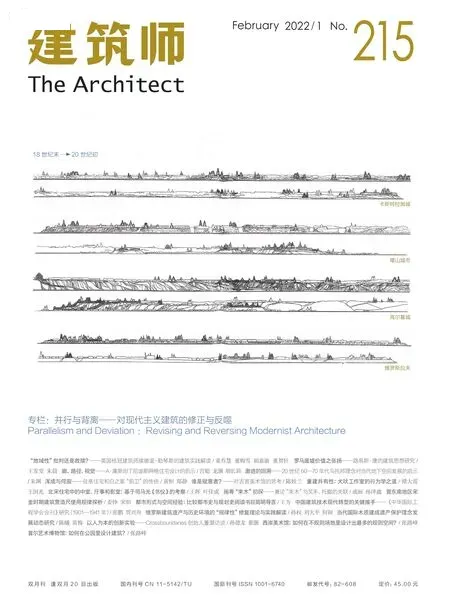以人为本的创新实验
——Crossboundaries 创始人董灏访谈
孙德龙
董灏
董灏,1973 年出生,1991—1996 年间就读于北京建筑大学,1998—2000 年间就读于纽约普瑞特艺术学院(Pratt Institute)并获建筑学硕士,2000—2002 年间就职于纽约TT 集团(Thornton-Tomasetti Group)。2003 年之后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BIAD)工作,并在诸多中外合作项目中起到重要作用。2005年作为合伙人与蓝冰可(Binke Lenhardt)共同在北京创立Crossboundaries 事务所(以下简称CB),同时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2020年成为清华大学开放式建筑教学课程导师,引导学生以“未来乐高学院”为主题,探索教育建筑未来的可能性。近年来,CB 在教育建筑等领域逐渐获得更多关注,代表性项目如深圳坪山锦龙学校、“无限6”未来学校、北大附中朝阳未来学校等。自2015 年以来,屡次斩获包括亚洲建筑师协会建 筑 奖、Architizer A+ 奖、German Design Award大奖、Master Prize 大奖等诸多奖项,还广泛参与House Vision、深圳/香港城市双年展、北京设计周等重要展览。除建筑、室内、标识、装置设计之外,事务所还开展了诸如教育工坊等社会实践项目。在这些跨界实践中,设计者对建筑师角色的定位以及对当前社会问题的思考是访谈中重点讨论的内容。

2020年9月28日董灏(右)于Crossboundaries北京办公室内接受孙德龙(左)采访(赛林彤摄)
一、关于设计理念
孙德龙(以下简称孙):请介绍一下您选择建筑专业的缘起,当时出国留学的初衷。
董灏(以下简称董):这跟我的生长环境有关,我在北京白塔寺附近的羊肉胡同长大(图1)。我和父母还有姐姐一起住在四合院中的一间,虽然只有二十多平方米,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家被我母亲收拾得井井有条,不仅有会客厅、小厨房、每人一张床,还有我和我姐姐各自的小书桌。充满人情味儿的四合院和融洽和谐的邻里关系让我十分怀念。那时我经常坐着101 路公交车去美术馆,一路上经过故宫、北海、景山,然后再回到白塔寺这边的四合院。白塔的白、民居的灰、皇家建筑的金和红,这些来自不同年代的抽象色彩,给当时的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低矮的四合院衬托出夕阳之下的白塔,仿佛定格的电影镜头。这让少年时代的我就意识到环境对人行为和心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可能是促使我学习建筑专业的重要原因。我读本科的时候,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当时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主要是通过一些杂志从西方传到了中国,经历了5 年的本科教育,我感觉还是应该亲身到西方去体验一下。

图1: 童年董灏
孙:普瑞特艺术学院以其艺术性的教育风格著称,这种艺术性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对您之后的实践有什么影响?
董:数字技术全球大行其道,普瑞特艺术学院反而从未放弃对学生有关手工模型制作、研究训练和分析图的逻辑思考过程的强调。至于艺术对更偏重实践与多学科交融的建筑学的影响,我认为更多是在整体学术氛围的熏陶中默默生发的。特别是21 世纪伊始,出国学习建筑学的人还没有今天这么多,普瑞特艺术学院对我的影响仿佛带有命运安排的色彩(图2)。最开始,我拿到的是萨凡纳州立大学( Savannah State University)的Offer,在 佐治亚州。电影《阿甘正传》开场镜头中,阿甘就是坐在萨凡纳州立大学学校门口花园的长椅上。但当时我内心其实更向往普瑞特艺术学院。毕竟在我看来,纽约大苹果这些都是美国人的美国梦。普瑞特艺术学院在建筑学领域也颇有建树,虽不是常青藤学校,却是我心中“皇冠上的明珠”。当时我替父亲看望纽约的亲戚,盘踞了半个月。就在离开纽约去佐治亚州上学前,我决定去看看那所心中向往的学校,于是带上了作品集直奔普瑞特艺术学院,那天我有如神助,建筑系主任马克(Mark)刚好在办公室,于是我拿出作品集和主任一通神侃后,竟然迅速拿下了 Offer。刚开始的两个月,作为亚洲学生,我一直感到迷茫,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将当时主流的西方现代主义与自己的文化及社会现实相结合,而不仅是形式上的简单复制。当我坐在纽约炮台公园,看着树影映射在刻于花岗岩石碑的人名之上,疏影流光间第一次产生了对建筑学的反思:建筑应是建立在人本主义之上的,而我之前学的科学技术以及工程学是人类经验的研究总结,是非“人性的”,这是我对建筑新认识的开始(图3)。

图2: 青年董灏与家人在普瑞特艺术学院毕业合影

图3: 纽约炮台公园的石碑
一路走来,我们一直相信“我们塑造空间,而空间也塑造我们”。同时,我们也相信世界是大家共同生活的场所,因此我们追求的是共生共赢,而不仅是建筑师或个人的观点表达。在纽约绿树成荫的大学校园中散落的各个雕塑作品都是百年以来学校的收藏,校园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更不用说每天发生的各种展览。“润物细无声”就是那些年城市与学校赋予我建筑生涯中的艺术性。说到艺术,有一个特别想分享的就是“沟通的艺术性”,这点是我作为一名无惧时代感的70 后建筑师的感触。同学、同行、师生之间的关系与交流是最值得珍视的,这些人文关怀才是我执业生涯中第一次被唤醒的最珍贵的情感体验。
孙:在国外求学期间,是否有对您产生重要影响的人?
董: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是当年在普瑞特艺术学院的导师杰克·特拉维斯(Jack Travis)[1],他是非裔的美国建筑师(图4)。在美国这种民族大熔炉的环境下,非裔还是很有特点的。导师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纽约人,带着我去看工地去看现场,帮助我很快融入了美国文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时刻保持清醒和敏锐,有自己的主张,不随波逐流。他时刻提醒我,作为一个亚洲人,应该更多考虑自己的文化和现代性的融合,未来才有发展的方向。20年后的今天回头再看,更加坚信我导师所说的。导师对我而言亦师亦友,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亲密联系。2019 年导师来中国的时候,见到我热泪盈眶,他认为我是他教学40 年以来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图4: 董灏在普瑞特艺术学院的导师杰克·特拉维斯(Jack Travis)
孙:您提到自身文化与现代性的融合,在之后的实践中是如何体现这种融合的?
董:我认为民族性、地域性和全球化并不矛盾,尤其在形式层面。形式其实是可以活学活用的,很多形式自身只在特定的时代才有意义,今天要考虑如何结合我们各自文化的特点,这样才是更有生命力的。我认为每个人在信息的接收上是没有门槛的,如今的建筑图像传播不再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单纯是靠一本外国杂志,所以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传达要更细腻,更融合一些。例如我们在北京做的宝马博物馆项目,这是宝马公司在德国以外的唯一一个博物馆,德方要求体现的是自身汽车产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项目又在北京,投资人是中方收藏家。之前中方的设计师做了一个故宫的大红门,大金钉子钉在木门上,后面展示的是德国的汽车,德方根本接受不了,认为太具象。我们的关注点是如何结合中德双方不同的文化诉求,因此选择使用帷幔从顶棚垂下形成一个门的轮廓,把空间的尺度变成一个更宜人的尺度,帷幔的颜色选择了故宫红墙的颜色(图5)。即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都能够接受和体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地域性表达。

图5: 宝马博物馆室内
孙:在回国工作之前,您又在纽约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对您之后的实践有什么影响?
董:我在纽约当时世界最大的 AE(Architecture&Engineering)公 司TT 集 团就职,具体是在公司内部的建筑部门工作。我上班的时候,正好赶上9·11 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三天,我们公司就受纽约市和世贸双塔的业主委托去做现场的损失调查。整个三年的工作过程,给予了我两方面的帮助。第一,认识到建筑不只是艺术,它还是技术,建筑内的所有要素,包括结构在内都是一个精密运行的系统,空调机电都应该是一体化的。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对项目可实施性要求非常高。这种大公司里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虽然刚刚毕业,但在导师带领下会参与整个项目,尤其是互联网项目从设计到施工管理(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的全流程。第二,这个公司的实力特别强,在全美国各地都有项目。当时公司在芝加哥有项目,我经常因此往返于纽约和芝加哥,早7∶00起飞,到芝加哥8∶00,当天晚上再回来。这也让我在工作的三年中能够快速地成长,还接触了很多互联网项目。作为一个北京人,经过三年的历练,我决定回国发展,为奥运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我的办公桌在美国老板斜对面,他经常鼓励我要好好工作接他的班,我并没有立即表态,直到辞职的时候我才说出真相,他特别激动,认为我很有抱负,也很支持我。
孙:您将事务所命名为Crossboundaries“跨界”,“跨界”这个词体现事务所实践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董:作为一个建筑事务所,我们的实践不仅仅局限于建筑设计。首先,从产业层面说,我们希望建筑设计能够突破既有边界,就像上述提到丘吉尔所说的“人创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我们尝试去拓展我们的设计领域:从建筑设计到室内设计,甚至到策展,标识设计,活动策划等。建筑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终极产品,它所容纳的人的体验和行为才是主体。其次,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十几年前我们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建筑设计、室内设计、标识设计之间并没有细分,我们认为一个建筑应该是表里如一的,所以我们也在特别推进室内标识系统。第三个层面就更加具体,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国内国外设计师的混合,当然这种设置也会因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带来很多工作上的麻烦,但与此同时也会形成很多设计上创新的想法。最后,Crossboundaries 也不把自己局限于某种风格或流派,而是尝试找到最适合项目的设计。
孙:在当代中国,大致存在两类建筑师群体:一类是大型设计院群体,面向市场,强调更大范围的社会服务;另一类是个人建筑师,强调对现实的批判,部分有自身明确的建筑语言。从您的实践经历看,您应该兼具这两类身份,您如何看待这两类群体对建筑行业的贡献?从目前事务所的组织方式和实践特征看,您是如何定位自身的?
董:之前我在国外事务所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国进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当时也有跟诸如福斯特(Foster),OMA 这类顶级国外事务所合作的经历,后来又创立自己的工作室。我的个人体会是,对现实的思考和批判是设计的核心和源泉,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不同的组织方式差别不大。大型建筑设计研究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与中小型民营建筑事务所并不存在显著的不同,在前后两个工作阶段,我所秉持的都是对空间塑人的思考。我认为它们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市场的分工。诚然,大型建筑设计院更多承接的是国家大型项目,体现着国家形象在国际上的展示,且大型建筑设计院在面对私人业主时没有个人建筑师这么多的自由度,但是,我们是否要否定设计院对最终使用者的批判性思考呢?圈层不同,大家的服务手法不同,我在这些不同的经历中更看重专业本身的批判性。据我观察,大家未来的发展都是殊途同归。以往可能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在BAT 行业出现之后,我相信没有那么多迭代的时间差,大家接受讯息的时空尺度都在改变,信息都是相对对称的。
孙:您现在的事务所是在20 人左右,整体工作方式上与您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时期有什么不同?
董:大到像福斯特、OMA 这种公司,小到几个人构成的工作室,在具体项目上还都是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这就是建筑设计的一个显著特征,小组始终是基本单元。从我个人来讲,从进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创作委员会到独立开业,这种创作模式没有太大变化。现代创新组织一个比较好的架构方式是团队共同进行头脑风暴。对我们来说,更多是用一种类型研究(typology study)的方式分析项目的需求,得出最能满足这种需求的形式,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建筑设计方法。
孙:在您新近的实践中有很多规模较大的公共项目,您如何看待建筑师在这类项目中的作用?在这类大型项目中建筑师如何体现创新性?
董:我们认为其中的创作过程和思考逻辑是发现问题之后的再定义。在公共项目中,建筑师可以引导甲方和项目向一个更好,更有利于公众的方向推进。我们常常是以问题为出发点寻求突破,建筑师永远是在约束条件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解答方案,项目本身的很多约束条件就可以激发出建筑师的创造力。比如在深圳坪山区锦龙学校中,因为项目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我们采用了装配式的建造方式,极大地缩短了建造时间。为了避免装配式建筑的重复单调,我们设计了6 种不同的预制板为建筑增加变化和韵律。同时,我们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不同的区域,为校园增添了活力(图6)。

图6: 锦龙中学外观
孙:您有两个著名的乡村教育建筑,您的大多数设计项目主要在城市中。在城市与乡村项目中,您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有什么不同?工作过程和方法在这两类项目中是否有一定的延续性?
董:这是个好问题,简单地说其实就是生活与人,人与空间关系的不同。在乡村,有其普遍存在的特定社会问题要回应。北沙幼儿园其实不大,3000 多平方米。江苏省盐城市是三线城市,幼儿园是当时江苏省教育厅邀请我们做的公益性试验基地。当时比较触动我的是周边的环境,那些幼儿园都是3~4 层的,刷点成人以为的童趣色并画上卡通形象:粉红翠绿之上画点白雪公主、米老鼠等;内部就是单边走廊串联三个教室。我们还注意到村子“空心化”很严重,村庄里都是留守儿童,这种农村的衰败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的衰败。后来我们就结合环境,做了群落式的布局,底层是游戏室,上层是睡眠室,组团之间形成了院落,小朋友之间可以进行更多即兴互动,建筑也被消解成了最多两层高的尺度,与周边自然和村庄环境和谐共生(图7)。这其中的意义有三个层面,第一,现在小孩上幼儿园不再哭闹了,跟回家没什么差别,因为幼儿园看起来跟周围农宅融为了一体(图8)。第二,小班、中班、大班各自形成组团之后,我们在小班和中班之间,中班和大班之间均设置了活动室,不同年龄层小孩之间的即兴活动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人的社交能力从小就被培养激发。第三,由于形式的开放性,幼儿园建成之后,自然演变成村庄的活动中心,促成了当地村庄的社区活动。我们通过建筑学的理念和手法,更多地寻求对社会需求的解决。北沙幼儿园不仅仅是留守儿童的幼儿园,她既是幼童美好人生的开始,又是空巢老人的聚会场所。在这里,友情、关爱,理解与成长,都自然而然的发生。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人与空间的关系是我在设计中最坚持的,这也是唯一的延续性。

图7: 北沙幼儿园的聚落设计概念

图8: 北沙幼儿园外观
孙:如果从建筑本身来说,当您在不同项目中将人的需求转化为空间形式时,是否有一些建筑语言、原型或类型的延续性?有哪些建筑作品或者建筑师对您启发最大?
董:其实我对带有明显个人标志性的建筑语言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建筑中,建筑师本身强烈的个人风格可能符合大众“喜闻乐见”的审美需求,但我作为一名没有走进公众视野的建筑师,目前还没有被“道德绑架”,我想我以后也不会这样去处理我的建筑作品。建筑作品与建筑大师都很难脱离其时代性,我在每个时期都会被不同的建筑师及其建筑作品感动。最近让我眼前一亮的是芬兰PES 建筑设计事务所中标的上海潜艇博物馆项目,这是近年来在国内公共建筑领域难得的好项目,PES 对于场域的深入思考与因形就势的巧妙处理手法,让人印象深刻,我非常期待建成后去实地参观学习。
二、建筑师、业主与使用者
孙:您在与业主的合作过程中经常受到认可,例如家盒子、北大附中等已经成为长期合作的客户,在您看来理想建筑师和业主的关系是怎样的?
董:你问到的这个问题,我是今年疫情以后才想明白的。我也失去过很多原以为“志在必得”的甲方和项目。好几次在最终竞赛入围时,我都深感我们事务所的方案具有极大的优势,但最后,甲方的反馈都不是关于建筑设计本身的意见。这其实和谈恋爱一样,你喜欢她,她不一定喜欢你。但最后真正能合作的都会给我推荐新的潜在项目,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还是因为双方有很多一致的追求。我们也希望能打破自己的专业壁垒走向社会,更倾向于去理解业主的需求,基于这些再提供更专业的方式和更好的设计,从而建立信任关系,这样大家的沟通成本才会越来越低。在这里,品牌的认同还是非常重要的。
孙:您在与业主沟通的过程中,为了平衡使用方诉求与建筑师个人诉求,是否遇到过一些难题?如何化解?
董:在创造建筑的过程中,理念的碰撞、繁琐的技术难题与沟通障碍,都是作为建筑师必然要应对的问题,也是对专业能力和沟通能力的考验。我认为在与业主的沟通中,最重要的还是展现出自己的专业程度。建筑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建筑师需要对项目有一个综合预判。我的合伙人冰可作为一个拥有德国教育和实践背景的建筑师,在建筑品质的把控上也会提出很多前瞻性的方案。初期业主或许不理解,但项目建成后,就会在实际使用中体会到其中的益处,这也帮助我们与业主之间建立了信任的关系。除此之外,同理心也很重要,要跳出建筑师或个人的视角,多从甲方和终极使用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设计中不要制造冲突,而是要找到各方的利益共同点。例如,在上面提到的宝马博物馆项目中,甲方分别是来自德国宝马总部和中国的投资人,虽然看似他们的诉求是来自完全不同的层面,但其实想要的结果是一致的,即建造一个能体现企业鲜明特征的博物馆。而作为建筑师需要有理解和挖掘业主需求的能力,英文中叫作UNSPOKEN NEEDS,因为很多时候业主自己都认知不到自己“真正”的需求。教育类建筑又区别其他建筑项目,业主往往是教育者本身。CB 的业主通常有很明确的教育理念,而教育者的观念与态度会对空间组织有很大的影响。CB 在这方面特别有能力和耐心去倾听,理解甲方、甚至更多的时候用建筑设计去启发甲方。使用者和建筑师的关系就像是舞伴一样,体现了一种互动的过程,这也是建筑设计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它变成了我们跟社会沟通的桥梁。
孙:您近期又完成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办公室项目。三联、久趣(QKIDS)等一些与您长期合作的业主都属于在产业理念上有很强先锋性的机构,他们的受众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是否可以说这也是您和业主契合的重要原因?未来在这一方面是否考虑有所拓展?
董:在多年实践中,我们事务所从来不参加免费的比稿,我们设计前期都会做大量研究工作,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也是关系到最终建筑或是室内作品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我相信找我们合作的业主也是在对CB 设计理念有足够了解的前提下才会来的,这是一个互相选择的结果。我们在未来很期待一个民宿项目,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涉及的领域,这类项目需要实用性与商业网红价值的平衡,我十分期待接受这个挑战。
三、建筑与技术
孙:您在装配式建筑方面已经有一些成功的探索,当前这种类型的建造技术给建筑行业带来的机遇是什么?
董:我们的态度一向是拥抱技术,但技术一定是为人的需求和情感服务的。既不能是技术控制一切,也不能回到原始社会。装配式建筑早已不是一个简易搭建或者临时建筑的概念,它结合了BIM、数字化建造及组装,甚至智能化、光电技术等。我们在这三四年时间里接触了很多装配式项目,如在深圳完成的坪山锦龙学校是一个建筑面积6 万平方米的装配式学校,这是一个从设计施工到建成仅用13 个月的永久建筑。此外还有2018 年在鸟巢参与的House Vision,与 TCL 合作的方向是将智能屏幕系统整合进居住空间(图9)。

图9: House Vision 中屏幕与居住空间结合的探索
大家普遍认为装配式可能不会产生那种诗意或是浪漫的表达,但我把它当成对建筑师专业技术的重要挑战。装配式的特点之一是标准化,但标准化不代表单一,更不是约束,通过设计是可以实现作品的千变万化。从另一个角度看,标准化其实贯穿在整个建筑发展史中,存在于任何一座建筑中,甚至早已成为了我们习惯的思维模式,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当然未来建造并非是标准化这么简单,也许会更像加工业,每一个建筑构件在图纸里都有它自己的身份,就像手机里的每一个零件。过去建筑都像雕塑一样被造出来,需要多少吨水泥多少吨钢筋,只有一个概算。但在未来装配式的体系下,任何一个物件只要被具体描述出来,就可以很精准地被造出来,就能实现效率与质量的双重保证。新的技术一定会带来更多的自由,赋予建筑师新的素材和语言,创造更具想象力的空间。就像没有钢铁的时代,人们只能想象教堂,无法想象摩天楼。在未来,传统建筑的评价标准、设计标准以及空间概念都可能被新的技术重新定义。
孙:您在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到了装配式可以作为一种积极的建筑语言吗?
董:装配式本身有一套自己的语法和逻辑,一旦掌握好这个逻辑,会有很多的优势。在锦龙中学项目中,建筑外墙使用的是预制板,虽然板的尺寸是难以变化的,但是厚度和边缘形态可以做出变化,而这种所谓的品质和美观的实现在其他的建造体系下需要很高的成本和很大的工作量;在装配式体系下,通过控制标准件的形态与类型,却显得轻而易举。
孙:您基于一系列教育建筑的实践提出了“移动学校”的理念,请您谈谈这种模式的应用前景。您如何看待这种移动性与建筑的永久性和地域性之间的关系?
董:未来教育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未来教育更强调一种互动,教育不会仅仅局限于学校内,而会发生在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情境下——教育变得场景化了。可以移动的学校才能更好地适应这种未来的趋势。移动学校便于安插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面的功能组合主要基于我们长期对教育项目的深入研究,我们总结出的6个场景可以涵盖未来交流的各种需求:
第一,要提供满足学生个人活动的空间;
第二,要有适应多种形式的集体教学的空间;
第三,教室内外的空间应该是流动的,以鼓励学生之间的交流;
第四,要强调建筑室内外,人工与自然的交流。
第五,要求校园空间内材料和色彩设计符合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第六,要满足智能化,云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
在这里装配式建筑也实现了技术与内容的统一,可以很好地为“移动学校“提供技术支持。我坚信,建筑不会永远存在,珠穆朗玛峰也会消失。我认为建筑的地域性更多是通过房子里面使用的人建立的。正如我前面所说,建筑本身并不一定是我们的终极产品,我们更在乎通过空间营造出的使用模式。在“无限6”未来学校产品中,地域性并非体现在建筑形式层面,而是创造出室内教学与室外空间最大限度的接触,让学习者不再孤立于周边的环境,这也是我认为与地域之间建立的紧密联系(图10)。

图10: “无限6”未来学校的使用场景
四、建筑教育与行业愿景
孙:您既从事建筑实践也从事建筑教育,您在清华大学大师班教学“未来乐高学院”中的主张与传统建筑教育模式有什么不同?您认为建筑教育未来会有哪些转变?
董:研究表明,当代人一生中有86.9%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剩下百分之十几的时间即便在户外,也基本是在被人工修饰过的空间中。因此,人造环境已在你我生活中占了绝对主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群行为。其中,就影响程度而言,教育场所或许是最为突出的。教学理念的转变在一些国际上的私立学校中已然发生很久,只是近十几年,才慢慢进入国内大众视野。尤其是近年来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开始强调终身学习的能力,教育理念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鼓励学生独立探索和求知为主。他们也希望通过空间设计,激发孩子的积极性,于是今天的教育空间也越来越颠覆“标准”。
在清华大学大师班教学中,除了传授传统建筑学教育中的建筑设计方法与规范外,更多的是进行“思维的练习”,我们更希望培养同学们对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能力。“授人以渔”我认为是最关键的。我们虽然强调乐高装配式,但没有刻意让大家深陷装配式的技术或构造里面,我们更希望学生在设计时有“软件与硬件”统一的概念(图11)。在8 周的课程中,前两周是让同学们阅读现代教育发展的书籍,让他们去思考什么是现代教育。因为教育对每个人来说可以像水和空气一样寻常,大家可能不会去察觉它们有什么与众不同。通过阅读,学生们会思考未来的教育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引导同学们创造自己的任务书,顺带了解一下装配式的技术。我们更希望能跨出自己的专业去看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专业不重要,建筑师仍然需要不断地去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但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出口不在我们专业内部,而是应从社会的现实需求出发。我们在很多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比较丰富,有时是建筑师,有时是老师,有时是活动的策划者,产出的内容也会更加丰富。我们在过去的六七年间也做了大量面对创新教育的项目,这些项目都代表我们对于未来教育或者说现在正在发生的教育改革的思考,也代表我们对未来教育的一种探索实验。

图11: 未来乐高学院学生作业b

图11: 未来乐高学院学生作业a
孙:说到教育工坊,这些工坊可以说是您践行空间塑人的重要组成,反过来,这些活动是否会带给您对于教育本身新的认知和理解?可否分享下您其中的一些点滴和感受?
董:这些年来,无论是工作室的教育工坊还是外校聘请我去做客座教授或是教学评委,我最大的惊喜,也是对我自己的反省就是“学无止境”。现在建筑学专业学生们的眼界,对事物认知的广度与深度,甚至是维度,都是同龄时期的我,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现在的我都难以企及的,我对于在工作中遇见的各种人都心怀尊重。建筑学一直是与新材料,新技术同频发展的,我认为永保一颗对未知事物好奇心和敬畏之心,这就是教育本身对我最大的启示。
孙: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建筑师应该具备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建筑学的内核与外延在哪里?
董:信息时代的特点是变化快、容量大、参与人员多、互动性强。而生长于信息时代的学生与上一代相比,他们的思维更加灵活,也能迅速接受新鲜事物。但总归来说,信息时代的创新人才需要有四个C: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Creativity(创造性),Communication(沟通),Cooperation(合作)。如果想在信息时代生活,我们需要具备这四个方面的能力。如果把这四个能力具体放到建筑系同学们身上看,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这四件事。这次乐高学院的题目中,我要推着同学们往前走一步的原因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让现状、让生活变得更好的想法:不是说“反正现在学校长这个样子我就觉得挺好”。生活要变得更美好,一定需要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有批判性思维。如果建筑师仅仅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按照规范去制图的工具,那一定会被取代。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在诸多解决策略的“排列组合”里面挖掘人的需求,那我们会越做机会越多。
同时,这个对生活更高的要求不是简单的、无意义的抱怨:首先,利用批判性思维,把看到的、可以提升的部分总结下来,按照逻辑编排好;接下来,就要求我们有创意;在此之后,和他人一起合作完成——这也是建筑学的特点。我们现在的作业会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将来做任何项目,也要组织其他人一起参与。一个简单的项目也需要建筑专业、结构专业、设备专业、水暖电专业合作,施工的时候包括施工团队,同时还有甲方一起完成,而这个过程就需要沟通、合作的能力。要知道,人和人有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过去的教育认为,豆子从一边装进去,另一边出来时最好完全一致,而今天的教育是让一百个豆子都不一样,所以应该认识到意见相左是常态。因为存在不同的意见,所以才需要沟通,交流,从而得到新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吧。
AI 的出现是否有替代建筑师的可能性,我个人觉得从技术上是完全可能的,这肯定是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结果。我认为建筑师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对建筑与社会关系最全面的思考,建筑设计者需要呈现对世界最深层次的理解,并对真实世界有所反馈和影响,而非再现真实世界本身。就连承认建筑师追求的是真实性,都是对这一目标的破坏。追求真实就是与设计本身的对立。我坚信,这是AI 算法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五、结语
由于董灏丰富的海内外求学和工作经历,身上既有先锋建筑师的实验精神同时又具备严谨的工程经验。从最初的北京“家盒子”、爱慕时尚工厂、正通宝马博物馆、到后来的北大附中系列项目,再到“无限6”未来学校、Qkids 久趣/英语中心和深圳坪山锦龙学校。我们看到了建筑师在城市、建筑、室内等各尺度层面的探索与尝试。从大型项目的品质把控,到小型项目的细腻考量,董灏始终贯彻并完善“空间育人”的设计理念,从最初“让儿童走出教室“的学前教育空间本土化到跨学科混合式教育空间的探索,建筑师与使用者以一种协作共赢的姿态共同促成了一次次社会实验。这期间还包含对特殊社会群体的细致考虑,而这些社会实验也同时拓展到教育建筑之外的项目中。
当今中国建筑实践已经逐渐从早期对建筑空间和建筑语言本身的关注,拓展到对社会问题和生产机制的关注。尤其是在当今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之下,物已经退居第二位,人则成为空间营造的主角。董灏认识到不应过度追求西方空降式的精致化,更多要从中国的语境出发提出解决策略:通过深入挖掘业主诉求,发现问题,并给出创新性的解答。这种创新性的解答有两层含义:第一,以人为本和对人的关注就意味着对制度的反思和革新。拒绝接受制度对人行为的约束和规范,深度介入物质空间的生产机制,充分挖掘现有资源,综合各类要素和技术,重新拟定任务书。在董灏的设计过程中,更多体现出对环境与人关系的深入思考,以及人的潜力如何被激发,如何创造出空间多样化的使用模式等。第二,正如Crossboundaries 字面的含义,建筑师的终极产品并非是建筑。董灏及其事务所将创新和批判性思维模式作为职业的核心竞争力,参与演绎多种社会角色,亲自参与到活动策划、教育课程,标识设计等诸多领域,这种围绕空间塑人而展开的社会实践不仅在项目生命周期的层面赋予空间更多可能,同时也使得建筑成为实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参与到更广泛的空间生产机制中。
正如董灏所言,建筑设计其实是一个从社会到个人,再从个人走向社会的过程。正因为这样,建筑才能实现超越个体建筑语言与想象的更持久的生命力。
注释
[1] 杰克·特拉维斯(Jack Travis)于 1985 年 6 月创立同名设计工作室。1994 年创立AC/DC(Afri-Culture/Design-Culture)工作室,旨在收集和传播与环境设计相关的黑人文化。入选全国少数民族建筑师组织(NOMA) “长老理事会”,曾任AIA NYC 荣誉委员,AIA NYC 董事会秘书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