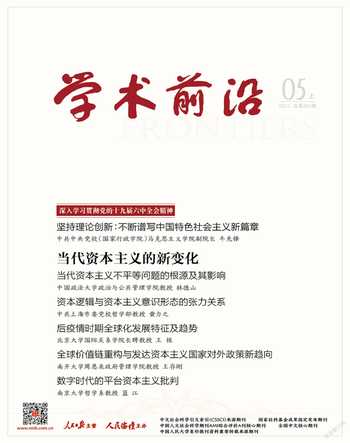后疫情时期全球化发展特征及趋势
【摘要】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全球化遭到严重冲击,全球经济贸易活动近乎停滞、全球产业链濒临断裂、资源短缺引发全球性恐慌。2022年初,世界经济在新冠病毒突变的不确定中艰难恢复,而俄乌冲突又加重了对全球化未来的悲观预期,尤其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对全球化发展的担忧与怀疑。后疫情时期,全球化发展挑战严峻、困难重重,但是全球化的主要趋势不会改变。当今世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数字技术迅速普及,区域合作成为各国缓冲外部环境冲击的首要选择。未来的全球化,将迎来重塑与再造,其数字化、区域性及慢速性等特征将更加明显,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再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成为全球治理的补位者,引领包容的、开放的、普惠的全球化发展。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化 再全球化 数字全球化 “慢球化”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9.006
进入调整期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指经济活动的国际化过程,是一种资本、商品、服务、劳动以及信息超越国内市场和国界进行扩散的现象,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演进的过程。[1]在超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化与变迁中,生产要素通过国际分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与重組,促进了更高效的生产,加强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实现了世界经济贸易的繁荣。全球贸易大幅增长、国际投资日渐活跃,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全球化不断地创造福利与收益。但是,这个过程也在不断产生公害(public bads)。从经济贸易维度来看,全球各经济体之间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中心与外围”国家的综合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各个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及地区分化也愈加严重。从政治社会维度来看,经济贸易的繁荣带来了对全球及各经济体内部特定的利益再分配,而这些利益再分配在不同国家和群体有不同的分配效应,进而影响国家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的制定。全球化作为一种政治分化与社会分层的力量,引发政治、社会层面的负面效应。
可见,全球化自诞生以来,以多维的、复杂的特征不断变迁,不断适应,其影响利弊共存,因国而异。全球化在发展进程中,经历多次的“逆”势与退潮。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全球经济遭受严重打击。随后几年,随着苏维埃革命胜利成立的苏联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制裁,退出世界贸易体系,西班牙暴发流感疫情,全球货币市场动荡不稳。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迅速下降。2001年的“9·11”事件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了逆全球化概念的传播与流行。2016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公开抨击“全球主义”(globalism),大搞“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大行其道;同年,英国公投“脱欧”,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的极右民粹主义势力抬头,逆全球化浪潮在西方世界不断涌现。2020年初,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再次被扩大,逆全球化表现越来越明显,西方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推动的全球化在多个方面已经深陷困境。
近年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饱受诟病,民粹主义(Populism)、非自由主义(Illiberalism)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从不同角度对自由主义叙事进行攻击。民粹主义政客呼吁对世界政治的规则和价值进行变革,认为新自由主义秩序框架下的全球化进程仅使得罪恶的精英阶层受益,却践踏了国家主权、传统价值及地方文化。[2]民粹主义的保守派对自由派所主张的自由、开放及多元的社会繁荣发展强烈不满,他们渴望每个人都信奉相同的宗教,拥有相同的种族的世界状态。[3]而非自由主义者(Illiberalists)煽动反抗当前的社会、政治秩序,诋毁科学与专业知识,崇拜欧洲古老的神秘身份认知。[4]民族主义者,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只有本国优先,才能实现发展,只有保护主义,才能够保障人类生命安全。民族主义者通过煽动种族偏见转移视线,鼓动回避根本性的经济失衡问题,而经济问题失衡导致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崩溃破坏了民主,反过来又“鼓励”了有毒害性的极端民族主义。[5]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已经成为过去,世界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大国对抗、战略脱钩形势更加严峻,国际权力结构将重新洗牌,中美将成全球战略博弈的中心地带。20世纪所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构架将会崩塌,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已经终结。[6]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施压各国对俄罗斯施加全方位的制裁。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Adam S. Posen)认为,这些制裁对俄罗斯的稳定发展及俄欧能源供应链将产生严重的影响,使得各国政府脱离经济联系、转而追求经济上自给自足的逻辑变得更加合理。[7]
后疫情时期,全球化发展步入调整期,其动力机制、发展模式都要发生重大变化。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再是全球化主要的动力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各国的经济贸易活动在全球性的合作平台上实现了快速增长。随后,世界银行(World Bank, WB)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相继成立,二者作为重要的多边机构,鼓励国际投资,促进国际贸易均衡发展,将更多不发达经济体纳入全球经济体系。可以说,在二战之后,全球化经历了快速的发展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美国也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成为世界霸主。然而,随着欧盟市场逐渐成熟、中国等新兴国家日益兴盛,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相对下降。另外,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现阶段拜登政府拉拢盟友的划线政策,严重瓦解了人们对美国引领全球化的信心,尤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上,不仅在保护本国人民生命安全时无能为力,更严重缺乏全球领导力。新冠肺炎疫情证明,美国政府的角色在全球事务中并不是不可或缺。[8]这将催生新的引领全球化发展的力量。其次,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穷国与富国之间分配不均与资源差距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反对不公平、不普惠、不均衡的全球化,反对应对全球性危机治理无效的全球化,因此,全球化亟需进行再造与重塑。本文认为,后疫情时期,全球化进入调整期,将呈现三大重要的趋势,即全球化的数字化趋势、全球化的区域性趋势以及全球化速度放慢的趋势。
后疫情时期全球化的数字化发展
全球化发展至今,国际货物及服务贸易的发展决定着全球化的速度。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贸易增长率大幅下降,伴随而来的是跨境数据流的大幅度增长。据统计,从宽带量来计算,跨境数据流从2008年至2020年,增长近112倍。至此,数据占据了全球贸易的中心位置。达特茅斯学院教授马修·J·斯劳特(Matthew J. Slaughter)称全球经济是数据的“永久动力机”(a perpetual motion machine)。[9]数据的超量应用,推动数字技术变革,而在数字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经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正走向更高级的形态。全球化的“数字化”趋势使得全球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后疫情时期,个人的生活、企业的运转、国家的发展,都包含了更多的数字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化的数字化发展,数字全球化迎来加速发展机遇。
从全球范围来看,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数据统计,2018年,信息与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产品占贸易总额的比例为12.31%,而2020年则达到14.97%。2020年,电子商务在全球显著增长,在线零售在所有零售中的份额从2019年的16%增加到19%。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21),新冠肺炎疫情对互联网流量产生巨大的影响,2020年全球网络宽带增长35%,是2013年以来幅度最大的增长。[10]疫情期间,线上会议、网络购物、在线教学、远程医疗等成为人们工作与生活的常态。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突破和融合发展推动企业向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双向创新不断努力。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入到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会在融合期内经历颠覆性的变化,并在全球化范围内重新布局;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企业的运营、数字硬件制造与软件开发、通信产业终端产品研发等,将会在数字全球化下呈现更明显的特征与趋势。从国家发展层面看,技术应用下诞生的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产业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成为支撑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更强劲的全球化。对外而言,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进入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由线上与线下相互融和、彼此促进的混合型外交成为疫情期间的常见形式。地缘政治冲击、数字技术将共同塑造国家关系的形成轨迹。[11]
全球化的数字化特征日趋明显,后疫情时期,全球化将进入数字全球化时期。这种更快速、更深入、更宽泛、更直接也更激烈的全球化,将虚拟世界与实体世界联系起来,全球化的影响在数字科技产业领域展现巨大的潜力,同时也为包容性、可持续性增长提供了有效的数字解决方案。全球化的数字化,显示出数据要素流动速度更快、程度更深、覆盖领域更广等特征。中小微企业加入跨国公司行列,成为推动数据要素流动的主力军。要素流动的内容也不再仅是货币交易,越来越多由知识密集型产业生产的免费的内容与服务成为跨境交易的主要内容。相比于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的构建过程较为简单,对地区本身的条件要求也较低,因此,数字全球化下,资源、教育、产业等发展需求在发展中国家表现更为明显,便捷的数字化供需关系使得一直处于边缘的国际与地区有机会重新融入全球化发展中。数字技术与数字媒介将推动多元化、多途径、多层级的数字联通方式,信息互换与观念沟通打破了国界的限制。[12]
然而,数字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其负面影响力更大、破坏力更强。数字全球化不仅是“数字”体现在实体经济中,更在很多方面产生替代或破坏作用,例如数字贸易对于传统贸易的替代。自动化世界中,对于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将会逐渐降低。当前,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在人工智能等数字领域,中国、美国等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将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数据的应用使得解读、预测甚至操纵人类行为成为可能,数据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与此同时,数字全球化同样面临各种壁垒与障碍,譬如数据本地化要求、网络审查、数字内容市场化的限制与冲突,数字隐私与保护内容对于数据自由流动的扰乱等。一方面,这些壁垒降低了数据的利用率及所可能发挥的最大价值;另一方面,正如约瑟夫·奈(Nye, Joseph S. Jr.)所言,没有规则、不受控制的数字秩序风险极大,不仅会对网络本身带来负面影响,其危险、灾难性的后果会波及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是当今世界需要探讨的最基本问题。[13]
后疫情时期全球化的区域性表现
2020年初,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署修订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即《美墨加贸易协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美墨加贸易协定》是特朗普政府极其重视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说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及美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美墨加贸易协定》不单单是一个贸易协定,更是美国将贸易、经济、政治进行组合的战略工具,收紧区域价值链、淡化发展性议题、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等意图均有体现。[14]2020年11月,中国、澳大利亚、东盟等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RCEP旨在与“一带一路”倡议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现亚太地区开放、透明、公平和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将极大增强亚太区域发展韧性。2021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CPTPP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而CPTPP基本保留了TPP的核心条款内容。中国一直将TPP与RCEP视为区域一体化“同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15]正式申請加入CPTPP凸显中国将用实际行动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与更高水平开放,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正式申请加入CPTPP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中国切实推行区域一体化,加强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另外,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CAI),促进达成一份平衡的、互利的、共赢的协定;同时申请加入《数字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推进深度参与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国际合作。从上述协定的成员国来看,当前重要的贸易投资框架协定所涵盖的地区,正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经贸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经贸区以及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区——这全球三大经济贸易圈。
当前,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来缓冲全球性波动给本国经济带来的震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首选。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国的应对及全球治理的表现再次证明,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衰退,全球化未来的走向可能是经济区域化。[16]而俄乌冲突将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生活产生持久性影响,俄罗斯很可能被西方国家排除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全球贸易体系有可能分化为两个或三个大型的地区性贸易集团。后疫情时期,至少在短期内来看,区域合作将取代全球合作,成为未来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合作方式。然而,全球“三足鼎立”的经济贸易圈并不是“三者孤立”;三大经济贸易圈之间所形成的产业链或价值链彼此依赖、互相联系。[17]而CPTPP、CAI等贸易投资协定正将这些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正因如此,本文认为,区域合作取代全球合作,并不意味着区域化取代全球化,区域化并非全球化的倒退,而是全球化的新的表现形式,是当前全球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且明显的特征,全球化仍是主要趋势。
后疫情时期速度更慢的全球化
早在2015年,荷兰学者埃迪耶德·巴卡斯(Adjiedj Bakas)创造了“慢球化”(Slowbalisation)一词,用来形容全球化性质和节奏发生变化,描述全球化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如何放慢了全球经济融合的速度。[18]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可以说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全球化开始进入“慢球化”时期:全球化的速度下降、范围收缩,动力点也发生新的调整。具体表现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加重,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慢于全球生产速度,全球贸易额占世界GDP比重逐年下降,美国等西方国家内顾(inward-looking)政策倾向严重,
随着全球化进入“慢球化”时期,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增长趋于平缓,改革议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停滞,各国对移民相关政策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的人越来越多。从相关数据来看,二战以后,1945年,全球出口贸易占GDP比重为10.1%,此后一直处于逐年上升状态,2008年至61.1%,之后开始下降。跨境资本流动的流量数据显示,1980年至2008年间,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及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均呈上升趋势,在2008年分别达到约1.48万亿美元、1.71万亿美元,2008年之后呈下降趋势。[19]从全球产业链建构角度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要经济体纷纷提出“本国优先”“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等政策,保护主义倾向日益明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又一次使世界出现分化,全球供应链断裂,各国争抢卫生应急物资,全球人员流动骤然停滞,世界各国和企业不得不对全球化下自身发展进行重新评估。这一全球健康卫生危机无疑进一步把全球推向“慢球化”的阶段。达特茅斯学院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A. Irwin)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慢球化”增加了动力,也增加了逆全球化加速的机会。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困局使得各国开始重新审视全球化并开始考虑如何降低外贸依存度。疫情导致的物资短缺也使得诸多国家相继颁布出口禁令。与此同时,世界贸易体系中出现的领导力真空也加速各国以邻为壑政策的形成。总体来说,世界经济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慢球化”驱使全球化中的“逆”行为可能会减缓甚至逆转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给世界经济带来数十年才能恢复的严重损害。[20]
“慢球化”确实令逆全球化发展的风险加大,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艰难恢复的世界经济又受到俄乌冲突的冲击,其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然而,慢球化并不是全球化的停滞不前甚至回流退势,而是全球经济发展遇到新冲突、新问题需要进行的调整阶段。各国应利用“慢球化”的缓冲时间,审慎对待并深入思考全球化,努力寻求使得全球化能够更健康发展的模式,推进“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发展。
中国引领再全球化发展
后疫情时期,全球化依然是主流趋势,只不过模式与功能的形式发生变化。近年来,“再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学术议题。然而,不少西方学者所讨论的“再全球化”仍然被西方霸权与零和思维所桎梏,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譬如加拿大学者保罗(T. V. Paul)认为,全球化在内部改革推进下,将迎来“再全球化”发展。有意义的全球治理改革能够提高全球化的国际适应性。尽管自由经济秩序竞争仍然会非常激烈,改革后的再全球化应该能够保证自由与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再全球化的建立不应再以安全为基础,而应基于道德与民族的亲近度。但是,中国、俄罗斯可能与这样的共同体产生强烈冲突,引发冷战式的竞争。[21]再譬如,奥地利学者安斯加·贝尔克(Ansgar Belke)等认为,全球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当前新的全球化要破除剩余的壁垒,而这些壁垒多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22]上述这种排他的、狭隘的“全球化思维”其内在逻辑与真正的全球化格格不入。
我们认为,“再全球化”,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模式升级与扩容效应。[23]“再全球化”并不是推倒全球化,而是翻转全球化,通过内部改革来实现对现有国际架构的升级,将由华尔街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格局转变为由新兴国家等大多数国家所主导的更普惠、更均衡、更包容的全球化。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数十年来,取得了舉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也正是中国融入世界、与外部世界联系日益密切的进程。[24]“再全球化”是中国嵌入式崛起,从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的一部分。近年来,全球发展环境与经贸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数字技术迅速普及,区域合作更加紧密,中国针对全球化“数字化”与“区域化”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制定了针对性强、符合实际的战略政策,在全球化的数字化与区域化的趋势中展现出显著优势。中国在政府施策、企业创新、消费市场拓展、数字基础技术与数字人才建设等方面均具备全球水平的数字竞争力。中国积极推进RCEP协定落实、CAI协定签署,同时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实际行动申请加入CPTPP和DEPA,是区域合作的坚定的支持者和践行者。
再全球化是包容的、是普惠的。再全球化打破了传统的全球化以“中心—外围”经济结构为基础的“二元格局”。随着新兴国家全面崛起,中国成为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全球化将更多处于边缘的经济体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与西方的思维不同,那种不给彼此空间的零和式的竞争往往难以带来长久的和谐,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逻辑中,万物和谐一家,方能实现天下大同。再全球化的过程,是打破由意识形态创造的阵营割据的过程,也是打破由政治制度差异造成的狭隘与偏执的过程,是中国将发展红利分享给世界的积极行为,是构建多元包容的共生网络。[25]欢迎他国搭便车既是维护自身利益,也是维护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将引领包容的、普惠的、新型的国际合作。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周边命运共同体”、“亞洲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均以中国哲学思想为底蕴,展现出中国推进“再全球化”方式的开放性、柔和性与务实性。
再全球化将塑造更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类似的突发性全球性危机,全球治理体系本应发挥关键性作用,促进各国合作,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治理体系却表现得无能低效。当前,全球“治理鸿沟”正逐渐加大。全球化发展面临新的经济、环境、安全问题,亟待通过国际社会的集体努力来解决,然而不少发达国家却缺乏真正合作的意愿或动力。全球治理的概念和方式都在危险边缘,一旦全球治理制度体系系统性崩溃,随之而来的治理危机即会出现。[26]面对当前复杂分化的世界格局,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组织或一套制度都不可能垄断全球治理的未来格局和形态。再全球化将促进更多全球化正面效应与影响的释放,让不同国家——不论实力强弱,不论贫穷富裕——都能够参与其中,共享全球化创造的红利,并为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共同努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1&ZD172)
注释
[1][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
[2]Cooley, A. and Nexon, D. H., "The Illiberal Tide", Foreign Affairs, March 26, 2021.
[3]Francis, F., "The War on Liberalism: Even before Vladimir Putin's Decision to Invade Ukraine, Liberal Values were Under Threat Around the World", Financial Times, March 5, 2022, p. 1.
[4]Laruelle, M., "Disillusioned with Democracy: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to Illiberalism", Institute Montaigne, October 22, 2021,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n/blog/disillusioned- democracy-conceptual-introduction-illiberalism, 2022-04-21.
[5]Klein, M. C. and Pettis, M., 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 How Rising Inequality Distorts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Pea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15-319.
[6]Niblett, R.,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 Foreign Policy, No.236, Spring 2020, p. 10.
[7]Posen, A. S.,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March 17, 2022.
[8]Slaughter, A. M., "The Seeds of Revolution", Foreign Policy, No.239, Winter 2021, p. 112.
[9]Slaughter, M. J. and McCormick, D. H., "Data Is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1.
[10]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21",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er2021_overview_en_0.pdf, 2022-04-13.
[11]Bjola, C. and Manor, I., "The Rise of Hybird Diplomacy: From Digital Adaptation to Digital Adop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8, Issue 2, March 2022.
[12][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疆域》,左玉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13]Nye, J. S. Jr., "The End of Cyber-Anarch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2.
[14]白洁、苏庆义:《美墨加协定:特征、影响及中国应对》,《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第123~138页。
[15]Wang Dong and Tu Xinquan, "China is Serious about Seeking CPTPP Partnership",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31, 2021.
[16]Petri, P. A. and Plummer, M. G., "East Asia Decoup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War, COVID-19, and East Asia's New Trade Blocs", Working paper from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une 2020.
[17]余淼杰:《關乎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重点和顺序的观点》,《金融论坛》,2021年第9期(总第309期),第5页。
[18]"Slowbalisation", The Economist, Vol.430, No.9127, January 2019, p. 9.
[19]数据来源:UNCTAD Statistics,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96740, 2022-04-25。
[20]Irwin, D. A., "The Pandemic Adds Momentum to the Deglobalization Trend",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pril 23, 2020,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pandemic-adds-momentum-deglobalization-trend, 2022-04-10.
[21]Paul, T. V.,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and Reglobalization: Adapting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7, No.5, September 2021, pp. 1599-1620.
[22]Belke, A. and Gros, D., "The Slowdown in Trade: End of the 'Globalisation Hype' and a Return to Normal?", Journal of Economics & Finance, Vol.45, No.2, April 2021, pp. 225-239.
[23]王栋、曹德军:《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24]王栋、曹德军:《“再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角色——以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为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7页。
[25]王栋、曹德军:《中国引领世界进入“再全球化”进程》,《人民论坛》,2017年第32期,第60~61页。
[26]Ikenberry, G. J., "Global Governance at Risk",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4.
责 编/张 晓
王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教育部)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冷战史、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中美关系。主要著作有《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Avoiding the "Thucydides Trap": U.S.-China Relations in Strategic Domain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