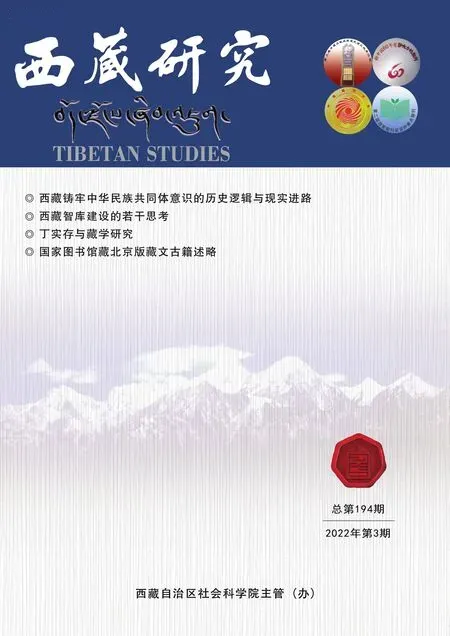喀且班钦释迦室利入藏弘法事迹考述
楞本先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41)
一、强调戒律传承,建立班钦律统
佛教认为,戒为无上菩提之根本。班钦入藏后,根据经典《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花鬘》讲授律部分,同时以极为严苛的戒律实践范世,逐渐形成了严持戒律、依戒修行的“班钦派”传承体系。
(一)班钦派戒律的创建
8世纪,吐蕃赞普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与寂护两位大师入藏,创建了桑耶寺。寂护大师为“七觉士”剃度,在西藏建立了僧伽制度,也开始了律学在西藏的传播。赞普赤祖德赞时期(815—838),吐蕃佛教逐渐兴盛,赞普敕令除“说一切有部”传承之外的戒律一概不得传入。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只记载了“说一切有部”法事规范文献(P.T.0930、P.T.0931)便是最有力的佐证(5)在佛陀在世期间,只有“说一切有部”存在,其余诸派皆为佛陀圆寂后形成。吐蕃时期的赞普和高僧或许认为在漫长的时间之流中,其他派系传承的戒律有被篡改和误读的可能,因此认为只有“说一切有部”戒律最为正统。。后来阿底峡尊者入藏传法,提倡戒律,重振佛教,但未曾弘扬戒律传承,大抵是因为阿底峡尊者为“大众部”高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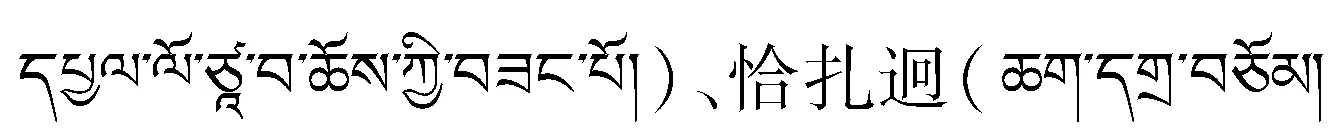
(二)“觉宕四支派”的形成

班钦戒律发展过程中四支派各自建寺,寺院所在地成为寺名,后又逐渐惯用于戒律传承之名。在四支派各自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主属寺院,授受班钦戒律,后来寺院名称逐渐用于四支派传承中,如却隆派、措钦派、且增派、根顿岗巴派、聪堆派、杰林派、贝康派、则派等。“虽然以上支派都自誉为绛朵二人初建首创,但是绛朵二人亲自修建,并以此直接分立的无疑为上述觉宕四支派”[13]。觉宕四支派的形成标志着班钦戒律在西藏的传承,而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受持班钦比丘戒,为班钦戒律在西藏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关于觉宕四支派的分离以及师承关系在哥廷根大学藏学博士约格·汉姆贝尔(Jörg Heimbel)的一篇文章中有专门探讨[14],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修订《释量论》,构建传统学科框架
班钦在藏弘法期间,除了在绰普译师的协助下宣讲显密经典外,还特别注重因明学的传承和教授。他与弟子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合作翻译修订的《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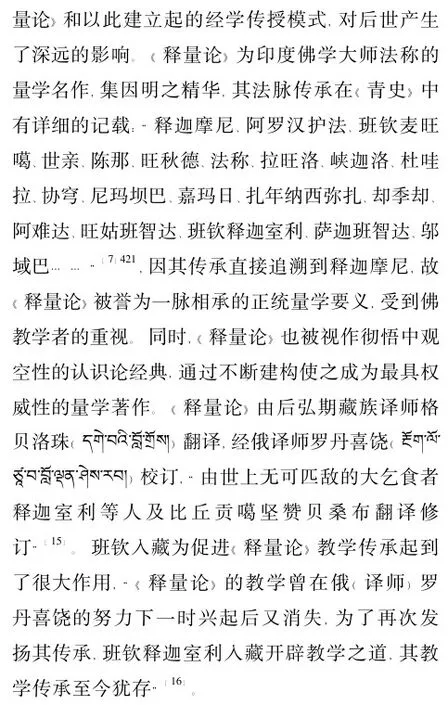
班钦在藏传法期间,吸引了众多的藏族僧侣前来学习,其中衣钵相传的“受教四弟子”有因明受教者萨迦班智达、戒律受教者绛曲贝与朵吉贝、秘法受教者绰普译师、密宗受教者结却桑[18]。不难看出,班钦把量学精要传授给了萨班,把秘决法“四不俗指令”传授给了绰普译师,把密宗系统传授给了确吉贝译师,把戒律传承之重任交付给了他的“觉宕派”。这些教法传承又通过经院的闻习讲授传给了藏传佛教诸教派的高僧,形成了后弘期独具特色的传承体系。
萨迦班智达在其求法生涯中广学博采,但对当时卷帙浩繁的藏文典籍未能作出有效的分别门类的学科体系,只是笼统地将所有的经典和译著都收录于《大藏经》中。这种学科混杂的情况不利于佛法的传承发展,亟需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班钦及其九位随从班智达的入藏,为当时的藏族学者提供了学习的良机。据班钦和萨班的藏文传记记载,萨班跟随班钦学习了《释量论》为主的经典,又跟随班钦的弟子们学习了小五明学科经典。史料记载:“班钦到卫地传法,法王(萨班)敦请班智达桑伽室利至萨迦寺,在寺院驻锡两年期间,精通学习了梵语、因明、辞藻、韵律、戏剧等经典”[19],由此可知,萨班在班钦及其随从班智达的引介下,系统地学习了印度“五明”学科的所有内容。五明学科的分类是典型的印度传统学科分类方法,但萨班终其一生从未涉足印度求法,对印度高僧的直接接触当属拜班钦为师。因此,不难判断出,萨班拜班钦为师的经历,对其后期建立藏族传统五明学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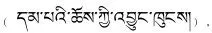
三、纠谬佛灭年代,传授“班钦纪年”
西藏较为权威的历算著作《佛历年鉴及五明论略述》中,罗列了佛陀纪年的萨迦派纪年、噶当派纪年、喀且班钦释迦室利派纪年、时轮派纪年等四种极具影响力的纪年法,对释迦牟尼的纪年存在较大偏差(见表1)。

表1:诸派的佛陀年谱表[22]7
由上表可知,诸派佛陀年谱偏差的焦点在佛灭纪年。关于佛灭纪年出现如此大的偏差的原因,藏文典籍中有较为完整的记载:“印度大众部学者,在计算佛灭纪年时,以为摩揭陀的释迦摩尼佛像是阿阇梨托尊珠杰与德协达布建造,并把这一年代与用檀香浆供奉时初现天然佛像的时间相混淆。”[22]10从中可见大众部对佛灭年代与佛诞年代混淆,导致了后来的纪年问题,而在后期的修订过程中顺从信徒的宗教情感又保留了较为久远的纪年法[23]20。
针对诸派纪年法的不同,“第四绕迥的火兔年(1207)仲春初五,喀且班钦释迦室利在索那唐波且寺计算:昴宿月之上弦,初八凌晨降临,月亮落山之时,佛陀终生涅槃,至此已有一千,七百五十之年,二月半之有余,再加五日为今日。自后余有三千二百四十九年,九月加上十日,期间佛教存世”[23]16,即佛陀涅槃年代为公元前543年,自此西藏出现了独具特色的班钦派纪年法。随后,“喀且班钦释迦室利于铁马年(1210)在萨迦寺夏令安居之时计算,至涅槃已有一千七百五十三年,今后佛法会继续兴盛三千二百四十六年”[23]18。这一纪年法与之前的西藏传统纪年有很大不同,更接近现代学者对于佛陀降诞、涅槃的纪年认知。班钦纪年被大多数佛教学者认同,芒堆鲁珠嘉措说:“诸种佛灭计算传统与喀且班钦派的佛灭纪年有很大偏差,班钦派纪年法不但被萨迦班智达所讲授,并且很多印度和尼泊尔班智达也持同样的观点。”[24]10由此可知,班钦派纪年法被视为较准确的佛陀年谱而被认可。同时,“与此派(班钦派)一样,印度、缅甸、锡金、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当今佛教国家也接受这种纪年法”[23]17,可见南传佛教国家普遍接受这种纪年法,柬埔寨和缅甸更是将佛灭日定为新年,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近代著名学者根敦群培更在其《佛国智游漫记·斯里兰卡篇》中认为班钦释迦室利是依上座部纪年法计算佛灭年代,斯里兰卡也依此计算,并用这种纪年法梳理了相关年代[24]36。
四、助力绰普译师,建造弥勒佛像
在绰普寺建造巨型弥勒佛像是绰普译师的主要功绩之一。据《绰普译师自传》记载,译师对弥勒佛有着坚定的信仰,隆泽哇大师为译师讲述了他能够实现的三大壮举,其中就包括建造巨型弥勒佛像[4]18。当绰普译师在尼泊尔北部拜见班钦时,班钦询问道:“建造巨型弥勒佛像的是你叔叔还是你?答道:是本人。又道:你如此年轻能否胜任翻译佛经之重任,生起建造巨型佛像的意念也绝非易事。”[4]52班钦通过考问,对译师的博学极为赞赏,此事也间接促成了班钦的入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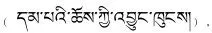
结 语
13世纪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重要节点,超戒寺末代堪布班钦入藏传法,讲授《律部》,强调戒律、建立“班钦派律统”,后通过藏传佛教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高僧的授受传承至今,不仅完成了藏传佛教戒律系统化,同时为藏传佛教的正本清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藏弘法期间,班钦培养了萨迦班智达和绰普译师等高僧,与他们共同合作修订了《释量论》并发扬其教学传承,实现了藏传因明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院化教育;纠谬了传统佛灭纪年法,首次引介并普及较为科学的班钦派佛灭纪年法;协助绰普译师建造了独一无二的巨型弥勒佛,为藏传佛教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喀且班钦释迦室利的佛教思想依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在佛学界有着很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