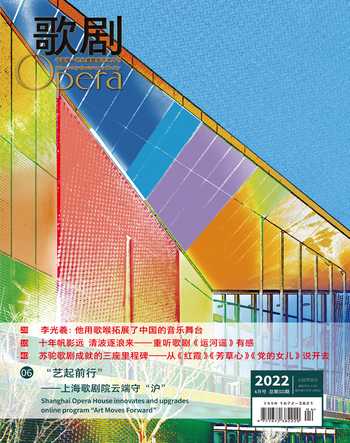论西洋歌剧的民族性(13):回顾与借鉴(上)
黄奇石





(接上期)
我们从西洋歌剧的过去,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歌剧现在的路应怎样走?歌剧的未来又将是什么?
毛主席是唯物辩证法大师,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曾说过这样的话:看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实,就知道他的未来。伟人此言亦适用于对歌剧的观察。
下面分别做简要的论述,作为全篇的结束语。
一、民族性是西洋歌剧的共性
关于这个道理,我们在全篇开始的说明部分,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若干欧、俄经典文学名家的论述,已做了相当充分的阐明。当我们对于西洋歌剧三百多年的发展史(即从16世纪末到整个19世纪)进行回顾之后,便可以从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一)意大利以“美声”取胜
欧洲戏剧产生很早,其源头便是古希腊悲剧。作为歌剧诞生地的意大利,在文艺复兴之后产生的歌剧,其渊源也是古希腊悲剧。歌剧最早的起因是为希腊悲剧的人物台词伴奏的音乐,加上希腊悲剧本身就有歌队的合唱,由此逐渐发展成为有朗诵调、咏叹调与合唱组成的新的音乐戏剧品种——歌剧(西欧教堂最早的唱诗班实际上也由此而来)。
意大利歌劇从雏形到成型,都是以声乐为主、器乐为辅的(早期乐队很简单)。歌剧中的“美声”便是意大利人独特的创造,是意大利歌剧最突出的民族性特征。如果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歌剧的诞生,更不会有意大利的民族歌剧的形成与发展。作曲家永远都只能成为希腊悲剧伴奏音乐的作者,音乐只能是其附属品。
当然,这只是就音乐形式的民族性而言,还有思想内容的民族性也同样重要。歌剧也必须从表现古希腊神话中解脱出来,转为表现意大利民族的生活与斗争(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
这一点,几乎整个欧洲歌剧都无一例外。
(二)德意志歌剧对意式歌剧进行革新,目标是求得器乐与声乐、音乐与戏剧的平衡
意大利歌剧诞生之后,在上百年间风靡整个欧洲。欧洲各国作曲家或顶礼膜拜,或模仿学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歌剧。德、奥、法都是这样,连东边的俄罗斯也是如此。
德国打破意大利歌剧垄断局面的是格鲁克,后继者瓦格纳更进一步“革新”歌剧,创造“乐剧”,几乎夺去了意大利歌剧的第一把交椅。与德国同一民族文化的奥地利则因莫扎特的天才成为西洋歌剧向一南一北拓展的关键性枢纽。
莫扎特以其独创性的“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引发了意大利“喜歌剧”的产生与发展(从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到威尔第的《法尔斯塔夫》);他又以“神魔剧”(《魔笛》)开启了德意志民族歌剧的大发展(以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四部系列为代表)。
德、奥歌剧不同于意大利歌剧的民族性特征,在于改变意大利歌剧偏声乐而不顾其他的不足,加大器乐在歌剧中的地位与作用,寻找音乐与戏剧的平衡。
瓦格纳的“乐剧”是其集大成者。他奠定了现代歌剧演出从乐队编制到剧场配置安排(包括乐队在“乐池”演奏、演出时“灯暗”等)的基本模式。这使瓦格纳的“乐剧”一时也风靡整个欧洲,成为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年青一代作曲家的歌剧“偶像”。声乐与器乐、戏剧性与音乐性较为完美的结合,使瓦格纳的“乐剧”一直影响到20世纪至今的现代歌剧的发展。
当然,他的“乐剧”也不是完美的,旋律性不足是其短处,故有论者评其“曲不好听”“歌不好唱”。这种不足与弱点,又为现代歌剧的发展留下了空间。
(三)法兰西歌剧将“歌”“舞”“乐”三者融为一体
法兰西歌剧起步较晚。文艺复兴后,浪漫的法国人尤其是追求奢华的贵族们,关注的是宫廷兴起的华美的芭蕾舞。启蒙运动兴起后,法国戏剧中首先引起新兴资产阶级兴趣的也不是浪漫主义的歌剧,而是古典主义的话剧,例如以莫里哀作品为代表的喜剧。
一直到17世纪70年代,“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与中国的康熙皇帝同时代,二人曾有“国书”往来),才有个别的作曲家提出“创造法国自己的歌剧”,受到皇帝的赞许与支持。在这之前,来法国演出的全是意大利人炫技式的“正歌剧”。德国的革新歌剧在法国只有到格鲁克手里才有一席之地,并在“对台戏”较量中让意式“正歌剧”败北。
由于起步较晚、人才准备不足,法兰西民族“自己的歌剧”从产生到发展也走了几十年曲折的路:草创初期被称为“三剑客”(康贝尔、吕利和拉莫)中的吕利等几位还是意大利来的移民,所创作的大都是意式歌剧的仿品,被称为“讲法语的意大利歌剧”。真正奠定法式大歌剧模式的是被称为“三杰”的梅耶贝尔、古诺和比才(梅耶贝尔还是旅法德籍犹太人)。
他们的几部杰作—梅耶贝尔的《新教徒》《预言者以古诺的《浮士德》《罗密欧与朱丽叶》、比才的《卡门》才真正确立了法国歌剧与意、德奥歌剧三足鼎立的地位。
在艺术形式上,法国歌剧“三杰”共同的模式与民族性特征就是“歌、舞、乐”融为一体,以表现法国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内容。其中华美的芭蕾场面与宏大的合唱、庞大的乐队以及装饰豪华的布景,构成了追求时尚的法国贵族与资产阶级所喜爱的华丽风格。这实际上也极大地影响了意、德如威尔第的《茶花女》《阿伊达》等意式大歌剧与瓦格纳气势恢宏的“乐剧”。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歌剧,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如果不创造新的、与别人不同的东西,总是盲目地模仿与学步,就很难在世界歌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很难自立于世界歌剧之林。
与一切艺术上的“奴隶主义”一样,歌剧中的“奴隶主义”也是最没出息的。所谓“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就是这个道理。
二、民族性也是世界歌剧的共性
马克思提倡过“世界文学”。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打开了世界市场,一切文学都成为全人类共有、共享的精神产品。
实际上,“世界文学”仍然是由各民族的文学组成的,并没有一种与此不同的、抽象的“世界文学”。抽象的“世界文学”其实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性也是世界文学的共性。
歌剧也是如此。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从西欧扩展开去,再简略观察一下俄罗斯以及美国与亚洲日、朝、韩等国家的歌剧、音乐剧的发展情况。
(一)俄罗斯是民族主义歌剧的先锋
和西欧歌剧比起来,俄罗斯歌剧起步更晚,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产生。格林卡(1804~1857)——他被称为“俄罗斯歌剧之父”——的第一部歌剧《伊凡·苏萨宁》首演于1836年。该剧可谓开了俄罗斯民族歌剧之先河,其奠基性地位有如中国的《白毛女。格林卡的第二部歌剧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1842年首演)。
在格林卡之前,俄罗斯作曲家对意大利歌剧可谓是“亦步亦趋”,所创作的全是拙劣的仿品,并未产生出真正的属于俄罗斯自己的民族歌剧。这种盲目模仿的局面到格林卡手里才被彻底打破。格林卡及以他的学生巴拉基列夫为首的五人“强力集团”为俄罗斯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民族民间音乐的歌剧新风。
随后,以“强力集团”为代表的一系列民族歌剧作品便相继问世。到了柴可夫斯基(1840~1893)时代,俄罗斯的民族歌剧才登上世界歌剧的巅峰,其代表作有《叶甫盖尼·奥涅金》(1879年首演)、《黑桃皇后》(1890年首演)等。
1.“强力集团”主要代表作
“强力集团”之一的鲍罗丁(1833~1887)写出了名剧《伊戈尔王》(首演于1890年,作曲家已去世):
“强力集团”之二的居伊(1835~1918)的《威廉·拉特克利夫》(1869年首演)、《安哲罗》(1876年首演);
“强力集团”之三的穆索尔斯基(1839~1881)的《鲍里斯·戈杜诺夫》(1874年首演);
“强力集团”之四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8)的《隐城基捷日的故事》(1907年首演《金鸡》(1909年首演)。
2.“强力集团”之外若干位的名作:
阿尔切莫夫斯基(1813~1873)的《多瑙河彼岸的萨波罗什人》(1863年首演);
达尔戈梅斯基(1813~1869)的《水仙女》(1856年首演)、《石客》(1872年首演);
阿连斯基(1861~1906)的《伏尔加河之梦》(首演于1890年)。
整个19世纪,建立在俄罗斯农奴制基础之上的沙皇专制政权激起人民强烈的反抗。以布加乔夫为首的农奴起义和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英勇斗争,尽管都遭到沙皇的残酷镇压,却极大地打击了以沙皇为代表的封建农奴主阶级,唤醒俄罗斯人民起来推翻沙皇的残暴统治。这种连续不断的反抗斗争,使俄罗斯沙皇的封建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同时,俄罗斯民族历来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的,1840年拿破仑军队的入侵更使民族的爱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进一步冲击沙皇专制统治的政治基础,使之一步步走向崩溃。
俄罗斯歌剧的民族性特征甚至要比西欧意、德奥、法更加突出与鲜明。从思想内容的层面上看,“爱国”与“民主”几乎是俄罗斯歌剧的两大主调,也是推动其迅速成熟并走向繁荣的原动力。从音乐形式的层面上看,俄罗斯一代代作曲家无不把民歌和民间音乐作为自己创作的最主要的源泉。从格林卡到受其影响的“强力集团”,再到将俄罗斯民族歌剧推向世界歌剧巅峰的一代音乐巨匠柴可夫斯基,在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一脉相承的。
和一切事物一样,俄罗斯民族歌剧之花也有一个从萌芽、生长、成熟,到繁荣、衰落的过程。它在一百年之内迅速成长起来,并走向繁荣与成熟。在柴可夫斯基之后,它也很快走向衰落。
19世纪未,俄罗斯古典歌剧衰落的命运,与西洋古典歌剧衰落的命运,几乎是同步的。略有不同的是,俄罗斯古典歌剧盛开得较晚,调谢得却较早。这是时代使然,非人意之可强求。然而,它毕竟在世界歌剧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之所以能如此,主要也在于它没有像早先那样一味的模仿西洋歌剧,而是走自己的路,因而有着别人所没有的鲜明的民族特色。
除了俄罗斯歌剧,还有东欧的民族歌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国战败、奥匈帝国解体,东欧的民族独立浪潮十分高涨,东欧的民族主义文学成为主流。东欧的民族歌剧也应运而生,最具代表性的是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名剧《被出賣的新嫁娘》。
东欧民族歌剧在西欧、俄罗斯歌剧之外又别开一枝,也是以鲜明的民族内容与民族形式取胜的。
(二)美国音乐剧是美国人的创造
风靡世界的音乐剧是世界歌剧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是先后由英国人、美国人创造出来的,并在美国人手里走向繁荣。
美国人最早从西欧移民而来,大多继承的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尤其是“英伦三岛”的“撒克逊文化”的传统,那本是他们文化艺术的根。
然而,这些移民的后裔同时也继承了先辈的另一个更为可贵的传统,那就是开拓性与创造性。他们在新的大陆、新的时代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崭新的音乐戏剧,那就是让世人羡慕的美国音乐剧。
正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其人员构成就不会是单一民族的。除了白种人之外,还有有色人种。有色人种中则以黑人为主体。他们都是一二百年前西方殖民者贩卖黑奴的年代里从非洲运过来的,大都是“黑奴”的后裔。
这是美国音乐剧的民族性基础。从这一基础上产生的音乐剧,其民族性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内容上,大都表现美国各民族现实的生活与斗争;其二,形式上,吸收西洋歌剧中现代“轻歌剧”成分,融合非洲原始的黑人音乐舞蹈,构成独具风情的、更加时尚的“歌、舞、乐”融为一体的音乐戏剧新品种—音乐剧。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与载歌载舞的形式,使之成为20世纪最受世界各国观众欢迎的现代音乐戏剧,风头甚至盖过了已走向衰落的西洋古典歌剧。
在美国音乐剧产生的一百多年里,其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早期音乐剧更注重观赏性与商业性,如《出水芙蓉》等,避免不了“大腿舞”之类的桥段以吸引观众的目光。同时,也有商业性与思想性都兼顾的作品,如《演艺船》,具有反种族歧视的内容。后来,音乐剧名剧渐渐削弱甚至剔除了“色情”的东西,更多地表现严肃的思想内容,如著名的《音乐之声》,表现的是女主人公在“二战”时从北美到西欧的遭遇,她目睹法西斯暴行并与之抗争。再后来,表现当代现实生活的音乐剧更多了起来,如《西区故事》,虽套用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节,表现的却是现代美国黑人区青年的生活现状与情感纠葛。经典音乐剧《猫》,用童话手法表现现实生活。那个乱七八糟的“猫窝”,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
同时,音乐剧作者们的目光还进一步扩大到美国社会现实之外,如《艾维塔》,写的正是著名的贝隆夫人的故事,表现她如何从乡间小酒吧的歌舞女成为阿根廷的第一夫人及女总统,其临终前的一首《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不知感动了多少观众。
随着美国音乐剧在全世界的走红,吸引了欧美大批音乐剧作者加入创作的行列,其中以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文化区的成绩最为显著。他们的加盟进一步把音乐剧的创作推向新的阶段:名著改编的几部音乐剧名作无论从思想内容上或艺术形式上,都大大地拓展了音樂剧的深度与广度,早些的如《窈窕淑女》,晚些的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演出都轰动一时。
和古今中外一切艺术品种一样,从萌生、成长到繁荣,欧美音乐剧经历了一二百年的发展历程,到世纪之末也已走向成熟。一般来说,成熟既意味着硕果累累,也预示着它将走向程式化,开始进入衰落期。
进入新世纪之后,音乐剧似乎有点后劲不继,至少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风靡世界的风头了。有一种感觉与判断正在显现:音乐剧随着美国称霸世界而兴起,它也必将随着美国的衰落而衰落。
美国音乐剧还能走多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么,与中国歌剧几乎在20世纪初叶同时诞生的美国音乐剧又能为我们歌剧界提供什么启示呢?
正是因为美国音乐剧摈弃了西洋古典歌剧的旧传统与旧模式,坚持走自己的路,吸收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民间的音乐与舞蹈,才能独树一帜,创造出崭新的现代音乐戏剧新品种,为世界各国广大观众所倾倒,也为世界特别是中国歌剧界所钦羡。
早就有中国的歌剧理论家公开喊出:“音乐剧,我为你疯狂!”也有作曲家大声疾呼:“音乐剧是中国歌剧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很容易理解:看到别人成功了,自己也想成功,最好是一剧成功、名闻天下。
于是,一时间,中国音乐剧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几乎达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任何一出戏,都想冠上“音乐剧”的金字招牌:明明是“花灯戏”,非称为“花灯音乐剧”不可;明明是话剧,非得称为“话剧音乐剧”。于是,“舞蹈音乐剧”“黄梅戏音乐剧”……纷纷出笼,令人眼花缭乱。几十出、几百出这类“音乐剧”出来了,迄今少有成功者。这把“为音乐剧疯狂”的理论家差点给气“疯狂”了,逐一加以痛贬:“音乐剧十病”!
其实,中国音乐剧的不成功,其“病”不在“枝节”上,而在“根本”上,仍然是犯了“盲目崇洋”的老毛病,也就是说:美国人走自己的路,中国人想要走美国人的路。自以为是“捷径”,实则是“误区”。
可以说,中国歌剧界并没有真正悟到美国音乐剧的真谛,从而陷入认识与实践的双重误区。早有美国音乐剧某权威(曾来中国导演过音乐剧《鹰》的那位名导演)就很恳切地提醒过:“你们中国人漂洋过海,到处寻找音乐剧。其实,《白毛女》就是中国最伟大的音乐剧!”但是,某些“盲目崇洋”的人总有一种很没出息的偏见:“月亮还是外国的圆。”他们哪瞧得上《白毛女》这“士货”?眼里盯着的全是“洋货”。
这个问题,留到后面谈及中国歌剧的成败得失时再谈。
下面补添“美国音乐剧小史”(以美国为主,也兼及欧洲),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1.萌发期:
美国并不是音乐剧的发源地,发源地在18世纪20年代的英国,重镇在伦敦西区。1728年,史上第一部音乐剧(又称“民间歌剧”)诞生。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光,至19世纪中叶,1866年,美国第一部音乐剧《黑魔鬼》才成功首演,宣告美国音乐剧这朵艺术新花产生。
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生长培植,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美国音乐剧才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一系列佳作的出现,使纽约百老汇成为与伦敦西区相匹敌的欧美两大音乐剧演出重镇。
二者的创作者与剧月演出往来频繁、互相交流(因此,谈美国音乐剧,几乎无法与英国人的创作截然分开,尤其是音乐剧的早、中期)。
2.成长期: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美国音乐剧的成长期,产生了一批具有创新性的作品。
(1)《演艺船》(杰诺米·科恩作曲,奥斯卡·哈默斯坦的脚本。1927年首演,标志着百老汇音乐剧的诞生):
“演艺船”是在密西西比河上跑码头的一艘游轮,实际上是活动的演出舞台。剧情故事是白人船长的女儿爱上了黑人歌手,把美国乡土故事与黑人歌舞结合起来。难得的是该剧具有鲜明的反种族主义色彩。剧中名歌《老人河》(黑人著名歌手罗伯逊演唱,苍凉、浑厚与低沉),传遍世界各地。该剧开创了音乐剧黑人题材的先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另一黑人题材的音乐剧《波吉与贝丝》。
(2)《波吉与贝丝》(格什温作曲,1935年首演):该剧表现20世纪20年代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黑人区(鲇鱼街)贫苦黑人的生活,写他们的爱恨情仇。剧中人物除一位白人律师之外,全都是黑人。波吉与贝丝,一个是乞丐,一个是美女。二人患难与共、真心相爱。又因贝丝曾沦为流氓头子的情妇而被人骂为“荡妇”,该剧名又译为《乞丐与荡妇》。该剧艺术上的成就在于其创新性,除了格什温出色地将黑人爵士音乐运用于剧情之外,还在于突出黑人舞蹈在音乐剧中的作用和地位,使之不再只是伴舞式的陪衬。
(3)《俄克拉荷马!》(1943年首演):
该剧以美国西南部俄克拉荷马垦荒为题材,艺术上受欧洲轻歌舞剧与爵士乐的影响(1955年拍成电影并获奥斯卡奖)。该剧在舞台展现上,有论者认为具有“里程碑式的典范意义”,创造性地运用民族特征鲜明的芭蕾舞,不再照搬传统的踢踏舞之类。其实,只要用得恰当,包括踢踏舞在内的各种拉丁舞也自有其民族特色,不可一概否定,关键是从剧情与人物出发。
3.繁荣期:
“二战”之后的五六十年代是美国音乐剧的繁荣期,产生了一批经典性作品。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更多地反映现实的生活与斗争,形式上也更加丰富多彩。
(1)《窈窕淑女》(据萧伯纳剧作改编,1956年纽约首演,1964年拍成电影并获奥斯卡奖);
(2)《西区故事》(1957年纽约首演,1961年拍成电影并获奥斯卡奖);
(3)《音乐之声》(二战题材、反法西斯作品,1959年百老汇首演,1960年夺得“托尼奖”五项大奖);
(4)《屋顶上的小提琴手》(该剧反映沙俄时代犹太人遭迫害的命运,1964年纽约首演,1971年拍成电影并获奥斯卡奖);
(5)《安妮,拿起你的枪》(艾文·伯林作曲,1964年首演);
(6)《长发》(越战题材,反战内容。艺术上追求新潮前卫,具有强烈的反叛性。剧中舞蹈多采用摇摆舞,甚至有脱衣舞的场面,更有不少年轻人的脏话,反映“垮掉的一代”一嬉皮士及“性解放”盛行的西方时代风尚)。
4.成熟期:
20世纪的70年代到90年代,可视为音乐剧的成熟期,出现了以天才作曲家韦伯与勋伯格、鲍伯利为代表的音乐剧大师。他们的代表作便是音乐剧成熟期的“四大名剧”——《猫》《剧院魅影》《悲惨世界》《西贡小姐》。
(1)《万世巨星—耶稣基督》(韦伯作曲,1971年首演):该剧取材圣经故事,是古典史诗与现代音乐(摇滚乐)的结合,歌曲通俗易唱,并引入电声,极富现代感,为韦伯音乐剧“四大名剧”之一;
(2)《艾维塔》(韦伯作曲,1976年首演):贝隆夫人的故事,韦伯音乐剧“四大名剧”之二;
(3)《悲惨世界》(据雨果同名小说改编,法国克劳德、勋伯格、鲍伯利作曲。1980年首演);
(4)《猫》(1981年首演于百老汇,韦伯作曲):该剧据英国艾略特童话诗改编,为韦伯音乐剧“四大名剧”之三;
(5)《刷院魅影》(1986年首演于百老汇):为韦伯音乐剧“四大名剧”之四;
(6)《西贡小姐》(勋伯格、鲍伯利作曲,1989年首演于伦敦西区,1991年再演于纽约百老汇,轰动一时,为百老汇经典音乐剧之一):该剧虽是越战题材,并无反战意识,实为普契尼《蝴蝶夫人》的现代翻版,也可视为花样翻新的仿品。该剧表现的是东方女子(越南妓女)为西方入侵者(美国大兵)“始乱终弃”后又甘心为其殉情的老故事。正因为其思想内容的不足取,该剧在“四大名剧”中成为口碑最差的一部,至少在中国是如此。观众难以接受剧中名为“爱情”实为欺骗的骗局。
(三)日本歌剧、音乐剧的得失:
与美国不同,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大和民族是善于学习的民族,古代是学大唐,派了大批“遣唐使”;近代明治维新之后转学西方。他们学而能化,并且保留着自己民族的特点(服饰、饮食、风俗等)。
奇怪的是,在歌剧这个领域,日本人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先是对西方古典歌剧“顶礼膜拜”,后也是对美国音乐剧“亦步亦趋”。更早的不说,仅从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中,日本尽管也熟知世界歌剧发展的动向,却始终也没有创作出多少属于日本自己的民族歌剧。美国音乐剧风靡全球之后,日本人又热衷于引进美式音乐剧。为了能常年演出当时炙手可热的美国音乐剧名作《猫》,日本居然盖了一座仿“猫窝”设计的剧场。
这样痴迷追随西洋、美国的歌剧音乐剧的结果是,忙了几十年,自己的东西能拿出来的很少。为中国观众所熟悉是“四季剧团”的一两个剧目: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部歌剧《夕鹤》;1990年代,又有一出名叫《李香兰》的音乐剧问世(中国民族歌剧的“元老輩”贺敬之、田川同志访日时都看过这个戏,均给予好评。该剧也到中国演出过)。到了20世纪末,日本创作了另一出音乐剧,名叫《想变成人的猫》。该剧从剧本构思到舞台展现,基本上还是从美国音乐剧《猫》生发出来的,严格来说还算不上是日本自己的东西。(记得中戏的音乐剧培训班还引进过,那已是等而下之的“二手货”了。)这种反常的状况,自然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不满。世纪之交,日本著名的导演、戏剧权威浅利庆太在自己的文章中就多次对此加以抨击。他很羡慕中国不仅早有自己的民族歌剧,近年来也创作了不少音乐剧。反观日本,20多年来,不仅没有自己出色的歌剧,也没有自己优秀的音乐剧(国内出版过他的一本评论集。因此书不在手边,无法引用原文,但大意是没错的)。
浅利庆太是日本音乐戏剧界大名鼎鼎的权威人物。他1953年创建了“四季剧团”。该团几乎所有的剧目都是他一手策划和导演的。1980年代后期,他改编创作了著名音乐剧《李香兰》,轰动一时,成为该团的经典剧目,久演不衰。
应该说,浅利庆太作为日本音乐剧权威,他对日本歌剧、音乐剧现状的不满和批评是严苛的,但也带有几分无奈:一方面作为清醒的艺术家,他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引进不能代替创作,引进再多也不是自己的。另一方面,作为剧团的创建人,他又必须维持剧团的生存与几百号人的生计,单靠原创剧目是远远不够的(连成熟的德国歌剧市场也需以引进百老汇新剧为主)。四季剧团建“猫”剧场并不完全是“纯艺术”的动机,票房收入的考虑应占了更多(当时《猫》一剧风靡欧美,票房达到数亿之巨)
尽管浅利庆太的感叹和批评是严苛的,也是有根据的,但这只是一方面,并不代表日本歌剧、音乐剧的全部;另一方面,还应看到日本近百年歌剧、音乐剧也有所作为与发展,即有追求、有成果的方面。
为看清这一方面,有必要回顾一下日本古典与现代音乐戏剧的产生、演变与发展历史。
日本古典音乐戏剧的历史源远流长,它的“咒能”源自原始祭神的巫舞,据说产生于中国的南北朝时期。14世纪产生“能剧”,为歌、舞、乐结合的歌舞剧。除了“能剧”,后又有“狂言”(短小的即兴笑剧,以滑稽诙谐取乐,常在“能剧”幕间插演。这与意大利早期喜歌剧的产生类似)。16世纪末、17世纪初又产生“歌舞伎”(出自巫女的狂舞,配上民间小调,歌舞与科白结合,为德川时代主要剧种)。
近现代以来,日本明治维新后转向西方获得成功。日本近现代的音乐戏剧之树花开两枝:一枝是对传统古典的“能剧”“歌舞伎”的坚守,另一枝是大量学习、引进西洋的话剧、歌剧与音乐剧。又由于他们的剧团几乎没有得到国家的资助(只有近代武士阶层一度保护过“能乐”。这一点与西欧歌剧早期主要靠宫廷与贵族扶植很不相同),剧团的运作完全靠自负盈亏,不得不面对相当严酷的商业演出市场。票房是第一位的,有观众才有票房,有票房才能生存。这与中国的中直与省市多数公有的院团很不相同。因此,必须从这一经济基础上观察日本歌剧、音乐剧的商业气息浓厚这个特点。
19世纪后期,西洋歌剧传入日本。20世纪以来,日本先后成立了宝冢歌剧团、四季剧团、东宝剧团,号称“三大剧团”(“四大剧团”的提法则包括了更后期成立的“新干线剧团”)。
1.宝冢歌剧团(1911年成立,源自兵库县宝冢市而得名):
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特色是由约400位清一色的未婚女子组成演出团(均为宝冢音乐学院毕业生),内分四个演出队:花、月、雪、星(后又加了“宇”队),极富日本民族特色,唯美、浪漫,享有世界声誉。
宝冢歌剧团代表性剧目有:
《梦巴黎》(1927年);《放浪记》(1961年);
《凡尔赛玫瑰》(1974年,极其轰动,剧团为之立塑像以作永久纪念);
《荷西与卡门》(1999年“宇”队版,风情独具、舞技一流);
《伊丽莎白:爱與死的圆舞曲》(经典改编);《新源氏物语》(古典改编),等等。
引进的百老汇经曲剧目有《西区故事》《飘》《剧院魅影》(2004年“宇”队版)等。
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将动漫故事改编为音乐剧,如《圣斗士星矢》、《美少女战士》(来华演过)、《犬夜叉》、《网球王子以《妖精的尾巴》《黑执事》(来华演过)、《火影忍者》等等,也算是被商业演出逼出来的新招数。
2.四季剧团:
该团原创歌剧作品不算多,最具盛名的有歌剧《夕鹤》与音乐剧《李香兰》(日本歌剧、音乐剧界限较为模糊,如《李香兰》也称歌剧)。
四季剧团主要引进欧美歌剧、音乐剧,特别是百老汇音乐剧新作,如歌剧《蝴蝶夫人》音乐剧名剧《猫》《万世巨星一耶稣基督》,还有改编自迪士尼童话故事的音乐剧《阿拉丁》等。
1964年四季剧团开始尝试家庭音乐剧的创演。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里,这类作品已达30多部。
该团年演出场次超过2000场,观众已达300万人,成为亚洲最大、最负盛名的音乐剧团,使东京也成为与伦敦西区、纽约百老汇齐名的具有国际声誉的音乐剧重镇。
下面着重介绍四季剧团原创的三部歌剧、音乐剧:《夕鹤》《李香兰》与《想变成人的猫》(三剧均先后来华演出过)——
(1)《夕鹤》(独慕歌剧,木下顺二据他的同名话剧改编,团伊玖磨作曲,1952年首演)
这是日本流传干年的民间故事。相传一个名叫“与平”的青年农民,救了一只受箭伤的仙鹤。仙鹤为了报恩,也喜爱小伙子的朴实可靠,便变成一位美丽的姑娘,名叫“阿通”。二人结为夫妻,过着恩爱而贫穷的小日子。
阿通为了让与平生活过得好一些,便悄悄一人躲进织布机的房间,又变回仙鹤,忍痛拔下身上的羽毛,织成“干羽锦”,光彩夺目。阿通借此卖得了很多的钱。不幸的是,不知底细的与平受到奸商的蛊惑,想赚更多钱,逼迫阿通再织更多的“千羽锦”,以实现当“富翁”的梦想。阿通为了不伤他的心,无奈之下答应再织两匹“千羽锦”,但要求与平不能进机房偷看。然而,与平受贪婪与好奇心的驱使,竟违背诺言,私下偷窥到阿通拔下身上羽毛织锦的情景。阿通发现后,万分伤心,含泪复化鹤飞去……
该剧故事与中国民间传说《白蛇传》《天仙配》《牛郎织女》类似,所不同的是该剧造成爱情悲剧的主要不是外力而是内因,是男主人公与平的贪婪造成阿通美好生活愿望的破灭。这曲令人唏嘘不已的爱情悲歌也是对贪婪的灵魂与拜金社会的揭露与控诉。
这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日本民歌的风味。音乐借鉴西洋歌剧的艺术手法,又有本民族的民族特点。它产生得较早,成为日本民族歌剧的示范性佳作。《夕鹤》曾于1979年来华演出,邓颖超亲临观看演出。此次访华演出颇获好评,反响很大。中国观众终于欣赏到过去难得一见的日本歌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2)《李香兰》(浅利庆太据《李香兰自传》改编,1991年首演)
浅利庆太创作此剧的缘由是日本年轻一代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无知使其深感震惊,想借李香兰传奇一生来表达反对战争、祈求和平及中日世代友好的心愿。
《李香兰》从日本投降后,伪满洲国头牌影星李香兰被送上军事法庭讲起。检察官要求判她死刑。李香兰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是日本人!真名‘山口淑子’。”
舞台暗转,故事回到李香兰的童年。父亲临终托孤,将年幼的山口淑子送给他的好友、中国的李将军当“养女”,也寄托他希望中日世代友好的心愿。李将军为她取名“李香兰”。这一天,李将军的女儿爱莲和未婚夫玉林,还有小香兰视为兄长的伪满“建国大学”的日本大学生彬本都来祝贺。一家人欢聚一堂,四个少男少女尤其高兴,共同为中日世代友好干杯……
伪满洲国成立,李香兰被选入伪满电影厂。爱莲和玉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来告别时,李香兰十分难过与不舍,也十分不解。李香兰以美丽的歌声迅速走红,成为伪“满影”头号“中国明星”。彬本尽管对日军暴行十分不满,为了心爱的人,只好随她加入“满影”。
太平洋战争前夕,李香兰在东京举办独唱音乐会,盛况空前,观众排长队绕剧场七圈。天真幼稚的她只顾着为“东亚共荣圈”歌舞升平,哪里知道华夏神州早已是遍地焦土、满目疮痍!
爱莲、玉林加入抗日游击队,彬本却被征入日本远征军。战场上,士兵一个个倒下,活着的他苦苦思念亲人、盼望归乡。又过去了几年。一天,爱莲找到李香兰,告诉她:日本即将战败,让她尽早回国,以免遭殃。这之前,李香兰在军方蒙蔽下一直相信日本必胜。她震惊而困惑,将信将疑,不知何去何从?
日本战败了。李香兰没有走,随即以伪满洲国头号“影星”身份被当作“汉奸”,送上军事法庭并判处死刑。她不得已据实交代并出示证件,说自己是日本人,不是“汉奸”。法庭上人们群情激愤、齐声怒吼,不肯饶恕她。
李香兰觉得自己罪有应得,愿接受死刑的判决。面临死亡,她最后满含眼泪深情地唱出对养育她的中国亲人的感激之情,和对自己不知不觉中所犯罪行的悔恨……听众多为之动容,场上寂静无声。
中国法官宣布:据事实证明,她确实不是汉奸,是受骗的日本艺人,应予以释放,同参战而投降的日本士兵一样,遣送回国。也有人依然不服,继续发泄愤怒。法官唱道:“让我们以德报怨!……”歌声起共鸣,嘈杂声化为大合唱:“让我们以德报怨!……”合唱歌声似乎化解了人们心中积压已久的仇恨。
正如鲁迅先生赠日本友人诗句所预言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法庭上,李香兰和爱莲相拥而泣。
该剧写得脉络清晰、很有新意又满含感情。从剧本结构上看,浅利庆太不愧是结构本子的高手。其一,把历史与人生两条线巧妙地拧成一股绳,使剧情有力地向前推进。他承认:“把历史和人生交织在一起,确实是费了不少力气。”为强化历史感,浅利导演还将许多历史影像投放到大屏幕上,产生很好的效果,让观众有重返历史现场之感。有论者评得好:“历史观照人物,人物反衬历史;历史因一个时代牺牲者的曲折命运而凸现,人物在一个充满阴谋和血泪的时代背景上化为典型。”其二,一头一尾相互呼应:从法庭判她死刑开场,到法庭判她释放收场,中间是回叙她的平生,实为无辜受骗的证据。浅利庆太指出:“李香兰可以说是时代的牺牲品,不过她是被利用了。因此只追踪她的人生,则难以理解她为什么仅由于不自觉地唱歌和表演,就险些被判处死刑。”任何个人的幸与不幸都脱离不开时代,都是时代造成的。《李香兰》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十年中每年都公演,已达800场,至今恐有千场以上了。该剧1988年来华演出过。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文化部邀请浅利庆太率《李香兰》剧组再度访华,在李香兰曾到过的城市一北京、长春、沈阳、大连一公演15场,获得很大成功。
(3)《想变成人的猫》(改编自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劳埃德·亚历山大同名小说,1979年首演)故事讲述了一只向往人类生活的“猫咪”,有一天,在主人的魔法下真的变成了人。剧中表现变成人的“猫咪”在所居住的小镇中与居民相处、相知、也尝到了人间之爱的奇异经历,富有魔幻色彩。这只“猫咪”先后遇见了各色人等:既有善良的医生、好脾气的大婶,以及天鹅皇后旅店可爱的姬莉安姑娘。当然,剧中免不了还有大坏蛋一贪梦邪恶的地方长官施瓦辛格。“猫咪”既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冒险,又感受到好朋友相随相伴的温情。该剧有巧思,意在表现人间总归有爱、善总能战胜恶的主题立意,演出后颇获好评,成为保留剧目。“中戏”首届音乐剧班曾以该剧作为学生的培训剧目并在京公演过。
3.东宝刷团:
东宝剧团的原创剧目也不多,大都引进德、奥、法的古典歌剧名作。为确保商演利益,剧目多元化,版权也与别的剧团共享。原创改编剧有《四月是你的谎言》等少數剧目。引进的剧目有《伊丽莎白》(具有反日本歧视女性的现实作用)、《老妇还乡》(撕下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假面具)、《堂吉诃德》(结构精巧,有讽世意义、《西贡小姐》等等。
4.新千线剧团:
成立于新世纪的新干线剧团的剧目有:《阿修罗城之瞳》(2003年)、《蔷薇和武士》(2010年)、《苍之乱》(2014年)等。
从以上日本“四大剧团”的原创与引进的歌剧,音乐剧新、旧剧目中,我们可以做出怎样的判断呢?
其一,原创剧目偏少,甚至少得有点可怜(浅利庆太的感叹与批评是有根据的,也是有的放矢的);其二,为商演所逼,为生存所计,不得不依赖大量引进欧美新旧名剧,名为“多元化”,实则扼制了民族歌剧“一元”的发展;表面看着五光十色、十分繁荣,实则“满台笙歌戏,一把辛酸泪”!
这是日本歌剧、音乐剧艺术家无可奈何的事,我们不能也不该责怪他们。然而,从歌剧未来的发展来看,仍然有值得总结的必要,而不该被其表面的光怪陆离所迷惑。
我们只能把赞许给那些坚守民族歌剧原创性的苦心经营的艺术家们,为《夕鹤》《李香兰》点赞。
而对那些为了商业利益、一味引进欧美的东西的做法虽表示理解,但却不敢苟同。因为引进再多,也代替不了自己的创造。
这不禁让我想起中国歌剧界也曾流传过一种说法:“只要多演、演好西洋歌剧,中国自然就有歌剧了。”在他们看来,中国至今并没有歌剧!这种“危言耸听”,我就曾听见有人说过。而在十几年前的一次福建师大歌剧论坛上,某位剧院的负责人大肆吹嘘其“政绩”,宣称其演出西洋大歌剧的日程表已排到2025年。而中国民族歌剧呢?则少得可怜。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这种说法与做法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其根子就像当年贺敬之同志所严肃批评的那样:“盲目崇洋,妄自菲薄。”那么,其教训又在哪里?一言以蔽之,可用两个成语加以概括:一是“邯郸学步”,一是“东施效颦”。这两个成语的毛病,中国与日本歌剧界的某些人都犯了。
先说“邯郸学步”。一般来说,“学步”并不丢脸。小孩子学走路,哪有不学步的?艺术上“学步”也是如此,哪位大师、天才刚一开始不“学步”的?中国孩子学书法,开笔总得“描红”。“描红”也是“学步”。但“邯郸学步”则不然,本来自己会走路,跑去向人家学的结果,却是不会走了,走不回来了。某些人学西洋歌剧、学美国音乐剧的结果,变成搞不出自己民族的歌剧、音乐剧了,正是犯了与“邯郸学步”一样的毛病。
再说“东施效颦”。西施很美,即使病了,“西子捧心”也不改其美。然而,东施虽不美甚至有点丑,不与人比美也没什么,如偏要学西施的“病态美”,也捧起心来,只能更丑。美是别人的,那种自然、本真的美,别人是学不来的。西洋歌剧和美国音乐剧也是美的,但那是西方人的,而非东方人的。东方人再学,也学不来人家那种出自本民族风貌的特点。长期模仿、效法与搬用的结果,留下的只能是仿品,不是真品而是伪劣品。辛辛苦苦搭成的“猫窝”剧场难道不正是绝妙的写照?不正是此类的“假洋货”?
(四)朝鲜对民族歌剧的坚守:
朝鲜民族是英雄的民族,朝鲜民族的艺术也是有其灿烂历史的。别的不说,光是朝鲜对民族歌剧的坚守,就令人佩服。朝鲜自20世纪40年代末建国以来,所创作的歌剧都是民族性特征很鲜明的:革命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结合得相当完美。“洋腔洋调”的东西,在他们那里似乎难以存活。
朝鲜著名的“五大歌剧”名作:
(1)《血海》:
《血海》是抗日题材,主题是“要把受难的血海,变成斗争的血海!只有革命才有活路!”(金日成语)1936年就有了《血海》话剧,1971年改编为同名歌剧。
该剧打破西洋歌剧的传统写法,唱段打破咏叹调与宣叙调的藩篱,采用更自由更多样的写法,为的是更加通俗化与大众化,动听动情、脍炙人口。剧中再采用旁唱与舞蹈,配以流动的舞美,开创了朝鲜新型革命歌剧之先河,在世界歌坛产生很大反响。该剧1970年代曾来中国演出,更是轰动京华。该剧魅力至今不减,已演出1500多场。
(2)《卖花姑娘》:
《卖花姑娘》据《金日成回忆录》创作。他1930年代在狱中就开始构思,1930年底十月革命13周年时该话剧首演。1970年代初改编为同名歌剧,演出后也轰动一时。后该剧来华演出,女主人公唱的主题歌《卖花歌》广为传唱。
(3)《党的好女儿》;
(4)《密林啊,说吧》;
(5)《金刚山之歌》。
由上所述,朝鲜最著名的经典歌剧《血海和《卖花姑娘》,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与中国称为歌剧“黄金时代”的五六十年代的一批“红色歌剧”经典相比,时间稍晚,但其艺术质量不仅足以媲美,在演出场面之恢宏、民族音乐之纯正、人物感情之浓烈,以及演员整体的演唱水平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艺术评价首先应是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当然,评判中的政治因素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外古今,概莫能外。尤其是当今世界并不平静,远非是无阶级、无政治分野的“大同世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艺术作品被西方贬斥的何其多,不考虑阶级对立,仅谈“纯艺术”“普世价值”,不是书生气十足,便是别有用心,是十分危险而有害的。
进入新世纪以后,朝鲜音乐戏剧的民族化又有所拓展,从革命历史题材扩大到民间故事传说了。大型音乐舞蹈诗剧《阿里郎》标志着这新的发展变化。(大型团体操与宏大音舞场面原是朝鲜最为擅长的。中国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多少也从中获得启示与借鉴。)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近年朝鲜歌剧《红楼梦》的出现。朝鲜歌剧的选材扩展到中国古典文学来了。该剧也来中国演出过。我未看过此剧,艺术上不好妄加评论,不过有一点应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朝鲜艺术家创演《红楼梦》应该不像他们搞《卖花姑娘》《阿里郎》那么得心应手。因为国别不同,正如中国人演《茶花女》总不如演《白毛女》那样亲切真实一样。尽管如此,该剧的推出,却是足以让中国歌剧界汗颜的。中国至今也没能创演出一部歌剧《红楼梦》来。
除《红楼梦》之外,朝鲜移植、改编的中国歌剧与戏曲还有《白毛女》与《梁祝》等。
可以说,在亚洲众多国家中,朝鲜的民族歌剧是独树一帜的。这一点,连其同胞韩国都难以望其项背。
(五)韩国音乐剧对民族性的强调
与朝鲜相比,韩国的歌剧一度几乎默默无闻。直至1971年,为与朝鲜的“血海歌剧团”相抗衡,才成立“相爱乐团”,创作本士的民族音乐剧。1983年著名音乐剧导师南京邑创办培训学校,先后教出3000多名学生(约占韩国音乐剧从业人员
三分之一),其最優秀的弟子曹承佑主演音乐剧《明成皇后》《义兄弟》一举成名,成为名利双收的大明星。
到了新世纪,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韩国文化艺术市场更全面地向欧美开放,韩式音乐剧发展很快,从《无理的英爱小姐》(2003年,改编自同名电视剧)、《寻找金钟旭》(2005年,三年后拍成同名电影)、《丑女大翻身》(2008年,改编自电影)、《冬季恋歌》(2011年,改编自同名电视剧)、《绿野仙踪后传》(2014年)等,风头似乎盖过日本。
下面重点介绍两部来华演出过的优秀音乐剧名作。
(1)《春香传》(2007年来华参加北大百年校庆演出):
该剧讲述300多年前(相当于中国的晚明时代),某艺妓的女儿春香是个绝色美女,端午节与少年公子李梦龙巧遇并相恋。李父为使道大人,调任他处,命儿子梦龙同行,但不许春香同往。二人挥泪而别,相约三年后,李公子学业结束便来接她。
三年后,新任御史(钦差)听闻春香有倾国之貌,欲纳为妾。春香誓死不从。御史恼羞成怒,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春香投入监狱……
《春香传》改编自同名古典小说。在韩国,《春香传》具有与中国的《红楼梦》同等地位,可谓家喻户晓。据古典名著改编的音乐剧《春香传》也成为经典名剧。
(2)《洗衣服——“屋塔房”恋歌》(2016年来华演出):
一间出租屋里住着好几个穷住户。因过于拥挤,屋顶又搭出一小间洗衣房,供洗衣姑娘娜英住。于是在小房间里唱了一出悲喜的恋歌。同租此屋的蒙古留学生松龙高爱上了娜英。二人心心相印,即使在穷留学生失学失业的艰难日子里,都未能使他们分开。这一对青年恋人相濡以沫,向往着幸福的明天。
同住在一起的其他几位,也都是在贫困中挣扎的不幸人这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小人物,通过洗衣、晾晒等活儿,苦中取乐,日复一日。他们洗着衣服,似乎也渐渐洗净了心上的尘垢。他们始终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更没有绝望。最后,各自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小片希望的天地。洗衣姑娘和松龙高这一对倾心相爱的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悲剧性的遭遇,以喜剧性结束。该剧题材类似普契尼的名剧《波希米亚人》,然而洗衣女娜英却比绣花女咪咪要幸运得多。
有论者评论:该剧依靠朴实无华的故事和优美动听的音乐,震撼人们的心灵。《首尔新闻》评曰:“令人热泪盈眶的《洗衣服》,连舞台、道具全都是韩国式的。”其民族自豪感溢于言表。
这群在城市里打拼的乡下人,类似中国的“北漂”。韩国的艺术家敏锐地抓住小人物的命运,创作出很接“地气”的本土音乐剧,值得中国同行效法。
与邻国日本相比,韩国音乐剧尽管也面向市场,追求票房是占首位的,但有两点与日本不同:一是强调音乐剧的民族化、本土化。二是国家提倡并扶植民族音乐剧的发展。2012年至2014年,韩国的文化主管部门一再公布支持原创音乐剧的创作与演出的计划与措施。其产生的直接效应是以男明星为招牌的韩式音乐剧进军日本,吸引了日本大批女性观众,对韩国音乐剧男明星达到狂热崇拜的地步,其票房自然也是十分可观的。
新世纪,韩国音乐剧市场收入以每年20%的增长率持续十年,2012年的数据显示,全年音乐剧上演达到44620场次,观众达到1100万人次。2013年上演收入达到3000亿韩元(17.6亿人民币)。这数字是很惊人的。然而,这种高度繁荣的背后,也应清醒地看到,市场收入70%多的份额仍由进的欧美音乐剧所占有,韩国本土的原创音乐剧的占有率还不到三分之一。这是商业化演出市场不可避免的严酷现实(连成熟的德国歌剧演出市场,也必须以引进百老汇音乐剧为主)。
这种状态也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正面的是,商业演出市场日新月异,有利于音乐剧的学习、借鉴与发展。现在韩国观众已有点“喜新厌恶”,早已不看《猫》与《剧院魅影》这类老旧的名牌音乐剧了。伦敦西区与纽约百老汇的新剧目,五年之内,必能看到该剧目韩语版的演出,且质量不差。
负面的是,是韩国本土原创音乐剧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稍不进取就有可能被排挤甚至被完全取代的危险,连30%的市场份额也维持不住。韩国官方一再推出扶植本土原创民族音乐剧的措施,恐怕也是意识到这种危机。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韩国音乐剧的发展,福兮?祸兮?韩国音乐剧界对此不会不加思考。中国每年都有不少学生到韩国学习音乐剧,他们同样不可以盲目而不加分析地对待韩国音乐剧。
总之一句话:在学习包括韩国在内的外国音乐戏剧方面,全盘接受或一概排斥都是错误的。我们只能学其好的(如力求本士化、民族化),弃其不好的(如过分依赖欧美音乐剧以维持市场的繁荣)。这一点,与中国歌剧的健康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也是其成败得失的关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