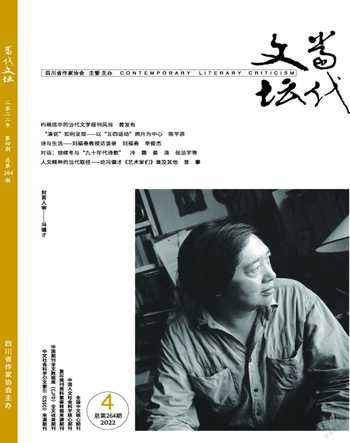茵加登文学作品结构理论置疑
苏宏斌
摘要:茵加登主张文学作品是一种由语音构造层、意义单元层、再现对象层和图式化侧面层构成的多层次结构,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第一,文学作品的语音和语义之间是层级关系吗?第二,文学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和事件是作家通过语言行为对意识行为进行再现的结果吗?第三,图式化侧面是处于再现对象层之外的一个独立层面吗?本文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文学作品的语音和语义之间并不是层级关系,而是一体两面的并置关系;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对象是作家通过语言符号直接建构起来的,因此称其为再现对象是不恰当的;图式化侧面并不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的一个独立层面,而是再现对象层的一种内在特征。
关键词:茵加登;语音构造层;意义单元层;再现对象层;图式化侧面层
茵加登的文学作品结构理论在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他既没有采纳黑格尔的内容-形式模型,也没有采纳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质料-形式模型,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层次结构理论,认为文学作品是由语音构造层、意义单元层、再现对象层和图式化侧面层构成的一个多层次结构。这种做法似乎成功地避免了割裂内容与形式的二元论弊端,因而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肯定和接受,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一结构模型实际上存在着诸多疑问,以下试逐一加以探析,以期推进对于茵加登文论和文学作品结构问题的研究。
一
茵加登把语音层和语义层视为文学作品结构中的两个层级,认为语音层处于文学作品结构的最底层,语义层则处于语音层之上。在他看来,最小的语音构造乃是单个语词的语音。在以索绪尔为源头的现代语言学传统中,最小的语音单位一般被认为是音位,用雅各布森的话说,“音位指的是一组共存的声音特征,语言使用这些声音特征来区分意义不同的词”①。茵加登则认为:“最简单的语言构造是单个的词语。”②比单个语词更为高级的语音构造就是句子和句群。茵加登认为,语词一旦处于句子或句群中之后,其语音的孤立性和封闭性就被打破了,转而与其他语词的语音发生了关联,这种关联必然使原有的语音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并不会使某个语词的语音变成另一个语音,但却会使每个词音都具备了某种关系性特征:“的确,当单个词音出现在特定的复多体之中的时候,其个体语音并不会仅仅由于一个特定的词音出现在它之前或之后,就变成另一个词音。虽然如此,这些词音有时仍会显示出可以感知到的关系性特征(如果可以这样称谓的话),这种特征正是源于和其他词音的接近。”③由于不同的词音之间发生了关联,由此就形成了更高级的语音单元,茵加登称之为词音复多体(manifold of word sounds)。依照这些复多体的复杂程度,他列举出了节奏(rhythm)、节拍(tempo)、诗行(verse)、诗节(stanza)等,其中后面的复多体总是建立在前面的复多体之上。具体地说,不同语词的重音变化就产生了节奏,有规律的节奏变化则形成了节拍,如此等等。与单个语词的语音一样,茵加登把这些更高级的语音单元也称作声音格式塔,其目的是强调单个语词的语音已经发生了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声音统一体。
和语音层的构造相似,茵加登认为构成语义层的最小单位也是单个语词的意义。在他看来,语义层和语音层一样,其内部也包含着不同的层面。单个语词的意义构成了文学语言的最小意义单元,在此之上则是由句子和句群组成的更为高级的意义单元。语词的意义问题是现代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对于这个问题,茵加登试图借助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来加以解决。以单个的语词为例,他认为名词的意义是由五个要素组成的意义统一体,这五个要素分别是:意向性指向因素、质料性内容、形式性内容、存在性特征因素和存在设定因素。具体地说,意向性指向因素指的是语词指向了哪个对象、以何种方式指向对象等;质料性内容是指语词所指涉的构成对象的材料方面的内容;形式性内容则是指对象的形式特征;存在性特征因素是指对象在存在方式等方面的特征,比如此对象是个别对象还是一般对象、实在对象还是虚拟对象等等;存在设定因素则是指语词在意指对象的时候是否设定了对象的存在。与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相对照,茵加登所说的语词意义的质料性内容、形式性内容和存在性特征等因素显然指的是胡塞尔所说的意向质料,属于意向对象侧;他所说的存在设定和意向性指向因素则属于胡塞尔所说的意向质性,属于意向作用侧。这说明在茵加登看来,语词指涉对象的过程就是首先从对象身上获得其质料、形式、存在方式等方面的材料,然后再通过意指行为来赋予这些材料以意义,由此形成了语词本身的意义。在单个语词的语义之上,则是由句子和句群等构成的更高的意义单元。句子和句群与单个语词的差异在于,其所指涉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所处的状态,茵加登称其为事态(state of affair)。这个术语原本是胡塞尔在分析判断行为时提出的,茵加登认为以之来描述文学语言也是适用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茵加登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语音和语义都包含着一个内在的层次结构:就语音而言,处于最底层的是单个语词的语音,在此之上则是句子以及句群的语音,通过这些更高级的语音组合产生了文学语言所包含的节奏和韵律;就语义而言,处于最底层的是单个语詞的语义,在此之上则是由句子和句群所投射出的事态,文学作品正是通过这些事态来描绘人物和事件的。茵加登的这一看法可以说是对文学作品构成方式的忠实描述,与现象学的座右铭——面向事情本身——是完全符合的。问题在于,语音和语义之间也是一种层级关系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茵加登的看法中隐含着传统思想的成见。表面上看来,我们在面对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总是语词以及句子的语音,而后才理解了它们所表达的意义。但实际上对于一个有经验的读者来说,对于语音的把握和对于语义的理解总是同步进行的,只有当我们面对一种用未知语言写成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才需要首先辨识语词的发音,而后再理解其意义。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在通过听觉把握事物的时候,本来就不是先被动地接受声音刺激,而后再赋予其一定的意义,而是直接把事物及其意义呈现出来。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我们从未首先并且根本地在物的显现中感觉到一种感觉的涌逼,例如乐音和噪音的涌逼——正如这种物之概念所预先确定的;不如说,我们听到狂风在烟囱上呼啸,我们听到三马达的飞机,我们听到与鹰牌汽车迥然不同的奔驰汽车。物本身要比所有感觉更切近于我们。我们在屋子里听到敲门,但我们从未听到听觉的感觉,或者哪怕是纯然的嘈杂声。为了听到一种纯然的嘈杂声,我们必须远离物来听,使我们的耳朵离开物,也即抽象地听。”④
单就语言行为来说,语音和语义之间也是无法明确切分的。索绪尔曾把语音和语义比作一张纸的两面,认为它们之间是无法切分的:“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⑤当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总是从一定的意义出发来识别语音的,反之亦然。或许有人会说,当我们还没有弄清楚语音的时候,怎么可能预先就把握到其意义呢?这就涉及到解释学和接受美学所谈论的期待视野以及视野融合的问题了。海德格尔早就指出:“解释向来奠基在先行见到之中,它瞄着某种可能解释状态,拿在先有种摄取到的东西‘开刀’。被领会的东西保持在先有中,并且‘先见地’被瞄准了,它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⑥这就是说,当我们在对任何事物做出解释之前,我们已经对其意义有了一种先行把握,只不过这种把握还处于一种非概念的潜在状态,当我们具体接触到该事物之后,就可以把这种潜在的解释上升为概念。就对于文本的解释来说,伽达默尔认为这种先见就构成了读者的先在视野,而解释本身就是这种先在视野与文本自身所固有的视野相互融合的结果。尧斯更是明确指出:“从类型的先在理解、从已经熟识作品的形式与主题、从诗歌语言和实践语言的对立中产生了期待系统。”⑦据此我们认为,当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已经对于语词和句子的意义有了某种先行把握,因此对于语义的理解并不是在语音之后才进行的。从具体的阅读实践来看,只有那些缺乏阅读经验和文学修养的读者才会十分笨拙地按照字典上的发音来辨识语词,有经验的读者则能够直接按照作品特有的风格和节奏来朗读语词,前者发出的只是词典规定的“标准音”,后者发出的才是语词在特定作品中的“正确音”。表面看来,这里的差别在于语音,实际上语音的差别与表义的需要息息相关。茵加登把语音和语义看作文学作品结构中的两个层次,这很容易诱导我们以为在阅读行为中这两者是依次出现的。因此我们主张,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层级的高低,而是一体两面的并置关系。
二
茵加登认为文学作品结构中的第三个层次是再现对象层。这个观点看似与近代的再现论十分一致,实则两者相去甚远。茵加登所说的再现对象涵盖了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各种事物,比如人物、事件、情节等等。他给这个概念所下的定义是:“文学作品中的再现对象是一些由意义单元投射出的衍生性纯意向对象。”⑧这个定义内涵十分丰富,至少包含以下三层意思:首先,他之所以把再现对象说成是意义单元投射而成的,是因为他主张作家用语言描绘某个对象的行为是一种意向性活动,这些对象就是由此产生的意向对象。其次,他之所以把这种对象说成是纯意向对象,是由于他把意向对象区分成了纯意向对象(“purely intentional” object)和准意向对象(“also intentional” object)两种类型。纯意向对象是纯然由意向行为所创造的,其存在是他律的,完全依赖并内在于意向行为;准意向对象则是通过对具有自主性的实在对象的意向性行为而产生的,因此其存在具有一定的自律性。茵加登主张作家所描绘的艺术形象并不是通过对某个实在对象的再现而产生的,而是借助于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因此是一种纯意向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茵加登尽管主张在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一个再现对象层,但他的观点与19世纪的再现论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然,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文学语言与实在对象之间的关联,他承认某些文学类型比如历史题材的小说,有时的确再现了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和事,但从根本上来说:他还是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种想象活动,因而文学语言所描述的对象就不是实在对象,而是一种想象之物(纯粹意向对象)。第三,茵加登之所以主张再现对象是一种衍生性意向对象,是因为他又把意向对象区分成了原初性意向对象(primary intentional object)和衍生性意向对象(derived intentional object)。原初性意向对象是通过纯粹的意识行为产生的,衍生性意向对象则是通过语言这种衍生性的意向性行为产生的。茵加登主张文学形象最初是通过作家的意识行为创造出来的,而后再通过语言及其意指行为将其加以再现。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茵加登何以一方面主张文学形象是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却仍称其为再现对象。
正是在这一点上,茵加登的理论引起了我们的质疑,因为这归根到底还是把语言当成了作家传达思想的一种工具,从而回到近代的工具论语言观中去了。当然,茵加登并非有意识地采纳了近代的语言观,而是受到了胡塞尔关于意识行为奠基理论的影响。胡塞尔认为,感知是最基础的意识行为,想象行为奠基于感知之上,两者共同构成了基础性的直观行为,图像意识、符号意识等非直观行为必须奠基于直观行为之上,而言语行为显然是一种符号行为,因此就只能是一种衍生性的意识行为。茵加登认为,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首先通过想象等直观行为构成了完整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形象,然后再通过一张语词之网将其捕捉并再现出来。用他的话来说,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对象“必然是‘陷在网中’的。或者换句话说,通过这种方式被分散开来,并被置入一张事态之网中的对象,就被相互关联的句子间接地勾勒出来,并通过事态再现出来了”⑨。问题在于,离开了语言符号,作家还能够通过纯粹的意识行为来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吗?从现代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一點显然是十分可疑的。正如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所说的,“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⑩,“语言对思想所起的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混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因此,这里既没有思想的物质化,也没有声音的精神化,而是指的这一颇为神秘的事实,即‘思想-声音’就隐含着区分,语言是在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形成时制定它的单位的”11。这意味着语言并不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因为在语言产生之前,思想只是一团混沌模糊的浑然之物,正是通过语言的分节连接(articulation)作用,这些混沌的心理现象才被分割成不同的要素,并按照语言的内在逻辑和语法有序地排列起来,从而转化为思想。美国学者福多也认为,语言是思维直接的、名副其实的媒介,任何思想内容都是通过语言而得到加工、储存和表征的,思维活动本身就是对思维语言的提取和处理。12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语言决定思维的观点,如萨皮尔、沃尔夫等。前苏联的许多心理学家也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的劳动和语言乃是思维和意识产生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总之,认为语言不只是传达思想的工具,而是与思维密不可分,已经成为现代思想的一种共识。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作家对艺术形象的想象和构思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活动,而是常常借助于语言来进行的。以人物形象为例,作家并不只是想象一个纯粹的感性形象,而是必须通过具体的语言和情节来刻画其性格。许多作家在构思人物形象的时候,都会预设某种特定的场景,然后推测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会说些什么话,借此来为描写人物的对话打下基础。屠格涅夫在孕育人物形象的时候,就常常不厌其烦地记录人物可能具有的各种言行举止:“围绕着我当时所感兴趣的主题开始浮现这个主题所应该包含的那些人物。于是我马上把一切记在小纸片上。我仿佛为了写戏似的规定这人物:某某,多大年纪,装束怎样,步态又是怎样。有时我想象起他的某种手势,也马上把这写下来:他用手摸摸头发或者理理胡子。当他还没有成为我的老相知之前,当我还没有看见他,还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之前,我是不动手来写的。我就是这样地写所有的人物,……其余一切,只不过是技巧的事情,那就轻而易举了……”13他在创作长篇小说的过程中,常常在脑海里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对话,以至于当作品完成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与熟悉的亲人分别的难分难舍的感觉。事实上,构思活动与写作活动的差别并不在于前者不需要语言,而在于它所使用的是内部语言,后者使用的则是外部语言。内部语言是作者心灵中的一种内部对话或独白,因此常常是支离破碎、不合逻辑或不够完整的,外部语言是一种与他人的交流,因此必须合乎逻辑和语法,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纯粹意义上的私人语言是不存在的,内部语言也是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的。
不过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作家的构思和想象必须完全依赖于语言,而是说完全离开语言符号的纯意识活动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作家的想象力常常是十分鲜活而生动的,因此其心灵中有时可以呈现出具有强烈直观性的形象和场面。在这些特定的时刻,作家的意识活动是可以脱离语言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意识活动仍然是具有符号性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作家所想象出来的感性形象仍然是一种符号形式。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皮尔斯认为,从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出发,可以把符号划分为三种类型: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规约符(symbol),其中像似符的特点就在于依托其与对象的相似性而成为表征该对象的符号。14在我们看来,出现在作家心灵中的感性形象其实就是一种像似符,它与作家所要塑造的人物形象之间具有外形上的相似性,因此就成了一种表征人物的特定符号。胡塞尔的错误就在于,他以为任何符号都必然是具有观念性和抽象性的,因此就把符号行为与直观行为截然划分开来了。事实上符号性与直观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以上述三种符号为例,规约符必然是抽象的,因为按照皮尔斯的说法,“规约符是这样一种符号,它借助法则——常常是一种一般观念的联想——去指示它的对象,而这种法则使得这个规约符被解释为它可以去指示那个对象。因此,它自身就是一种一般类型或法则,也即它是一种型符,而且它所指称的对象具有一种一般本质。”15但像似符却完全可能是具有直观性的,无论是一幅实际的图画,还是存在于艺术家心灵中的画面,都是如此。茵加登与胡塞尔一样,忽视了感知和想象活动中的感性表象所具有的符号本性,把语言等符号行为当成了一种衍生性的意识行为,因此错误地以为通过语义投射出的对象只是对纯意识对象的再现,殊不知这里所出现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符号行为,作家实际上是用语言这种规约符对想象所依赖的像似符进行了转译而已。
三
茵加登理论中第三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再现对象层和图式化侧面层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茵加登讨论文学作品的两部代表性著作《论文学的艺术作品》和《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他都采取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每当他简要概括这一理论模型的时候,他总是把图式化侧面层置于再现对象层之前,而当他依次论述这些层次的时候,却总是把两者的顺序颠倒过来,先讨论再现对象层,再讨论图式化侧面层。在《论文学的艺术作品》中,他先在第三章里把文学作品的结构概括为语音构造层、意义单元层、图式化侧面层和再现对象层,然后却在第七章中先讨论再现对象层,而后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再讨论图式化侧面层。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他又是先在导言中把图式化侧面层放在再现对象层之前,而后却在第一章里先讨论了再现对象的具体化问题,再讨论图式化侧面的现实化和具体化问题。在茵加登的文学作品结构理论中,处于后面的层次必然建立在前面的层次之上,如果再现对象層处于图式化侧面层之后,那么它就是以后者为基础的,反之亦然。因此,这种前后关系是不可逆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两种相反的排序方式。那么,在文学作品中再现对象层和图式化侧面层究竟孰先孰后?茵加登为什么会在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左右摇摆?
从茵加登自己的论述来看,他显然是把图式化侧面层放在了再现对象层的后面,这似乎意味着他主张图式化侧面层是以再现对象层为基础的。不过需要主要的是,茵加登在处理这两个层次顺序的时候,与其他层次是有所不同的。正如德国学者伊瑟尔所指出的,在茵加登的文学作品结构理论中,“每个层次都具有双重特性:(1)它基于另一个层次之上;(2)它产生该层次所缺少的东西”16。比如他在分析意义单元层的时候,就先指出其建立在语音构造层之上,接着分析了意义单元层的内在结构,然后指出它的功能就是投射或构成再现对象层。但他在分析再现对象层的时候,却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个顺序,而是在讨论了再现对象层的构成之后,接着讨论了图式化侧面层及其功能,然后再回过头来分析了再现对象层的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茵加登实际上是在分析再现对象层的过程中插入图示化侧面层的。他究竟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奇怪的处理方式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隐含在《论文学的艺术作品》一书第七章的最后一节中。这一节的标题是“再现对象的未定点”,其主要内容是对再现对象与实在对象的详细比较。茵加登的主要观点是,实在对象具有三个特点:不包含任何未定点、具有无限多的规定性、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物。与之相比,文学作品中的再现对象则包含许多未定点,原因在于这些对象是通过名称和事态被意指和再现的,名称大多数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只是描述了事物的一般特征,因此对象的许多个体性特征就处于空白和未定状态;文学作品所能描绘的事态必然是有限的,因此所投射或构成的再现对象就必然充满着许多未定点。17从这里可以看出,正是对于再现对象的未定点的发现,促使茵加登认识到,再现对象具有一种图式化(schematized)的结构,从而引入了图示化侧面这一概念,因为图式(schema)一词在日常语言中包含“图解”“程式”等意思,指的是一种介乎于图像和概念之间的程式化表达方式。正是因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把中把图式视为感性表象和知性范畴之间的中介物。茵加登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说明再现对象并不像实在对象那样具有无限的规定性,而只包含某些有限的规定性,因此具有许多未定点或不确定性。换言之,图式化侧面其实并不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的一个独立层面,而是再现对象层本身的一种内在特征。只有弄清了这一特征,才能完成对于再现对象层的分析。
然而我们的这种解释与茵加登自己的看法却似乎并不相符。无论他如何处理再现对象层和图式化侧面层的先后关系,他始终都将其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以为跟他引入了胡塞尔的“侧显”(adumbration)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理论是胡塞尔在分析知觉经验时提出的,所谓侧显是指对象在知觉经验中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直接显现出来的,而是每次只展示有限的侧面,因为我们总是从一定的视角(perspective)出发来观察对象的。另一方面,我们的知觉经验又是一种时间意识,意即对象总是在由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维度所构成的时间视域中呈现出来的,时而处于意识的焦点,时而又退居于背景之中,这样一来,这些侧面在我们的知觉经验中就呈现为一系列显相(appearance),由此就形成了一系列侧显复合体(multiplicities of adumbrations)。18茵加登认为,文学作品对于意识对象的特殊再现方式让对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知觉对象,因而也就蕴含着许多图式化的侧面。问题在于,一切知觉对象都是实在之物,而文学作品中的再现对象则是一种纯粹意向对象,其存在是纯然他律的,何以能视其为知觉对象呢?对此茵加登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对象尽管不同于实在对象,但却仍具有知觉对象的直观性。他的依据是,文学语言在通过事态来投射或建构再现对象过程中,采用的是一种感性的展示(exhibiting)方式,因此所产生的是一种与知觉对象相似的可直观对象。用他的话说,“诸事态可以说是为对象的各个侧面准备了所有的条件,因此当各种主观条件被满足之后,对象就可以自明地被直接知觉到”19。尽管再现对象归根到底只是一种意向对象,但它也是像知觉对象一样以侧显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正是这种“侧显”理论的引入使得茵加登的思想陷入了混乱,促使他把再现对象层和图式化侧面层当作两个不同的层面,并且在对其先后顺序的理解上动摇不定。这是因为,所谓侧显说的是实在对象在知觉经验中的显现方式,以此来说明再现对象,就使得茵加登把文学作品的结构问题与读者对作品的接受问题混为一谈了。具体地说,所谓图式化侧面其实只是构成再现对象的内在要素,由于茵加登把再现对象类比为知觉对象,图式化侧面就变成了再现对象在读者的阅读经验中的显现方式了。伊瑟尔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事态就是透过其中我们观察意向性客体的‘窗户’,图式化观相20则是展示意向性客体的模式。”21对于茵加登的这种做法,张永清曾经给出过这样的解释:“作为意向对象的文学作品由语词的意义意向、作者的意义意向、读者的意义意向这三者交织而成。其中,作者的意义意向已被编织在文学的艺术作品中,它与语词的意义意向共同形成了文学作品的图式化客体,这一图式化客体存在诸多的未定点;在读者的意义意向将其充实即具体化之后,客体对象层即再现世界及其审美特质才得以感性呈现。”22我们认为这段解释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茵加登未曾明言的观点,也就是说茵加登把对文学作品结构的分析延伸到了读者的接受活动中,这样一来,图式化侧面就变成在再现对象层之后出现的一个新层面了。
张永清的这段话还从另一个方面启示我们,茵加登何以在概括其理论时又把图式化侧面层放在了再现对象层的前面,因为茵加登的文学作品结构理论中也隐含着一个作者视角。如果说文学作品中包含着一个图式化侧面层的话,那么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这个层面就应该看作构成再现对象层的基础。张教授在文章中认为:“从内在逻辑看,意义单元层之后应为图式化观相层而非再现客体层。”23我们以为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解释得通。伊瑟尔更是在同一句话中把这两个角度都包含在内了:“意向性客体建立在图式化观相上,通过后者,意向性客体得以展现并被带进观察的视野。”24显然,前一句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说的,后一句则是从接受的角度来说的。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说法即便与茵加登本人的意思相吻合,却并没有揭示出茵加登思想中的谬误。我们认为,图式化侧面并不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的一个独立层面,而是再现对象层的一种内在特征。
注释:
①钱军选编:《雅各布森文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8页。
②③⑧⑨1719 Roman Ingarden,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Translated by Eorge G. Grabowicz,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p. 35,p. 47,p. 218,pp. 159-160,pp. 246-251,p. 194.
④〔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⑤⑩11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第157页,第157-158页。
⑥〔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4页。
⑦〔德〕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12参看宋荣、高新民:《思维语言——福多心灵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3转引自〔俄〕列特科娃:《关于屠格涅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1415参看〔美〕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第60页。
162124〔德〕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谷婷婷、潘玉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8对此可参看〔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5页。
20中国学者一般都把茵加登的术语schematized aspects译为“图式化观相”或“图式观相”,本文则主张译为“图式化侧面”,理由是“观相”一词指的是事物在直观行为中的显相(appearance),但茵加登所说的aspects指的是再现对象内部所包含的诸侧面,并不是指这些侧面在读者意识中的显现物,因此译为“观相”显然是不恰当的。
2223张永清:《问题与思考:茵加登文论研究三十年》,《文艺研究》2011年第2期。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斯拉夫文论经典汉译与大家名说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編号:17ZDA282)
责任编辑:伍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