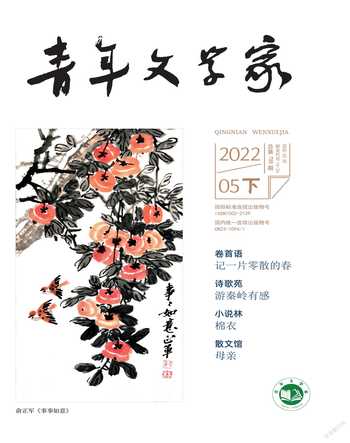风雅第一山
孙燕超
第一山在盱眙县城山中,处于中心位置,左拥翠屏峰,右揽凤坡岭,背倚清风山,面临长淮水,形如一把“太师椅”,如此山形地势,以古代风水学论,可谓绝佳风水宝地。站在山腰,背山临水,极目远眺,顿有豁然开朗,心旷神怡之感。
据史料载,宋代大诗人贺铸、陆游、杨万里等,大画家、大书法家米芾等,还有右仆射、参知政事、监察御史、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河道总督、翰林院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朝廷官员,他们都曾游山上老街、第一山,题诗作文,勒石留名,由此使第一山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意蕴。
这里的文化遗迹都深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符号,没有历史遗迹的城市不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好山好水滋润了盱眙的风雅,就是在这无尽岁月的绵绵延延中,生成了名山之恋,情感之恋。
在长长的碑廊前,我看到历史如阳光一样安详,所有的遐思全都要走到这里驻足,碑廊上沉默的文字记录着第一山的前世今生。南宋时淮河是宋、金两国边界。地处南宋边境的第一山,竟成了北望故国的名山,题咏累累,如杨万里的“第一山头第一亭,闻名未到负平生”,颜师鲁的“闻说淮南第一山,老来方此凭栏干”,蔡戡的“自古东南第一山,于今无异玉门关”,等等。这些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加以生动的描述,从而构成了色彩浓艳的长卷,不论是截取一句或展开整个画面,都会带你进入到第一山的景色之中。文化本原和归属,积淀成诗人心中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底蕴。
一座山守望如水年华,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一杯清茶如烟,一段往事翩跹。北宋哲宗绍圣四年,大书画家米芾赴任涟水知军,由国都汴京(今开封)经汴水南下就任,一路上舟船劳顿不说,两岸皆平原,无甚风景,很是无聊。自汴口入淮时忽见对岸一山,葱茏奇秀,如翠屏耸峙,米芾精神一振,弃舟上岸,在当地官员陪伴下登山览胜,并作诗一首:“京洛风尘千里还,船头出汴翠屏间,莫论横霍撞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并书写“第一山”三个大字。“第一山”三字,写得气势磅礴,有行云流水之感,又有意到、笔到之内涵,可谓是神来之笔,是发自内心的赞颂盱眙第一山的溢美之辞。
这桩雅事,从北宋地方志和此后的文人笔记文学中均有详细记述。凝神看米芾书写的“第一山”三个大字,仿佛自己穿越到北宋,伫立在他身旁,看他率性归真,寄情缥缈泼墨,忽然间又把整个画面建构成浑厚与潇洒的审美内涵,更能于平淡中见真味。
沿着石阶向上,来到“杏花园”。你可以在这里寻觅当年苏轼与他同游的人“共寻春,飞步孱颜”。果然多情的春天亲近了诗人:“和风弄袖,香雾萦鬟。”同时,他也找到了欢笑:“正酒酣时,人语笑,白云间。”
至如今,时光已流逝千载,几经风雨沧桑,“玻璃泉”依旧自信,它斑驳的躯体上附着了太多的人文记忆,汩汩流淌的泉水自然里浸透了文化的汁液,填满了故事的重量。
这山珍藏的艺术财富是摩崖石刻,堪称“石制天书”,这里共有摩崖石刻一百六十六块,摩崖石刻主要分布在秀岩、瑞岩和西域寺三处,且以秀岩为多,多出自历代名家、政要的手迹,字体有正、草、隶、篆、行五体。摩崖石刻将书法与奇岩怪石融为一体,更增添了它的艺术魅力,其书法石刻艺术堪称“国之瑰宝”。
摩崖石刻是古人留给今人一笔无价的文化艺术财富,既蕴含了旷古幽远的韵味,也让人感到回归历史的亲近。在现代五彩缤纷的生活中能亲临第一山,以悠闲的心情读到这些摩崖石刻的佳作,无疑是旅途中的一大意外收获,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欣赏历代文人墨士在摩崖上留下的锦词玉篇,游人须沿着千层青光石板路向上左转右拐攀登,仰目山顶,透过葱茏的秀木,便可隐约看到米芾写的神采飞动的“第一山”三个大字。
米芾书位于一山碑上,字径一尺五,笔力遒劲,飘逸灑脱,素有“风樯阵马,沉著痛快”之誉。我才知道,我和这个宋代第一书法大家真的相隔一千年的距离,及至一千年的仰望、敬慕和崇拜。
这里的山水荡涤着苏轼渐已疲惫的心灵,也使癫狂不羁的米芾归于宁静,韦应物的那些解不开的心思已经化作了山上的淡淡清烟。智者乐山。他们写的是字,是诗,是流光溢彩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