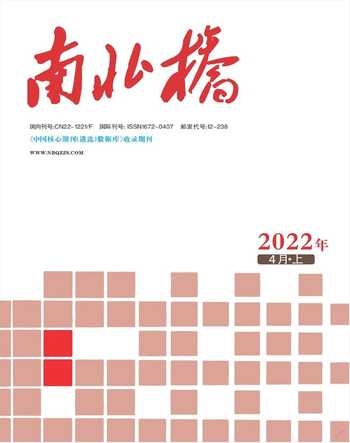黑龙江红色文学跨文化翻译技巧研究
许昊冉
[ 作者简介 ]
许昊冉,女,山东济南人,东北林业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英语。
[ 项目名称 ]
东北林业大学国家级大创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黑龙江省红色旅游外宣文本英译研究(202110225190)。
[ 摘要 ]
黑龙江红色文化是中国璀璨历史长河中的耀眼瑰宝,黑龙江红色文学作为黑龙江红色文化的载体之一,在时代更迭中经久不衰,传递着中国声音。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经典红色文学作品《生死场》跨文化翻译中直译与意译的技巧进行了研究,进一步阐述了红色文学传播的重要性、翻译过程中跨文化交际的难点以及利于外宣的策略。
[ 关键词 ]
黑龙江红色文化;翻译技巧;红色文化外宣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22.07.053
1 萧红与《生死场》
萧红是一名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中国近现代女作家。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人民在日寇的劫掠下悲惨度日,这样的历史背景既是萧红的生存环境,也是她的创作素材。1933年,她以“悄吟”作为自己的笔名,开启了文学创作生涯。1935年,萧红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萧红作品的阶级观念不止是政治、经济,还包括文化。抛开“抗日”的政治内容,她的《生死场》依然有直逼人心的惊心动魄的力量。《生死场》是以萧红自身经历为背景创作的,主要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民无助无望的日常生活以及逐渐觉醒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小说的后七章,抗日的时代主题渐渐明晰,萧红将其对于国家兴亡的思考融入那些混沌无光的苦痛生活的描写当中,为黑龙江红色文化增添了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1979年,葛浩文翻译的《生死场》与《呼兰河传》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举将《生死场》推向了西方,让世界认识、了解了那一时期宝贵的中国文化。本文参考其2002年版译本,对《生死场》的翻译技巧进行了研究。
2 《生死场》英译本的跨文化翻译技巧
不同文化孕育出不同语言,不同语言传承延续着不同文化。为了使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尽可能地理解中国文化,《生死场》的英译过程大致采取了如下技巧:
2.1 直译体现原文的文化色彩
直译是翻译策略中最常见的方法之一,顾名思义,这种翻译方式旨在保持原文与译文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直译有助于忠实传达原语言的中心思想,在保证作品具有可讀性的前提下,直译可以反映原语言的表达方式、作品背后的民族特色、甚至整部作品的风格。
以《生死场》为例,村民逐渐觉醒的民族意识是体现萧红作品抗日主题的重要部分,如村中的寡妇表达即使千刀万剐也要与日本侵略者抗争,这里“千刀万剐”被直接翻译为“be cut into a million pieces”。“千刀万剐”本用于形容人的罪恶深重,用这个词本意是要表达抗争到底的决心,因此直译出来更能直观体现反抗的决心之坚定,侧面反映出对侵略者的痛恨以及日本侵华的残忍事实。又如老赵三要在自己的坟顶插上一面中国旗子,并呼喊道:“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为了更好地还原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更淋漓尽致地体现慷慨激昂的抗战情绪,译者选择直接翻译为“I dont want to be a nationless slave.Alive Im Chinese,and when Im dead,Ill be a Chinese ghost...”译者类似的直译处理,既使得语言直白、情感充沛,也直接明了地体现了作品的抗日主题,把读者迅速领进了当时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真正做到了对读者负责。
中西文化的差别使得许多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无法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对应物,强行翻译既无益于读者理解,也使得文章赘述过多。因此对于那些《生死场》中出现的难以找到对应物的文化元素,译者选择直接异化。异化翻译是一种在翻译产出目标文本的过程译者用的翻译策略,旨在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的独特之处。韦努狄将异化翻译描述为一种“民族偏离的压力”,认为它能够“记录外来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使读者置身国外”。例如,“红枪会”指的是民国时期农民武装自卫的团体组织,因其武器多为长矛,并在长矛上系以红缨而得名,在抗日战争时期该组织迫于外国帝国主义压迫而奋起反抗。译者将其翻译为“Red Gun Society”,并未对此组织名称做过多解释,旨在让读者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作品情节,体验抗战时期特有的文化特色,而非以其为载体的某个元素名称。
为了实现文化在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译者还采用了音译的方法,用与原语言相近的声音符号代替原语言,对人名、地名或某些特定事物名称直接翻译。比如文中多次出现的“炕”,便是东北地区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是用砖、泥等砌成的床,床下有洞,可以烧火取暖。这个在东北地区极为常见之物在英文中却找不到能与之对应的单词,若直接翻译成“bed”则失去了它的地区独特性,因此直接音译为“kang”。读者能根据小说内容推测出“炕”的用处,也能感受到“kang”这一词背后的文化特殊性。语气词也是翻译中的一个难点。文中常常出现许多中式化的语气词,如“唉”“哎呀”“哎哟”等,如何处理好这类语气词,尽量使读者感受到与原语言作者相同的情绪,是译者需要重视的地方。在本文中,译者选择直接音译,如将“唉”直接翻译成“ai”而非西式的“oh”。读者能根据情节体会到角色的情绪,也对这种异国化的表达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更加体验到了异国文化色彩。
2.2 意译文字表达的文化内涵
意译是区别于逐字直译的一种翻译技巧,它指的是根据原文的大意进行翻译,而不是一字一句完全照搬原文进行翻译,只要译者能够正确翻译出原文的内容,使读者理解便可以。当直译难以化解文化差异带来的阅读障碍时,译者通常会根据原文的大意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用目的语读者更能理解的方式表达,使译文既能体现原文大意,也不会对读者阅读造成困扰。
诸多翻译实例表明,意译在体现民族文化内涵与语言特色,尤其是涉及宗教、社会习俗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文化的各类表现形式也各有差异,如果不了解原语言的文化背景,目的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极其容易根据自己文化而形成的观点对作品进行评价,若译者处理不当,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从而不能更好地了解作品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如译者在处理“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青,你们去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这句话时便采用了意译的技巧。首先,“国亡了”是很中国化的拟人化的表达方式,意思是国家受到侵略而沦陷覆灭,如果直接翻译成“the nation is dead”则是“国家死了”的意思,反而既不通顺,也不地道,并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让目的语读者也很难接受,因此译者在此将其译为“the nation is lost”,读者便能明白是国土失陷的意思。同样的,“亡国奴”一词指的是自己的国家沦陷而被侵略奴役的人,若是直接翻译成“the slave whose nation is dead”则显得十分生硬,读者无法接受“国家死了的奴隶”这一说法。尤其是西方读者可能会受曾经的殖民文化影响,从而对“slave”一词产生误解。此处译者选择将其翻译为“a nationless slave”,使读者更易理解,也与前文“国亡了”的翻译方式相呼应,前后一致。既能理解这个称呼用于国家遭受侵略而被侵略者奴役的人,也能前后呼应,从而加深对抗日战争这一主题的理解。
通常来说,译者在采用意译这一方法时,经常会通过增词或者是减词的方法进行翻译,必要时为读者解释原文内容,或省去有碍于阅读但不影响整体的细枝末节,以求更好地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这样处理也更容易被目的与读者所接受。例如,原文中有“报庙”一词,指的是人在去世后亲属会到土地庙中向土地报告其死亡的消息。译者为了向读者解释其意,选择增译的方法,将其译为“to perform the initial rites at the temples”。
3 针对红色文学跨文化翻译的思考
红色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走出去的新途径之一。通过对《生死场》这部黑龙江经典文学作品英译本的研究,本文对于红色文学跨文化翻译做出了如下思考:
3.1 红色文学传播的意义
红色文化是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协作下共同创造的先进文化。作为中国重要历史时期形成并发展的文化,红色文化不仅应深深植根中国人民的心中,还应该得到恰当的弘扬与传播,让更多人认识并了解到中国人民在那一段特殊历史时刻中的坚毅果敢、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等宝贵精神,让中国的大国形象得到正确的展示。红色文學作品是红色文化的载体之一,它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并展示革命战争时期蕴涵着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红色革命精神。黑龙江地区是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黑龙江红色文学对外传播不仅能够起到丰富世界文学宝库的促进作用,还有利于传播中国精神、树立友好大国形象。文学作品以其文学性更易潜移默化地进行作品主题与价值观的传递,因此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更易使外国读者接受,从而对中国形象有进一步的认识、了解甚至改观,这对中国在国际上与各国建立和维系友好的外交关系有着积极的作用。跨文化翻译行为凸显了语言的文化属性和交际功能,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3.2 红色文学翻译的难点
文学翻译指的是用不同语言实现原语言文化信息向目标语言读者的传递,这并非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还涉及了跨文化交际。国家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国家在宗教信仰、社会习俗、语言表达等方面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化解这些差异并搭建两方文化沟通的桥梁便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并克服的难点。以黑龙江红色文化为例,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东北黑土地上诞生的这段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性文化内涵,比如深厚的爱国主义、伟大的集体主义、敢于献身的英雄主义等精神未必能被认可个人主义的外国读者完全理解,这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很难让其他国家读者在没有历史知识储备的前提下全部认同,如若翻译不当,会直接影响信息传递交流的质量和效果,不同的意识形态、语言行为等表达易成为阻碍阅读的文化隔阂而非便于阅读的文化桥梁。
3.3 红色文学外宣的策略
红色文学作品外宣不仅是红色故事的传播,更是红色精神的弘扬。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理解、认可红色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具有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意识是指人们对与本民族文化有冲突的文化现象的态度、认识、看法以及对这种文化差异的接受、包容和适应状况。在翻译过程中要注重翻译技巧的灵活运用,将直译与意译有机结合。首先,要让读者读懂中国东北故事。黑龙江红色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东北地区特有的表达,如方言、谚语、歌谣、诗词、特定称谓、语气词等,在翻译这类表达时,译者既要让这些中式表达的含义通过其他语言得到解释与理解,也尽量展现出中式表达特有的饱含文化独特性的魅力。其次,要让读者逐渐了解、认同并欣赏黑龙江红色精神。这便需要译者忠于原文,同时站在读者的角度进行翻译,为读者提供作品背后的文化背景,注重译文的前后一致性与行文的连贯性,必要时还可向读者就某些黑龙江地区特有的别国文化较难理解的表达、观念等进行解释。
4 结语
经典红色文学作品《生死场》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注重跨文化交际的效果,采用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技巧,有效实现了红色文化的传播,让西方读懂并认可了中国的红色文学。此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对外传播红色文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并有利于国际友好交流,虽然红色文学在跨文化翻译方面的确存在难点,但善用直译与意译等技巧可以有效减轻文化隔阂,成功实现红色文学的跨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1]章海宁. 萧红画传[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萧红. 生死场[M]. 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80.
[3]XIAO H.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Tales of Hulan River[M]. Boston:Cheng&Tsui Company. 2002.
[4]方菁,郭继荣. 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翻译:时代意义与实践难点[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23):112-115.
[5]陈嘉铭. 跨文化视域下的文学作品英语翻译问题[J]. 韶关学院学报,2018,39(10):51-54.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