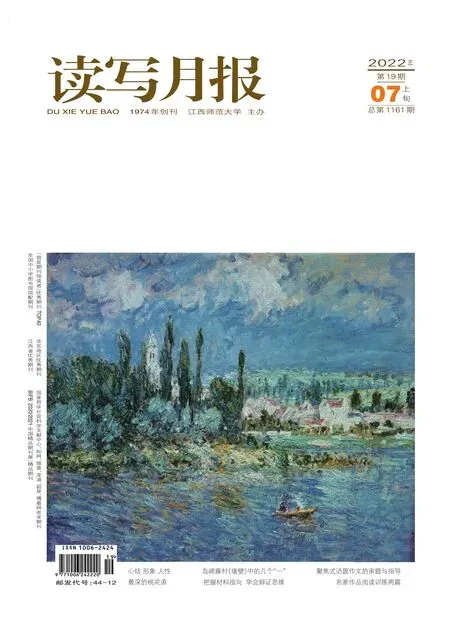心结 形象 人性——《百合花》解读的一条路径
马月亮 张丽丽

茅盾先生曾这样评价《百合花》:“一如静夜的箫声,初读似觉平凡,再读则从平凡处显不平凡了,三读以后则觉得深刻。”[1]《百合花》没有宏大的画面场景,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缘何深刻?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通过对人物内心波澜的描写,塑造了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示了纯洁美好的人性。
一、“我”的心结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我”是整个故事的串联者。面对通讯员,“我”的内心几经起伏:“生气”——“发生了兴趣”——“着恼”——“越加亲热起来”——“这都怪我了”——“从心底爱上”。
“我”生气,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通讯员却“撒开大步”“把我撂下几丈远”,“我”既有怕他“笑我胆小害怕”的顾虑,又有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有“迁怒”的意味在里面,在分配任务时,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团长抓了半天后脑勺才叫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我”的反应是“包扎所就包扎所吧!”从这勉强的语气中能够感受到那时的“我”已经有些许不悦了。
通讯员总是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一细节蕴含着作者颇多的心思,看似写“我”因好奇而产生的心理转变,实则把这个刚刚出场还没让我们看清模样的通讯员写得鲜活生动。送“我”去前沿包扎所,对他而言是一个不愿意却又不能不完成的任务。他“撒开大步”就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后文也写到“我”让他回团部时“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他一路送“我”到前沿,心却一直在团部,而且是“主攻团”的团部。文中还提到他是大军北撤时“自己跟来的”。一个年轻、稚嫩却渴望战斗的形象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足见他时刻关心着“我”的一举一动。作者对通讯员的描写并不是凭空想象的,在《˂百合花˃的写作经过》一文中,作家提到了自己跟一个通讯员去前沿的切身经历,“一上了路,他却不愿意我傍着他走,要我拉开距离,拉开距离的意思我懂,是为了减少伤亡,这是军人的常识”[2]。对此,作者在前文也做了暗示——“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因此,通讯员的行为是特定环境下关心、保护“我”的一种特定表现。
写“我”“着恼”实为欲扬先抑。面对通讯员“冷漠”的表现,“我”带着反抗的情绪坐到他对面,而他的局促不安、张皇失措却一下子消除了“我”内心的不满。“我”从反抗到接纳,内心从封闭到打开,这种瞬间的强烈的情绪反差,意在凸显通讯员的讷讷寡言、羞涩腼腆、忸怩可爱,同时也为下面“我”与他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插叙“我”对故乡生活的想象,看似多余,实则还是为了刻画通讯员这一形象:“垫”“扛”“拖”“刮打”等一系列的动作让“我”从“熟悉的故乡生活”中看到一个勤劳、朴实的小伙儿,“我”不免对他“越加亲热起来”。
“我”内心的变化还表现在交谈的内容上。从“哪里人”到“在家时干什么”到“多大了”到“怎么参加革命的”到“家里还有什么人”到“你还没娶媳妇吧”,“我”问的内容越来越“私密”,说明“我”对他越来越亲近。通讯员永远只是被动地回答,尤其是“我”问他“你还没娶媳妇吧”时,他更是“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这一系列细腻传神的描写,让通讯员的形象越加清晰、丰满、立体起来。面对被“我”问得满头大汗的通讯员,“我”自责起来——“这都怪我了”,此时“我”已经彻底接受这个年轻人了。
“借被子”的过程中,当他听了“我”的玩笑话而为是否送回被子矛盾时表现出的“认真”“为难”“好笑”“可爱”,更是让“我”“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
作者描写“我”的心理变化实有“醉翁之意”,背后站立着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形象,他忸怩、可爱、单纯、善良、朴实,不善言辞却关心别人。随着“我”的心结一点点打开,这个形象逐渐向我们走来,慢慢变得清晰。正如茅盾先生评价这篇小说时所说:“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3]
二、新媳妇的心结
新媳妇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另一个形象,她有过借被子与不借被子的矛盾,擦身子与不擦身子的犹豫。
通讯员向她借被子却空手而归,当“我”硬着头皮再去借时,她的表现也是“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看看我,看看通讯员”。这种不舍与犹豫不仅不会矮化新媳妇这一形象,反而使得人物形象愈发真实。这是“一条里外全新的花被子”,新媳妇有些不舍是人之常情。更重要的是,这是她唯一的嫁妆,“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儿,才积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这虽然是“我”和通讯员开玩笑时说的话,但应该是现实情况的真实写照。这条被子凝聚着新媳妇深深的情感,她会犹豫是必然的。从身份而言,她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要将自己唯一的嫁妆盖到陌生的男人身上,不舍之中应该还有一些害羞。想必她还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并说过类似的话,通讯员才有了“老百姓死封建”的抱怨。
当“我”要她帮忙拭洗伤员身上的污泥血迹时,她表现得更加犹豫。尽管“我”再三劝说,最后她也“只答应做我的下手”。对于一个没有战争经历的女性来说,面对伤口、血迹必然会害怕;作为一个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要去擦拭陌生男人的身体,一定会感到害羞。
这一系列的描写刻画出了一个最本真的农村女性形象,同时也是在为她崇高人性的绽放蓄势。
借被子时,她听“我”说完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后,“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犹豫过后,“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真实的内心斗争之后的选择彰显出的是她识大体、顾大局的品格。
通讯员的牺牲成了彻底打开她内心的钥匙。面对这个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别人的年轻人,她心底最美的人性完全被激活了。在“我”还在打发其他同志走的时候,她“解开他的衣服”,“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仪式,一种向英雄致敬的仪式。当所有人都已经明白通讯员的生命无法挽回时,她却“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这一针一线缝补的是借被子时她让他受气的愧疚,是他走时没给他缝上肩头的破洞的懊悔,是对这位少年英雄的无比崇敬和痛惜。
茹志鹃并没有把小说的高潮设置在通讯员舍己救人的情节上,而是设置在新媳妇献出自己被子的那一瞬间。看到有人要揭掉通讯员身上的被子,一向爱笑的她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悲伤和恼怒,“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特别是她气汹汹地嚷出那半句“是我的——”更是她内心复杂情感的最为悲痛的宣泄。当新媳妇把自己唯一的嫁妆盖在通讯员身上的那一刻,这两个纯洁、质朴、水一般清澈的形象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种光辉的人性便牢牢地交织在一起,两个高洁的灵魂如同百合花一样一同绽放。
三、作者的心结
程翔老师曾说:“大凡优秀的小说,其核心任务是塑造人物,塑造人物的核心目的是表现人性,至于表现什么样的人性,则与作家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4]
《百合花》是茹志鹃“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5]写本文时,她心中也有郁积的心结:“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6]当她面对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病、自己丈夫堪忧的境遇、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却无能为力时,便“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7],因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能使人有深交。有时仅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一个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8]。
于是,作者将“我”、通讯员、新媳妇三个素不相识的人放在一起,通过细微之处彰显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以小见大地呈现人性的真善美。《百合花》是作者情感的一种寄托,更是她在人生困境中打开的一扇探寻美好的心窗。作者想要通过这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表达对高洁美好的人性的讴歌和颂扬,对真诚的人际关系的渴望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