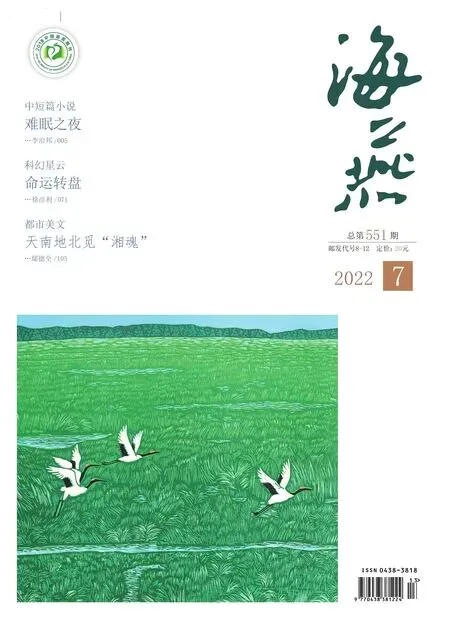铁马冰河入梦来
文 雪 归

一
你爹死了,你赶紧回家。
接到我娘的电话时,我正在为一个稿子绞尽脑汁。有个村子每到下雨天,自来水就成了浑浊不堪的泥水。前不久,我到这个村里进行了采访,就这个村的变化写了一篇通讯。我刚写完了这个村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它就出问题,实在让人头疼。
更让我头疼的是我娘。我娘从不给我打电话。每次我打电话过去,她说不了几句话便挂电话,我和她之间隔着山隔着水,还隔着无法跨越的障碍——那就是我爹。
说实在的,相对于我爹的死,我娘主动给我打电话更让我吃惊。我离家八年,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打电话。
我爹是个酒鬼,一个粗暴的、沉默的酒鬼。这个塌鼻头的矮个子胖男人,他既不爱我娘,也不爱我——他唯一的儿子。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娘爱他,爱到没有原则,爱到没有底线,爱到心甘情愿承受来自他的一切暴风骤雨。
我实在想不明白我娘为什么爱这么一个男人。我娘长得非常好看,用貌美如花来形容并不为过。村里的男人见到我娘时,眼神总会在我娘身上绕好几圈。我娘嫁给我爹,有许多人都说可惜了。但这个男人,从来没有对我娘展示出他温柔的一面,至少我和他生活的十八年里没有。
这种爱太可笑了,我替我娘不值。然而,我娘不许我说他的不是。他是你爹,我娘总是这样说。我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如果一个人甘于深陷泥潭,别人是没有任何办法拯救的。
二
我爹生前最大的爱好有两样,早年是打鼓,后来是喝酒。
我们安村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我爹对打鼓的痴迷。擂、敲、砸、刮在他这里都算不得什么。他敲鼓边,他击鼓心,他打鼓帮,他顶鼓腔,他磕鼓环,他搓鼓槌,他磨鼓钉,所有由他借助鼓槌和鼓制造的声音犹如一股气流,会从你周身的毛孔里浸入,然后聚集在丹田,再一点点汇成涓涓细流,涌向全身……
村里打鼓最好的就是张秋生和我爹。如果一定要论个高下,当然是我爹杨正泰更胜一筹。用村里人的话说,他把鼓擂活了。尽管张秋生也打得好,但总是缺一些东西。具体缺什么呢?他缺灵气。张秋生死板,每次拿着鼓槌,都是一板一眼地打,机械地打,刻板地打。而我爹不同,他的鼓槌仿佛能和你说话。每一下,都能打到人的心里。雨打芭蕉,雷霆滚动,万马奔腾,都可以来自我爹的鼓槌。
我爹擂起鼓来像神灵附体,有使不完的劲儿。鼓声时缓时急,缓时如小河水静静流淌,急时则如惊涛拍岸浪花飞卷。
村里人说我爹一分钟能打出八百多个鼓点,而张秋生一分钟只能打出五百多个。
鼓楼上,我爹先是站成马步,然后是抚摸鼓面,接着是举起鼓槌,却并不急于落下,他要缓一会儿。这个时间,或长或短,全由我爹控制。当你以为他要开始了,他绝不会开始。而当你以为他不会开始,鼓槌会突然落下,有时是一支,有时是两支。刹那间,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锵咚咚锵……
时而高亢,时而低婉,全由着他的心情。
真是神了,安村人说。那时候,每有重大活动,我爹的打鼓是唯一的保留节目,而张秋生,则是我爹的备胎。谁都知道张秋生也想打鼓,想像我爹一样打出个天花乱坠,打出个地老天荒。然而,张秋生却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只要在舞台上,我爹既是主角也是独角,他永远不要陪衬,不要烘托,他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他。
三
让所有人都想不通的是,我爹突然就不打鼓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别说打鼓,他连鼓都不摸了。不但如此,他甚至还亲自把那面鼓当着许多人的面打破了。
那天,天气好得不见一丝云彩。一切如常,没有一丝迹象显露出我爹要发疯。那时,鼓楼下有三个人围在一起打牛九,他们为四牛可不可以吃四虎吵得面红耳赤。其中一个人突然吐出一口浓痰,他侧身吐的时候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有痰星子溅到另一个人身上,正好就是刚和他吵得最凶的那一个。
这边他们在吵架,另一边,一个没人看管的小孩看见鼓被我爹搬了出来。见我爹一时不知去向,那个小孩就大着胆子想自己敲着玩一下。他小心翼翼地靠近那面鼓,怯怯地伸出手,又四下观望,踌躇不决。
天上有几只鸟拍打着翅膀飞过,一阵扑棱棱后,不知道从哪只鸟身上落下的羽毛飘飘忽忽落下来,落到鼓楼前顿了一下,又飘走了。
鼓楼右侧的一丛蜀葵红得滴血,几只蜂子绕着花朵时飞时落,心不在焉一般,却被一只蝴蝶占了先机。

插图:包 蕊
一个女人趿拉着鞋无精打采地走过,没有人敢告诉她,她男人此时正在另一个女人家里风流快活。
这个时候,我爹拿着一块石头出现了。
父老乡亲们,大家做个见证,从今往后,我杨正泰再不打鼓了。说完后,他双手将那块石头举过头顶,然后用力砸下来。
那个黑不溜秋,像上了一层黑漆似的鼓,那个由我爷爷传给我爹并一直被视为至宝的鼓,在鼓面和石头突遇的瞬间,传出闷腾的一声音响,鼓面破了一个洞,滚到了一边。
所有人都惊呆了,一如他们看我爹打鼓时的模样,似乎那雄浑的鼓点犹在耳畔。
我爹疯了。我想。
这个奇怪的、操蛋的、不可理喻的男人,我打心底里瞧不起他。
不打鼓的他,开始喜欢上了酒。以前他爱鼓如命,现在他嗜酒如命。
他喝酒倒也罢了,最让我气不过的是他喝了酒就打我娘。
酒喝少了打,酒喝多了也打,没酒喝他就吹胡子瞪眼睛冲我娘发脾气。
一个只知道打女人的男人,不配当我爹。
四
我恨这个男人。以前是,现在还是。
时间像一件破旧的外套,记忆是打在上面的补丁。
无数次我让记忆回到那个雨夜——这实在太像一部蹩脚的小说或电影。那晚,我挥起拳头,把杨正泰揍得像狗一样趴在地上,只剩下喘气的份儿。他脑袋上仅有的头发,原是从头的左边梳到右边的,此刻,那绺头发斜搭在他的额头上,让他看起来可笑又可厌。
他的衣服上沾着他的口水,他的鼻血,以及地上的泥和土。
他那么狼狈,那么虚弱,与他在台上鼓楼上的神气活现有天壤之别。
那一刻,我有着前所未有的痛快。每打他一拳,我会说上一句:让你喝酒!去你娘的!你去死吧!
那晚我娘不知道去了哪里,她刚刚又挨了这个男人的打,现在可能躲在哪里偷偷哭泣。
我娘不回来也好,我正好可以放开手脚出口恶气。我对着他倒下去的身体又补上无数脚。
就在我把他打到半死不活的时候,我娘突然从天而降。我娘当然不是突然出现。当时我沉浸在打倒他的兴奋里,完全没留意到我娘的到来。
你干了什么?你这个畜生!我娘发现她的男人倒地不起之后,她跪下去抱着他。她心疼地撩开他额上的头发,她用她的袖子擦去他脸上的污渍。她的手和身体都在发抖,仿佛挨了打的是她而不是她的男人。她生气地质问并斥责我。她脸上的肌肉在抖,布满细密皱纹的皮肤抖动的时候像风中的网。她的脸前所未有的扭曲,前所未有的狰狞。她像发怒的母狼红了眼睛,她恨不能扑上来咬我一口。这个时候,躺在地上的男人不失时机地补上一句,你养的好儿子,竟然打我。
她的愤怒于是到达了顶峰,她小心翼翼地放下怀中的男人,站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给了我一巴掌。
她这一巴掌让我猝不及防。我站立不稳向后退了几步,她又狠狠推了我一把,我一下子倒在地上。
她嚎啕大哭,仿佛有天大的委屈。我的脸上火辣辣的,我的胸口有种说不出的钝痛。更大的疼痛来自我的内心,我终于看清楚了这个女人:这个甘心承受那个男人暴虐的女人,这个女人的眼里从来只有这个男人,从来没有我。
我想起小时候她把好吃的留给这个男人,在我偷吃后还会挨她打;我想起小时候我没钱买作业本,她却给这个男人买酒喝;我想起小时候过节,我穿的是她用旧衣服改小的衣服,这个男人穿的是她扯的布做的新衣……
她的眼里,只有这个男人,哪怕这个男人打她骂她。想明白了这个,我被巨大的疼痛攫住,我的心在滴血。
我在那个风雨之夜离开了那个家。离家那晚鼓楼檐角的铃铛发出的声音像被泼了水,不再清脆。那些柱子、台阶模模糊糊,难辨轮廓。在黑夜,在风雨中,鼓楼摇摇欲坠。我期待更猛烈的风雨摧垮这个楼。
整整八年我没有回家。
我没回家,她也没找我。这就是我的娘——一个眼里只有男人没有儿子的女人,愚昧又无药可救。
五
写假条,批假,我准备回家了。在单位,他们都叫我工作狂,因为我从来不请假不休假。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请假,我的主任显出很开心的样子说,小杨啊,你早就该好好休息下了,工作重要,但也要劳逸结合。你好好休息下,才能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工作。
我笑了笑,很牵强。如果不是我娘打电话叫我回家,天知道我有多么不想回家。我不是怕面对那个男人,如果有可能,我还会再饱揍那个男人一顿。我庆幸老天还是长眼的,替我收了他。我是不想面对我娘——那个没有骨气、没有自己的女人。
我可以想象出我娘有多难过,从电话里她颤抖的沙哑的声音,我知道她肯定又哭了,而且哭得声嘶力竭。这样想的时候,我又原谅了她,我想把她接到城里,让她安度晚年。
我花两百块钱租了一辆出租车回家。
我并不是迫切地想见到我娘,我只是想缩短这个过程。另外,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爹要把他的鼓给砸了。这些年,我没问,他们二人也不提,仿佛从未发生过。
又一次经过鼓楼,鼓楼依旧很安静,破旧,沉默,苍老。仿佛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强撑着身子等待生命的尽头。
看着鼓楼,我突然发现,整整八年过去,我依旧不喜欢鼓楼。一如我不喜欢那个男人,不喜欢我娘喜欢他。
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鼓楼的倒塌,期待那些被虫子吃过的大梁断裂,期待那些破损的壁画被风吹走,期待那些破旧不堪的楼梯塌陷。
想到要见到我娘,我的心情并不激动。而想到那个男人已死,我倒是还有一点高兴,毕竟从此我娘再也不用在他的拳头下生活。
我家的大门上,门神画早已褪色,对联只剩下一边,虚掩的大门像一个瞌睡的人在张嘴打哈欠,又极力掩饰。
我推门进了院中,院中倒也如曾经的整洁有序,爬在架上的豆秧结着豆角,有的已经长老,估计是要留作种子;有的还鲜嫩鲜嫩的,正是摘来吃的时候;有的还开着花,为成为果实做着准备。院中靠墙的一角种着几排葱,地边一排是向日葵,一盘盘葵花正向着日头绽开,过不多久,它们就要结出饱满的籽实。我想起那个男人生前最爱吃这个,可惜他再也吃不上了。
我进了屋,发现家里异常安静。我原以为那个男人死了,会有不少人到我家来探望和安慰,事实却刚好相反。
我娘坐在炕头,炕上躺着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男人。
那一瞬间,我被我娘惊到了!难道她昨晚和这个死人过了一夜?这也太……
我娘看见我,一下子泪如泉涌,说不出一句话。
她的脸变得通红,尤其是鼻尖,红得透明。她的额头上沟壑遍布,她的嘴边左右各有半个括号,她的嘴角、眼角全是细密的皱纹。她变老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她远超过同龄人的衰老模样让我十分难受。她原本可以像村里其他人一样,或者选择外出打工,或者选择和我生活在一起,她却选择了在这里陪着这个粗暴的男人,直到他咽气。
我看了一眼炕上的男人,他的脸上盖了一块白布。
看看你爹吧,以后你再见不到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又哽咽了数次,说得断断续续。
她几乎是期待我揭开那块布,我也如她所愿揭开了那块白布。
那个男人看起来像睡着了。神情安详,如果不是他嘴唇发青,脸色发灰,呼吸全无,我简直要怀疑他还活着。
他怎么死的?我问。
他喝醉了,睡在这里,都怪我,睡得太死,不知道他会出情况。我娘抽抽噎噎的样子像一片风中的叶子。
我估计他是脑溢血突发,他这么胖,血压高,又嗜酒。这是他自找的,和你没关系。我说。
不是的,都怪我,都怪我。我娘说这话的时候,满眼是泪,嘴唇发抖,看起来可怜巴巴的。
这个女人,这个生我养我的女人,她的一生,几乎除了吃苦受累再无其他。我忘不掉她背上的背篓里永远是比她的个头还要高出许多的柴草,忘不掉她在地里劳作时几乎和地面平行的上半身,忘不掉忙碌了一天的她到家第一件事是给那个男人端茶倒水,忘不掉她在那个男人的拳头下瑟瑟发抖的样子,忘不了……
这些事,每次想起,总会刺痛我,让我难过又无奈。从今往后,她终于要摆脱这些了,她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我觉得应该马上通知村里人,赶紧给他办丧事。从此,她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我准备了一块木板,她和我一起把他从炕上搬到了木板上。
她已经给他换了衣服,他全身都是簇新的。新衣穿在身上,却未见得有多光鲜。此时,我不再生他的气,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让我生气了。
我去通知村里人,请教年岁高的老人怎么办丧事。
对于他的离世,他们并没有一人显出意外的样子,似乎他们早知道这一天会很快到来,而现在正当其时。
我爹的丧事,将由村里岁数最大的安大爷出面主持。他说,你爹这辈子,就是让鼓给毁了。
安大爷建议我不要大操大办,这和我想的一样。我同意丧事从简,这个男人不配我为他花钱。虽然为他花钱办一场隆重的丧事,对我来说并不困难。
我本着一切从简的原则,让繁琐的丧礼一简再简以最快的速度让他入土为安。
我娘像被抽去了筋骨,一切听从我的安排。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入土的时候,我娘再次嚎啕大哭。她说,正泰,你带我走吧。
我和两个女人紧紧拉住要往棺坑里跳的她。我实在想不通,这样的男人她有什么好留恋的。这个女人,真是愚蠢又愚昧。
六
我爹入土后的第六天,我娘要我陪她去看他。
都没到头七,娘,你好好在家养养不行吗?我说。
我睡不着,也吃不下。她说。
她的样子,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她似乎一下子垮了,人显得憔悴又衰老。
我不知道怎么劝慰她。从小,她和我就没有太多的话。她原也不是多话的人。她只会默默做事,默默挨打,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
我不得不陪她去坟地。
这个男人被葬在一块没有墓碑的坟里。
坟地离我家有一段距离。新起的坟头上光秃秃的。有人用馒头形容坟头,实在不恰当。坟头就是坟头,和馒头没有一丝半点联系。在我看来,坟头更像是金钟罩,罩里罩外,两个世界,从此天人永隔。它坚硬,无情,冰冷,一如生前的他。
这块地是他生前就看好的。他曾经给我娘说过,他死了就想在这里。这里只有这一块坟包。
他总是这样,说的做的都与别人不同。我娘说。
天阴沉沉的,浓云在天边翻滚。
此时,我娘不像以前那样流眼泪。她脸上的表情凝重又庄严。她跪在地上用手一点点培土。她的双膝沿着坟包一寸一寸地挪动,我站在一边以陌生人的眼光打量她。她身上穿着一件藏青色半袖衫,下身是一条深色旧裤子,皱皱巴巴得像一块抹布。她的头发胡乱挽了一个髻,风吹着她的碎发,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
她伸出的手臂枯干如木,手上青筋突起,手指关节异常粗大。
她的手,是她辛勤劳作的佐证。她这一生,几乎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不是在地里劳作,就是在家里忙碌。她爱的男人,从来没有给过她一点温存,她却始终逆来顺受,没有过半点怨言。
想到这里,我突然有些鼻子发酸。
你是不是还在生他的气?她突然问我。
人死如灯灭。我现在也没什么可气的了。我说。
这就对了。其实,你不知道他,你不了解他。她说。
他是我爹,但他似乎也没给我了解他的机会,除了他的拳头。我说。
你不能这么说他。她还想继续说什么,却又打住。
风更大了。一场酝酿已久的大雨即将到来。她说,我们回家吧。
她起身,连身上的土都没有拍。我给她拍膝盖上的土,她阻止我说,不用。
我们默默走路。
经过鼓楼时,她停了下来。
这时,已经有雨点落下来。她说,你爹曾在上面表演过。
我知道。
你不知道,当时他们有多风光。
他们?还有谁?
她又顿住,似乎陷入了往事,全然不顾落下来的雨。
我催她,别受凉了。
人受凉没啥,就怕心受凉。她说。
她的话让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只能拉着她快走。
雨打湿了她的衣服,贴在身上,她的头发紧紧贴在脸颊和额头上。她看起来落魄又失魂。
我们到鼓楼躲一会儿雨吧。我提议。
她没说话,但跟着我来到鼓楼前。
我们沿着台阶上到鼓楼。
这是我第一次上鼓楼。站在鼓楼往下看,视野开阔了很多。
八年过去,这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棵柳树变粗变大了,开着红花的蜀葵没有了,变成了由栅栏围着的一小片绿化带。
她随着我看向远处,幽幽地张口,我对不起他。
娘,他那样对你,你有啥对不起他的?
她艰难地咽了一口说,我真的对不起他。我想用我的后半生赎罪,没想到,他还是像以前一样拒绝了我。
娘,你在说什么啊?
你听我说,你别打断我。她说。她的语气凌厉又决绝。
我站在一边默默听她说。
她说,你爹不是你亲爹。她说,你爹叫张秋生,不是杨正泰。
娘,你胡说啥呢?张秋生?我知道啊,不就是县剧团招走的那个人吗?他怎么就成了我爹?
你听我说,不要插话。此时,她显得异常平静,仿佛在讲述一些和她无关的事情。
原来,杨正泰是我的养父。当时县剧团准备招收一名打鼓手。能够借此改变命运吃上公家饭,再不用在庄稼地里刨食吃,这当然是村里人求之不得的事。杨正泰和张秋生二人都是这个村里的打鼓手,县上要二选一。
那时候,我娘正值青春年华,她喜欢长相英俊的张秋生。她拿出所有私房钱交给张秋生让他去活动,最终,张秋生成功入团。张秋生表达感激的方式就是提前和我娘结合了。然而,接下来的现实是张秋生到了城里就和许多人所预想的一样,再不提娶我娘的事。
我娘那时有了我,她曾几次到城里找张秋生,但是张秋生给了她二百块钱后再也不见她了。
怎么办?风言风语已经传开。我娘能想到的只有死路一条。
那一天,自觉无脸见人的我娘,准备去跳河。这时候,杨正泰义无反顾地救了她。
我娘一心求死,杨正泰坚决不同意。最后,杨正泰娶了我娘,成了我爹。
我娘的命,以及我的命,都是杨正泰给的。我娘于是对这个男人言听计从,百般包容……
如此狗血的剧情,竟然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我听见我的血液在血管里汩汩的流动之声,听见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怦怦的跳动之声。我的生父和我的母亲夺去了我的养父的所有风光,他们却不知道,张秋生——我的生父,早在几年前死于一场车祸。我之所以关注张秋生,是因为他很是红火了一阵,还接受过我的采访。张秋生虽然在剧团里吃了几年所谓的公家饭,但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剧团不得不解散,团员们四处打零工维持生计,活得一个比一个艰难……
他们中有许多人羡慕还有着一亩三分地的安村人。他们中许多人老了以后的心愿,就是有一个小院,种点菜,栽点花。他们说,如果张秋生没来城里,也许还好好活着,命运可真是捉弄人。
站在鼓楼上,我有片刻的茫然。我回来原是想寻求我爹砸鼓的真相的,看着夜幕下的安村,我突然就不想要什么真相了。我深深后悔没有和我的养父好好沟通过,后悔没有亲自问一下他为什么要把鼓砸了。如今,张秋生,我的生父死了。杨正泰,我的养父,也死了。愿他们安息!
这个晚上,我想我应该再去一下那个村子,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水龙头出浑水。也许我解决不了问题,但我至少可以探究真相,而不是错过。
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锵咚咚锵……这一夜,我的耳朵里传来阵阵鼓声,似铁马冰河入梦来。
鼓声落在黑夜里的大地上,声声铿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