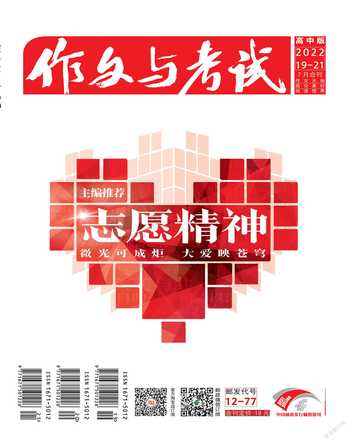北京大爷的文化沙龙
张心月
在北京,逛过的书店可谓不计其数,其中最舍不得的,是一家叫“盛世情”的小书店。
书店坐落在西城铁狮子坟公交站附近,斜对面就是北师大的东门。因为离我家里近,常常在下晚课后,去里面转上一转。
书店的门脸很小,原先的门面无奈之下,被截出一身宽,作为通道租给了一个开在二楼的美容美甲店。走进贴着降价促销的玻璃门,里面三排大书架,让空间显得更逼仄,看书的人彼此经过时,都得轻声说一句“借过您”。老板坐在把门口的老写字台后面,姓范,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这叔叔人挺瘦,但脆生的京腔,让他像一个铜锣,聊天到兴奋处,会拉长音或者挑调儿,真就像锣声一样清亮。
大爷特擅长给人推荐书。我看书一直很杂,许多门类跳着看,以获得些细碎的走马观花的快乐。常常是我插着腰站在书架前,大爷像房产导购一样,扯着嗓门给我推荐。“想看关于苏联的啊,给你推荐这个——《寻墓者说》,作者蓝英年,就是对面北师大的教授,苏联解体的时候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个大学交流,当时给国内写了一个专栏,介绍苏联时期文化名人的。这书好看,但是现存很少,快绝版了。”我还记得,在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时候,大爷特意顿了顿,似乎在等着我赞美他对细节的把控和口齿的清晰。
大爷的书店地下还有一层,两层卖的基本都是有些阅读难度的人文社科书籍。毕竟在一个泛娱乐的时代,读书人成了小众群体,用大爷夸我的话讲——“就这爱看书的,有一个算一个,我没有见过哪个年轻人这样上进的”。因为“上进的年轻人不多了”,每次一进来,看到的只是寥寥数人,地下一层更是人跡罕至。有时候我在下面看书入迷了,一抬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不太亮的白炽灯和几个顶到房顶的大书架,一时间,真有些“山中无甲子,岁尽不知年”的感觉。
大爷也会抱怨,感慨生意不好做,自己和老婆一身的病,想早一天关了这店退休。也曾问过我的意见,要不要卖些教辅,毕竟相对于社科书籍,前者利润空间大,加上附近学校多,也好卖。他妥协过,在关门前的日子,曾经把一楼最中间的书架腾空卖文具。但是他也挺固执,就是盘算已久的卖教辅的计划,到关门也没有执行。
后来我搬家了,那里就去的很少了。再后来,通过朋友得知大爷真的关门了,走的时候写了一封致读者的短信,贴在玻璃门上:
辛丑春,因近花甲,羸弱多忧,奈何子不承父业,又罹诸孽,故不再寻新址,店即关停,安度残年。
伴圣贤(书)及读者襄助三十余载,受益良多。一介尘民做喜欢且能安身立命之本,乃人生一大幸事。
书店渐远,记忆永存。愿文化殷盛,书人祥和。
评点
最近一则短讯引发网友的热议,无数疫情下的流调记录,去过的地方五花八门,却唯独都缺少书店的影子。书店曾经被视为城市的文化地标,如今自己也处于一种迷失的状态。在这篇散文中,作者也抒发了这一沉重的伤感。因为实体书店的没落,不仅是经营者的生计无着,更是城市精神生活的日渐枯索。
虽然沉重,但是作者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少了匠气的的渲染刻画和廉价抒情,而是用精练的笔法选取典型事件去刻画人物,情感表达也非常克制,这样的留白就让文章有了余味,作者不去代表读者去抒情,把抒情权、思考权给到读者,使得散文平实却亲切自然。
(指导教师:杨睿/编辑:关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