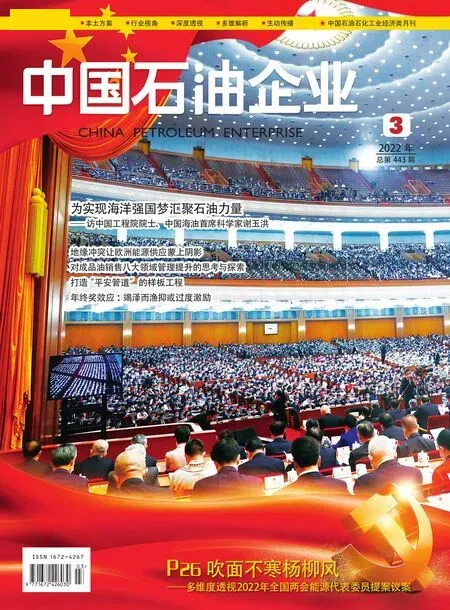“我始终都是一名科技工作者”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石油地质与构造地质学家贾承造
□ 文/唐大麟

记者:
贾总您好,您作为在企业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工作经历?
贾承造:我在石油工业的工作经历大体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经历是在新疆参加塔里木油田会战,从1987年入疆到2000年调回北京总部,前后13年时间;第二段经历是从2000—2008年担任中国石油股份公司的总地质师和副总裁,到2012年卸任中国石油学会理事长,期间兼任过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第三段经历存在交叉,从2008年开始至今,我一直担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油气开发专项的技术总师,期间从2008—2013年我还担任国家科技部973项目专家顾问组能源组组长。这三段经历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始终从事技术工作。无论是开始做具体技术研发还是后来从事技术管理工作,我始终都是一名科技工作者。
记者:
您这三段经历表面看似平常,实际波澜壮阔。请介绍一下这些经历背后您分别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贾承造:首先说塔里木会战吧,这个时期我认为主要做了三件事。首先是地质基础研究。当时塔里木盆地是个新盆地,研究程度很低,而且它的地质情况要比渤海湾盆地和松辽盆地都复杂。这种盆地类型,在我们过去的勘探中是没碰到过的。所以我去了以后做了很多地质基础的研究工作,比如说塔里木盆地的性质是什么?这个当时有不同看法。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它是叠合复合盆地,提出它应该是中浅层中新生代前陆盆地叠加了深层小克拉通盆地。对油气勘探而言,盆地性质很关键,因为它决定了油气系统,因此也决定了油气资源类型。通过研究,我们认识到塔里木盆地有特殊的叠合盆地结构,因此它有两个油气系统—一个是中新生界独立的陆相油气系统,还有一个是其底下的古生界海相油气系统。这就把根本性问题解决了。另外,我们对塔里木盆地构造地质、地层、资源评价等都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后来归结起来被统称为“塔里木盆地石油地质理论”。这套理论我们当时做的还是比较扎实的,一直到现在虽有补充完善,但没有大的变化。至今发现的油气田也是两大类型,属于两大油气系统,这说明我们当时的认识还是比较到位的,塔里木盆地的地质基础研究在油气勘探开发和重大发现突破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是对塔里木盆地勘探方向的调整。塔里木会战伊始,我国天然气工业整体规模较小,天然气勘探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会战目标是发现大油田,接替东部老油田,勘探思路还是以找油为主。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探曲折和地质研究之后,我们认为塔里木盆地是个富气盆地,其主要勘探方向应该是找气。所以从1994年开始,根据我们提出的建议,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王涛决策,塔里木勘探的方向由原来的“寻找大油田”,变为“油气并举”。我们当时同时提出库车坳陷中新生界油气系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勘探方向,所以调整部署,针对库车坳陷进行了物探和钻井攻关,前期钻探时也是困难重重,打了好几口干井,但大家坚持不懈地勘探,最终发现了克拉2气田,克拉2和其后的克深、大北、博孜等大气田。这些大气田的发现最终证实了塔里木盆地是个富气盆地,这是我们地质工作者做出的很大贡献。
再次是克拉2气田的发现和探明。我在克拉2井钻探中,经过对地质层位预测和在钻井现场的分析研判,通过一粒砂岩碎屑发现了克拉2气田主力气层,被媒体宣传为“一粒岩屑发现大气田”。在克拉2气田评价和储量计算中,我组织领导运用地质建模,山地二维地震和5口探井钻井取芯录井测试,探明了克拉2气田,申报批准了2580亿立方米天然气地质储量。这是全国最大的优质高产气田。这个气田成为西气东输工程的基础和起点,也是其后20年我国天然气工业大发展的开端。从发现到储量探明,我们前后只用了2年多时间,可以说速度极快。与此同时,我们发展了“前陆盆地冲断带陆相煤系生烃超高压大气田成藏理论”,指导了克深、大北等气田的发现,建成储量2万亿立方米、年产量250亿立方米的库车大气区。在2000年克拉2气田投产前,那时全国的天然气产量大概只有300多亿立方米,到2020年则达到了1925亿立方米,产量增长6倍多。2000年,我们在世界主要产气国里排不上名,到2020年时,我们已排世界第四名。第一名是美国年产气量约9000亿立方米;第二名是俄罗斯产气量约7000亿立方米;第三名是伊朗,比我们略高一点,年产2000多亿立方米。估计将来我们有可能会超过伊朗,成为世界第三大产气国。应该说克拉2气田的发现,对我国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它的发现促成了西气东输工程,而西气东输工程则带动了我国天然气工业的跨越式发展。
在总部担任总地质师及副总裁期间,我也做了三件事。一是在国内的勘探上,领导中国石油率先开展了岩性地层油气藏的勘探。我们过去搞油气勘探,目标主要是背斜、断块等构造油气藏。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除了塔里木盆地以外,其他大型盆地的勘探基本都遇到了困境,因为这些大盆地的构造油气藏勘探发现的差不多了,基本所剩都是较小区块,开采难度大。所以我主管勘探后,就提出要战略性调整方向,从构造油气藏转向岩性地层油气藏。方向的转变当然不能只是一句话,还得有一系列相应的配套,包括对地质规律的认识、物探钻井等勘探技术的改变等。勘探历史证实这个改变的影响是巨大的,从2003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从中国石油到中国石化,基本国内陆上勘探目标和重大发现都是以岩性地层油气藏为主,海上也已开始进入这个阶段。现在国内勘探新发现的储量主体,70%以上都是岩性地层油气藏。这个成果在2006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二是在勘探管理体制中推行了“风险勘探”,这个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并已在三大石油央企中全面推广。过去了这么多年,改革不断进行,领导不断调整,但这种勘探的管理体制却始终没变,这是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它本身是一个很先进的体制,契合目前“高难度、高风险、新领域”的勘探阶段。另外,“风险勘探”照顾到了各方积极性,能把总部机关、勘探院,以及油田各方力量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而风险由总部承担,利益由油田享有,勘探院发挥技术优势出谋划策,所以它能够长盛不衰地一直推行至今。我看过一个统计,自风险勘探推行以来到现在,仅中国石油所有的重大勘探发现里,80%以上都是风险探井发现的,比如安岳气田,就是风险探井的功劳。
三是在我分管科技业务时,大力加强了科技的基础研究力量,投入巨大资金加强了科研平台建设,新建了一批研究院所,增添了大批科研设备,这股力量也成为今天中国石油不断推进科技创新的主力。
从2008年至今,我的主要精力则放在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上,长期担任专项技术总师,即专项技术负责人,如今这项工作即将完成。这项工作开始于2006年,当时国家决定由中国石油牵头组织实施“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简称“专项”),以提升我国石油工业科技创新能力,确保油气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的实现。那时我已当选中科院院士,又是中国石油主管科技的副总裁,所以领衔的重任就落到了我的头上。立项之初,我国油气增储上产稳产难度大,我们围绕国家战略布局,以产业目标为引领,遵循科研项目基本规律,建立理论基础与机理突破、应用基础与技术创新、示范工程与先导试验、规模推广四个层次的目标体系,构建攻关内容,设立135个项目,22项示范工程。专项在技术和管理双重挑战下,探索实践了由企业主导的重大科技项目管理,建立了部委、产业、企业和项目组四级组织,分别负责专项的引导和督导、综合协调和技术指导、部署和推进、一体化执行。油气专项充分发挥技术总体组的技术统领作用、实施管理办公室的组织协调作用、实施单位的主体责任作用,形成科技攻关项目与示范工程有机衔接的“研究-示范-产业化应用”一条龙的模式。联合170余家企业、50余所高校、30多家科研院所,举全社会优势力量协同创新。作为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唯一由企业牵头组织的专项,充分发挥了行业领军企业主导重大专项的优势,成功开创了企业主导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的先例。
通过组织专项科技攻关,我国油气勘探开发整体技术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取得了丰硕的知识产权成果,已申请发明专利7892项;形成了全面覆盖石油工业上游科技领域,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组成的高水平联合攻关团队,建成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中国油气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为实现原油持续稳产2亿吨、天然气产量1925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产量和能源消费结构占比3个翻番提供了技术支撑。该专项的管理经验还被评选为第二十八届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第一名。
记者:
可以说您过去的工作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我国油气行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您认为这些过往的经历对您成为一名石油地质与构造地质学家有何影响?
贾承造:我虽然做了一些事,不一定影响深远,做事的时候也没有想着要成名成家,但确实是有些体会的。首先从初心上讲,我从来没有想着要当官,也没想着发财,而是想通过自己的所学所思做点实事报国。俗话说无欲则刚,所以我能够清清白白地走到今天。其次我一直以来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技术专家,是科学家,尽管因为工作需要我走上了领导岗位,也是一直在从事科技管理和技术研发工作。我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探索地球,而不是工作中的权力和利益,这是我的性格使然。而人类对自然的探索永无止境,我也就一直探索到终老。现在回过头再看,我的这种性格和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也帮我避免了风险。再次我觉得无论搞科学研究还是技术研发,同时,还要有广泛兴趣、广博的科学哲学基础,才能走向更高的思想境界、更远的科学未来。
记者:
您长期在塔里木盆地从事地质科研与石油勘探工作,为塔里木盆地油气开发做出了杰出贡献。目前塔里木盆地非常规、深层超深层油气资源占比逐渐变重,稳产成本越来越高,如何突破开发瓶颈,寻找油气稳产增产新支点?
贾承造:我认为要寻找塔里木盆地油气持续发展的新支点,还是要加大勘探力度,尤其要在非常规油气方面寻求新的突破。目前塔里木盆地还存在几个比较有潜力的区域。在天然气方面,首先是库车白垩系,它有2万多亿立方米储量,目前产量大概是250亿立方米。它有最好的油气富集条件,资源潜力可以达3万亿-4万亿立方米,所以这里的勘探潜力巨大。其次是库车坳陷的侏罗系,它主要在库车坳陷的东部和北部。我们当年曾在那勘探出致密气,未来一定会有新的突破。再次是台盆区,6000-7000米下面基本都是凝析油气,凝析油和天然气出来以后进行分离,这里油气同出,所以台盆区大规模开发后,它的轻质油和天然气产量也会增加。在石油方面,首先是深层勘探奥陶系和寒武系。当年我们勘探时觉得7000米就到头了,因为工程难度太大,没有经济效益。但现在无论地面条件还是打井技术都已大幅改善,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在深层超深层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其次我们要加大科研投入,加强科技攻关力度。未来随着地下勘探的难度越来越大,我们对新技术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我们要有信心通过发展新技术来提升自己的勘探开发能力,从而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量,降低成本。这一点不仅仅是塔里木盆地的个例问题,也是全国性的共性问题。
记者:
请您介绍一下我国石油工业上游发展现状,面临哪些重要机遇和重大挑战?与之相对应的技术需求有哪些?

贾承造:目前我国共有500个沉积盆地,其中含油气大盆地包括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和南海盆地等,油气资源十分丰富。含油气盆地类型多样、结构复杂,已发现的油气资源以陆相为主,构成独具特色的油气分布区。据BP能源前景研究,202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4.8亿吨油当量,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占比分别为19%和9%;2035年一次能源消费量将达到56亿吨油当量,石油和天然气占比分别为15%和13%。近10年来,我国石油年产量稳定在2亿吨左右,天然气取得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7%。2020年,我国原油产量达1.95亿吨,天然气产量达1925亿立方米。展望未来,天然气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原油产量保持稳定,占比将逐年下降。
历经70多年的艰苦创业,我国已建立完整独立的石油工业体系,满足了国家发展的能源需求,保障了油气供给安全。我国石油工业上游发展高度依赖石油科技进步。一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和工程进步,支持石油工业上游建成规模宏大、专业齐全、先进开放、初步国际化的科技研发体系。所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如陆相石油地质勘探理论和大庆特大型陆相砂岩油田开发技术,至今仍保持国际领先地位。经过几代石油科技工作者的努力,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石油行业通过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攻关,整体大幅提升了上游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目前,我国陆上油气勘探开发水平位居国际石油行业前列,海洋石油勘探生产与装备研发取得重大进步,非常规油气开发获得重大突破,石油工程服务业的装备技术实现自主化,常规技术装备已全面国产化,并具备部分高端技术装备的研发和生产能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我国石油工业上游发展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主要包括未来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油气需求和保障油气供应安全的挑战、石油长期稳产2亿吨/年以上的挑战、天然气产量上升至3000亿立方米/年并长期稳产的挑战、海洋及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先进技术与装备的挑战、新一代石油工程服务技术装备和数字化转型的挑战等。中国应大力实施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解决油气勘探生产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努力提升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形成新一代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系列,使我国石油工业上游2035年达到全球领先技术水平。支撑国内石油产量长期稳定在2亿吨/年,天然气产量上升至2600亿-3000亿立方米/年,并长期稳产,支撑我国石油企业全球业务重点在“一带一路”的发展,支撑我国油气技术服务行业成长为国际领先的服务与制造产业,全面满足国家社会经济未来高效发展的能源油气需求,保障国家油气安全。
目前,亟须重点攻关的技术需求有6个方面,分别是:石油大幅度提高采收率技术、大气田勘探与复杂气田提高采收率技术、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海洋及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技术与装备、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新一代石油工程服务技术装备和数字化转型等。
记者:
经过半个多世纪高强度开采,我国易开采油气资源已消耗殆尽,在双碳背景下,我们要不要继续开采自己的油气资源?我国未来油气勘探开发的技术路径是什么?

贾承造:目前我国的石油工业正面临几个问题。首先就是能源安全问题,这也是非常重大和关键的问题,而且我们的能源安全实际上非常脆弱。其次就是能源转型问题,现在关于双碳以及能源转型的声音非常多,而能源转型本来是个很漫长的社会发展问题,它取决于替代能源的规模、价格、技术条件以及可持续性。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石油天然气目前不仅是主要能源,而且这种现状未来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国的石油工业界要有定力,要踏踏实实的把国内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搞上去,坚持不懈地发展新技术,以实现油气稳产增产,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具体来讲,我认为有六大技术发展方向。一是发展大幅度提高石油采收率的技术。我国目前已开发油田的动用地质储量为286亿吨,地质储量采出程度为22%,剩余地质储量为222亿吨,主要集中于中-高渗透油藏、低渗透油藏、稠油油藏和缝洞型碳酸盐岩油藏4种油藏类型中,平均标定采收率为29.5%,亟待技术创新与突破。通过高效挖潜和大幅度提高采收率,我们也可实现老油田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发展大气田勘探与复杂气田提高采收率技术。我国陆上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约为40万亿立方米,累计探明地质储量为8.2万亿立方米,已开发动用探明地质储量为5万亿立方米,具有持续增储上产的发展潜力。为应对大气田发现难度增大、气藏提高采收率技术储备不足、缺乏先进的储气库建库技术等重大挑战,我们需要重点攻关大型气田勘探、复杂气藏高效开发与提高采收率、新储气库建设与优化运行等三方面关键技术。三是发展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技术。非常规油气具有储层致密、孔隙度和渗透率极低、油气赋存状态多样、大面积连续分布、仅通过水平井体积压裂改造才能取得经济产量等特点。目前,我国非常规油气开发关键技术已取得重大突破,但关键核心技术及效率成本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差距,需要持续攻关,研究快速准确地找到“甜点区/层段”、精准布井和高效储层改造、大幅度提高单井产量及采收率,以实现低油价下非常规油气资源的规模建产及有效开发。四是发展海洋及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技术与装备。海洋及深水油气勘探开发需要重点针对深水勘探技术与工程技术装备、海上稠油开发及提高采收率技术、近海低渗透天然气勘探开发技术和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开发技术进行攻关。并通过持续攻关,推动海洋物探、钻井、测井、工程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深水工程装备国产化;同时使海上深层油气勘探取得重大突破,低品位油气田得到有效开发。五是推动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升全球获取油气的能力。通过研发全球油气资源信息系统,我们已基本明确了全球油气地质和资源分布规律,集成创新了复杂裂谷盆地、含盐盆地和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的油气地质理论与勘探技术,初步实现了海外油气勘探开发从国内成熟技术集成应用到特色技术创新的跨越。未来,围绕“一带一路”含油气盆地勘探开发,需要攻关的关键技术包括油气资源评价与投资选区、碳酸盐岩油藏注水注气提高采收率、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深水-超深水勘探开发等。六是发展新一代石油工程服务技术装备和数字化转型,从而降低油气开采成本,提高采收率与劳动生产率。
记者: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工作结束之后,您有什么新的工作计划?
贾承造:我将长期固守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科技研发领域,服务于公司勘探开发业务发展,为公司海内外勘探开发重大技术问题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咨询、顾问工作。同时,我计划继续做一些学术研究,初步有两个方向。一个方面就是继续对“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的研究,这是我2005年提出的一个新科学观点。这个体系是一个巨型陆内盆山体系,是我国新构造运动的重要单元,面积达到550万平方千米,包括塔里木、准噶尔、吐哈、柴达木、酒泉、四川和鄂尔多斯等沉积盆地和天山、昆仑山、祁连山、秦岭、龙门山等山脉。它是巨型挤压性陆内盆山体系、是印度-欧亚大陆碰撞及持续推挤运动的结果,我国古亚洲构造域小克拉通拼合的软弱基底是构成盆山体系分异的内因。该盆山体系是全球最大的陆内盆山体系之一,具有独特的地质结构与地球动力学特点,应该与青藏高原一样受到重视。关键是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的盆地群具有良好的油气地质成藏条件,蕴藏着我国将近90%的天然气资源,其内部的含油气盆地群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气富集区,有望成为世界级的大气区,所以我们应该加快对其的勘探开发与科学研究。
另一个方向就是对石油天然气地质学理论的改造。非常规油气的出现,对经典石油天然气地质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冲击,它证明传统的含油气系统理论仅包括常规油气,没有包括非常规油气,因此具有重大缺陷。我们目前正推动“全油气系统”理论的建设,全油气理论将包括:烃类生成演化全过程与含油气盆地地球动力学过程;全油气系统内因为储层致密程度差异形成两个流体动力场,浅部为浮力成藏的常规油气达西流动场,深部为自封闭作用成藏的非常规油气局限流动场;全油气系统统一油气成藏事件中常规油-致密油-页岩油序列沉藏规律;非常规油气自封闭作用成藏机理与局限流动场特征;常规油气浮力成藏与达西流动场特征。
记者:
您心目中的“石油科学家精神”是什么?
贾承造:关于石油科学家精神,我想首先还是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它的核心就是爱国奉献,这也是我们石油人血脉中的底色。石油行业的科学家,更应该热爱石油事业,热爱石油科技,并且有把我国建设成世界油气科技强国的信心和决心。第二是科学精神,石油科学家要热爱科学,崇尚科学,追求真理,不图虚名,不图私利,还要志存高远,追求一流,通过我们的努力,早日让我们的石油工业走向全球,成为世界石油工业中的一支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