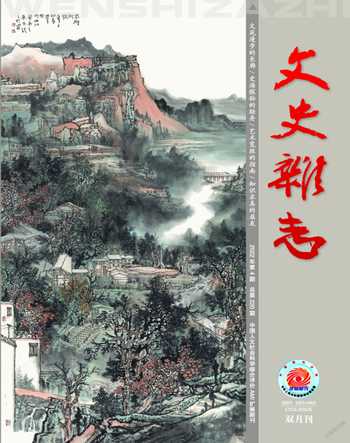关于推进三星堆文化研究的思考
屈小强?李殿元?段渝
摘 要:
《三星堆文化》在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2020年10月—2022年5月)大体完成、发掘报告尚待出来之际推出修订本,适逢其会。在此,我们对八个坑的一些具有神秘性或迷惑性的问题(包括丝绸、陶三足炊器、面具、货币、青铜文化、三星堆文明等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对三星堆文化今后的研究方向,我们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着手进行:一、继续建构三星堆学;二、深入研究青铜器、金器和丝绸文化;三、坚持比较史学、比较考古学的路径;四、让三星堆文化走进大众。
关键词:
修订;解读;丝绸;金面具;奇奇怪怪;大众化
1986年夏秋之交,广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以满目的沧桑和绚丽横空出世,震撼了世界。它从容而坚决地揭示出三千多年前长江上游一个偌大古国、古城、古文化的恢弘面貌,令川人倍感自豪、国人备添自信、人类充满遐想。两年后,国务院即公布三星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届耄耋的张爱萍将军欣然为之题词:“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与此同时,我们一群当时尚属中青年的学人集合在锦江之滨,以舍我复谁之概,自觉担当,砥砺切磋,焚膏继晷,终在1993年仲春时节完成第一部探讨三星堆的理论专著——《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亦紧锣密鼓,快马加鞭,于年底将其付梓面世。一年后,它即为川人捧回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又过了28年,即2020年10月—2022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二度大发掘,以六个祭祀坑的美丽景致向世界又一次证明:三四千年前的成都平原原是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坐标系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
一、缘起: 《三星堆文化》的修订适逢其会
三星堆文明的生成、发展史是地方文明演进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模式及总体格局的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范例;同时,它也是地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进行碰撞交流并在这一过程中丰富自己、壮大自己、发展自己的一个最具创造力的典型。其实,这也是近30年前《三星堆文明》一书的中心内容及核心观点。30年后回过头来再加审视,它的内容、它的观点并未过时,依旧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当年它在“绪论”里指出的“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十大论争”,后来取得一致意见者并不多;它所发表的“三星堆文明研究展望”,虽已化为学者们在30年间的工作,却仍在进行中;它所提出的关于“三星堆学”的建构,以后并未有大的行动,更不用说形成整体框架了。
鉴于此,面对三星堆新一轮(六个祭祀坑)考古发掘的大体完成、发掘报告还待出来,学者们正忙于观察、鉴定、思考,大众则正以渴求的眼睛、浓厚的兴趣翘首以盼,希冀获得更多解读或答案之际,推出《三星堆文化》修订版,虽说不上暗室逢灯,但起码是适逢其会,或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可以给人知识、给人思路、给人获得感与新鲜感——尤其是对未曾读过原版的年轻考古人和年轻研究者以及对三星堆文化缺乏了解而迫切需要了解的一般读者。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将一号坑器物埋藏的年代推定为殷墟一期之末与殷墟二期之间,器物本身的年代约在殷墟一期;二号坑器物埋藏的年代应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器物年代大致在殷墟二期范围内。[1]对新一轮发掘出的六个坑埋藏年代与器物年代尚待考古工作者的测定、研究而定(据央视2022年6月13日报道,考古队对三、四、七、八号坑埋藏年代的碳-14的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前1012年)。这大致在一两年内才会有结果;但对三星堆器物(包括新一轮发掘的器物)内涵、性质的界定,制作工艺、材料来源的判断,关联、影响的论定,恐怕还要等待更长时间。下面我们将对八个坑所显示出的几个具有神秘性或迷惑性问题的理解抛砖于此,以期为读者阅读新版《三星堆文化》作个提示。
二、解读: 对三星堆若干问题的看法
1.丝绸问题
在三星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先是在四号坑出土一块长宽约3.8×3.1毫米的丝绸残留物,继而在八号坑又出土更大面积的丝绸残留物,尺寸为18×8毫米。此外,在三、六、七号坑亦发现丝绸残留痕迹。在此之前,考古工作者还在1986年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物上发现同类痕迹。[2]这说明,三星堆文化时期,人们的衣饰,普遍采用丝绸,至少上层人士是如此。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疑是国王或巫师的形象)身上的三层华服,最外层的深衣及法衣可能属于丝绸质地。大立人像描摹的是“一位身着‘衮衣绣裳丝绸华服的领袖主持隆重祭典的场景”。三星堆出土的青銅人物雕像的服饰多姿多彩。四号坑出土的三件扭头跪坐人像的服饰纹样(手、腿上的可能是文身纹样)就有交错V形纹、羽冠纹、燕尾纹及歧羽纹。研究者多认为,这三件扭头跪坐人像大致属于下层人物,所以其服饰或许不是丝绸。不过,对已发现的丝绸残留物的分析,其组织结构大概有平纹和斜纹两种;品种则有绢、绮和编织物等,其中绮为平纹地起经浮花(即“织素为文”)的提花织物,为较高档的丝织品。[3]
三星堆在七个坑中发现的丝绸残留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成都平原是丝绸文化的一处发源地和繁盛地。而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汉代蜀锦护膊以及《史记·大宛列传》记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邛竹杖与蜀布事,则说明古蜀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走上外向贸易和文化传播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今人所讲的蜀布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蜀锦护膊不在这条线路,而在北方丝绸之路上,说明蜀人对北丝路的凿空也有贡献。)而这条道路,早在夏商之际就已开通,所以西亚的青铜雕像、金杖文化得以影响到三星堆文化。
2.陶三足炊器问题
在四川各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陶质、青铜质的炊具与酒器,其中仅青铜酒器(以三星堆青铜酒器为代表)就达上百余件,包括罍、壶、尊、觯、钫、缶、彝、鍪、勺等,多带有中原风格。这应当是模仿中原礼制,反映出巴蜀文化见贤思齐的品格;同时也说明其时社会经济的繁荣,餐饮生活的富足。不过在这里面,三星堆有一件1986年出土的商代陶三足炊器引人瞩目。三足为袋状,中空,与口沿相通,盛水用;三足下烧火,使水沸。其高44厘米,口径19.7厘米;三足部分与北方红山文化(距今5000多年,主要在辽宁、内蒙古)、龙山文化(距今4500年—4000年,主要在山东、河南)、齐家文化(距今4000年,主要在甘肃)的三足袋鬲相似。上半部分类似今天川人的泡菜坛子,不过坛沿盘极宽大,盘径38.5厘米,远远超过一般泡菜坛子的盘径。经我们计算,三星堆陶三足炊器沿盘的实用面积约为858.9平方厘米。这么大面积的沿做什么用呢?既是炊器,则可以推想这沿盘应是用来盛放菜肴的。联想到川渝各地(如成都、万州、忠县)出土的东汉庖厨俑面前案板上堆放的鱼、乌龟、猪头、羊头、鸭子、葱、姜、蒜甚至饺子等食材、食物,三星堆三足炊器的沿盘上也一定是琳琅满目的馔食吧!5A658E7D-0967-48DC-9A56-A34935DEEDF6
三星堆的这件三足炊器,在全国同时期及之前的陶器群中属于另类,可谓仅此一件,这便愈显宝贵。它是古代四川人民在烹饪器具、烹饪方式上的一大创新。它或许是中国最早的火锅(涮锅)吧?
3.面具问题
2021年6月23日,在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一件青铜大面具,其宽131厘米,高71厘米,深66厘米,重65.5公斤。35年前,在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著名的纵目人大面具,则宽138厘米,高66厘米,重80公斤。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还出土十几件金面具,其中比较完整的一件是三号坑出土的,宽40厘米,高27厘米。而1986年于二号坑出土的四件金面具则紧贴在青铜人头上,据研究,其黏合剂为土漆。早年在三星堆遗址就出土有雕花漆木器。这说明,三星堆古蜀工匠已十分谙熟割漆、生漆加工、制胎、上漆等一整套髹漆技术。它们显然是以后数千年名噪天下的蜀中漆工艺的先声。1916年,朝鲜平壤附近的古墓中出土了一批蜀郡和广汉郡的竹木漆器,其中最早的印记为西汉纪年。
三星堆八个坑出土的七八十件面具,除了青铜面具、黄金面具外,还有兽面具。三星堆面具中的大者如前所述,宽138厘米,小者宽50厘米—20厘米。过去西方研究者总是将考察面具文化的主要视点放在古希腊与古埃及上。至于亚洲的面具,有的西方研究者认为,其最早产生于印度;中国的面具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但是,中国考古工作者与民俗学者却在中国史前文化遗址里发现了大量的面具形象;特别是在公元前1500年—前256年的商周青铜器中,发现了大量耳部或顶部开有孔洞(用于悬挂或穿绳索)的青铜面具。它们主要分作中原系统与巴蜀系统两大部分,尤以三星堆面具为代表的巴蜀系统为大宗,最具代表性。它们以无可置喙的实证有力地说明,中国面具文化既与古希腊、古埃及的面具文化不同,更与印度面具文化有别。中国面具文化渊源有自,个性鲜明,自成一统。中国也是人类面具文化一个古老而辉煌的摇篮。
4.货币问题
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海贝4660余枚,[4]新一轮发掘亦出土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可能是从印度洋至西太平洋的广阔海域辗转而来。它们背部大多磨有穿孔,便于穿线为朋(郭沫若说“朋必十贝”),这是海贝用作货币的一个特征。当时的蜀人可能用海贝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即货币。三星堆海贝反映了古蜀人与中原以及沿海地区甚至海外进行经济交流的盛况。
在三星堆二号坑还出土四枚仿海贝形态的有环铜贝。1953年和1971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与山西保德林遮峪村晚商墓曾出土过100多枚无文铜贝,钱币史专家朱活先生认为它们是中国最早的金属币。而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在“中国古代钱币”条下则判定说:“中国的金属铸币出现于春秋末期”,即晋和周使用的空首布。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三星堆祭祀坑》一书将二号坑器物的年代定在殷墟二期,约当武丁后期—祖庚—祖甲时代,即公元前13世纪下半叶至前12世纪上半叶。这也就是说,在考古文化的时间上,三星堆铜贝早于晚商铜贝约莫一个世纪(或至少与之持平),早于晋、周空首布七个世纪,亦早于被誉为“西方金属铸币之祖”的小亚细亚的吕底亚(Lydia)金属币(公元前7世纪中叶发行)达五六百年。不过,这一切须建立在三星堆铜贝果真是货币的前提下。而对三星堆铜贝是否具有货币职能,则尚无定论,还需要深入研究,并期待在以后的发掘中或有更多的铜贝出现,以获取丰富的证据。
5.青铜文化问题
1986年三星堆两个坑出土青铜器九百余件,[5] 2020年—2022年新一轮发掘的六个坑,则出土一千二百余件。其类型有大型青铜雕像群,包括大立人像、扭头跪坐人像、倒立神人顶尊像、尖帽立人像、大立人神兽、虎头龙神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神坛、神树、动物雕像、海洋生物雕像;青铜礼器,如尊、罍、盘;青铜兵器,如三角形援无刃锯齿无胡戈;青铜杂器,如轮形器、龟背形网格状器等。其中2021年9月公布的三星堆四号坑出土的三件扭头跪坐青铜人像,“小腿腿部肌肉紧绷,线条优美,体现出整个人是在用力蹬地的状态”;而其扭头合掌、怒发冲冠状,颇具个性,呈怒目金刚的神态,表现出处于下层的民众(或者是奴隶)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愤怒或蔑视的强烈情绪。中国文化艺术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风格,早在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上,就已崭露锋芒。
三星堆青铜礼器的大多数造型,反映了与商代中原文化或者与长江中游荆楚、陕西汉中、安徽阜南等地同期文化相一致的特点,但又不乏地方特色,如八鸟四牛尊。
三星堆青铜神树群中最大一棵经复原后,通高达396厘米。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形体最大的一件青铜文物。
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通高260.8厘米,不算底座则高180厘米。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所见到的年代最古老的青铜立人像。它在制作工艺上所采用的范铸法,也远优于距今约4300年的古埃及第六王朝法老沛比一世父子铜像的分段打造法。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是古蜀青铜文化和古代中华青铜文化的代表作。
商代后期,青铜文化审美艺术及铸造技术得到很大提高,其以安阳殷墟、安徽阜南、湖南宁乡、江西新干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典型代表。尽管如此,商代的青铜器铸造业仍主要以制造兵器、生产生活工具、礼乐器为主;成批制造青铜人像乃至形成青铜雕像群的记录,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揭露出来以前,还未出现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广汉三星堆遗址两次大发掘所出土的造型各异的大批青铜人像,才会一而再地惊动天下,在世界东方树立起古蜀青铜文化的鲜亮旗帜。它既有别于古埃及、古希腊的青铜文化,亦有别于黄河青铜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的其他同期文化,比如新干大洋洲的青铜文化。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最直接的意义,是将典籍所述发轫于秦始皇“金人十二”的中国青铜人像造型艺术史,上推了近一千年,填補了中国造型艺术史上早期无青铜人体艺术品的空白。它坚强地印证了古蜀人在三千多年前立足于长江上游西南腹地而面向黄河、面向长江中下游、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创造性与无比的自信力。5A658E7D-0967-48DC-9A56-A34935DEEDF6
三星堆青铜文化中的大型神树、大型立人像、大型神坛以及金杖等,在国内同期出土文物中乃属仅见,但是,在古埃及、古西亚、古爱琴海、古印度文明中,青铜雕像、青铜或黄金神树、金杖等,却并不鲜见。它们的典型器物,在时间上都比三星堆青铜文化早。它们除了神权与神祀的意义外,也兼着王权与礼祀的意义,就这点来看,三星堆文明里或许含有外域文化的因素,值得研究。
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铜、锡、铅等原料,有可能来自于今川西龙门山地区,或说今滇东、黔西地区。另有学者指出,包括三星堆、宁乡、吴城、新干、城洋在内的青铜器群,均使用了殷墟青铜文化广泛使用的高放射性成因铅。这说明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的确有紧密的沟通。
青铜器造型内涵以及器物原料、工艺、冶炼技术的早期面貌一直是考古学的一个重大课题。(比如原料来源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即成谜——现今中国境内并没有此类铅同位素的铅矿。)三星堆遗址的两度大规模发掘出的青铜器群,以其大量造型特异而富于魔幻色彩与写实主义以及创造精神的各种形态,令世界惊讶不已。三星堆青铜器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青铜器”也因之被推为“2021年历史学研究十大学术关键词”之一。青铜器在三星堆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国际的过程中功莫大焉。
6.三星堆文明问题
一般认为,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当具有三要素,即金属、文字和城市,有的还加上礼仪性(祭祀)中心,甚至手工业、农业和围绕城市的乡村等条件。用这些标准衡量,三星堆古蜀社会已是文明社会,应当没有问题。较有争议的是三星堆时代有无文字。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及玉石璋上,发现有刻划符号,它们同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陶纺轮上的刻划符号属于同一类型。或可说,三星堆和十二桥的刻划符号,当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方块表意字的上源;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方块表意字,则应视为对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刻划符号的继承、发展和演化。我们相信,随着三星堆遗址的进一步发掘,是会发现能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即或真无这样的文字,也不要紧——三星堆社会的文明状态就真实而清晰地摆在那里,谁也无法否认。南美洲著名的安第斯文明(公元前16世纪—公元16世纪)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但却给后人留下了马丘比丘、库斯科城、太阳神庙以及独特而富有创意的制陶、冶金、纺织、建筑和发达的种植业及灌溉技术。又有谁能因为它未见有文字而剥夺它“文明”的称号呢?
1995年—2003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成都平原陆續发掘出包括新津县龙马乡宝墩古城、都江堰市青城乡芒城古城、温江县万春乡鱼凫城、郫县古城乡郫县古城、崇州市双河古城、崇州市紫竹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在内的史前古城址群(前六个古城作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于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前1700年;2001年2月,又在成都西郊金沙村发现了年代略晚于三星堆遗址的商周遗址。它们像众星捧月一般,拱卫着距今约莫3500年的三星堆古城址。三星堆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其中三星堆古城墙内的中心范围约3.6平方公里。其规模庞大的城墙体系、众多的建筑遗址以及从八个祭祀坑出土的造型宏大、工艺成熟的两千多件青铜重器、金器及大批玉石器,再加上它们所显示出的较为发达的城乡分化、阶级对立与社会分工,足以说明当时的三星堆地区已拥有城市、青铜器、大型宗教祭祀中心(甚至可能还有文字),已拥有比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以及文化艺术和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王权—神权体系,呈现出一种“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清晰面貌。它告诉人们,这里就是古蜀文明的源头(至少也是一个主要源头),这里就是古蜀文明的一个爆发点,这里曾拥有一个光彩夺目的可与同时期任何一处文明(包括中原殷墟文明)媲美的早蜀文明——三星堆文明。它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一期文化的绝对年代距今4800年—4000年),下迄商代晚期(三星堆一号坑器物年代距今约3300年,二号坑器物年代距今约3200年,三、四、七、八号坑的埋藏年代则大约距今3153年—3034年),时间跨度一两千年之久。这是在今天的四川腹地内土生土长起来的属于古蜀社会的发达的奴隶制文明。它有着自身的发生背景和发展规律,自成体系,特色鲜明,富有创造性与生命力。过去人们常说的从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的蜀文明,当是对它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它在夏商之世,以成都平原为辐射中心,其影响向北曾达至汉水流域与渭水上游,向东远及今宜昌长江两岸,向南向西则深入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流域(在上述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与三星堆古蜀文明面貌相类甚或一致的文化因子)。此外,它还通过包括古栈道、古长江及其支流水系、古蜀布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中原文明、荆楚文明、吴越文明、滇濮文明以及南亚文明、西亚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海文明等诸文明的优秀成分或合理因素大方地采借过来,用来发展和壮大自己。因此,三星堆文明—古蜀文明虽地处四川盆地,周围大山环抱,却并不封闭四塞,并无“盆地意识”。可以说,它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开拓性、创造性,同当时中国及世界其他先进文明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三、展望: 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方向
1.继续建构三星堆学
一般认为,一门学问能否成为一个学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应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二是应有独立的理论及方法;三是应有独立的知识系统。可以说,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的成熟之果,但并非凡是研究最后都能形成学科。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里提出“敦煌学”的概念,就包含了上述三方面的内容。陈寅恪的初心,是要将中国学者对敦煌遗产的研究,发展成一门独立的敦煌学学科;但是直到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学科建设才告大体完成。其间经历了数代人的薪接火传,其含辛茹苦,艰辛劳劬,可想而知。我们在1993年提出建构三星堆学,至今也近30年,却仍在学科建设的路上。其间原因,一没有当年敦煌学人的紧迫感,二没有当年他们的团结一心,三没有当年他们的坚韧不拔与吃苦精神。我们面对三星堆遗址八个坑出土的一万四千余件编号文物,应像当年敦煌前辈一样,勠力同心,砥砺奋发,“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蔚成“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语),以不辜负三四千年前三星堆蜀人给我们留下的那一大堆令人疼爱的宝贝。当然,要达成此事,除了研究者的单兵作战以外,还须集中力量办大事。当前,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已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正式揭牌成立(2022年3月19日)。在此基础上,可否于省社科院或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三星堆文化研究院,就像神话研究院(2019年6月14日在四川省社科院成立)那样,组织精英力量,制定战略规划,克难攻坚,形成包括专著(如三星堆学概论、三星堆学大辞典、三星堆读本、相关考古报告等)、期刊、定期或不定期简报以及文物保护、学会(或研究会)、定期学术研讨会、媒体报道等工作。当年陈寅恪期盼清华大学成为全国学术研究的重镇。在四川,省社科院、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是三星堆研究的重镇。四川甚至海内外的三星堆研究者可以以它们为研究中枢、为大本营,在它们的大旗下去研究三星堆文化、宣传三星堆文化、传播三星堆文化,并由此形成一系列成果。5A658E7D-0967-48DC-9A56-A34935DEEDF6
2.深入研究金器文化与丝绸文化
在三星堆的新一轮发掘中,尤以青铜器、金器和丝绸残片引人注目。对青铜器,省社科院已专设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拟定8个课题展开深入研究。这里便只说金器和丝绸。
三星堆一、二号坑共出土金器65件,新一轮发掘则在三、五、七、八号坑里出土543件金器(另有大量金珠),前后六个坑合计金器608件,其中以一号坑的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三号坑的金面具(宽37.2厘米,高约16.5厘米,重约100克)最为出彩。因为在同时期的考古文化中,还未发现如此多的金器,且如此神秘、怪异!而同时期或此前的“半月形地带”(东起大兴安岭南段,沿长城一线西抵河湟,然后向西南弯折,沿青藏高原东侧南下,直至云南北部)的其他居民也没有这样的用金传统。因此,研究者身上的担子不轻,要获得合理的、科学的答案,讲清三星堆金器的内涵(如用黄金贴面的意蕴,雕有穿箭鱼、鸟和太阳冠人的金杖的意义,五号坑出土的金斧形器与大批小金珠的用途)与古蜀政权、祭祀礼仪以及社会生活的关系,是很有挑战性的。还有,三星堆蜀人所用金器的原料采自何处,是采自龙门山地区的河金或盐源的砂金吗?像直径仅1毫米左右的圆润的小金珠是怎样成型的?又是如何将其提炼到99%的纯度的?用的是什么燃料(其时不可能用煤)使黄金达到1064.43℃的熔点?炼金(包括冶铜)会使用什么样的鼓风设备?三星堆是炼金、冶铜的第一现场吗?……这些都是有趣而又必须下功夫的课题。
新一轮的三星堆发掘,除了五号坑未发现丝绸痕迹外,其他五个坑都有发现,且还有弥足珍贵的丝绸残片。在三星堆一、二号坑的青铜器物上也有类似残留物。与三星堆青铜器大量使用丝绸包裹相类,1976年在距今3200年的殷墟妇好墓青铜礼器上亦发现四十件左右的丝绸包裹物。同时期的这种丝绸包裹青铜器入坑的现象的文化意义是什么?再者,二号坑青铜大立人像的服饰,也显然是华贵的绸料。那么当时的服饰文化有哪些特点呢?那时的衣上繁华是如何形成的?联系到1980年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18件陶纺轮、14件石纺轮,2012年至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四台西汉提花织机模型,三星堆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真是遍地蚕桑、户户机杼么?其生态环境如何?能否在成都平原或盆地其他地区(如盐亭)甚或川西北高原4000年以上的考古地层中找到丝绸痕迹?须知在距今85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村、距今5300年的郑州荥阳青台村、距今4700年的良渚文化钱山漾等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的七八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发现有丝绸残留物。与此相应,印度学者也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哈拉帕和昌湖—达罗遗址的青铜器表面发现蚕丝纤维。国内外的4000年以上的遗址均有丝绸残留物的发现,它们同三星堆遗址的丝绸是否同一路数?是谁影响了谁?或者说均是各地的独立发展,并无先后影响之分?蚕桑丝绸问题涉及到具体种植、具体工艺、具体传播方式与传播路线,考古工作者恐难单独完成,可以与有关方面(如四川农科院、四川农业大学、中国丝绸博物馆、四川丝绸博物馆、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协同作战,共解三星堆丝绸文化之谜。
3.坚持比较历史学、比较考古学的路径
比较历史学、比较考古学不是历史学、考古学的分支,而是一种方法或路径。比较历史学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归纳、确立的。在中国,梁启超、陈寅恪等很早就在使用它了。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就运用比较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佛教文献,将域外之文与中土之文相互参证,以解决印度佛教文化如何影响中华文化的问题。而比较考古学的概念,则是李学勤于1991年在《比较考古学随笔》(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版)一书里提出来的。我们在1993年出版的《三星堆文化》一书走的就是比较史学、比较考古学的路径,对三星堆青铜文化、面具文化以及金杖等与中原、与西亚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了较为客观的结论。通过编纂《三星堆文化》,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将立足点置于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更高处,才会看见浩瀚广阔天地中的人、物、事潜伏的连接点与隐形的关联线索,从而作出更能揭示本质、更符合科学与逻辑的论证。所谓“居高声自远”,正是这个意思。
三星堆以大立人像、神树、扭头跪坐人像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以纵目人面具、黄金面具为代表的面具文化,以黄金面具、金杖为代表的金器文化在殷商时期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中鹤立鸡群,个性张扬。1986年当三星堆二号坑的大立人像、纵目人面具等文物出土时,人们就大为讶异;到了2021年六个坑的各色文物再惊天下时,人们都目瞪口呆了,呼之为“奇奇怪怪”(如三号坑出土的“飞天”造型)。我们将其与同样表现怪异、不可思议的墨西哥北部玛雅文明遗存、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等比较,就会发现都在北纬30度-31度之间,由此捕捉到文化、地理的参照坐标,从而对三星堆文物的怪异特征进行世界视域与哲学视域下的合理解释。当然,这种比较不仅仅是跨地理的比较,而且也应是跨文化的比较。毕竟三星堆文明與同纬度的上述文明相比,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文物在夸张性、宏大性、独特性上却是一致的。它启示我们:在这些同纬度文物“奇奇怪怪”之下,都隐藏着一个宗教—礼仪(祭祀)的宏大主题、庄严内核。这既是催生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的一个作用力,也是三星堆文明的一个生长点。
比较史学、比较考古学应该是破解三星堆之谜的一把好用的钥匙。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科学地运用好这把钥匙,将三星堆文化—古蜀文化拿来与包括殷墟文化在内的各区域的考古文化、历史文化相比较,与域外文化相比较;在四川范围内,与营盘山文化、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与成都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相比较;在三星堆遗址内,各个地层相比较,各个祭祀坑相比较、不同器物相比较、同类器物相比较;还要将三星堆时代与之前、之后若干百年、若干千年的文化、地理、政治、经济相比较;亦可以将三星堆文化置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视域予以观察、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与之联系的变化、演进特点及发展规律……事虽细、虽烦、虽难,但探索之路亦不乏快意、享受与惊喜!5A658E7D-0967-48DC-9A56-A34935DEEDF6
4.让三星堆文化走进大众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说:“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物属于全社会,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在三星堆考古工作者、研究者那里,就是要让三星堆文化贴近大众,走进大众,向大众宣传、传播三星堆文化,讲好三星堆故事,让四川民众、全国民众、甚至海外华人、外国友人都知道三星堆、了解三星堆,人人都说三星堆。倘若有了这个局面,那么,学者理想中的三星堆学,也便有了雄厚和广大的基础;其建构的完成也就水道渠成了。
让三星堆走进大众,其實是一个双向过程,含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三星堆文化对大众的宣传与传播,这是最主要的工作(具有主导性)。其二,是大众介入三星堆文化的探索与传播。大众介入的热情及其程度,则是由三星堆考古人、研究者让三星堆走进大众的意愿与热情决定的。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说:“考古学家的任务则是客观地告诉人们古人曾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的命运,以便今人为未来做出决定时可以汲取古代的教训”(《考古学》第133页)。三星堆考古人与研究者要有与大众交流的愿望甚至欲望,把自己的发掘心得、研究成果及时地告诉社会、告诉大众。譬如对三星堆祭祀坑的认识,有的学者便认为是古蜀王或贵族器物的埋藏坑或是战胜者对失败者器物的毁坏掩埋坑。这里面又牵涉到古蜀王朝的改朝换代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全盛期是鱼凫王朝,在商代后期则走向衰亡。所谓埋藏坑或掩埋坑就是对这段历史形象的记录(器物的气质反映鱼凫王朝的辉煌,它的破损与埋藏或掩埋说明王朝的式微或战败)。将这样的认识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公众号等媒体分享给大众,可以使学者、使三星堆贴近大众。当然这样的认识乃属于个人的思考,不是定论——也不怕告诉给大众——但至少可以引起大众对祭祀坑、对三星堆的兴趣,为大众进一步理解三星堆文化,添了一条思路。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也是沟通学者和大众的桥梁或媒介。他们在讲解时,则应尽量多言多数派的观点或定论,也可以掺杂些少数人的意见甚至讲解员自己的推想——但一定要讲明是推想;至于哪些属于真实的历史,哪些属于神话传说,更不能含混,以免误导大众。
三星堆考古人、研究者要放下高冷的架子,从考古现场、从书斋走出来,充分利用传媒和科技手段,向大众及时报道考古成果、研究心得。三星堆遗址属于全体人民,人民有权知道三星堆的事情。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六个坑的发掘高潮期间,考古工作者就将各大媒体人请进三星堆现场,让其近距离了解考古发掘情况,实时向人民群众传递消息。
特别是2021年3月20日至23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连四天在央视新闻频道推出《三星堆新发现》特别节目,实时报道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的巨大成果,向公众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灿烂成就。2021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四川省人民政府又在三星堆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主题活动(当晚还举行了“三星堆奇妙夜”的文化盛宴),让包括中外媒体记者在内的200多名有代表性的中外人士走进三星堆发掘现场和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三星堆文化的魅力,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及其他各大媒体亦滚动式地不断推出三星堆专题片、纪录片持续介绍三星堆(包括新一轮发掘)。发掘者、研究者或现身说法,或发表看法。大众受到鼓舞,也热烈参加进来,在公众号等新媒体上指点文物,七嘴八舌,一下子拉近了三星堆考古与大众的距离。
与此相应,有关方面盛情邀请群众进考古现场、进博物馆,由群众提问,专家讲解,专家与群众线上线下互动。2022年4月,成都博物馆就曾邀请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研究馆员在线上开展讲座,向广大群众讲解三星堆丝绸发现过程及发现意义,让更多人知道三星堆丝绸的了不得。[6]这次讲座采用多领域平台同步推广的形式,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成都日报·锦观、文博园等一起直播。嗣后,还在“成都博物馆”公众号播放讲座全视频。
在这次讲座中,周旸向受众特别指出:“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亦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秦并巴蜀,蜀地以及西南广大地区则陆续融入华夏。在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考古发现均表明,关于丝绸,巴蜀和中原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成都博物馆”2022年4月15日发布)周旸抓住丝绸这个切入点,揭示了巴蜀文明何以快速融入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巴蜀人民何以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和谐大家庭一员的核心要素;向广大群众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三星堆考古文化,传播了三星堆文明与中华文明趋同的认识论、价值观,让广大群众受到一次考古—历史知识的生动普及和爱国主义、唯物主义的深刻教育。
考古界、文博界对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的宣传,是三星堆考古、三星堆研究的一场生动的大普及、一个优秀的大型行为艺术、一次成功的考古秀、文化秀。
考古学界、历史学界过去对来自民间的三星堆话题甚或猜想或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其实,民间的议论质朴直率,有的甚至稀奇古怪,却反映出大众对本土早期文化的关注,对中国考古、中国历史或中华优秀文明的自信。三星堆考古人、研究者不妨放下身段认真听听,可以帮助我们放开眼界,别开生面。更重要的是,倾听民间声音这个行为的本身,就是三星堆考古、三星堆文化向大众的贴近,是向大众普及、弘扬、交流、传播三星堆考古、三星堆文化的机会,何乐而不为?
将三星堆考古、三星堆文化用通俗的语言、亲近的姿态,摆给大众听,让三星堆文物在大众中活起来,是当代考古人、当代学者的责任和义务。三星堆六个坑的发掘、宣传与传播,成为中国考古学大众化历程里的一段难忘的记忆、一个宝贵的经验。它将激励三星堆考古人、研究者坚持走考古学与人民群众亲密结合的路子,使三星堆考古与研究在更高更强的科学化的同时,实现最大最好的大众化,让世界看到中国考古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在探索、弘扬、传播三星堆文化的路上辛勤并快乐着。
注释:
[1]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432页。
[2]参见郭建波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部分青铜器表面附着丝绸残留物的发现与研究》,《四川文物》2022年第1期。
[3]参见《成都商报》公众号“红星新闻”2022年4月12日报道。
[4][5]综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23页、158页数字统计。
[6]参见《潇湘晨报》2022年4月11日报道。
(《三星堆文化》修订本年底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 屈小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四川省秦巴文化研究会(院)学术顾问
李殿元:中共四川省委讲师宣讲专家
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副会长
段 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四川省社科院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5A658E7D-0967-48DC-9A56-A34935DEEDF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