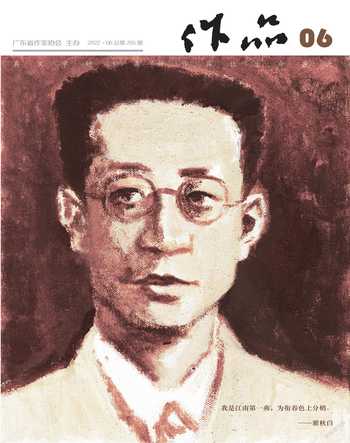谈雅丽的诗
湖水与逝者
砍掉数棵水杉后
沧山湖忽然把我的视野拉远
面朝一座青盈盈的大湖
这里是绝佳的风水宝地
傍山小路通向林海深处
白头芦苇轻拂带松香味的湖波
冬天湖岸后退,但湖波秀美
寒风扫完落叶后,又开始扫荡人间
这个清晨我们吹吹打打——
把劳碌了一辈子的舅舅安放此地
这天夜里,山鸡叫了整晚
我们感叹时光易逝,生命孤独卑微
第二天清晨飘起了鹅毛大雪
把湖水和逝者,都藏得无踪无影
傍晚雁群飞过
我们踏上归程,像一群候鸟曾倾心某片水域
如今要挥挥翅膀,准备了三千公里的远行
我们站立在漉湖堤岸——
天空青蓝,夕阳薄红
一排疏落的榆树林装点一顷碧波
恰有温柔的你,指给我看一群迁徙的大雁
雁鸣声声惊心动魄,当候鸟飞过
留下孤寂的我,独自在空阔的湖镜徘徊
百转千回想回绿洲,重回大雪来临前
小天鹅在青山湖的陪伴与相恋
我们仰望天空,想留住一些瞬间
曾经陪你走过最美的风景
一起看候鸟飞的日子
那些“一”字“人”字形的雁阵
迷失在秋光潋滟的湖波深处
唯有洞庭湖扇动一双试飞的翅膀
模拟了爱的双向奔赴
而湖水苍茫柔软,荡漾出永生的醉意
鹤翅舞动洞庭湖
这股力量比我对你的爱更加蓬勃
春风开始只撬动一小块碧翠的湖洲
候鸟飞越——几乎都化为你的幻影
放纸鸢的孩子们沿堤岸奔跑
在晴蓝的天空上,悬挂着一颗燃烧的星球
一顷碧波,暖流轻漾
魚群在我们周围跳跃、欢呼
江豚随我跃入梦境,它们黑色的拱背
沉浮在激荡的流水之巅
麋鹿奔腾,头顶高耸的枝角指向命运的磁针
我的心在热烈跳动,呼唤你的名字
呼唤每一个候鸟醒来的清晨
药香人间
父亲花几千元买了一台中药制成机
点好的荷叶、黄芪、决明子等汤剂
都倒入这台深蓝的机器里沸腾
等在外面的胖男人相信父亲能妙手回春
少年的他背熟千味中药汤头,退休后经营鹤镇
唯一的诊所,木抽屉里的草本植物
每年夏天都要拿出来曝晒几次
祖传的《本草纲目》且一味味背来
乌头汤,护肝汤,降脂汤,清肺汤
不能有丝毫差错,父亲把药材放在三楼
防鼠防虫防潮,确保每样都在保质期内
父亲邀请我们回乡参观他的新机器
中药熬好打包,放在塑料袋里
机器绿灯亮起,汤汁由淡转浓
前来拿药的人赞美他的医术,顺便赞美高科技
父亲往往一丝不苟,拿出称量的小秤
传统不能有差错,工艺却要创新
一剂上好的药汤静静沉淀下来
药香弥漫,如同烟火人间
不急不缓——熬得恰到好处
江水微蓝
与那人相逢,仿佛数生命中的一罐细沙
江水荡漾蓝色的伤感
正有春风向那棵深情树袭来
校园夹竹桃盛开的粉红心情
墙角白色雕像,树下细密笑脸
我只迷恋一封从未寄出的长信
地址不详,心动不详
来由和结局皆不在我的掌握
少女蜻蜓点水似的问候
十米外的对视,有笛声婉转穿越
如今的我,像一个心事苍茫的人
——隔夜听雨
那人脸上有薄荷的清凉——和微甜
那人心里有薄荷的清凉——和微甜
时光滴漏,如一粒细沙柔和经过
我手心是满天星斗,是满天星斗映照
暮色沉沉的码头
梧桐落叶
男人微瘸腿,一双大手冻得通红
打碎的肉泥装盆,加胡椒、盐、味精和辣椒
他揉捏上料,把猪肉灌进薄薄的肠衣
一长溜排队等候的摊子铺
老太太不急不慌等着香肠成形
一边和他聊着家长里短,夸夸其谈
女人忙着切肉,碎肉,称重,装袋
一声不吭,他五大三粗
戴着狗皮帽子,围着整块塑料布
干起活来却十分细腻多情
他们租用小摊位卖香肠
春天后回乡打理镇上的饭馆
他夸张地说起当年的家族兴旺
出自书香门第,从小爱好古诗
可惜高考落榜,被迫沦为手艺人
他拿出微信让我扫码支付——
网名叫“梧桐落叶逢秋雨”
我没看出他与这句古诗有何关联
但却看到他与生活达成的妥协与和解
野柿子树
秋天我们穿过京郊一片野柿林
远眺铁轨,连接青黛群山
一树树火红的柿子亮起星辰
变软的柿子从枝上掉落
香甜弥漫,枝丫轻摇——
我们从隐秘的小道走来
柿叶间有吵闹的蚊蝇轻舞
莺雀飞来,旋即飞走
灯灯拿起长杆,我撑起伞接柿子
唐果漫不经心,走在时间之外
我记得欢声笑语,斑斓之光闪现
灯灯的眼睛是柔和东海,波浪轻摇
小聂的男中音反复说道
“我接到了,我接到了——”
当时一列绿皮火车穿过燕山
并不知晓野柿林会被时间收走
只有记忆撞击我们的心灵
并在流光中画下斑驳的足迹
明年将春暖花开
转暗的暮色中我点燃了炭炉
一壶上好的普洱暂做我的知己
赶在下雪前,炖一锅香气扑鼻的腊猪脚
我们在这间斗室温了一壶糯米酒
就座的亲人谈论风雪中的收成
一年的悲喜交加在酒里在热腾腾的劝慰中
想想这一年走丢的姨妈和二舅
树枝上的黄花,坟地上添的新土
想想中年后会面临更多失去
我将手摸在温热的壁炉
恍惚地想起恋人已久无消息
亲人聚于这间斗室,唯有相聚
才能经得起风雪交加的流年
我凝神听到窗外雪的步子近了
岁月无法更改,黑暗终将替代光明
好在我们永存一扇窗
期盼着明年会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