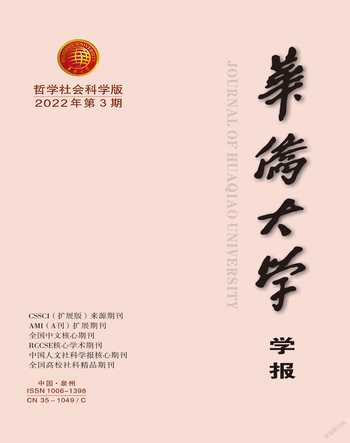智慧旅游城市建设能否提升旅游业绩
樊玲玲 谢朝武 吴贵华



摘 要:智慧旅游城市试点政策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城市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但其政策效应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2007—2016年170个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城市旅游业绩水平的影响效应并对其传导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旅游业绩且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城市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对不同区域、规模的城市旅游业绩均呈现正向显著效用且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提升差异,其正向推动表现为“边际效应递增”规律。机制验证方面,智慧旅游城市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来实现旅游业绩的提升,促进旅游业发展。
关键词:智慧旅游城市;旅游业绩;城市异质性;双重差分法
作者简介:樊玲玲,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旅游经济和智慧旅游(Email: 2284252490@qq.com; 福建 泉州 362011)。谢朝武,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旅游安全、旅游服务和智慧旅游;吴贵华,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实验室老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旅游经济和旅游实验。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2)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2)03-0042-13
20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病问题日益加剧,“智慧增长”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趋势。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范围内掀起智慧化浪潮,智慧旅游、智慧城市等新的产业发展形式和载体应运而生。智慧旅游成为促进旅游产业化、信息化的重要目标,智慧城市建设则逐渐成为推进城市信息化、抢占城市竞争位置、调整城市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黄松、李燕林、戴平娟:《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地理学报》2017第2期,第242—255页。)。其中,智慧旅游城市成为智慧城市结合智慧旅游发展的重要建设领域。截止2013年底,国家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先后颁布两批智慧旅游试点城市,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建设的重要亮点之一。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提出释放数字化活力、提升产业发展质量的政策导向。可见,推动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是我国重要的政策实践,检验智慧旅游城市领域早期政策的成效,对于优化我国智慧旅游城市的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智慧旅游、智慧旅游城市的研究多集中于信息化与旅游的关联性(Yuan H, Xu H, Qian Y, et a.Make your travel smarter: Summarizing urban tourism information from massive blog dat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6, 36(1), pp.1 306-1 319.)、智慧旅游系统开发与管理(王建英、谢朝武、陈帅:《景区智慧旅游设施的优化布局——以泉州古城为例》,《经济地理》2019第6期,第223—231页。)(Koens K, Melissen F, Mayer I, et al.The Smart City Hospitality Framework: Creating a foundation for collaborative reflections on overtourism that support destination design.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2021, 19(3), pp.100-376.)、智慧旅游评价体系(Boes K, Buhalis D, Inversini A.Smart tourism destinations: ecosystems for tourism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Cities, 2016, 2(2), pp.108-124.)和智慧旅游发展现状(Gretzel U, Sigala M, Xiang Z, et al.Smart tourism: foundations and development.Electronic Markets, 2015, 25(3), pp.179-188.)、發展路径及对策研究(A García-Milon, Juaneda-Ayensa E , Olarte-Pascual C, et al.Towards the smart tourism destination: Key factors in information source use on the tourist shopping journey.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 2020, 36(10), pp.1-9.)等方面。总体上,学界面向智慧旅游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建议,但对于智慧旅游城市发展政策的有效性却缺乏明确的实证依据。截止2020年,国家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政策已经实施了长达7年。但是,这一政策对城市旅游经济是否有助推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评估。如果城市旅游业绩有提升,则旅游业绩的提高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智慧旅游城市试点区设立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作用?这一政策效应对旅游业绩提升的影响过程和传导机制如何?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客观的评估和检验。为回应这些问题,本文对智慧旅游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探讨。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且处于持续演化发展过程中,其自身的发展变化也会在研究时段内对智慧旅游城市建设产生新的影响。在借鉴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石大千、丁海、卫平,等:《智慧城市建设能否降低环境污染》,《中国工业经济》2018第6期,第117—135页。)(袁航、朱承亮:《智慧城市是否加速了城市创新?》,《中国软科学》2020第12期,第75—83页。)(王敏、李亚非、马树才:《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财经科学》2020第12期,第56—71页。)(张治栋、赵必武:《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分析》,《软科学》2020年第11期,第65—70,129页。),本文将信息技术变化对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影响作为一个外部全局变量来考量,在这个前提假设背景下开展本文的研究。014C7B63-A0F3-407B-A447-0D6F456619EF
综上分析,研究将以2007—2016年全国170个地级市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為研究样本,以智慧旅游试点城市样本为实验组,其他城市为控制组,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对智慧旅游城市试点区的政策效应和影响机制进行相应的统计研究和科学评判,并对政策所引致旅游业绩效的稳健性、城市差异的异质性进行检验和分析。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点在于:基于地市级样本检验我国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绩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为我国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政策优化提供实证依据和策略建议。
一 政策背景和文献综述
(一)政策背景
随着21世纪新一轮信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并对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99年Stefan Klein和Hannes Werthner指出信息技术将对旅游业产生巨大的冲击。2000年Phillips首次提出智慧旅游概念,认为在旅游发展中的规划、开发、经营以及营销过程中都应该体现智慧旅游。2004年韩国推出“I Tour Seoul”应用服务系统,力图为首尔旅游者提供掌上移动旅游信息服务平台。2006年新加坡提出“智慧国2015计划”,提供一站式注册服务、智能化数字服务系统以及交互式智能营销平台。2008年美国IBM提出智慧酒店概念,旨在为住客提供自助入住登记或退房等服务,满足客户智能化、人性化需求。
伴随世界各国掀起的智慧旅游热潮,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提出和升级支持智慧旅游和智慧旅游城市发展的政策体系。在中央政府方面,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制定旅游信息化标准,加快智慧景区、智慧旅游企业建设,完善旅游信息服务体系;2015年旅游局印发《关于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智慧旅游是游客市场需求与现代信息技术驱动旅游业创新发展的新动力和新趋势;2017年《“十三五”全国旅游信息化》颁布,以推动信息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进一步满足游客和市场对信息化的需求,助力旅游业蓬勃发展。在地方政府方面,海南早在2010年就提出基于物联网建设“智慧国际旅游岛”,把物联网应用与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相结合,建立面向游客的旅游融合平台;2012年江苏省“十二五”智慧旅游发展规划提出景区的智慧化服务;天津市在2014年提出围绕智慧旅游建设“1369工程”,实现平台、载体和系统全部智能化;云南省在2018年开始建设“一部手机游云南”智慧旅游平台,实现智慧大交通、精品路线推荐、智慧导览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为进一步推进智慧旅游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原国家旅游局于2012年和2013年先后颁布两批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共33个城市,这标志着智慧旅游、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在国家层面的正式启动。可以预见,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智慧旅游是新时期中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整体迈向旅游强国的重要举措。而智慧旅游城市作为智慧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十四五”期间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同时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将会对中国旅游经济发展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二)文献综述
学界对于智慧旅游城市目前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概念,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戴平娟:《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5年,第21页。)(焦慧元、李丹、吴士锋:《秦皇岛市智慧旅游城市研究》,《河北企业》2020第7期,第63—64页。)(王恩旭:《基于G1-熵值的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水平评价模型及实证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第2期,第68—73页。),智慧旅游城市一般是指在智慧城市背景下,以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利用为基础,以全面感应旅游要素、整合分析旅游信息、智能响应旅游需求等为手段,以旅游体验、服务和管理决策智能化为目标的城市发展模式。同时,其建设发展过程中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依托城市自身的智慧化建设背景。城市信息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城市信息服务和管理系统等都是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基础,旅游信息服务作为重要组成部分需充分融入其发展过程中,二者相互支撑,如“数字福建”建设;第二,满足个性化旅游需求,实现游客的智能化旅游体验。旅游信息服务提供方式多层面、多形式,游客获取方式多渠道、多载体,通过实现消费需求和市场经营需求的对接,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如“一部手机游云南”实施;第三,通过资源整合,推进旅游经营主体的科学管理。信息技术发展改变企业传统经营环境,合理利用大数据及信息化运营环境来挖掘消费者潜力,实现精细化管理,提升整体运营管理能力是旅游企业面临的新挑战,如智慧旅游服务中心落户镇江。
智慧旅游城市的评价(A X W, B X R L, C F Z, et al.How smart is your tourist attraction?: Measuring tourist preferences of smart tourism attractions via a FCEM-AHP and IPA approach-ScienceDirect.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4(6), pp.309-320.)、建设(Jahanyan S, Shafiee S, Ghatari A R, et al.Smart Tourism Destin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Tourism Review, 2019, 31(7),pp.287-300.)与影响因素(Del Chiappa G, Baggio R.Knowledge transfer in smart tourism destinations: 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a network structure.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5, 4(3),pp.145-150.)等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而智慧旅游城市与旅游发展、旅游业绩等的关系逐渐引起重视(Lee H, Yang S B, Chung N.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nomic Effects of Smart Tourism City, Busan : Analysis Using an Inter-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Journal of Tourism and Leisure Research, 2019, 31(4),pp.87-101.)(Park J H, Lee C, Yoo C, et al.An analysis of the utilization of Facebook by local Korean government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network of smart tourism ecosyste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6, 36(6),pp.1 320-1 327.)。一般认为,城市发展对旅游经济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胡付照、曹炳汝:《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旅游发展格局的影响》,《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8第5期,第113—118页。)(王新越、刘兰玲、安烨:《长江流域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第3期,第12—17页。)(王坤、黄震方、余凤龙,等:《中国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研究》,《旅游学刊》2016第5期,第15—25页。)。智慧旅游城市是将智慧技术与平台充分应用于城市旅游发展的载体城市,它代表着一种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张宏祥:《中国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基本状况与国际经验借》,《对外经贸实务》2018第5期,第85—88页。),它既要求促进城市信息技术的创新与运用,也强调以此为基础变革城市发展和治理模式,由此将带来城市旅游业运作效率的提升,推动城市智慧旅游管理、智慧旅游营销、智慧旅游服务等核心业务的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翁钢民、李维锦:《智慧旅游与区域旅游创新发展模式构建——以秦皇岛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4第5期, 第35—38页。),由此产生的综合效率将推动旅游产业的竞争力提升(许金如:《论旅游城市转变旅游增长方式的智慧化路径》,《开发研究》2014第6期,第120—123页。)。因此,一般认为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于城市的旅游业绩具有促进作用(杨艳、丁正山、葛军莲,等:《江苏省乡村旅游信息化与区域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关系》,《经济地理》2018第11期,第222—227页。)。但是,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为智慧旅游城市的建设、发展与政策建构,这些研究忽视了对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政策本身的客观评价和检验分析。因此,本文将对2012年实施的国家智慧旅游城市试点政策进行实验分析,检验其对旅游业绩的影响作用,这既是对这一全新城市发展模式成效的分析,也是对该政策本身的综合评估。014C7B63-A0F3-407B-A447-0D6F456619EF
二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2009年中國提出智慧城市建设构想,原国家旅游局于2012年、2013年正式设立智慧旅游试点城市。两批智慧旅游试点城市类型多样,包含直辖市、地级市及县级城市在内的33个城市。本文将利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对智慧旅游城市试点政策进行一次“准自然实验”评估。双重差分模型作为政策分析的常用工具,其优势在于考量政策实施的净效益,即考察控制组和实验组的政策行为在政策实施前后的相对差异(吴贵华、张晓娟、李勇泉:《高铁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第5期,第53—64页。)。在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之前,需要对其他政策影响以及政策内生性影响进行排除。在排除其他政策影响方面,本文发现所有智慧旅游试点城市同时也是国家优秀旅游城市(除龙岩之外),由此,对于控制组城市同样选择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在排除政策内生性影响方面,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将各类特征变量综合为一个倾向得分值,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依据倾向得分值的相近程度进行匹配,从而保证两组样本更好地满足双重差分方法估计所需的平行趋势假设。最后对匹配成功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减弱城市样本的系统性差异和单独使用双重差分方法造成的估计偏差。
本文对智慧旅游试点城市旅游业绩的评估主要基于2012年的试点样本城市,将2012年智慧旅游试点城市作为实验组,非试点旅游城市作为控制组,对于2013年的第二批智慧旅游试点城市,本文利用其来检验本文结果的稳健性。由于实验期数据样本较短,目前对智慧旅游试点城市的旅游业绩评估应是短期效应,对之后的长期效应需进一步的完善数据进行分析。为保障样本城市的相对统一,在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的选取过程中,对样本城市进行如下处理:(1)智慧旅游试点城市类型多样,涉及直辖市、地级市以及县级城市等,城市间异质性较大。为减少因城市异质性所带来的平行趋势不稳定,对于直辖市或地级市内的某一个区或县的试点城市,本文将这一类试点城市从样本中剔除,最后统一使用地级市样本数据(两批试点城市共有33个,为避免城市行政级别差异过大对评估的干扰,北京和天津2个直辖市以及县级市武夷山市未选入此次实验组,同时铜仁市在2011年行政区划发生变化导致数据差异同样未被选入。)。(2)本文以2012年智慧旅游试点城市为实验组进行基准回归,为保证文中估计结果为2012年智慧旅游城市试点政策的净效应,将实验组和控制组中2013新出现的智慧旅游城市剔除。最后选取2012年智慧旅游试点城市中16个城市作为实验组样本,选取141个优秀旅游城市为控制组样本(截止2010年,国内共有214座地级市及以上优秀旅游城市,在删除重合智慧旅游试点城市和直辖市的基础上,同时结合本文运算相关数据可得性,最后选取141个优秀旅游城市作为本次实验的控制组样本。)。
依据上述分析,本文运用DID方法的模型公式设定如下:
同时基于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估计,具体步骤为:利用PSM找到和实验组相匹配的控制组,将匹配后的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DID回归。具体模型公式如下:
其中,Tourism代表旅游业绩;DID为双重差分估计值,表示智慧旅游城市试点区交互项;估计系数α1为本文所求的政策效应,若α1显著为正,则说明政策有效;α0为常数项;bj为控制变量系数值;x为控制变量,控制其他影响旅游业绩的相关变量;ε为扰动项。模型(1)为旅游业绩效应模型,用于评估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绩的影响,其中控制变量分别包括经济水平、政府干预、人力资本、旅游资源、资本投资和产业结构。
(二)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旅游业绩。旅游业发展的产出指标主要表现为规模指标的旅游人次和产值指标的旅游收入。多数学者采用旅游收入单一指标来衡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王洪桥、袁家冬、孟祥君:《东北三省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分析》,《地理科学》2014第2期,第163—169页。)(沈惊宏、陆玉麒、周玉翠,等:《安徽省国内旅游经济增长与区域差异空间格局演变》,《地理科学》2012第10期,第1 220—1 228页。),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旅游人次对于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贡献性。因此,本文借鉴相关文献(陈浩、陆林、郑嬗婷:《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演化》,《地理学报》2011第10期,第1 427—1 437页。)(秦伟山、张义丰、李世泰:《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变》,《地理研究》2014第10期,第1 956—1 965页。 )利用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数构建旅游业绩指数模型(旅游业绩指数模型:spn=∑pisi(i=1…n)式中pi为权重(由于本文只有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两个指标,因此本文分别对其进行0.5的权重赋值),si为指标的无量纲化指标。),来反映城市旅游业绩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智慧旅游城市试点区交互项DID(DID=treatmentc×timet)。智慧旅游试点城市自2012年开始设立,treatmentc和timet分别为政策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当城市属于智慧旅游试点城市,treatmentc=1,反之则取为0;当t≥2012时,timet=1,反之则取0。
控制变量:除了智慧旅游城市试点政策会影响地区旅游业绩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对其产生影响,因此,需要添加控制变量减少这些外生因素的干扰。借鉴相关学者的相关研究(吴媛媛、宋玉祥:《中国旅游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地理科学》2018第9期,第1 491—1 498页。)(薛明月、王成新、赵金丽,等:《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空间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经济地理》2020第4期,第19—27页。),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利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2)人力资本水平,利用高等在校人数占第三产业人数之比来表示;(3)旅游资源禀赋,选取城市4A及以上景区,对其加权赋值求和表示;(4)政府干预水平,用地方一般财政支出占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表示;(5)资本投资水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表示;(6)产业结构水平,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014C7B63-A0F3-407B-A447-0D6F456619EF
本文所有使用的数据来自2008—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区城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EPS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利用平均增长率和平均值进行补齐,最终形成170个地级市10年的面板数据。为消除价格影响,所有涉及价格的变量数据以2007年为基期,借鉴GDP价格平减法对数据进行相应的平减。具体描述性分析见表1。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智慧旅游城市建设作为旅游城市建设的重大举措,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手段对现代城市的运行和治理提出新的方式方法。本文用DID方法对智慧旅游城市试点政策在旅游业绩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在表2中,模型(1—8)是对旅游收入、旅游人次以及旅游业绩分别做相应的基准回归分析。模型(1—4)为智慧旅游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的影响分析,模型(1)、(3)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模型(2)、(4)为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不论控制变量加入与否,智慧旅游城市政策对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均为正向影响。模型(5—8)为智慧旅游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业绩的影响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智慧旅游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业绩同样呈现正向影响,且不论加入控制变量与否,试点政策对旅游业绩的影响都高于旅游收入或旅游人次;其中模型(7)对个体效应进行控制,模型(8)对个体效应和时期效应进行控制,实证结果整体上保持一致,即试点政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由于个体异质性或经济发展波动影响造成估计偏差,但实证结果显示控制变量的加入、个体或时期效应的控制都反映出试点政策对旅游业绩发展的正向影响,且系数的估计值稳定在10%以上,整体上说明智慧旅游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旅游业绩水平。
(二)稳健性分析
1.双重差分法分析前进行倾向得分匹配(PSM+DID)。依据前文分析可知,在实验过程中,实验组旅游城市和控制组旅游城市的变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系统性差异,为减少双重差分模型在运行中的估计偏差,本文运用PSM-DID方法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在运行PSM-DID方法之前,先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包括共同支撑假设检验以及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匹配效果检验。从表3可知,共同支撑假设检验中,控制组和实验组的结果变量旅游业绩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而协变量均值在双重差分前后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该结果表明PSM-DID方法的使用是可行的。图1为倾向得分值密度函数图,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样本匹配,删除不匹配的2个样本(武汉和苏州)后发現,匹配后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倾向得分值的概率图相较于匹配前概率图更为接近,表明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匹配效果较好,进一步证明PSM-DID稳健性检验方法的合理性。表4中智慧旅游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业绩显著提升近9.3%,PSM-DID稳健性检验和上文双重差分结果无显著差异,二者都表明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绩的提升作用是显著的。
2.第二批智慧旅游试点城市。为进一步检验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2013年的智慧旅游试点城市加入回归样本来检验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影响旅游业绩的稳健性,具体结果如表5中(5)所示。估计结果表明,智慧旅游城市建设依然对旅游业绩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系数估计值符号和显著性与前文没有明显的显著差异,表明文中结论是相对稳健的。
3.改变时间窗宽。为识别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绩影响是否会随着样本时间长短的变化而变化,本文通过改变回归时间节点识别政策对时间变化的敏感性。文中以第一批智慧旅游试点城市颁布时间为中间点,分别选取前后1年、前后2年以及前后3年的样本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中(1—3)所示。估计结果表明,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绩的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通过改变回归的时间区间,依然和前文结果相一致,从而证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4.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在回归分析中所选变量与设立智慧旅游城市试点区之间可能会产生反向影响,由此,为降低变量之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文本将所有控制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具体结果如表5中(4)所示。实证结果表明,系数符号和显著性的结果和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估计系数相对上升,这可能是由于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所导致控制程度变弱所引起的,但实证结论再次验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三)异质性分析
1.城市区位异质性。上文分析结果表明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于城市旅游业绩提升具有显著作用,但城市所处地理区位对城市旅游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那么对于不同区域城市,其提升作用是否同样存在,同时这种作用的存在是否具有差异?为检验这种异质性,本文从地理区域角度出发,对存在区域异质性的智慧旅游城市的旅游业绩进行分析。表6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不同区域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绩影响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东中西部区域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均显著提升了旅游业绩,但各区域提升效应存在一定差异,提升效应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47.82%>10.11%>7.74%)。可能存在原因为,一方面智慧旅游城市建设能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旅游发展的集聚效应,从而提升旅游业绩,这就说明各区域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绩的估计系数值均为正。另一方面东中部旅游城市的现代化信息水平和科技水平发展程度高且时间积累长,而西部地区旅游城市整体信息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且时间积累短,但西部地区旅游城市的信息技术对旅游业绩发展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大于东中部地区旅游城市。
2.城市规模异质性。本文从城市规模的角度出发,对不同规模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旅游业绩进行了分析。关于城市规模等级划分,国务院2014年颁布《关于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衡量标准,将城市划分为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超大城市。但城市规模等级是一个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体现,多维度衡量城市等级更符合本文实际,由此,本文采用由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等5个维度塑造的城市等级排名(城市等级划分参考2016年《第一财经周刊》名单,将338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划分为6个等级,分别为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本文在数据处理中将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统归为一线城市。)来进行城市规模等级划分。表6结果表明,控制变量加入与否,不同规模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绩的提升作用均显著为正。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其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绩提升的效应值越高。原因可能在于一线旅游城市的信息技术发展有一定基础,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在原有信息技术基础上会进一步增强旅游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从而促进旅游业绩提升,而城市规模等级相对较低的四五线城市,由于信息技术的欠发展,初期阶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城市建设的作用并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效应,它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改善。014C7B63-A0F3-407B-A447-0D6F456619EF
3.城市特征异质性。智慧旅游城市建设需要依托城市自身特征。智慧旅游作为旅游业和科技创新融合发展模式,其本质是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在内的信息通讯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在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的基础上,实现旅游资源以及城市社会发展资源的融合及综合运用。因此,智慧旅游城市建设作为智慧旅游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样需要依托强大的信息技术实现相应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但是,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所需的信息技术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人、财、物等的支撑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城市人、财、物的发展水平对于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在提升旅游业绩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从城市发展的人、财、物特征等方面考量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绩的作用分析。在具体实证过程中,本文用城市高等在校人数表示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在人力方面的支持,用政府科技支出表示财力方面的支出,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来衡量物力方面的支持,具体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指标代替。同时对所有指标进行三等分,其中一至三等分组分别表示低等、中等和高等三种水平。
具体实证结果如表7所示,在人力资本水平方面,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智慧旅游城市建设都显著提升旅游业绩,且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城市对旅游业绩系数估计值越高。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对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具有较强的支持作用,能够提升旅游城市的旅游业绩。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智慧旅游城市建设需要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而信息技术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具有一定的门槛限制,即较高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比较低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能够更快更高效率地掌握相关技术并运用于实践工作中。因此,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具有一定要求,即人力资本水平高的智慧旅游城市对提升旅游业绩工作更容易展开。在财力支持方面,财力支持水平较低的城市,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提升旅游业绩的作用不显著,而拥有中高等财力支持的城市,旅游业绩提升效应显著为正。这是因为,一方面财力支持用政府的科技支出指标表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政府对于信息技术水平的支持和接受力度,当政府对信息技术的投入支持力度越高,则信息技术手段和运用水平越高,其在智慧旅游城市建设中的运用范围更广,从而提高城市旅游发展效率,提升旅游业绩。另一方面低财力支持水平的城市表明政府对于科技支出力度相对不够,某种程度上说明要通过信息技术提升城市旅游发展需要一定量的积累,同时也说明智慧旅游城市建設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政府对其投资是一个长远计划,应看到其长远经济效应。在物力支持方面,控制变量加入与否,不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绩提升效应都显著为正,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城市对旅游业绩提升效应越明显。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同样城市信息基础设施越完善才能更加充分发挥城市智慧建设效应,才能进一步为城市旅游业绩发展提供基础保证,进而促进旅游业绩提升。
(四) 影响机制分析
1.智慧旅游城市对旅游业绩的影响机制。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是利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使得旅游流和旅游产业在城市空间集聚发展的过程,通过扩大规模和提升质量推动城市旅游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流通,促进城市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和旅游技术效率提升的过程。因此,本文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种效应来阐述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绩的驱动效应。第一,智慧旅游城市的建设通过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促进旅游业发展所需资本、信息和人员等多种要素集聚,同时在对政府政策、信息交流等创新环境进行改善的基础上,依托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投入更多的知识、技术要素,降低旅游业发展成本、增强收益和提升效率,推进旅游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因此,在结构效应作用下,旅游产业和服务不断细化和提升,增强旅游吸引力,进而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第二,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在利用信息科学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城市环境等方面来提升城市化质量。伴随城市化质量的提升,进一步刺激政府在旅游景区或景点、旅游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开发建设,增强地区旅游接待能力,扩大旅游消费规模,形成旅游发展的规模效应。因此,在规模效应下,旅游相关设施得到改善,提升旅游发展所需的容纳能力,进而推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第三,智慧旅游城市在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利用知识、技术要素的投入打破旅游地和客源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旅游信息传递和传播。同时通过对旅游信息平台的建设、旅游服务系统的改善,为旅游者提供完备的旅游信息服务,提升出游旅游效率。另一方面新型人才的引进和相关劳动人员的技术知识培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而且相关旅游基础设施通过对技术的运用,不仅可以提高基础设施的应用效率,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在技术效应作用下,旅游服务系统得以改善,出游效率提升;同时旅游基础设施资源利用效率得以改进,进而推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具体如图2所示。
2.智慧旅游城市影响旅游业绩的实证分析。综上分析,智慧旅游城市建设驱动旅游发展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并通过上述三大效应来提升旅游业绩。本文分两步对机制进行验证,第一步,以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政策为解释变量,三大效应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如果系数显著,说明智慧旅游城市建设产生了上述三大效应。第二步,以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政策、三大效应为解释变量,旅游业绩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加以验证,借鉴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张国建、佟孟华、李慧,等:《扶贫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政策有效性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19第8期,第136—154页。),构建相应检验模型进行验证。具体模型结构如下:
模型中,M为中介变量,分别表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政策的总效应为α1,直接效应为φ1,中介效应为β1φ2。根据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步骤,α1显著为正,如果回归结果中φ1和φ2均显著为正且φ1的估计系数有所减小,则M为部分中介变量;如果φ1显著为正,φ2显著为负,且φ1的系数有所增大,M同样为部分中介变量;如果φ1不显著,φ2显著,则M为完全中介变量。其他变量与系数设定与主回归方程式(1)一致。规模效应用政府科技支出表示,智慧旅游城市建设依托信息科学技术,提升城市旅游发展容纳能力,进而改善旅游经济水平;技术效应用城市创新指数(城市创新指数数据来自于复旦大学产业发展中心《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来表示,智慧旅游城市建设促进旅游发展效率改善,旅游效率的提升进而优化旅游资源配置,从而提升旅游经济水平;结构效应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智慧旅游城市建设促进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旅游业经济提升。014C7B63-A0F3-407B-A447-0D6F456619EF
实证结果具体如表8所示,估计结果表明所选取的中介变量均为部分中介变量,系数估计值均为正符合理论预期。第一步实证过程,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智慧旅游城市建设过程中对三大效应具有正向影响;第二步实证过程,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和三大效应同时放入回归模型中,三大效应均显著提升了旅游业绩,且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绩的提升效应依然显著。这一实证结果表明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是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来提升旅游业绩的,这一理论机制也得到验证。由表8可知,目前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提升旅游业绩的效应更多依赖于结构效应(16.17%),规模效应(0.06%)和技术效应(0.05%)对其产生的作用贡献相对较小。可能的原因在于,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分别用政府科技支出和城市创新指数来表示,二者在智慧旅游城市建设中的投入需要长时间积累,导致其作用的发挥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2007—2016年为研究时段,形成中国170个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绩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
1.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政策实施显著提升了城市的旅游业绩,且此结论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2.试点政策对不同区域城市和不同规模城市的旅游业绩都显著为正,且初始的资源要素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会导致试点區对地区旅游业绩的作用不尽相同,其正向推动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规律。
3.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作用在于影响旅游相关设施、旅游服务系统的路径,扩大旅游规模并提升旅游效率,进而发展旅游经济。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国家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提升旅游业绩具有一定实践指导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启示与参考:
1.支持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来推进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鉴于智慧旅游城市建设这一政策对地区旅游业绩产生正向带动作用,因此,重视并支持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来应对当前旅游经济新挑战是目前地区经济政策的可行选项。试点城市需充分发挥其“政策试验田”作用,积极探索、积累经验并逐步推广。特别是对资源禀赋或要素发展水平较低的智慧旅游城市,国家和地方政府都需进一步在政策或资源要素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倾斜。
2.各地政府应充分认识自身的异质性,依据自身发展现状与条件合理有序地推进城市智慧旅游发展。一方面对城市智慧建设水平较高的城市可以大力发展并注重智慧技术的运用,将其充分应用到旅游业发展的各个行业,提高旅游资源的整合与配置效率,提升旅游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旅游者的体验感。另一方面对城市智慧建设水平较低的城市可以在保持自身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利用智慧旅游发展红利,有选择性有针对性的引入并运用适合本城市智慧旅游发展特点的信息技术、智慧项目,以最大限度提升城市智慧旅游发展的治理和运用效率,并为后期的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各地政府应准确把握自身在智慧旅游城市建设中的角色转换。一方面政府要扮演好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加大对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投入力度,为城市智慧旅游发展提供信息基础设施并搭建科研创新平台,提供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严格做好管控和监督的角色,单纯的数字技术无法实现数据与人之间协同要求,需注重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人力资本结构,释放人和数据的双重创新能力。同时,设立相应的检测或监督平台,保障信息或数据的获取和使用合理合法。
作为探索性实证研究,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信息技术处于持续快速的演进过程中,如何将信息技术变化对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影响进行客观论证,有待进一步研究;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未基于微观经营主体视角考察智慧旅游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企业发展的政策效应和微观作用机制,这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Ca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Tourism CitiesImprove Tourism Performance?
FAN Ling-ling, XIE Cao-wu, WU Gui-hua
Abstract: The pilot policy of smart tourism citi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urban tourism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economy, but its policy effect needs to be further teste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70 tourist cities from 2007 to 2016,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impact of smart tourism city construction on the level of urban tourism performance with the DID model and analyze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gets the resul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tourism cities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urban tourism performance, and the empirical result is reliable. The analysis of urban heterogeneity shows that the pilot policies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urban tourism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scale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improvement, and their positive promotion manifested in the law of “increasing marginal effect”. Mechanism verification shows that the smart tourism city construction has realized improvemen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rough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cale effects, technical effects and structural effects.
Keywords: smart tourism city; tourism performance; urban heterogeneity; DID(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责任编辑:吴应望】
收稿日期:2021-07-29014C7B63-A0F3-407B-A447-0D6F456619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