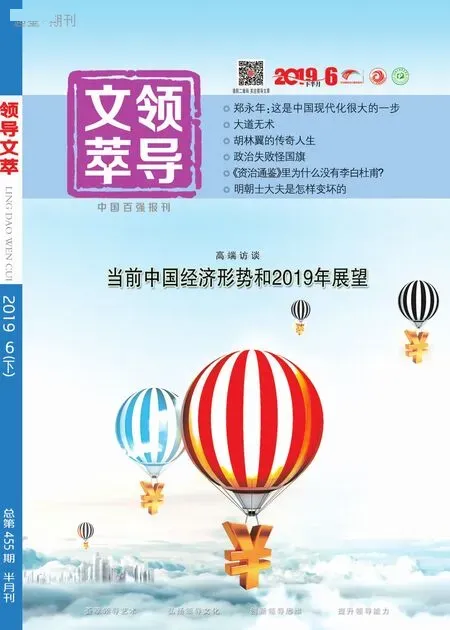菜碟之间的疆界:建立饮食归属感
[法]让-马克·阿尔贝/ 文 刘可有 刘惠杰/译

“告诉我你成天吃什么,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是19世纪布里亚-萨瓦兰的一句名言,现在的人还经常这么说。用这句话形容吃与人的关系应该最合适不过了。
19世纪关于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里,多有奇奇怪怪的关于吃的故事。比如,“拿破仑”是一种很难消化的立陶宛千层饼式的糕点。当时的人们用它比喻拿破仑在当地推行的司法改革的复杂性,层儿多是讥讽《民法典》太厚呢,还是形容法国对立陶宛的压迫呢?
有几种食物意义深远,或者连着一个战役,或者和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比如“拿波里比萨饼”,本来不过是面粉加盐加酵母做成的一种家常烙饼,在19世纪末意大利统一的进程加速的时候,它却成了“国家食品”。1889年,意大利的新君主亨伯特一世和玛格丽塔王后要和拿波里的人讲和,在王家城堡请客,当时最有名的比萨饼师傅拉斐尔·埃斯库斯托到场,在御前推荐了几种比萨饼。王后最后迷上了一种用莫扎里拉奶酪、西红柿和罗勒制作的比萨饼,这种饼有着和意大利国旗一样的颜色。王后欢喜得不得了,干脆给了个名字:“拿波里比萨饼”。20世纪初,这款比萨饼被隆巴尔迪家族引入纽约,从此它举世闻名。
英国布丁也表现了与国家形象的关联,其渊源和它的成分一样模糊不清。19世纪中期,在英国人的食物里,布丁不可或缺,尤其是圣诞节前后,几乎家家都在吃布丁。布丁的形状和用料这些年也趋于稳定:面粉、面包渣、牛肾、牛油、红糖、葡萄干、李子干、鸡蛋和啤酒,把这些料用豆包布包起来煮,煮到最后呈球状。布丁和另外一种“国家食品”——烤牛肉一样,是英国人炫耀民族精神的资本,还有各种王室的冠名,比如“维多利亚布丁”“王子布丁”……老百姓喜欢布丁,有时候甚至吃之前祷告一番,给了布丁一些信仰上的意义。英国殖民地纷杂,各地制作布丁用料不同,很多史学家认为,布丁反映了大英帝国文化的多重性和英国社会的和谐。
比利时也是这样一个例子(虽然它到了1830年才有了今天的国家面貌),尽管瓦隆人和弗拉芒人关系微妙,比利时的国家建设和其烹饪历史却是密切相关的。一直到20世纪初,也许是因为流亡布鲁塞尔的法国人太多,法国深刻地影响了比利时的饮食。1870—1900年间比利时王室的一些宴会菜谱记载,比利时上流社会很能接受法国菜,菜的名字暴露了一切,比如“巴黎焗龙虾”,还有“波尔多红酒牛里脊”,尽管也有和法国没什么关系的“罗马沙拉”和“荷兰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爱国主义成为国家主旋律,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比利时人的“比利时食品意识”渐浓。芦笋必定是梅赫伦(梅赫伦以及下文提到的列日、奥斯坦德均为比利时城市)的芦笋,烤鸡必定是“鲁本式”的烤鸡,巧克力必定是列日产的巧克力,连牡蛎的身份也变了,一夜之间一定要吃奥斯坦德附近出的牡蛎了。1910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后,比利时饭菜大行其道。“新厨艺”的热情在战后有增无减,受爱国主义情绪的鼓动,不管是上流社会还是普通百姓都热衷于此,而法国或者巴黎的厨艺逐渐淡化。旅游指南类的刊物里,法国菜名没有了,一些地方菜品升级成为“国家食品”。“炖牛下水”本来是一道平常不过的地方菜,此时被“国有化”,升格为“比利时菜”。苦苣、炸薯条、华夫饼、啤酒和精制巧克力摇身一变,都有了“国家级待遇”。
建立“国家菜品”并不容易,海鲜饭就是一个例子。海鲜饭最早成型于19世纪初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原本是一道农家午饭,富裕人家用料讲究些,多添几个虾,平常人家用料简单些,多几个淡菜,渐渐地可以從中看出人所属的社会阶层。海鲜饭传至各地,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用料和烹制方法。巴伦西亚和阿利坎特两地的海鲜饭风格迥异,主要是米的做法不同,另外,离海岸线近的地方用鱼多,反之火腿多。不管海鲜饭有多少变异,权威美食文学还是将巴伦西亚作为菜系的标识,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只要说海鲜饭,只能是巴伦西亚海鲜饭。19世纪末海鲜饭风靡安达卢西亚,到了1960年,在佛朗哥政权旅游政策的强推之下,西班牙全境的海鲜饭完成了统一。大力推举巴伦西亚海鲜饭造成了菜谱的多样化,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鸡腿、青蛙腿和猪排。但是,这种对原始菜谱的“稀释”让巴伦西亚居民愤愤不平,他们创立了针对“西班牙海鲜饭”的“巴伦西亚海鲜饭”,在当地的餐馆,店主听到你说“西班牙海鲜饭”,会客气地纠正你:是“巴伦西亚海鲜饭”。在19世纪中期,欧洲通过美食文献正式认识了海鲜饭,这种情况下,“国家食品”和“地方菜”的对立情绪已经显得无关紧要。法国菜谱里对海鲜饭的解释,主要是强调其“外国特色”,对于菜的味道形容不多。“二战”前后,大批西班牙人移民法国,这一道“西班牙菜”才真正融入了法国人的日常饮食。
有时候,有的菜品已经成了“国家食品”,但是菜品的原产地并不这样以为,“自家”的菜一不留神成了“别人家”的菜。匈牙利烩牛肉如今是匈牙利国家的招牌菜,其实早在1870年,这种菜在奥地利普通人家的桌上经常见到。匈牙利还有“酸菜肉”,用发酵变酸的圆白菜切丝配熟肉,这道菜虽然是整个中欧的家常菜,其实是生活在当地的德国人创造。匈牙利人把这道菜视为匈牙利的象征和骄傲,而且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地位甚至在语言和宗教之上。
(摘自《权力的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