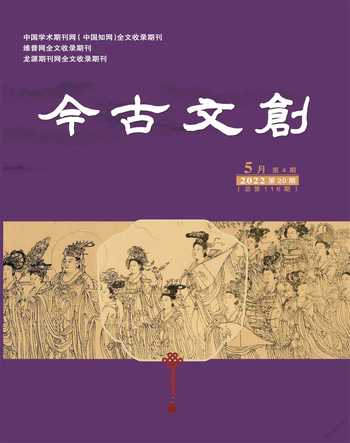从“洞穴喻”看柏拉图对“善”的追求
【摘要】 柏拉圖通过“洞穴喻”,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哲学使命,洞穴中的囚徒在挣脱了枷锁之后走出洞口、寻求太阳的道路,便象征着人们对于统摄一切的原则——“善”的追求。在追寻万物生长真正的原因即太阳的过程中,即便有痛苦也无法阻挡囚徒对于真正知识的向往,他甘愿为此割断以往经验所带给自己的虚假的知识,并且忍受光线的刺眼。在走出洞口外看到真正的太阳即“善”后,他又义无反顾返回洞穴去解救那些仍然被锁链困住的同胞。
【关键词】 洞穴喻;善;哲学王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0-005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0.014
一、“善”在“洞穴喻”当中的重要地位
在柏拉图关于“洞穴喻”的描绘中,当囚徒挣脱了锁链,他在洞内的走动使其逐渐发现洞内世界的虚假,并且看到了造成洞内影像的真正原因。在经过一番探索之后,他也发现了在洞穴之外有着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因此他不顾火光刺眼的疼痛,不断靠近火光,并最终走出了洞口。这时他才看到了洞外阳光下真实的事物,他不禁感叹于洞内世界的渺小以及自身长期以来被虚假经验所欺骗,并得知太阳才是万物生长和四季更替的真正原因。当囚徒逃出洞穴后,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继续留在洞穴外太阳照射下的世界,另一条道路便是再次回到洞穴之内。最终他选择了回到洞穴之内并且试图劝服他的同伴一起去往洞穴外的世界,然而洞穴内的其他囚徒早就已经习惯于洞内虚假影像,并且认为他在胡言乱语。
在“洞穴喻”中,柏拉图用洞穴内外的事物来比喻不同的哲学概念。在洞内,雕像象征着自然物,影像象征着幻想,因此被锁住的囚徒凭借洞内的火光所看到的雕像的影像,就象征着人们在可感领域凭借自身意见所看到的关于自然物的幻想。而当追求自由的囚徒挣脱了锁链之后,能够在洞内自由移动,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能够分辨清楚雕像以及被火光照射下投影在墙上的影像。此时,自由的囚徒看到的真正的雕像便象征着人们凭借意见在可感领域所达至的信念,但这仍然停留在经验领域,并非真正的知识。在这里,柏拉图区分了知识与意见,在柏拉图看来,知识来源于对事物的本质性认识,掌握知识的过程也是把握理念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会因知识的不易显现而显得艰苦卓绝。对于一般的大众而言,他们根据自身并不值得信赖的经验所形成的意见,仅仅是停留在事物表面的看法,未能深入到真正的知识层面。
当自由的囚徒走出洞口,凭借阳光所观测到的事物,才是真正的、关于事物的知识,给予万物照耀、从而使得自由人能够观测到事物的太阳则是最高的原则,象征着“善”。因此,“洞穴喻”中的太阳,及其所象征的“善”,便是理智最终认识的本源,是统摄一切的原则,是人们真正应当追寻的目标。从柏拉图另一个比喻“太阳喻”中,我们便可清晰得知为何洞穴中渴求自由的囚徒会不断走向洞口,只为寻得真正的太阳,即“善”。在日常经验生活中,我们凭借太阳的光线得以认清万物,因此太阳是视觉的源泉,“太阳一方面不是视觉,一方面又是视觉产生的原因。”[1]269这正是因为并不是太阳创造了事物,而是事物原本就在那里,只是通过了太阳的光线,我们才能够对事物进行清晰的观察。柏拉图认为“善”因为其含义的深刻而并不能直接将其表述出来,因此柏拉图想借用太阳——这个“善”的儿子来比喻“善”。当我们注视着被太阳所照耀的事物时,事物便清晰的显现了出来,当我们离开太阳去注视暗淡的世界时,事物也会因此变得模糊起来;与此相对应的,善则是心灵认识事物的源泉。源于心灵的理智,潜藏着把握理智对象的能力,然而此种能力的展现需要通过一定的契机,仅仅凭借着理智与理智对象,无法使我们通过理智真正把握理智对象,只有在“善”的帮助下,为理智提供动力,如同人眼在辨别事物时太阳所提供的光线,才能使得理智对象向理智显现出来。
因此,当囚徒在离开洞穴后凭借太阳真正辨别事物后,会对曾经在洞穴当中的一切发出无限感叹,一方面,他不仅会感叹于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则与存在方式竟是如此,太阳照射下的事物所呈现出的面貌竟与洞穴内的影像如此不同;另一方面,也感叹于曾经在洞穴里被幻想所欺骗,并且这种欺骗显得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当人们真正认识到“善”之后,我们也会发出如同囚徒般的感叹,不禁感叹于“善”让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知识,从而摆脱了曾经受意见支配的情形,同时也感叹于“善”超越一切的规定性,彰显着事物真正的价值并且统摄所有的存在及其本质。
二、追求“善”所受到的痛苦
尽管在洞穴之中,他们自出生之日起便被锁在固定的地点,头也被铁链固定住而不能够回头张望,把火光照射在雕像上从而投影在墙壁上的影像当作真实的事物去看待,然而囚徒们早已习惯此种生活,并不会感觉到悲惨。相反,他们会把此种境遇当作天然的、不可更改的情形去对待,并且衍生出了一系列处在此种限制下生存的经验。但当囚徒偶然挣脱了锁链,回头观望到火光以及真正的雕像,便是痛苦的来源。此时他所遭受的痛苦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源于违背经验之痛苦;另一方面来源于难以忍受光线之明亮。
违背经验之苦,源于使用同一感官面对同一事物得到的不同经验。在洞穴内,面对着投影在墙壁上的影像,他们一生都在观看此种类似于皮影戏的事物,并将不同的皮影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仿佛这就是他们生命中的全部。而当某个囚徒挣脱铁链之后,同样是利用感官,他却看到了与此前生命截然相反的事物,这时他会首先迷惑于自己的感官是否出现了问题,因为既往经验在他身体上留下了足够深刻的烙印。他甚至会对自身产生怀疑,怀疑自己的感官是否出现了混乱,为何他们都没有看到此种景象而偏偏是自己看到了。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他会逐步相信自己的感官没有出错,而下一个痛苦便接踵而至。从逐步适应洞内的火光再到适应洞外的阳光,这些真正的知识会极大冲击自己曾经对于世界的认知。当面对着真正的知识之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立刻去接受,而会处在纠结与犹豫的痛苦之中,一方面是真正的原则与事实,另一方面则是长久以来塑造了自身价值观与世界观的经验。选择了洞穴外的阳光,那么便意味着与过去的一切做出诀别,包括我们曾将自身融入进去的那个世界,我们被之前被“错误”的幻象所塑造出来的身体此时也变为了可以抛弃的对象,因为它沾染了“落后”的观念。而此时,这种在面临不同选择的纠结可以被概括为“真理与生活”的抉择。在一定的境遇下,我们对于真理的追求是有助于我们进行更好地生活的,因为真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认清经验对象,并能总结出足够的规律从而应对未知的挑战。在洞穴内就有这么一批善于思考的囚徒,他们依据影像出现的惯例,能够推测出下一个影像出现的时间,从而帮助他们在洞穴里更好地生存。然而,当经验世界的“真理”被逐渐掌握之后,真理对于人们的意义仿佛戛然而止,面对着已经获得的“真理”,这似乎足够我们进行更好地生活。当囚徒惊叹于洞内的火光以及洞外的阳光之时,会沉浸在此种发现真理的喜悦之中,然而这种喜悦必然是短暂的,此种只有自己得知却不能将其分享的感受让他陷入沉思。而且洞外的世界过于庞大,得知真理后的喜悦也会逐步被孤寂感和空虚感所代替。但如果他转身回到洞穴,在洞穴内习得知识能够让他很好地继续生活下去,只要他能够抛弃对真理的“欲望”,生活会像往常一样继续发生,而且他并不会感到孤独,尽管他知道洞穴里的囚徒都是错误的,但他仍能将自我融入此种错误之中,通过此种附和来消解掉个人的无力感。他甚至会这么安慰自己:比真理更重要的是生活,真理只是为了达至更好生活的手段,但绝不是目的,而且比起洞内的确定性,洞外的真理是以极大不确定为代价的。
难以忍受的光线的明亮,在此意义上,便是追求“善”道路上的痛苦。在囚徒走出洞口的过程中,他会经历两次刺眼的痛楚,第一次是在洞穴内,他回过头看到火光的刺痛,第二次便是逃离到洞口外,阳光带来的刺痛,这种刺痛更甚于洞穴内火光的刺痛。越是靠近光亮,疼痛越能灼伤人,但囚徒还是选择了直面光亮的勇气。因此,在柏拉图看来,“善”绝非是直接摆在我们面前可以轻松直观的物质,我们对于“善”的追求,必定是对自己的不断逼问,此种逼问便是对施加在自身的经验物质不断剖析、追问,“要他能在洞穴外面的高处看得见东西,大概需要有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首先大概看阴影最容易,其次要数看人和其他在水中的东西最容易,再次是看东西本身;经过这些之后他大概会觉得在夜里观察天象和天空本身,看月光和星光,比白天看太阳和太阳光更容易。”[1]277因此两次面对光线便象征着在获取真正知识的渐进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也会对自我不断产生怀疑,因为之前人生是未经审视的,一旦审视过后,便意味着要对某些自身曾仰仗不已、赖以生存的物质做出告别,此过程必定充满了痛苦,如同洞穴内外的光线般刺眼。在柏拉图看来,囚徒不会因为光线刺眼而停滞了向前的脚步,这便意味着我们不能因审视自己的痛苦而放弃了对于“善”的追求。因为我们会在“善”的追求中逐步认清哪些是真正的知识,抛弃掉的虚假的知识则是不值得留恋的,尽管我们曾经靠这些虚假的知识度日,但在真正的“善”面前,它会赠予我们真正的知识并让我们因此感到喜悦,此时我们才能得知只有“善”才真正符合我们的理性审美,因为在柏拉图那里,“善”是事物的原因,是真理的源泉。
三、寻得“善”后为何再次归穴
当囚徒获得解放之后,他回想起了曾经与他一同关在洞穴里的囚徒们,他同情他们,面对着洞外世界的光明,他还是怀抱着解放同胞的信念,再次回到黑暗的洞穴中。然而当他真正回到洞穴之中后,洞内的囚徒嘲笑他不能适应洞内的黑暗,看不清晃动的影像,并且质疑他在洞外看到的一切,解放的囚徒于是便与洞内的囚徒争论真理与幻觉,最终因激起民愤而被处死。很显然,囚徒解放失败的故事正是对应着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悲剧。在《理想国》中,佩莱坞和洞穴以及冥府分别有与其相对应的东西,“实际上佩莱坞就是洞穴,也当然就是冥府。在这个洞穴中,克法洛斯等人就是无法转头的囚徒,而苏格拉底则是下降回到洞穴来的哲人。”[2]28苏格拉底宁愿选择死亡,也要告知人们真相,贯彻自己的信念,这正如同再次返回洞穴的囚徒。
当囚徒在洞外得知真正的“善”后,他本可以独自享受这由真理所带来的喜悦,但他仍然选择回到洞穴,解救同胞,对于柏拉图而言,这个被解救的囚徒就是他描绘的理想当中的“哲学王”。如同逃离洞穴的囚徒不惜放弃洞外的世界转而再次回到洞内的世界,哲学王也为了城邦内人们的幸福而放弃了个人思辨的乐趣,甚至要用类似于影像的语言来尝试表达真理。在柏拉图看来,人们所生活着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纷繁复杂的,只是将理念进行歪曲的影子,只有理念才是事物的真实存在并且永恒不变,如果不具备真正的知识或者智慧,便无法把握理念。哲学王便是这个能够对理念进行把握的人,也是带领群众探寻到真正知识的人。
柏拉图生活在一个民主制与僭主制冲突的时代,他十分清楚雅典民主正在逐渐堕落,无节制的自由以及缺乏理性的多数人统治原则让僭主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而面对着如此的社会情形,他只能构想出一个只存在于理想当中的城邦,在这个城邦当中,人们根据各自的禀赋,被自然的分为了不同的阶层,分别是生产者、武士和政治统治者,因此对于柏拉图而言,哲学与政治密不可分,“哲学家和政治家应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3]83“哲学王”便是一个国家的最好的统治者,此种统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的占有,而是处在统治地位的“哲学王”能让国家更好地运转。柏拉图将城邦看作扩大版的个人,同时个人也被当作缩小版的城邦。在城邦之中,生产者、武士和政治统治者有着各自的职责,分别对应着生产、保卫和统治,同时,不同的职责对应着不同的特性:哲学家作为统治者代表着国家的理性,武士作为保卫者代表着激情,生产者要进行粗鄙的生产活动,需要克制自身,因此代表欲望,只有处在不同职责上的人相互协调才能使得城邦运行良好,从而体现最高的善。对于个人而言,同样包含着理性、激情和欲望三种内在品格,如同城邦内的分工一样,对于个人而言,理性应当居于统帅地位,激情应当居于中间地位,欲望则应居于最低的层次。因此,如同城邦内的分工一样,如果个人想要实现善,就应当使理性处于统治地位,对激情进行统帅,对欲望进行克制。在城邦当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便是“哲学王”,“哲学王”必须是通晓智慧、具有真正哲学思维的哲学家,对“哲学王”而言,积极参与政治、为城邦众人谋取幸福的优先级高于自身在思辨领域获得的愉悦,他不应当有私心,他的全部义务都只能是为了国家和民众,他的途径是启蒙以及教育。“哲学王”象征着逃离洞穴、见识过太阳进而又再次回到洞穴当中的人,因此,这里暗含着柏拉图对于“善”的另外一种看法:寻求到善的人应当带领那些仍然处在洞穴之中的人追求善,这一过程同样也體现出了善的内涵。
因此,在柏拉图的“洞穴喻”中,被解救的囚徒一定会再次回到洞穴,这不单单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使命,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思辨的乐趣,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帮助那些仍然处在混沌中的人们,即使处在混沌中的人们并不乐意接受哲学家的引导。这更像是哲学家们为了自己赋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会让后世的哲学家以发现真正的知识为己任,并将其分享给未获得这些知识的群众。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郝兰.哲学的奥德赛[M].李诚予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3]张汝伦.作为政治的教化[J].哲学研究,2012,(06).
作者简介:
马俊逸,男,汉族,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