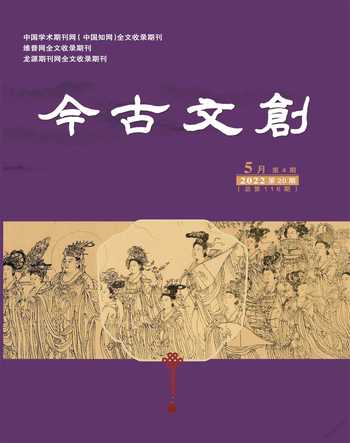兼收汉 、佛两学
【摘要】 《今昔物语集·恋子至阎魔王宫》讲述了一位父亲去阎魔王宫祈求见死去的儿子一面的故事。该故事原典为《法句譬喻经·道行品》,《经律异相》《法苑珠林》亦引用了原典故事。父子亲情的描述挣脱了汉文典籍中利己主义的束缚,实现了由“理智”向“情感”本位的置换。该父亲求见亡子的历程显示了“悟道”与“遂愿”的背离。虽然故事的时空被设置为古代天竺,母亲与孩子相继“失语”,但它依旧拥有以“恋”为情感内核的故事结构。笔者认为,通过改写,《今昔物语集》的编纂者显示了应对汉学、佛学两种外来文明的内化能力,编纂者充分吸收并内化了外来文明,重塑了日本的主体性。
【关键词】 《今昔物语集》;《经律异相》;《法苑珠林》;恋子;阎魔王宫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0-0014-08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0.004
《今昔物语集》的中译本①第四卷《天竺 佛涅槃后②》第四十一篇故事《恋子至阎魔王宫》第271页的注释这样写道:“原典为《法句譬喻经》第三卷第三十篇之道行品(《法苑珠林》第五十二卷之眷屬篇哀恋部、《经律异相》第四十卷第五篇中也转载有此故事)。” ③
本文以《法句譬喻经》《经律异相》《法苑珠林》为参照系,对本则故事《今昔物语集·恋子至阎魔王宫》进行了比较阅读——《今昔物语集·恋子至阎魔王宫》与《法句譬喻经》第三卷第二十八④篇《道行品》 ⑤、《经律异相》 ⑥第四十卷梵志部第五篇《梵志丧儿从阎罗乞活儿不亲从诣佛得道五》 ⑦、《法苑珠林》 ⑧第五十二卷《哀恋部⑨第二》为同一故事。通过阅读笔者发现,汉文典籍《法句譬喻经》《经律异相》《法苑珠林》的故事大致类似,而日本说话集《今昔物语集》中的该故事发生了显著变化,该故事大致讲述了天竺比丘得子——丧子——乞求阎魔王⑩允许见子——徒劳而返的历程。下面将从以下几个视角描述并分析该文本的变化。
一、孩子的特征——理智与情感的冲突
四篇故事对男婴的叙述存在不同,在孩子的出身方面表现为——
生得一男,端正可爱,至年七岁,书学聪了,才辩出口,有逾人之操。?(《法句譬喻经》)
生得一男,端正可爱。?(《经律异相》)
生得一男,端正可爱。至年七岁,书学聪了,才辩出口,有逾人之操。?(《法苑珠林》)
妻子随即怀孕,生下一容貌端正之男婴。父亲对其疼爱有加。?(《今昔物语集》)
通过上述描述可以看出,《法句譬喻经》《法苑珠林》重视孩子的才学而对孩子的容貌并不看重。书法、辩论的口才、过人的节操等都是儒家的重要评价标准。《经律异相》虽然在此处没有直接对外貌有正面或者负面的评价。但在下文该小儿斥责比丘“痴騃老翁,不达道理”的情节中也可以推断,《经律异相》借由七岁小儿之口主张了对冷静与理智的推崇,这种对抽象才学的信仰实际上反讽了对姣好外貌的迷恋。
与汉文典籍对理智、理性的推崇大相径庭,《今昔物语集》表现除了浓厚的以情感为主导的思维方式,“生下一容貌端正之男婴。父母对其疼爱有加”的叙述表明:可爱是这个孩子容貌端正所造成的结果,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即因为容貌端正,才有资格获得父亲的宠爱;端正的容貌本身是孩子被人认为可爱的评价标准。《今昔物语集·恋子至阎魔王宫》通篇未提该子具有才学、智慧等以理性为主导的评价标准。
对容貌的重视符合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尤其在同属于平安末期的《唐物语》中出现了对容貌的极度重视: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的典故在中国被认为是夫妇和睦的佳话,妻子孟光虽然容貌丑陋,但是都丈夫梁鸿毕恭毕敬以致夫妇和睦。但《唐物语》第四篇《孟光,恭敬侍奉丈夫梁鸿的故事》?结尾表现了对容貌的异常执着——“如果感情深厚,就算没有美丽的容貌,也不会感到无趣吧。(但是,也难以将丑陋的容貌看做成不丑陋的容貌)。”
同样,在《今昔物语集·恋子至阎魔王宫》中端正可爱的容貌与“恋”这种心理及行为构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对美丽容颜的执着是热情洋溢的,它与对“恋”的执着的内在逻辑一致,都是由情感作为主导的思维方式生发的外在行为,强调人的本能需求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通过对爱子的思念与痴迷,《今昔物语集》强化了人的主体地位,人不再是佛法下的平面化、均质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活生生的个体。
在比丘与孩子的再会时对孩子的描述表现中,同样可以看到汉文典籍与日文典籍在理智与情感层面的差异——
梵志即往,见儿与诸小儿共戏,即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昼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宁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儿惊唤,逆呵之曰:“痴騃?老翁,不达道理。寄住须臾,名人为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间,自有父母,邂逅之间,唐自抱乎?” ?(《法句譬喻经》)
即往,见儿与诸小儿共戏。前抱啼泣曰:“我昼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宁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儿唤逆呵之曰:“痴騃老翁,不达道理。寄住须臾,名人为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间,自有父母。?(《经律异相》)
梵志即往,见儿与诸小儿共戏。即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昼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宁不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儿惊唤,逆呵之曰:痴騃老翁,不达道理。寄住须臾,名人为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间自有父母。邂逅之间,唐自手抱。?(《法苑珠林》)
父亲欣喜,按大王指示来至后院,得见孩子。其时,孩子正与几个相仿的孩童玩耍。父亲见此,呼孩子近前,告曰:“我数日来对汝思念不止,向大王请求得以见汝。汝亦同心思念我否?”说罢眼泪汪汪。然孩子毫不动容,不以为是父亲,只是继续同孩子奔跑玩耍。父亲悲伤流泪,孩子却不以为意,对父亲无话可说。?(《今昔物语集》)D118055A-3802-4AFB-BC79-04153FB8070A
汉文典籍高度一致的叙述强调了以下逻辑:首先,“汝念父母辛苦以不”的啼哭,反映了要求子女铭记父母养育之恩并且来日回报的“孝”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现实利益的意味。
反观比丘关于一定要到阎魔王宫寻回孩子的理由的阐述:
答言:“我有一子,辩慧过人,近日卒亡,悲穷?懊恼,不能自解。欲至阎罗王所,乞索儿命,还将归家,养以备老。” ?(中略)梵志启言:“晚生一男,欲以备老,养育七岁近日命终,唯愿大王垂恩,布施?还我儿命。” ?(《法句譬喻经》)
答言:“我有一子,近日卒亡。欲至阎罗王所乞索儿命。” ?(中略)梵志启言:“晚生一男,欲以备老。养育七岁,近日命终。唯愿大王垂恩布施,还我儿命。” ?(《经律异相》)
答曰:我有一子,辩慧过人,近日卒亡,悲穷懊恼,不能自解。欲至王所,乞求儿命,还将归家,养以备老。?(中略)梵志启言。晚生一男,欲以备老。养育七岁,近日命终。唯愿大王垂恩布施,还我儿命。?(《法苑珠林》)
答曰:“我为某某。我儿七岁离世,因对其爱恋之心难耐,欲请求阎罗王许我见之,来至此地,愿大王心怀慈悲,许我见儿。” ?(《今昔物语集》)
三部汉文典籍中都强调了“养以备老”这一理由,对于年逾六十、老来得子的比丘来说,该子与其说是情感上的寄托,不如说是老年物质生活的依靠,比丘的出发点在于满足肉欲。
尤其在《法句譬喻經》 《法苑珠林》中,辩慧过人(孩子的特质)、悲穷懊恼,不能自解(自己的情感)的主张具有将孩子物质化与私有化的意味:年迈的比丘很有可能不能再生出下一个孩子,即使再次生子也不能保证他是辩慧过人的男孩子,这就如同失去了价值连城的珠宝,是一种绝对的财富损失。为此,比丘悲伤不已、懊恼的原因也是将丧子归因为自己的失误——实际上该子是重病离世。这种归因的心理的潜在逻辑是,比丘自认为对子嗣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感动悲痛也不是为了孩子的死去而悲痛,而是为了自己的损失而悲痛。所以比丘的思考方式是以理智主导的,他在斤斤计较自己的得失,具有较强的功利性;他的思考中,冷彻的生存需求以绝对优势压制了情感需求。
相反,《今昔物语集》中,“对其爱恋之心难耐”“许我见之”的阐述则丝毫看不见物质层面的诉求。比丘不仅不在乎孩子是否博学多才,而且也没有为自己的养老问题担忧,他所追求的不是自身的安稳,而只是片刻的情感满足。“我数日来对汝思念不止,向大王求得以见汝。如亦同心思恋我否?”说罢眼泪汪汪。然孩子毫不动容,不以为是父亲,只是继续同孩子奔跑玩耍。父亲悲伤流泪,孩子却不以为意,对父亲无话可说。当再次见到孩子,比丘只是表达了思念之情,并且期待着孩子与自己共情。这是一种发自人的本性的无私的爱意,是极其自然的情感流露。在其他三部汉文典籍中都见不到的“眼泪往往”的细节刻画,是《今昔物语集》编纂者能动性的移情与想象。“父亲流泪——孩子玩耍——父亲流泪——孩子不以为意”的反复叙述,看似累赘,实际上形成了父亲——孩子两相对照的镜头切换,塑造了一种真实的画面感。此处,父与子是单独的两个人,而不存在附属关系。两相对照的描述改变了汉文典籍中利己主义的主题,实现了由“理智”向“情感”本位的置换。
二、求子的历程——悟道与遂愿的背离
从比丘的“所求”与“所得”中可以看出,《今昔物语集·恋子至阎魔王宫》实际上是与三部汉文典籍貌合神离的另外一则故事。
因汉文典籍该故事大致相同,故以《法苑珠林》版本为例,该比丘是少年出家,而到了六十岁还没有得道;而《今昔物语集》中没有交代该比丘开始求道的年纪,那么其求道可能是几十年,也有可能开始修行佛法较晚,不过几年光景。
这就涉及虔诚性的问题。《法苑珠林》中的比丘是在潜心修行佛法,只是缺少一个开悟的契机。所以,在比丘放弃之时,比丘通过“得子——丧子——寻子——求见子——遭子斥责——求佛问法——得道”一连串的经历完成了悟道——“梵志闻已,豁然意解,即于座上得阿罗汉道”。那么这个老年所得的孩子,在文中就只是引导比丘开悟的工具人。比丘的诉求看上去是找回儿子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最终求而不得。但这一层物欲的诉求实际上包裹在对佛法的诉求这一更为长久、深层的诉求中,形成了一种嵌套结构。丧子对比丘而言看似是损失,但从最终结果上看是收获,他完成了悟道的夙愿。
汉文典籍中比丘之子为何一定是“辩慧过人”的?除了汉文学中看重才智的文化传统的规约外,比丘自己无法独立完成开悟这一点,也要求必须有人强力地刺激他。通读全文会发现,《法苑珠林》中的比丘远比《今昔物语集》中的比丘要虔诚得多:《法苑珠林》中的比丘,少年时代就早早出家了,修行佛法的时间要长得多;还俗是因为求法不得,不得已为之,与《今昔物语集》中“比丘虽为此事叹息,然终有心无力。一日,回家后心想:为了成为罗汉,常年修行,却未修成,不如还俗回家”所体现出来的还俗的任意性和随机性大为不同。
《今昔物语集》中的比丘显然对求得佛法并没有特殊的执念,他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多年的投入,但也尚且能够自得其乐。《法苑珠林》中,在启程前往阎罗王宫之前,比丘沐浴、斋戒、焚香、持花,仪式完备;而《今昔物语集》中没有这一情节。另外,《法苑珠林》中比丘“行数千里”表明路途极为漫长,并且阎魔王宫不过是阎魔王暂时歇息的行宫,比丘必须在“四月四日”这一限定的时间赶到;而《今昔物语集》中阎魔王宫只需前行“几许路”,且“七宝宫殿”的描述更像是永久的居住地而不是阎魔王临时的办公和歇脚的场所。——《法苑珠林》中的整个旅途要比《今昔物语集》中的求子之路艰辛得多,路途的艰辛是考验比丘求道的虔诚性的重要条件。
《法苑珠林》中寻子的艰辛为后文埋下了伏笔,旅途越艰辛,后文中七岁孩子对比丘的斥责就更加激烈、刺痛、发人深省。比丘看重的“辩慧过人”的特质对其自身造成了反噬效果:“小儿惊唤,逆呵之曰:痴騃老翁,不达道理。寄住须臾,名人为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间自有父母。”的反应是出乎意料的,也是令比丘痛心和迷惑的。在此处,小儿实际上担任了解说佛法的角色:即人的身体不过是灵魂暂时的寄居地,你的儿子也并非属于你,只不过是你自以为是地将其命名为你的儿子;而须臾之间,我已经有了新的父母。丧子的强烈抨击更触发了比丘问佛的结果,并最终助比丘一臂之力完成了“悟道”。D118055A-3802-4AFB-BC79-04153FB8070A
所以,《法苑珠林》等三部汉文典籍忠实了宣扬佛法的目的,并且逻辑连贯,情节完整——“所得”即为“所求”。而反观《今昔物语集·恋子至阎魔王宫》,比丘求的是什么呢?不是悟道,而是再见爱子一面的夙愿。至于孩子回不回来自己身边并无强求。整篇故事中,比丘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告知阎魔宫殿位置的人是“有人”,询问比丘来意的人是“一高贵之人”,比丘甚至没有直接面见阎魔王,孩子的具体位置是由“此人”通报的。孩子的位置也不是《法苑珠林》中单独的东院,而就在“后院”。整个历程中的其他人都被背景化、模糊化了,盖是比丘深刻地“浸泡在”自己的悲伤中,周边是些什么场所、什么对象都已经变得无关紧要。所以最后,比丘见到了爱子;爱子也没有痛斥他愚痴,只是表现出一个七岁孩童本该存在的天真。
《今昔物语集》中爱子的“失语”一举摒弃了佛教说法的力量,“失语”使得“丧子——恋子”现象成为不存在任何罪孽的纯自然现象,而在该纯自然现象中悲伤也好、眷恋也罢,人类的所有情感具有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的正当性。
《今昔物语集·恋子至阎魔王宫》的“话末评” ?尤其耐人寻味:“此为生死相隔,死者已失本心之故。父亲身在现世,故有此悲情。”对于孩子的不以为意,既没有斥责其忘恩负义、不守孝道;也没有反讽比丘愚痴,痴迷于生死亲情;而是平淡地道出原委,使得双方都可以接纳自己。笔者猜想,它同时也是编纂者对世人的教诲:“你们和该比丘一样身在现世,那么一样也会产生悲情,但这是极其自然的,可接受的,不需要为难自己。”
三、消失的母亲——比丘的独角戏
在四篇故事中,孩子的母亲都是“失语”的——
“然后归家娶妇为居。生得一男” ?(《法句譬喻经》)
“法应归家,娶妇为居士。生得一男” ?(《经律异相》)
“然后归家娶妇” ?(《法苑珠林》)
“其后,娶妻成家。妻子随即怀孕,生下一容貌端正之男婴。” ?(《今昔物语集》)
对比丘的配偶的描写仅寥寥数笔。《今昔物语集》第一卷“天竺”的第十九篇《佛陀姨母憍昙弥出家》?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女子需要守“八戒”:“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百岁比丘尼也应礼拜刚入佛道的僧人,七、尼不骂僧,八,比丘尼不得举僧人罪过”。?
那么,该比丘六十岁所娶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她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呢?她在婚姻中的诉求是什么呢?她怜爱自己的儿子吗?她在“丧子”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呢?通过文本,我们不得而知。在强调对儿子的疼爱时,也是表述为“父亲”十分疼爱,而不是“父母亲”十分疼爱。母亲形象的空白——“失语”使得儿子只成了父亲生命的延续。
那么,为什么《恋子至阎魔王宫》所凸显的是父子关系呢?在《今昔物语集》的其他“物语”?中,僧人的家庭关系是如何构造的呢?
四、天竺故事?本朝故事?
在讨论僧人的家庭关系之前,存在这样一个疑惑:“该物语的主人公始终被称为‘比丘吗?”
答案是否定的。
《恋子至阎魔王宫》中开篇就交代了“从前,天竺有一比丘……(中略)……不如还俗在家。其后,娶妻成家……”那么从此刻开始,他就不再是僧人的社会身份,这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六十岁的普通老翁——可能也不普通,在医疗水平低下、瘟疫横行的古代,属于相当长寿的老翁。
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被赋予一个新的姓名呢?至少他在出家之前应该是有与法号相对的俗名的。但实际上,《今昔物語集·恋子至阎魔王宫》中他始终没有姓名。这可能与《今昔物语集》的编纂目的相互关联——隐去姓名可以将物语普遍化,使得听取教诲的平民阶层能够带入感同身受的想象。
这样一看,《今昔物语集》似乎在没有姓名这一点上沿袭了汉译佛典的传统。《法句譬喻经·道行品》中称“昔有婆罗门”“梵志怜惜”“梵志欢喜”“梵志既往”“佛告梵志”……即使还俗,文本也始终没有改变对此人的称呼。这从根本上制约了故事的走向,它暗示了“结婚——生子——丧子”不过是“悟道”的“绕远路”,此人终究逃不过“悟道”的命运——在佛祖释迦偈语之后,“梵志闻偈豁然意解,知命无常,妻子如客……即于座上,得阿罗汉道。”
《经律异相》和《法苑珠林》也同样将此人始终称之为“梵志”。在此不再赘述。
但《恋子至阎魔王宫》还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的,尽管该变化发生得悄无声息。那就是:对此人的称呼从“比丘”变成了“父亲”,而且此种变化在故事开端就发生了——“……生下一容貌端正之男婴。父亲对其疼爱有加……”从此以后直到故事结束,对此人的称呼,再也没有出现过“比丘”一词。
是佚失的二手资料对汉译佛典做了根本性变革吗?还是《今昔物语集》的编纂者(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不得而知?。但不能是二者中的哪一种,都显示出一种倾向:《恋子至阎魔王宫》虽然以“天竺”赋予人物身份与存在的空间,但是本质上是一个“本朝”物语,即讲述的不是印度的故事,而是关于日本的故事。
《恋子至阎魔王宫》对此人的身份的定位是“父亲”,“父亲”的概念是在与“儿子”的对应关系中建构起来的。那么它可以归类为日本平安时代家庭“丧子”类故事,书写的中心可以确认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性思考”“和歌文学在丧(亲)子之痛主题上的物语化(散文文学)表现”“超越贵族——平民阶级的日本情感”……总之它不再是一个佛教故事,而是披上了佛教外衣的世俗物语。
而“梵志”的概念与建构在亲子关系上的“父亲”概念迥异,“梵”是建立在梵语基础上的佛教,“志”是拥有皈依佛教志向的信徒。“梵志”是一个宗教概念。同样“比丘、比丘尼”是日语音译,也是等价或者意义近似的宗教概念。三部汉译佛殿保持了“梵志”的用词,而《恋子至阎魔王宫》扬弃了“比丘”、转换成了“父亲”;三部佛殿还在佛教框架内,而《今昔物语集》至少在《恋子至阎魔王宫》这篇物语中跳脱出了佛教的框架。强调了前文分析过的作为人的情感的正当性。D118055A-3802-4AFB-BC79-04153FB8070A
所以,《恋子至阎魔王宫》应该与平安时代末期——镰仓时代初期的“本朝丧子故事”等进行横向比较分析,而不应该放在天竺的时空范围内。
再者,文章中实际并没有限定该比丘的社会阶级。不能因为《今昔物语集》是面向庶民阶层的说话文学,就认定该比丘一定是身无分文被迫出家,难道不也存在出身贵族的可能性吗?如第十五卷第三十六篇《小松天皇的孙女出家为尼往生极乐》,况且《今昔物语集》第十九卷中出家的贵族也不在少数。
与中国、朝鲜半岛不同,日本的僧人结婚生子是普遍现象。而且平安时代的婚姻制度是“走婚制”。此处有必要探讨平安时代——镰仓时代的孩子的意义与家庭关系。
五、“丧子”与家庭关系
平安时代继承了前代的走婚制度。根据电子词典《大辞林》,走婚(通い婚)的定义是:“結婚後も夫婦が同居せず、夫または妻が相手の居住場所を訪ねる婚姻形態。”即走婚制,也称访婚制,结婚后夫妇不同居,丈夫或妻子走访对方的居住场所的婚姻形态。
“在家庭生活的层面上,原始社会以来的母系家庭形态并没有完结,维持了由夫妇分居造就的妇女独立,未能完全实现女性隶属男性的社会制度。财产由包括男女在内的子女共同分割和继承……” ?
这里必须考察比丘的妻子的社会地位。如果该妻子是普通女性,那么由于经济拮据,她必须承担经济责任、作为生产劳动主力存在,并且很有可能与比丘同住,并且孩子没有专门的乳母,由自己喂养。如果是贵族女性,她就不需要承担社会劳动,家中可能有乳母、仆妇;她会拥有“甚高的社会地位” ?,但是没有“特定的社会功能” ?——“除了是男性的性爱对象外,缺乏存在的理由,从这一点来说,她们所处的地位是极其脆弱的。并且,丈夫拥有随时终止走婚并转向其他女性的自由,因此,分居的妻子比同居的妻子更加怀有可能被抛弃的不安,感情上总是难以摆脱被丈夫所左右的忽喜忽忧的状态。” ?
不论是哪一种,比丘的妻子相对于比丘而言都应该是处在劣势地位的。与现代的男女平等的“爱”不同,日本古代的“爱”是一种处于高位的人(常常是男子)对于处于低位的人的一种“怜爱”。比丘的妻子的“失语”意味着她是被纳入以比丘为中心的家庭构造中的。
但这不意味着《今昔物语集》中的家庭关系都是以男子为中心叙述的。如第十六卷第七篇《越前国敦贺女子蒙观音赐福》?、第八篇《殖规寺的观音救助贫女》?等都是从女性的婚配的角度描述家庭关系的,他们关注的是女性的幸福。相同点在于“婚配=幸福”的家庭观念,“良缘+生子+富贵+长寿”是幸福家庭的评价标准,并且叙述者存在一种将“婚配”当作一次性“赌博”的思想:幸福就在这一刻,稍微踏错一步,人生就再也不会回到幸福的状态;而只要抓住这一次良机,夫妻就能一直幸福下去。这种故事构造渗透了命运的神秘主义色彩,有利于宣扬佛教。
所以,虽然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男女平等的家庭关系,但是与现代日本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结构?是不同的,它是以“恋”为中心、以夫妻关系为基本构架的家庭关系。例如《古今和歌集》 (905)在20卷中用5卷来收录以“恋”为主题的和歌,直到《新古今和歌集》(1205)仍旧延续了这一传统,加上《伊势物语》《源氏物语》《蜻蛉日记》等一众主流文学皆仅仅围绕“恋”的主题,男女关系被日本文学阶层(贵族)构建为一种核心的家庭——社会基本结构。《恋子至阎魔王宫》的“恋”,笔者认为是男女关系“恋”的延伸,它构成了该故事的情感内核。
在这样一种家庭——亲子关系下,《恋子至阎魔王宫》的“恋”的概念变得具有强烈的日本本土色彩。这种对情感的强调还可以从该物语在四部书中的名称和排版位置中体会到。
六、不同的故事名与排版位置问题
对比阅读可以发现,四则故事虽然是同一故事的不同呈现,但是故事名却并不相同。《法句譬喻经》为《法句譬喻经二十八 道行品》,《经律异相》为《经律异相卷第四十(梵志部)·梵志丧儿从阎罗乞活儿不亲从诣佛得道五》,《法苑珠林》为《法苑珠林校注卷第五十二·眷属篇第五十六·哀恋部第二》?,《今昔物语集》为《今昔物语集·卷四 天竺 佛涅槃后·第四十一篇恋子至阎魔王宫》。
不同的故事名不仅本身具有探讨的意义,与在书中的排版位置也存在某种主题上的、逻辑上的关联。下面将一一论述:
《法句譬喻经二十八 道行品》的前一篇为《二十七 奉持品》 ?,讲述的是婆罗门长者萨遮尼犍高傲自大向释迦挑衅,质问一系列佛教奥义,最终被释迦感化,带领五百弟子集体皈依出家的故事。《奉持品》的张力在于,释迦用规整、气势磅礴的偈语平静地教化了高傲的长者,激烈的冲突加深了故事的意蕴。该篇的目的在于说明修行佛法之人应该戒除傲慢、贪婪、奢侈等品质,奉持谦虚、严于律己之品行,是对修行者的基本道德要求。后一篇为《二十九 广衍品》 ?,讲述的是憍?萨罗国王贪恋美食、日渐肥胖,得释迦教化瘦身成功并传播给国人饮食方法的故事。《广衍品》的张力在于对贵族阶层因为骄奢淫逸而丑态百出的反讽。“广衍”指的是延年益寿,背后是佛教的人与自然相调和的生命观。那么将《道行品》放入排列结构中,可以看出《奉持品》是对修行僧人入门前基本——综合性品质的规范,《道行品》劝导信徒放下生离死别的执念、顿悟万事无常、引导信徒一心向佛,《广衍品》继续讨论以严于律己实现终身信佛的可能性。《法句譬喻经》三十九篇均以“品”命名,均以“发问——释迦偈语——顿悟”的结构谋篇布局,篇章之间又存在逻辑上的继承与展开,最终以“譬喻”的方式将整个佛教思想体系具体化,起到教化世人的作用。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梵志部)·梵志丧儿从阎罗乞活儿不亲从诣佛得道五》的前一篇为 《摩因提梵志将女妻佛四》?,讲述的是摩因提梵志想要将容貌端正的女儿嫁给释迦,但女儿见到释迦时心中淫乱之意熊熊燃烧,释迦守“不邪淫”戒律拒绝娶妻的故事。后一篇为《梵志谄施比丘说一偈能消六》 讲述的是梵志为人悭吝想要假装通过施舍僧人一顿饭获得五百牛马的回报、但心思早已被僧人看穿、受僧人教诲后“悟道”的故事。《经律异相》第四十卷“梵志部”共12篇讲述的都是梵志的故事,将《梵志喪儿从阎罗乞活儿不亲从诣佛得道五》放入比较可以发现,第四的主旨是守“不邪淫”戒律,即不近女色;第五的主旨是放下对亲人生老病死的执念,执念在佛教看来也是罪孽;第六的主旨是劝人放弃“贪”。“梵志部”通过各类“禁止”,相互呼应,共同规范僧侣行为,为修行佛法制定了细致的操作准则。D118055A-3802-4AFB-BC79-04153FB8070A
如果说《经律异相》是以“梵志”这一身份汇集了诸故事的话,那么《法苑珠林》的编纂体例可能更加规整、条理清晰、结构明确,展示了编纂者释道世(唐)深厚的汉学与佛学双重功底 。《法苑珠林校注卷第五十二·眷属篇第五十六·哀恋部第二》从属于“眷属篇” ,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探讨的是家庭关系。《述意部第一》提纲挈领,阐述“眷属篇”的主旨,“窃寻眷属萍移,新故轮转。去留难卜,聚会暂时。良由善恶缘别,升沈殊趣……” 《哀恋部第二》讲述了两个故事,一是释迦劝解死者须摩提亲眷宗族脱离‘恩爱 的束缚,皈依三宝,诚心信佛;二是本文所论述的“丧子”故事:两则故事都强调放下对亲眷生死的执念,虔心修佛。《改易部第三》讲述了四则故事,将“哀恋”用“改易”即“转世——前世今生”来解释,均旨在用“转世”的概念解构现世的亲子关系、亲眷关系,强调跳脱生死亲情,皈依佛门。《离著部第四》则否定了“家”的价值:家是“难满”“五足”“无息”“苦性”“障碍”……“无常”“众苦”“假借”“眠梦”“朝露”等等。并补充了佛性的榜样范例。后面的“感应缘”部分则用晋朝、唐朝、宋朝共7则本土灵验谭,补充《述意部第一》的观点 。那么本文讨论的“丧子”的故事在佛教看来,“死亡”是轮回的一部分。
这么看来,《今昔物语集·恋子至阎魔王宫》在整部《今昔物语集》中所处的位置就有些怪异。前文也提到,先行研究认为《恋子至阎魔王宫》排列错误,应该是佛涅槃前的故事,因为三部汉译佛典中都不是在“比丘徒劳而返”处将故事完结的,而是该比丘(梵志)寻找到释迦面前询问为什么自己的儿子不承认是自己的儿子,释迦教诲到:“汝实愚痴,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缘合居,譬如寄客,起则离散。愚迷缚著,计为己有。忧悲苦恼,不识本根。沉溺生死,未复休息。唯有慧者不贪恩爱,觉苦舍习,勤修经戒,灭除识想,生死得尽。”
即释迦(佛教)关于“丧子”一事的主要观点:(1)身体只是灵魂寄宿的器皿;(2)亲人不过是偶然的缘分,终将离散;(3)愚蠢的人苦恼于生死,智慧的人不再贪恋亲情、通过修行佛法跳出生死轮回。
那么,我们就无法从排列位置上去讨论它的前后关联。
我们当然可以同意先行研究的观点,甚至可以尝试将该物语重新排列、插入到《今昔物语集·卷二 天竺》或者《今昔物语集·卷三 天竺》中的某个位置,以符合“佛涅槃前”这一标准。
但也可以假定该位置是合理的,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它为什么在现在这个位置。
它的前一篇为第四十篇《天竺贫女写〈法华经〉》,讲述的是母女情深的故事:(1)贫女求佛得以生产一女,此女儿容貌端庄秀丽;(2)由于一贫如洗,女儿为了满足母亲书写《法华经》的愿望,四处变卖自己的头发;(3)到王宫买发招来杀身之祸;(4)心中求佛,得救,从王宫获得无数财宝,母女团圆。
如果说《恋子至阎魔王宫》是父亲对儿子的依恋,那么前篇则是女儿对母亲的依恋,它不是单纯的“孝养”,如果是的话应该编纂成“天竺 孝养”卷,如同《今昔物语集·卷九 震旦 孝养》一样。
两篇故事有相似的情节,该贫女无依无靠,得女不易,如同比丘六十得子;两个孩子都拥有秀丽的容貌,备受疼爱;都为了夙愿踏入陌生的环境——贫女的女儿的身份同样属于受隔离、歧视的最下层民众,能进入王宫是难以想象的,如同阎魔王宫对于活着的人来说也是不可能踏入的地界;最终实现了母女/父子的再会。女儿所担心的是母亲陷入悲伤,却没有在乎生死;同样,比丘的驱动力在于想念。两篇故事的内在联系在于,生育最初的目的可能的确在于老后得到赡养的经济利益,但是亲情的力量已经超越了现实利益,显示出以无法随心所欲控制的感情羁绊为中心的强大感染力。
下一篇是《今昔物语集·卷五 天竺 佛前·第一篇 僧伽罗带五百商人共至罗刹国》,讲述的是与罗刹鬼斗智斗勇、开疆扩土的故事。有研究 认为,对罗刹鬼(常以美貌女子形象出现)的征服与开疆扩土的文学叙述中,存在着征服和驯化自然力量和超自然力量的激情。不过可能是跨卷的原因,与此文联系不明显,不再赘述。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三部汉译佛典是一种“向心结构”——说尽千般万般故事都有一个共同指向,即“劝人向佛”;而《今昔物语集》是一种“离心结构”——虽然用外来宗教重塑了本土文明,尤其是本土的世界观,但众多的故事纷纷脱离佛旨,庞大的世俗故事最终取得了优势地位,成功压制了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保留并重塑了“本朝”的主体性。
《今昔物语集·恋子至阎魔王宫》通过上述不同,尤其是对后文释迦说法的彻底删减,颠覆了佛教劝人抛妻弃子的训诫,强调了人类情感的正当性、合法性和主导性。
七、结论
《今昔物语集·恋子至阎魔王宫》中父子亲情的描述挣脱了汉文典籍中利己主义的束缚,实现了由“理智”向“情感”本位的置换。该父亲求见亡子的历程显示了“悟道”与“遂愿”的背离。虽然故事的时空被设置为古代天竺,母亲与孩子相继“失语”,但它依旧拥有以“恋”为情感内核的故事结构。笔者认为,通过改写,《今昔物语集》的编纂者(们)显示了应对汉学、佛学两种外来文明的内化能力,编纂者(们)充分吸收并内化了外来文明,重塑了日本的主体性。
注释
①张龙妹、赵季玉译:《今昔物语集:天竺震旦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②新古典文学大系《今昔物语集(一)》第282页注释指出,根据与《法句譬喻经》的对照比较,本篇故事是释迦在世的教化谭,而不是在佛涅槃后。后文也会加以分析。
③同上。第217页。
④大概是《今昔物语集:天竺震旦部》(见注释1)的注释错误,不是第三十篇,而是第二十八篇。諸网页显示也是第二十八篇。“道行品”是可靠的检索线索。
⑤《法句譬喻经》《经律异相》《法苑珠林》均为繁体中文,从上往下、从右往左书写,为方便阅读本文中均改为简体中文(中国)。此处的“道行”不是指修行法力的高低,而是指僧人的德行。D118055A-3802-4AFB-BC79-04153FB8070A
⑥荆三隆、邵之茜:《法句譬喻经注释与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⑦《经律异相》均为繁体中文,为方便阅读本文中均改为简体中文(中国)。
⑧(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⑨大概是《今昔物语集:天竺震旦部》(见注释1)的注释错误,不是“眷恋部”,而是“哀恋部”。
⑩汉译佛典中常为“阎王”。
?荆三隆、邵之茜:《法句譬喻经注释与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6页。
?(梁)宝唱等编纂,董志翘,刘晓兴等校注:《经律异相校注》,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1332。
?(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49页。
?张龙妹、赵季玉译:《今昔物语集:天竺震旦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页。原文为——其ノ妻即チ懐妊シテ、端正ナル男子ヲ生ゼリ。父此レヲ愛スル事無限シ。
?小林保治,全訳注:《唐物語》,講談社学術文庫2003年版,第45页。
?不慧,愚蠢。
?荆三隆、邵之茜:《法句譬喻经注释与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
?(梁)宝唱等编纂,董志翘、刘晓兴等校注:《经律异相校注》,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1332页。
?(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50。
?张龙妹、赵季玉译:《今昔物语集:天竺震旦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页。原文为——父喜ビノ心深クシテ、教ヘニ随テ其ノ所ニ行テ見ルニ、我ガ子有リ。同様ナル童子共ノ中ニ遊戯シテ有リ。父此レヲ見テ、子ヲ呼ビ取テ泣ク泣ク云ク、「我レ日来汝ヲ恋ヒ悲ム心深クシテ、王ニ申シ請テ見ル事ヲ得タリ。汝ハ同心ニハ不思ルカ」。涙溺レテ言フ二、子敢テ歓ク気色無クシテ、父トモ思ヒタラズ遊ビ行ク。父、此レ恨ミテ泣事無限シ。然而モ、子何トモ思ヒタラズシテ言フ事無シ。同注?,第383页。
?哀痛绝望。见王毅力:《〈法句譬喻经〉词语考释》,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学位论文,第15页。
?荆三隆、邵之茜:《法句譬喻经注释与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由于古汉语书籍没有标点符号,不易断句。但笔者倾向于将“垂恩布施”连在一起阅读。《法句譬喻经》的句读问题依旧存在较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如程慧:《〈法句譬喻经〉断句商榷》,《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1)期,第105-106页。
?荆三隆、邵之茜:《法句譬喻经注释与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梁)宝唱等编纂,董志翘、刘晓兴等校注:《经律异相校注》,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1332页。
?(梁)宝唱等编纂,董志翘、刘晓兴等校注:《经律异相校注》,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1332页。
?(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49-1550页。
?(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50页。
?张龙妹、赵季玉译:《今昔物语集:天竺震旦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页。原文为——答テ云ク、「我レハ然然ノ人也。我ガ子七歳ニシテ亡ゼリ。此ヲ恋ヒ悲ム心難堪クシテ、其レヲ見ム事ヲ王ニ申請ムガ為ニ参レリ。願クハ王、慈悲ヲ以テノ故ニ我ニ子ヲ見セ給ヘ」 ト。同注?。
?话末评,在《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等“说话文学”中,每一篇故事被成为一话,结尾编者对本话的评价通常起到教化世人、宣扬佛法、传播生存智慧的作用,称为“话末评”。
?荆三隆、邵之茜:《法句譬喻经注释与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6页。
?(梁)宝唱等编纂,董志翘、刘晓兴等校注:《经律异相校注》,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1332页。
?(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49页。
?张龙妹、赵季玉译:《今昔物语集:天竺震旦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页。原文为——其ノ後、妻ヲ儲タリ。其ノ妻即チ懐妊シテ、端正ナル男子ヲ生ゼリ。同注?,第382页。
?张龙妹、赵季玉译:《今昔物語集:天竺震旦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2-63页。
?张龙妹、赵季玉译:《今昔物语集:天竺震旦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
?物语(ものがたり),通常理解为讲故事。日本文学界将带有佛教教义、社会启蒙性质的物语重新归类为说话(せつわ)。二者其实是同一性质的文学体裁。物语与小说的区别在于:“物语的本来面目是一五一十地描写人生全般,结构散漫,但是对这种散漫安之若素。而小说有描写的重心,作者围绕中心布局事物。”详见小西甚一《日本文学史》第40-41页。
?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佚失的日本书籍对汉译佛典进行了根本性变革,然后《今昔物语集》的编纂者(们)摘录的时候单纯沿袭了文本,因为要编纂31卷共1000多篇物语工作量太大(?),而他(们)对此篇物语的变革是不自知的。又或者,佚失的日本书籍变革了一部分,《今昔物语集》的编纂者(们)又变革了一部分?由于没有证据,暂且不讨论这两种可能性。
????(日)家永三郎著、赵仲明译:《日本文化史》,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页。
??北京编译社译、周作人校:《今昔物语:浮世绘插图珍藏版》,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D118055A-3802-4AFB-BC79-04153FB8070A
?(日)中根千枝著,陈成译,东尔校:《校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法苑珠林》的特点是:一“篇”可能由于书写内容庞大,分布在连续的好几“卷”;也可能每一“篇”内容短小,一“卷”中囊括了好几“篇”。“卷”与“篇”并不保证序号总是一致。例如本文讨论的故事《哀恋部第二》就是在第五十六篇“眷属篇”之下,与其并列的还有《述意部第一》《改易部第三》《离著部第四》;但是整个“眷属篇”占据了第五十二卷的前半部分。第五十二卷的后半部分又包括下一篇“校量篇”的七个部分。
?荆三隆、邵之茜:《法句譬喻经注释与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5页。
?荆三隆、邵之茜:《法句譬喻经注释与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247页。
?书中为异体字,是“憍”的简体。
?(梁)宝唱等编纂,董志翘、刘晓兴等校注:《经律异相校注》,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1331-1332页。
(梁)宝唱等编纂,董志翘、刘晓兴等校注:《经律异相校注》,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1334-1335页。
可参考吴福秀:《〈经律异相〉与〈法苑珠林〉分类之比较研究——兼论唐初知识体系发展特征(二)》,《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年第(03)期,第78-79页。
(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47-1566页。
(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47页。
此处指的是广义的家族亲情关系,而不是婚姻层面的恩爱。
“《法苑珠林》除了广引佛典外,也博采外典来证明佛法所言都是真实无妄。引用外典,一方面是利用中国古代先圣先贤的见解来支持佛法的见地,而另一方面则是广引中国志怪故事,把志怪当作史实来徵引。释道世充分引用中土故事,作为佛法可信的力证,以此种方式,使当时中国的文人和民众相信佛法的内容,从而减少印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隔膜。”见安正燻: 《〈法苑珠林〉叙事结构研究》,复旦大学2004年学位论文,摘要部分。
Eubanks, Charlotte. "Envisioning the Invisible: Sex, Species, and Anomaly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Women's Fiction." Marvels & Tales 27, no. 2 (2013): 205-217,348. https://www.proquest.com/scholarly-journals/envisioning-invisible-sex-species-anomaly/docview/1449840480/se-2?accountid=14426.
参考文献:
[1]张龙妹,赵季玉译.今昔物语集:天竺震旦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荆三隆,邵之茜.法句譬喻经注释与辨析[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
[3](梁)宝唱等编纂,董志翘,刘晓兴等校注,经律异相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18:3.
[4](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12.
[5]今野達校注.今昔物語集一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3[M].岩波書店,1999.
[6]唐物語,小林保治.全訳注[M].講談社学術文庫. 2003.
[7](日)小西甚一.日本文学史[M].郑清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6.
[8](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赵仲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1.
[9]北京编译社译,周作人校.今昔物语:浮世绘插图珍藏版[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
[10](日)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M].陈成译,东尔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1]王毅力.《法句譬喻经》词语考释[D].华南师范大学,2007.
[12]程慧.《法句譬喻经》断句商榷[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1):105-106.
[13]Eubanks, Charlotte. "Envisioning the Invisible: Sex, Species, and Anomaly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Women's Fiction." Marvels & Tales 27, no. 2 (2013): 205-217,348.https://www.proquest.com/scholarly-journals/envisioning-invisible-sex-species-anomaly/docview/1449840480/se-2?accountid=14426.
[14]吳福秀.《经律异相》与《法苑珠林》分类之比较研究——兼论唐初知识体系发展特征(二)[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03):78-79.
[15]蒋玮.《法苑珠林》中的女性故事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8.
[16]安正燻.《法苑珠林》叙事结构研究[D].复旦大学,2004.
作者简介:
卢康,男,清华大学外文系日语语言文学方向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日本古代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D118055A-3802-4AFB-BC79-04153FB807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