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之歌
黄熙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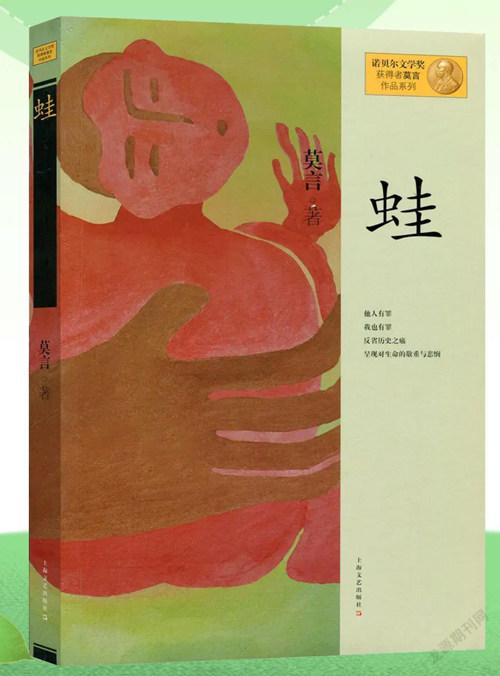

我用几天时间读罢全书,竟读得意外顺畅:《蛙》这本书没有《檀香刑》中血腥重口味的描述,没有《生死疲劳》里天马行空的情节,也不像《丰乳肥臀》庞大杂乱的结构,它真实平淡地浓缩了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围绕着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展现出各种人群在“计划生育”大背景下不同的命运。
读到一半,我便不觉产生了疑问:为何以“蛙”为题?直到接近作品的尾声,半疯癫状态的姑姑才点出:“人跟蛙是同一祖先。蝌蚪和人的精子形状相当……为什么蛙与娃同音?为什么婴儿刚从母腹出来时哭声与蛙声十分相似?为什么我们东北乡的泥娃娃塑像中,有许多塑像娃娃怀抱着一只蛙,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wā”被赋予了各种含义,但由一个喻体引申出的多个本体,都与生命有关。这本书不仅是单纯的纪实作品,还记录了鼓励多生时期,计划生育时期和现如今人们对待生命的不同态度,充分演绎出在各种时期“蛙”所喻本体的变化。
在鼓励生育期间,主人公的姑姑万心在四年间接生了1645名婴儿,几乎为零的失误率使其被冠以“送子娘娘”的美称。正如书中的描写,“她将婴儿从产道中拖出来的那一刻会忘记阶级斗争,体会到的喜悦是一种纯粹的感情”。莫言用无数个动词“飞车而下”“冲”“搡”“扯”等把一个热心正义,热爱生命的妇产科医生呈现在读者面前。四年间,高密东北乡经济繁荣,新生儿人数倍增,这时候“蛙”是生机勃勃的意象。雌蛙每次能排出大约八千到一万粒卵子,如此快的繁殖速度象征了生命的强盛和蓬勃。
好景不长,“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后,忠诚敬业的姑姑便从“送子娘娘”变成“杀人的恶魔”。姑姑笃定地响应党的号召,奔波在每个乡镇之间,给男人结扎,给女人带环,做各种流产手术,成为了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同时也成为了“重男轻女”思想的主导抗衡者。正因为阻断了一贯的传统,加大了某些家族“断后”的可能,姑姑被视为全民公敌。尽管如此,她仍然一丝不苟,尽最大力度打击超生。这时候的姑姑似乎被新政策“洗脑”,似乎并不像从前那般充满神圣和敬畏地对待生命。但果真如此吗?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村里同样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表哥,他需要做的也是在村镇里搜查超生的人。实施者往往处在计划生育工作架构的最底端,这也是政策的优劣之处。这类人受保护程度低,可能会被该家族暗中报复。但也正因如此,想用金钱了事的许多人,无法瞒天过海。可见即便是在现在,社会上也需要有“丑人”和负隅顽抗的落后者作斗争。何况,当孕妇在逃脱中生命垂危时,姑姑也毫不犹豫地去接生救人,尽管在经历生死时速的抢救后,只换来一句叹气,道:“又是个女孩。”
无数的骂名终究给姑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姑姑噩梦缠身,“那天晚上蛙声如哭,仿佛是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哭……对于一个妇产科医生来说,初生婴儿的哭声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啊!可那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这时候,“蛙”是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被姑姑做流产手术时抹去的生灵,但这又何尝不是那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下的牺牲品呢?
时代在更替,观念在转变,值得肯定的是生命无可比拟的意义。莫言在书中写道,“生育繁衍,多么莊严又多么世俗,多么严肃又多么荒唐”,它神圣庄严,是因为一个细胞被孕育成熟,脱落母体来到世界上,品尝酸甜苦辣,体会人情冷暖,何其幸运!它世俗,是因为生育不是空中楼阁不可攀越,它是每一个家庭都应该经历的。它严肃,是因为当一个生命的诞生,就有活着的权利,有独立的思想,有充沛的情感。它荒唐,是因为总有一些其他不可避免的因素在生命诞生前后赋予其负面的影响。
在对于蛙的各种隐喻当中,莫言传达出孕育生命的珍贵与伟大,这种伟大是超越一切的、神灵般的存在物。但令人感到沉重的是,在莫言构造的三个时段中,每个时段的人们都被不同的落后思想缠绕,从而衍生出各种巨大的矛盾,而矛盾背后的人们都没有给生命以足够的尊重。莫言在多种冲突的环境中,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被腐朽思想蚕食的个体,被贬损的苍白无力的生命,虚假无效的自我救赎,隐晦地表达出他的生命倾向,讴歌了生命的至高无上。
《蛙》无疑是一本生命之书。书中所描写的生命形态多种多样,是尚未出生的婴儿,是母爱泛滥的小狮子,是秉正无私的姑姑,是中立愧疚的万小跑……这些角色都会在温暖的母体中孕育出的细胞,却对生命有如此迥异的演绎。
生命如蛙,而蛙声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