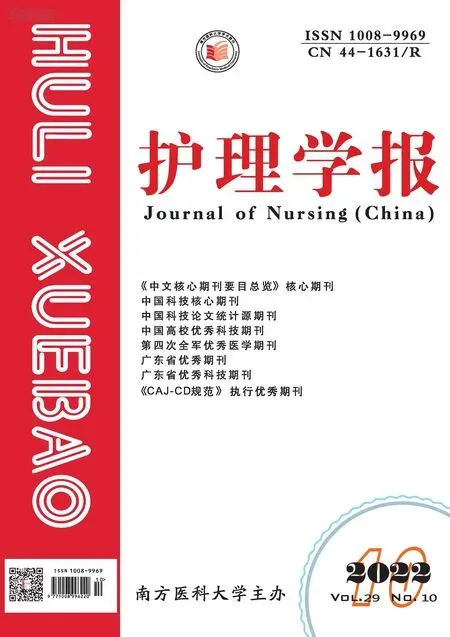疼痛共情的研究进展
人类作为一种高等生物会有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体验,在人与人的相处中, 不仅自己经历着各种情绪体验,还可能对周围其他人的情绪体验产生认知评估及相应行为反应, 这种感同身受的过程就是共情(empathy)
。共情包括了情感和认知2 个方面
。疼痛共情是与人际互动密切相关的心理现象,指的是个体在察觉到他人的疼痛或受伤状态时产生的对他人疼痛的感知、判断和情绪反应
。 疼痛共情(empathy for pain)是共情中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形式,是一种亲社会行为,也包括情感和认知2 个方面。 疼痛共情不仅能够促使个体感知他人的痛苦,产生同理心,维持良好人际关系;还可帮助个体保持警惕状态,规避可能出现的危险。近年来,有关疼痛共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病理生理演变过程
、测评方法
及影响因素研究
。笔者将从疼痛共情的概念、理论模型、评估工具和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综述,旨在引发人们对疼痛共情的关注,为疼痛共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综上分析,修水八洞湾地区地温梯度整体较高,为每100 m 4~6 ℃,而孔深830~870 m地温梯度有所降低,分析认为与导热系数降低,传热效能降低、岩石生热率降低有关,但也存在往深部地温梯度继续升高的可能。
1 疼痛共情的理论模型
1.1 知觉- 动作模型(Perception-Action Model,PAM) 2002 年,Preston 和de Waal 提出了知觉-动作模型, 该模型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是镜像神经系统(mirror-neuron system, MNS)
。该模型提出,当个体知觉到他人行为时会自动激活其与该行为有关的个人经验的表征。因此,当个体知觉到他人的动作或者情感时, 其大脑中表征相应动作或情感的部位会被自动激活,从而令个体产生同形的表征。 然而,镜像神经系统只能解释疼痛共情的情感共情部分, 无法解释疼痛共情中的认知共情部分。
1.2 疼痛共情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 for Pain Empathy)
2005 年,Goubert 等提出了疼痛共情认知模型, 该模型较为完整地阐述了疼痛共情的认知机制。 该模型阐明了个体产生疼痛共情的过程包含了2 个阶段, 分别是早期阶段对他人疼痛产生的自下而上的情绪共情(affective empathy),以及晚期阶段自上而下产生的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
。自下而上的情绪共情指的是个体目击疼痛表情、语言和肢体动作这些疼痛线索后, 会自动激活产生与疼痛相关的情绪和感知觉的体验。 自上而下的认知共情指的是各种认知因素对疼痛共情的调节作用,这些认知因素包括自身的疼痛经验、分享的知识、疼痛灾难化思维、观点采择、注意、疼痛评估等。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合在一起会影响个体对他人疼痛的体验,进而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这些情绪反应包括悲伤、焦虑、害怕、反感等自身感受和同情、安慰等移情反应。这2 种情绪反应可能发生在同一时间,但是前者是一种利己行为,后者却是一种利他行为。 相比于认知-动作模型,疼痛认知模型内容更加完整,但该模型并未阐明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的关系。
1.3 早期评估模型(Early Appraisal Model)与后期评估模型(Late Appraisal Model) 这2 个模型由De Vignemont 和Singer 于2006 年提出,早期评估模型认为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的调节作用在共情反应中处于早期阶段,而后期评估模型则认为是处于后期阶段的。这2 种模型均只有理论假设,未得到实证研究支持。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评分结果采用组间配对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 疼痛共情的沟通模型 (a Commmunication Model for Pain Empathy) 该模型认为疼痛共情的发生可划分为3 个阶段
:(1)疼痛者感受到疼痛;(2)疼痛者将自身的疼痛感加以编码,并以言语、动作或面部表情的形式传达给观察者;(3) 观察者识别疼痛信号,进而了解他人的疼痛状况,这一过程相当于解码。
2 疼痛共情的评估工具
2.1.2 其他普适性共情量表 除了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用于评估共情能力的普适性量表还包括多维度共情测验中文版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ultifaceted Empathy Test, MET-C)
、 咨询及关系共情量表(the Consultation and Relational Empathy Measure,CARE)
、共情沟通编码系统(Empathic Communication Coding System, ECCS)
等,但是这些问卷与IRI相比,在评估疼痛共情方面并无优势,且在疼痛共情方面的应用未进行信效度检验, 很少被用于疼痛共情的评估。
分析:原文中的显性连接词“但”在译文中反映了出来。原文后半句省略了主语,根据英语必有主语的语法规则,添加了主语“This”。
数学实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世界,里面充满了学生的情感和认知。学生的想法各式各样,从学生的经验出发,和他们一起去体验、思考、探索。数学隐性知识需要活动经验来滋养,因此数学实验任重而道远。
2.1.1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
IRI 由美国学者Davis 于1980 年编制,2010 年张凤凤等
将其进行汉化,中文版IRI 的Cronbach α 为0.75, 是最常用的评估疼痛共情能力的普适性量表。 该量表采用自评法, 涉及了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PT)、想象力(fantasy, FS)、共情性关心(empathy concern, EC)和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PD)等4 个维度。 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746~0.751,重测信度为0.663~0.770。 采用Likert 5 级评分法,部分条目反向计分。 该量表在美国、瑞士、中国、比利时等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已被应用于双相情感障碍
、精神分裂症
、抑郁症
等患者的疼痛共情能力评估。2015 年,意大利学者Ingoglia 将其改良为简略版的人际反应指针量表(the Brief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B-IRI)
,B-IRI 有16 个条目, 内部一致性好,保留了原量表的心理测量特征,Cronbach α 在0.65~0.79,因条目较少易于填写,目前暂无汉化版本。
2.2.3 神经科学技术手段 基于疼痛共情的神经生理基础可以用脑电图
、事件相关电位、经颅磁刺激等
方法对疼痛共情能力进行研究。 使用此类方法需借助脑电图仪、 经颅磁刺激仪、MRI 等医疗仪器,对操作者要求较高, 适用于对小样本量人群的疼痛共情能力进行深入研究。
2.1 普适性的共情评估工具
2.2.2 疼痛共情量表 (the Empathy for Pain Scale,EPS) 该量表由澳大利亚学者Giummarra 等
于2014年编制,是一种评估疼痛共情能力的便捷工具。该量表量表Cronbach α 系数为0.91, 各维度Cronbach α 系数在0.70~0.93,信效度良好。 其包含了情感痛苦、移情反应和替代疼痛3 个维度。 该量表包括了4 个疼痛共情场景,分别是目击手术、病人术后康复、遭遇袭击和误伤,每个场景设置了12 个涉及到情感、同理心和感官回应的闭合式共情反应条目, 分别是心里不舒服和/或揪心、全身不适、反感、感同身受、胃肠不适(如恶心)、坐立不安或想要离开、害怕、需要转移视线、同情、想要介入或给予帮助、躯体疼痛(如刺痛、跳痛)、躯体不适感觉(除躯体疼痛以外的其他不适感,如刺麻感)。 每个条目按照Likert 5 级评分法可评定为1~5 分,其中1 分代表完全不同意,5 分代表完全同意。 除了闭合式条目, 每个场景还设有1~2 个开放式问题, 用于进一步了解应答者在该情景下的情感体验。 Giummarra 等将该量表应用在152例特发性疼痛患者、68 例截肢后疼痛患者和245 例无痛对照组人群中,验证了其良好的信效度。 Tommaso等
将EPS 与脑电图实验同时应用于纤维肌瘤患者中,发现纤维肌瘤患者的EPS 评分与疼痛共情相关的脑电图相关。 2020 年, 国内学者尚静等
将EPS 汉化,并应用于531 例医学本科生中,中文版EPS 的Cronbach α 系数是0.914,各条目内容效度为0.83~1.00。 相比于原量表,中文版EPS 在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提取了2 个公因子,命名为“身心不适反应”和“移情反应”。 这可能与中西方人群文化背景差异有关。 相比于疼痛共情范式,EPS 简单、便捷、可操作性强,但是在更多人群中的心理测量学属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3.1 观察者因素 观察者因素是疼痛共情沟通模型中的主要因素之一,也称后者因素或者主体因素。 面对同一疼痛者发出的疼痛信号,不同的观察者会呈现出不用的疼痛共情能力。这可能与观察者既往的疼痛体验、疼痛治疗史及对疼痛的理解认知有关。 医务人员在医疗场所中往往是作为观察者对患方产生疼痛共情的,因此研究疼痛共情的观察者因素尤为重要。
2.2 疼痛共情专用评估工具
王飞:深圳市龙岗区实施政府资助学校这一新的办学体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不同于公办学校,也不同于民办学校,校长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办学校。在这种顶层设计下,校长办学有很大的权力,特别是用人机制比较灵活,可以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
3 疼痛共情的影响因素
2.2.1 疼痛共情范式(Empathy to Pain Paradigm)
该方法在应用时需要E-prime 编制程序、 相等数量的疼痛图片和中性图片,操作较复杂。疼痛图片是一些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疼痛场景如手被针扎的图片。中性图片是一些描述日常生活中非疼痛场景或非疼痛面孔表情的图片。 所选择的疼痛图片和中性图片要求具有相同的对比度、亮度等图片性质。所有图片必须以第一视角拍摄, 涉及的身体部位只包括手或脚,尽量避免身体其他部位。 被试者需要在单独的、适宜的实验室内完成测试。 实验步骤如下:(1)选择不参与研究的人群对实验图片(疼痛图片、 中性图片)进行5 点疼痛等级评定,其中1 分代表“不疼”,5 分代表“非常疼”。 如果评定结果显示疼痛图片和中性图片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则可以进行下一步骤。 (2)计算机编程下随机呈现图片。 每张图片出现之前在屏幕中央呈现一个注视点“+”,时间固定为400 ms,然后呈现实验图片,时间固定为1 000 ms,之后空屏1 500~1 700 ms,要求被试者快速判断图片中人物是否感到疼痛及疼痛的部位,并按键。其中,判断图片中人物疼痛与否属于疼痛判断任务(taskpain,TP),反映外显情感共情;判断图片中肢体侧别属于左右判断任务(task laterality, TL),反映内隐情感共情。(3)被试者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对图片中人物的疼痛程度进行5 点等级评定,这一步骤反映的是疼痛认知共情,无时间限制。在该实验中,电脑编制程序自动记录被试者在判断任务中的选择、 反应时间及具体评分,并将这些内容作为实验范式的共情指标。 柏晓蒙等将疼痛共情范式与IRI 同时应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发现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呈正相关
。
3.1.1 观察者的个体特征影响其疼痛共情能力 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和性格特征的观察者面对疼痛场景时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杨东等
研究发现处于焦虑或抑郁状态的观察者对他人的关心程度下降, 疼痛共情能力较弱。 女性受雌激素水平的影响,比较感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共情
。1 项有关疼痛共情的ERP 结果显示,长期性施暴人员疼痛共情水平较低,呈现出脑电成分上的差异
。
3.1.2 观察者的疾病史影响其疼痛共情能力 一些精神类疾病也会影响对他人疼痛的共情能力。 Peng等
使用疼痛共情范式和脑电图等工具证实了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存在疼痛共情认知和情感能力的下降。 代迎菊等
探讨了无先兆偏头痛患者的疼痛共情能力,发现很多偏头痛患者伴有述情障碍,表现出共情能力较差,这可能与偏头痛患者5-HT 功能受损有关。
3.1.3 观察者的疼痛经历及疼痛用药史影响其疼痛共情能力 1 项研究表明
,当使用安慰剂镇痛药的研究对象疼痛减轻时,其疼痛共情能力随之下降;当安慰剂镇痛药药物效应被阻断时, 疼痛共情能力随疼痛恢复。这说明,观察者自身的疼痛经历与疼痛共情能力相关。 Serbic
的研究表明,观察者对疼痛的恐惧感和对自身健康的担忧会影响自身的疼痛共情水平。 此外, 止痛类药物可影响个体的疼痛共情能力。 Mischkowski 等
研究发现,应用对乙酰氨基酚止痛的患者的疼痛共情能力较未应用对乙酰氨基酚止痛的患者的疼痛共情能力弱。
3.2 疼痛者因素 疼痛者因素是疼痛共情沟通模型第一阶段的主要因素,也称前者因素或者客体因素。由于疼痛是一种主观的体验,疼痛者自身的因素对疼痛共情的过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疼痛者的自身要素主要有性别、性格、文化、道德水平和表达能力等
。比如,生理系统发育不健全、语言功能尚未完善的婴幼儿无法用除了哭泣以外的其他方式表达自身的疼痛,这无疑会干扰观察者对其经历的疼痛产生共情。同理,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昏迷患者、气管插管患者等因为疾病原因导致表达疼痛的能力受损,这也会使得观察者只有采取行为学观察方法判断其疼痛程度和疼痛部位,造成疼痛共情的偏差。
3.3 疼痛者与观察者的关系因素 疼痛者与观察者的关系是疼痛共情沟通模型第2 阶段的主要因素。观察者与疼痛者之间的人际距离(social distance)越近,就越能感知对方的疼痛。 1 项动物实验表明,当小鼠看到关在同一个笼子里的其他小鼠受伤时,会对其产生疼痛共情; 而当面对另一个笼子里的小鼠受伤时,情绪却比较平稳
。宋娟等
的研究发现,人类对于朋友和陌生人遭遇疼痛体验时产生的共情存在差异,疼痛者与观察者的人际距离会影响共情。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发展,然而他们的孩子却在农村成了“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关乎中国未来和谐发展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希望通过这篇调查研究,能够给人们一些启示,唤起全社会对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重视,使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得到改善。
4 展望
对于医务人员而言,疼痛共情能力可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疼痛患者的信息, 同时提高疼痛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主动参与度,并间接影响疼痛评估的准确性和缓解患者因疼痛产生的恐惧感。 目前,国内外对于疼痛共情的研究多集中在神经机制方面,虽然研究时间不长但是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在评估工具方面,有关共情能力评估的工具很多,但是专用于疼痛共情的测评工具很少,且多依赖于计算机编程系统或各种医疗仪器设备,不适合大样本研究。 EPS 作为一种便捷式的疼痛共情评估工具,仅在医学生和纤维肌瘤患者中应用,在其他人群中的信效度未得到证实。 疼痛共情评估工具的匮乏直接影响到了多样本多类型人群疼痛共情能力的相关研究。 将来,希望有更多专用于测评疼痛共情能力的便捷工具诞生,以便更好地探讨各类人群的疼痛共情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提高疼痛共情能力的干预策略。疼痛共情的影响因素可从疼痛者、观察者、二者关系3 个方面分析,但相关定量研究目前仅有1 项针对医学生的疼痛共情影响因素分析
,缺少其他人群的相关研究,今后可进一步研究。
[1] Guidi C,Traversa C.Empathy in Patient Care: From ‘Clinical Empathy’ to ‘Empathic Concern’[J].Med Health Care Phil,2021,24(4):573-585. DOI:10.1007/s11019-021-10033-4.
[2] Jolien VDG, Meeus W, De Wied M, et al. Motor,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Empathy in Adolescence: Interrelations be tween Facial Electromyography and Self-reported Trait and State Measures[J]. Cogn Emot, 2016,30(4):745-761. DOI:10.1080/02699931.2015.1027665.
[3] Navot N, Christiane R, Schaare LH, et al. The Neural Networks Underlying Reappraisal of Empathy for Pain[J]. Soc Cogn Affect Neur Osci, 2020,15(7):733-744. DOI:10.1093/scan/ nsaa094.
[4] 代迎菊, 吴兴启, 高建国, 等. 无先兆偏头痛患者疼痛共情能力研究[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17,26(1):17-21.DOI:10.3760/cma.j.issn.1674-6554.2017.01.004.
[5] 王雪, 蔡春岚, 谢雯, 等. 抑郁症患者疼痛共情的初步研究[J]. 中华精神科杂志, 2018, 51(1):5. DOI:10.3760/cma.j.issn.1006-7884.2018.01.008.
[6] Giummarra MJ, Fitzgibbon BM, Georgiou-Karistianis N, et al. Affective, Sensory and Empathic Sharing of Another’s Pain: The Empathy for Pain Scale[J]. Eur J Pain, 2015, 19(6):807-816.DOI:10.1002/ejp.607.
[7] 尚静, 叶旭春, 王怡, 等. 疼痛共情量表的汉化及其在医学生中的信效度检验[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20, 26(9):1140-1145.DOI:10.3760/cma.j.cn115682-20190725-02673.
[8] 毕轩懿, 尚静, 王婧婷, 等. 医学生疼痛共情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21, 27(31):6.DOI:10.3760/cma.j.cn115682-20190725-02673.
[9] Cheng Y, Yang CY, Lin CP, et al. The Perception of Pain in Others Suppresses Somatosensory Oscillations: A Magnetoencephalography Study[ J ].Neuroimage,2008,40(4):1833-1840. DOI:10.1016/j.neuroimage.2008.01.064.
[10] Goubert L, Craig KD, Vervoort T, et al. Facing Others in Pain: The Effects of Empathy[J]. Pain, 2005, 118(3):285-288. DOI:10.1016/j.pain.2005.10.025.
[11] Fan Y, Han S. Temporal Dynamic of Neural Mechanisms involved in Empathy for Pain: An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Study[J]. Neuropsychologia, 2008, 46(1):160-173.DOI:10.1016/ j.neuropsychologia.2007.07.023.
[12] Hadjistavropoulos T, Craig K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Self-report and Observational Measures of Pain: A Communication Model[J]. Behav Res Ther,2002,40(5):551-570.DOI:10.1016/s0005-7967(01)00072-9.
[13] Holgado Tello FP, Delgado Egido B, Carrasco Ortiz MA, et al.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Analysis of Invarianc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Spanish Youths[J]. Child Psychiat Hum D, 2013, 44(2):320-333.DOI:10.1007/s10578-012-0327-9.
[14] 张凤凤, 董毅.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的信度及效度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2): 155-157. DOI:10.3969/j.issn.1005-9202.2014.20.130.
[15] 杨静月, 张蕾. 双相情感障碍疼痛共情能力研究[J].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2015, 41(12):740-748. DOI:10.3969/j.issn.1002-0152.2015.12.008.
[16] 魏格欣, 杨静月, 阚博, 等. 不同发病时期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疼痛共情能力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26(5):933-937.DOI:10.16128/j.cnki.1005-3611.2018.05.021.
[17] 柏晓蒙, 朱春燕, 董毅, 等. 精神分裂症患者疼痛共情能力的研究[J].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2016, 51(11):1661-1664. DOI:10.19405/j.cnki.issn1000-1492.2016.11.025.
[18] Markus Rütgen, Pletti C, Tik M, et al.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not Depression, Leads to Reductions in Behavioral and Neural Responses to Pain Empathy[J]. Transl Psychiat,2019,9(1):164.DOI:10.1038/s41398-019-0496-4.
[19] Ingoglia, Sonia, Coco, et al. Development of a Brief Form of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B-IRI)[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2016, 98(5):461-471.DOI:10.1080/00223891.2016. 1149858.
[20] 朱玉, 陈新贵, 吴小玲, 等. 多维度共情测验的编制及信效度分析[J].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2018, 53(7):1100-1105. DOI:10.19405/j.cnki.issn1000-1492.2018.07.023.
[21] Mercer SW. The Consultation and Relational Empathy(CARE) Measure: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and Reliability of an Empathy-based Consultation Process Measure[J].Fam Pract, 2004, 21(6):699-705. DOI:10.1093/fampra/cmh621.
[22] Parkin T, De Looy A, Farrand P. Greater Professional Empathy leads to Higher Agreement about Decisions Made in the Consultation[J]. Patient Educ Couns, 2014, 96(2):144-150. DOI:10.1016/j.pec.2014.04.019.
[23] Corbera S, Ikezawa S, Bell MD, et al. Physiological Evidence of a Deficit to Enhance the Empathic Response in Schizophrenia[ J ]. Eur Psychiatry, 2014, 29(8):463-472.DOI:10.1016/j. eurpsy.2014.01.005.
[24] Tommaso MD, Ricci K, Conca G, et al. Empathy for Pain in Fibromyalgia Patients:An EEG Study[J].Int J Psychophysiol, 2019, 146:43-53.DOI:10.1016/j.ijpsycho.2008.07.018.
[25] 闫栋. 躯体化疼痛障碍患者EEG 改变及相关骨骼肌衰老机制研究[D].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 2015: 14-19.
[26] Fabi S, Leuthold H. Empathy for Pain Influences Perceptual and Motor Processing: Evidence from Response Force,ERPs, and EEG Oscillations[J]. Soc Neurosci-UK, 2017,12(6):1.DOI:10.1080/17470919.2016.1238009.
[27] 杨东,李志爱,余明莉,等.金钱启动对疼痛共情影响的ERP 研究[J]. 心理学探新, 2015, 35(2):140-146. DOI:10.3969/j.issn.1003-5184.2015.02.008.
[28] 王晓灿, 栾贝贝, 王维利, 等. 医护人员共情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J]. 护理学杂志, 2015,30(20):110-112.DOI:10.3870/j.issn.1001-4152.2015.20.110.
[29] 高雪梅, 翁蕾, 周群, 等. 暴力犯的疼痛共情更低: 来自ERP 的证据[J]. 心理学报, 2015,47(4):478-487. DOI:10.3724/SP.J.1041.2015.00478.
[30] Peng WW, Meng J, Lou YX, et al. Reduced Empathic Pain Processing in Patients with Somatoform Pain Disorder: Evidence from Behavioral and Neurophysiological Measures[J].Int J Psychophysiol. 2019, 139:40-47. DOI:10.1016/j.ijpsycho.2019.03.004.
[31] Markus, Rütgen, Eva-Maria, et al. Placebo Analgesia and Its Opioidergic Regulation Suggest that Empathy for Pain Is Grounded in Self Pain[J]. P Natl Acad Sci USA, 2015,112(41):E5638-5646. DOI:10.1073/pnas.1511269112.
[32] Serbic D, Ferguson L, Nichols G, et al. The Role of Observer’s Fear of Pain and Health Anxiety in Empathy for Pain: An Experimental Study[J]. Brit J Pain, 2020, 14(2):74-81. DOI:10.1177/2049463719842595.
[33] D Mischkowski, Crocker J, Way BM. From Painkiller to Empathy Killer: Acetaminophen (Paracetamol) Reduces Empathy for Pain[J]. Soc Cogn Affect Neur, 2016, 11(9):nsw057. DOI:10.1093/scan/nsw057.
[34] 吕悦. 乳腺癌患者化疗后疼痛共情障碍的研究[D]. 合肥:安徽医科大学, 2019:11-13.
[35] Cui F, Ma N, Luo YJ. Moral Judgment Modulates Neural Responses to the Perception of Other’s Pain: An Erp Study[J].Sci Rep, 2016, 6:20851. DOI:10.1038/srep20851.
[36] Y Yu, Li CL, Du R, et al. Rat Model of Empathy for Pain[ J]. Bio-Protocol, 2019, 9(12). DOI:10.21769/BioProtoc.3266.
[37] 宋娟, 郭丰波, 张振, 等. 人际距离影响疼痛共情:朋友启动效应[J]. 心理学报, 2016, 48(7):833-844. DOI:10.3724/SP.J.1041.2016.00833.